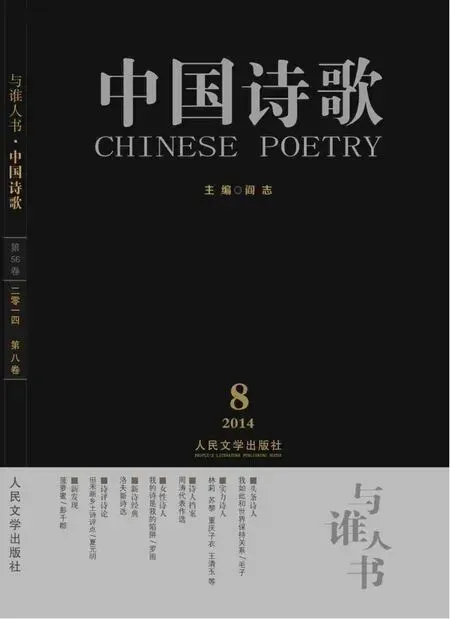现代诗的探路者
——洛夫新诗导读
□袁循邹惟山
现代诗的探路者——洛夫新诗导读
□袁循邹惟山
洛夫,当代台湾杰出的诗人与散文作家。作为一个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而至今依旧活跃的诗人,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他在诗歌思想、艺术以至于诗歌理论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就的探索。他在东方与西方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中饱食营养,并且自由独立、自在悠游,其诗歌艺术独具个性与风格。他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抒情时期”、“现代诗探索时期”、“反思传统,融合现代与古典时期”、“乡愁诗时期”、“天涯美学时期”五个阶段。“抒情时期”时间较短,诗风甜美,意象鲜明,以诗集《灵河》为代表。“探索时期”是其第一个创作高峰,以《石室之死亡》、《西贡诗抄》为代表,深受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向内挖掘,整体显得艰深晦涩。“古典时期”他走出了封闭的心灵,而走向人间烟火,反思传统,追求现代与古典的融合,以诗集《魔歌》为代表。“乡愁时期”抒写乡愁情结,以《边界望乡》、《蟋蟀之歌》等为代表。“天涯时期”追求人在天涯,心在六合,以《漂木》为代表。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汉语诗歌,并且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在二十世纪中国诗人中极少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
一
洛夫的诗歌内容广博并且极具探索性,主要表现在三个开掘上:向人类内在世界开掘;向现实社会人生开掘;向传统历史文化开掘。
第一,向人类内在世界开掘。早期的洛夫被贴上了超现实主义的标签,对人的内在世界开掘达到了极高程度。五十年代远离大陆的满腹乡愁,当地物质条件匮乏的满目萧条,考取陆军军官学校的理想破灭,“自我”成长所经历的种种苦难,文化封锁所造成的对中国传统文化难以亲近,以及“五四”新文学的传统遭遇隔绝,如此种种的人生与文化现实,导致洛夫内心产生极度抑郁,因此其诗歌创作从一开始,便着力于反思人的存在,关注人类内在焦虑。洛夫作为创世纪诗社的领军人物,高举“超现实主义”大旗,早期代表作《石室之死亡》就是典型的代表。据说长诗《石室之死亡》,写于金门炮战的地下碉堡之中。在战争中面对死亡的残酷与威胁,面对生命的真实与脆弱,让他写下了这首杰作。诚如洛夫所说:“揽镜自照,我们所能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就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洛夫自选集》,217)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与文学,建立在反思人类理性的基础之上,于是“荒诞”、“焦虑”、“非理性”成为了核心词汇。超现实主义重视人类的非理性世界,认为人类的潜意识世界是绝对真实可靠的。诗人总是以人类能够直觉到的荒诞与焦虑,映衬战争与人的存在。长诗的一开始,便是死亡的阴暗与恐惧,“只偶然昂首向邻居的甬道/我便怔住/在清晨,那人以裸体去背叛死/任一条黑色支流咆哮横过他的脉管/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扫过那座石壁/上面即凿成两道血槽”。诗人清晨出门便见一具尸体,黑色支流咆哮,显然是有人以生命的挣扎与扭曲,来对抗死亡的恐惧,白晃晃血肉与血液流淌凝结的黑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几欲令读者产生呕吐。“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扫过那座石壁/上面即凿成两道血槽”,“凿”与“槽”突出目光的猛力,更是对人的直觉的一种放纵,“我”所有的感觉与理性,只是表达一种震颤与无言。顺势而下,我们看到的是死亡中的恐惧、饥饿、残暴、愤怒、自虐乃至复仇,一连串非理性心理活动喷涌而出,造成一系列幻象的交织并列。生命的脆弱、死亡的恐惧、杀戮的残暴,读来令人窒息,苦涩与沉郁,犹如淫雨中野鬼啾啾。此后的诗歌创作中,也有类似的情境出现,如《长恨歌》中唐明皇性欲的泛滥,因为“我是皇帝”而存在的残暴兽性的惟我独尊,其实都是对自我潜意识世界的一种反映。
从超现实主义出发,洛夫笔下对人性的反思相当深刻。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金门炮战、越战,一生颠沛流离的洛夫见识了太多的死亡和杀戮,因而形成“悲悯情怀”,对生命深处最阴暗处尤为敏感。以《沙包刑场》为例,“一颗颗头颅从沙包上走了下来/俯耳地面/隐闻地球另一面有人在唱/自悼之挽歌”,这是一个令人惊骇的场面,诗人赋予了头颅生命和感官,竟然能听到挽歌。也许是藏于地球深处的鬼魂发出的幽怨,也许是诗人自我代替死去的人唱出“自悼之挽歌”。诗人面对杀戮场面的愤怒和对死去人的怜悯,在此得到了具体而深切的表达。告示随风飘走是在警告人们,每天对镜自视自恋自以为万物之灵长、天地之精华的人类,在面对自己残酷行为和卑劣人性的时候,原来是多么的丑陋与恶心,于是,“一幅好看的脸/自镜中消失”便理所当然。
第二,向现实社会人生开掘。抒写人生体悟与浓烈乡愁是洛夫诗歌的重要主题。作为一个主体精神强大,不断由内而外探寻生命诗意与精神高度的诗人,他对人生中的理想、信仰、神性、孤独、死亡等等关键词,有着深刻独到的感悟。在《烟囱》中,人生局促而良朋悠邈,如同烟囱被钉住保持固定永恒不动,只能日夜聆听脚下护城河盈盈流动,淘尽脂粉。生命如同牢笼枯井,只能艳羡“生活在别处”。此首诗成,洛夫痛哭流涕,可见刻骨铭心。《血的再版——悼亡母》是诗人泣血之作。三十年前的未能会面的离别,三十年来未曾会面的思念,母亲亡故六七年未能祭奠的痛楚,所有情绪、感情的累积与积淀,让诗人如哭泣的孩童,于是跪地幽咽与昂首咆哮,以指天问地。在《边界望乡》中,家乡近在眼前,却如同幻影,无从企及,少小离家,而今两鬓染霜的落寞,即便回到故乡,“儿童相见不相识”的陌生,了无功名,蹉跎岁月的“不敢问来人”的惭愧,岁月更迭,故人已成黄土的“近乡情更怯”的忧虑,如此多纷繁复杂情绪如开闸洪水,一发不可收。以至于诗人到了海岛边缘,竟被撞成了“严重的内伤”;随着鹧鸪的啼叫,杜鹃的声声咯血,眼睛烧成火红望向远方,却又只好急转回来;满腔的热血沸腾,换来大陆一边冰冷的“冷不冷”的一盆冰水;热情冷却之后,期待春分、惊蛰、清明,时间分秒逝去,乡愁未曾退却,“我”听懂了大陆那边的广东乡音,然而伸手,只是一团迷雾。
第三,向传统历史文化开掘。洛夫的诗歌向人类历史文化汲取营养,同时也向中国历史文化开掘。在《长恨歌》中,诗人对这样一段混合着个人爱情、家国天下、历史兴亡的题材,充满着一种现代性的批判。一开始,诗歌呈现给读者的便是白晃晃的“肉体”和“体香”、“嘴唇”、“象牙床”、“烧焦了的手”等极富感官冲击力的意象,将两人的夜夜狂欢与无边肉欲,极度夸张地表现出来。战争一触即发,然而,君王却在棉被中以“舌头”与“两股”度过日日夜夜。“马嵬坡前”贵妃化为“一堆昂贵的肥料”,一切终于得到了平息。“恨”于是开始,对贵妃的思念令“他”容颜一夜老去,然而换来的只是“她”的一缕烟、一片云,满是绝望的脸以及黑如一口井的眼睛——“她”已淡然,战争已无从怨恨。七月七日长生殿,“他”化作飞鸟向着月亮振翅高飞。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与之相伴的只是“一个没有脸孔的女子”,一场“他”制造的幻影。由此可见,洛夫的《长恨歌》与白居易同名诗作存在巨大的差异,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不再美好,取而代之的是无穷的肉欲与女性的牺牲,唐明皇的思念不再是忠贞,而是“自我”的沉湎与制造的幻影。洛夫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对历史进行了深刻而深重的反思,表现了极为丰富和广阔的历史感。
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势必走向寻求历史文化与现代的融合,众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在洛夫的笔下苏醒复活,并融入了现代意义。在《与李贺共饮》中,骤雨初歇,秋意正浓,乍见窗外枯瘦李贺,穿越唐宋元明清骑驴而来,口中嚼着绝句,满是鬼哭神嚎,手中提着花雕,满是意象狂舞——奔赴“我”的邀约。“我”慷慨热情邀他共饮、把酒言欢,暂时抛却怀才不遇、身世飘零之烦恼;豪情万丈,将权贵视作粪土,以诗歌蔑视朱门;两人促膝而谈,题诗互赠,引为高山流水,抛却流俗。李贺之才气、豪情、洒脱、狂放,与诗人的向往与追求交融统一,其实暗含的是诗人对读书人慷慨风骨与独立人格的崇敬,是在日趋流俗、人类异化的现代社会中对古典诗意的追寻。在对古典文化的反思与借鉴中,洛夫执着于禅诗的理论探索与写作实践,“顿悟”与“心物合一”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顿悟”即是灵光乍现的豁然开朗式的领悟,而“心物合一”即是佛教教义中的“空”与源于老庄的“无”的结合。洛夫致力于禅与超现实主义的统一,提出其所谓的“中国的超现实主义”。在思维方式上,禅宗注重顿悟见性与不立文字,主要是指直觉所带来的豁然开朗,反对语法逻辑对于人的直觉之束缚,强调追寻生命本真与生命智慧。禅宗强调明心见性,即挖掘心中佛性,以领悟佛法。洛夫的禅诗主要表现禅悟的心理过程与生命智慧。在《金龙禅寺》中,黄昏来临,游客们在钟声里沿着小路蜿蜒而下,羊齿植物低低矮矮,错落于白色石阶两侧,整个画面呈现一种动态的平静。一只灰蝉在不经意间渐次点亮山中灯火,诗歌于此戛然而止。结合当时诗人的处境来看,此诗抒写的正是诗人禅悟的心理体验。深秋中的黄昏时分,作为旁观者和苦苦寻觅诗歌灵感的灵魂流浪者,诗人心境或许一片茫然失落,在凄寒中渴望一场小雪的降临。然而,“当灰蝉惊起而鸣,掠过暮霭中內的树枝山岭,山中的灯火也全给吵醒了,点亮了,这时你会顿然感到心一片澄明,突然惊悟,生命竟是如此的适意自在。”(洛夫《禅诗的现代美学意义》,64)
洛夫寻求“心物合一”的哲学观念,在诗歌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渗透。“诗的力量……产生于诗人内心世界与外在现实世界的统一,只有我们把主体生命融入客体事物之中,潜意识才能升华为一种诗的境界。”(洛夫《禅诗的现代美学意义》,63)后期“天涯美学”观念包含深厚的宇宙情怀,将诗人超时空的本能提升为一种浩瀚的宇宙情怀。长诗《漂木》正是“天涯美学”的完整体现。所谓“漂”正是一种漂游、漂浮的状态,古典诗歌中有屈原《离骚》中对于天地漫游的苦苦追寻,有苏轼“我欲乘风归去”、“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宇宙宽广、人生微小的感叹,都是“心物合一”的典型表现。在《漂木》中,诗人能在历史的、现代的、民族的、世界的微尘中、宇宙间自在遨游,形成深厚的思想内涵与宽广的艺术空间,实在是不易的。
二
洛夫诗歌在艺术形式与艺术风格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独特的意象艺术。洛夫认为:“诗语言与散文语言不同之处,主要乃在诗是意象的呈现。”(洛夫《诗的语言和意象》,91)诗人执意于诗歌意象的经营,其特点,可以用一个“魔”字概括。其一是“魔”的比喻艺术。在《烟囱》中,诗人将自己比喻成一只想飞而不得的烟囱。透过烟囱的眼睛,诗歌呈现一片静止与运动、有限与无限的交融统一景象:城墙下的护城河,盈盈流动,淘尽岁月铅华;宫宇倾圮,往日繁华光影已随流水,骑楼上古老钟声却依旧清越。诗人深刻的孤独与命运的苍凉,通过“烟囱”传达了出来。在《午夜削梨》中,诗人以梨自喻,将剖开的梨的果核比喻成一口深深的井,以深深的黑暗无边、压抑无边的井,比喻藏于胸中的深深似海的乡愁。以白色的果肉比喻诗人纯粹真醇的内心世界,又以梨被剥落的黄色果皮比喻被剥落的“黄铜色皮肤”,一水之隔而无从接近祖国的痛苦,被生动地呈现出来。在《长恨歌》中,诗人以叠加的河流比喻唐明皇与杨贵妃交媾的躯体。在《危崖上蹲有一只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鹰》中,诗人以危崖上雄鹰的飞舞,比喻诗人对精神王者的渴望。在《边界望乡》中,诗人将因乡愁而憔悴的“我”,比喻成“凋残的杜鹃”。在《与李贺共饮》中,诗人将消瘦之李贺比喻成“一支精致的狼毫”。这些比喻往往别出心意,准确生动,蕴含丰富,富含“魔”的特性。一是喻体选择上的奇特。钱钟书认为比喻的双方:“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洛夫诗的比喻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的奇特性,出乎日常生活的通俗比喻,喻体奇特而与本体相距甚远,如《边界望乡》将乡愁比喻作风中的散发,乡愁的激荡比喻成撞向诗人的大山。二是在比喻的方式上,常常不单是单个的、片段的比喻,而是博喻,连串的、整体的比喻,以形成整体关照。三是比喻的双方往往不单有视觉上的相似性,而更融入了听觉、嗅觉、味觉等感觉的并列对照。在《未寄》中,诗人将自己寂寞中心境跌入谷底的失落,比喻成深山中骸骨的轰然倒塌,听觉上的震颤烘托的是诗人感受的强烈。在《石室之死亡》中,诗人将自己在战争中目睹死亡与残酷所激起的,于恐惧与震颤中的静默无言或吞吞吐吐,比喻成被锯断的苦梨的风声与蝉声。比喻的妙处并不在于比喻双方的形似,而在于比喻双方的并列对照与交织融合所形成的广阔艺术空间。其二是意象的冲突与融合。钱钟书认为诗歌语言能调节虚与实、色彩强烈反差等矛盾冲突,从而令诗歌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在《长恨歌》中,唐明皇“开始在床上读报,吃早点,看梳头,批阅奏折/盖章/盖章/盖章/盖章”。报纸是现代的事物,奏折则又是古代的事物,而四个连续的“盖章”又像是现代官员的作风,十分滑稽可笑。诗歌予人一种既非现代又非过去的模糊空间,是虚与实的融合,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对唐明皇的批判,而涵盖了更为广阔的内容。杨贵妃化作肥料,却“营养着/另一株玫瑰/或/历史中/另一种绝症”,暗指漫长的时空中杨贵妃后继之人,继续着一出一出悲剧。“肥料”、“玫瑰”、“绝症”这样一些看起来毫无联系的意象,被统一和融合在一起,于是广阔的历史空间和深沉的历史感慨,同样被融合在了一起。在《石室之死亡》中,一方面是白晃晃的肉体,一方面则是肉体上黑色的由血液凝成的粗犷线条,造成震撼的心灵感受。其三是赋予笔下意象自觉能动的生命。洛夫诗歌中许多意象不是静止而了无生气的,而是能动的、自觉的,具有了“魔力”。在《边界望乡》中,“乡愁”竟然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乡愁原本无形无迹,难以捉摸,这里的“乡愁”,却具有了动作与形态,甚至具有了主观思想。在《沙包刑场》中,头颅一颗颗滚落,表现杀戮的恐怖,表现对杀戮的控诉与对人性的讽刺,头颅具有了感官功能,能倾听,能“自悼”,还能辨别“挽歌”来自于地球深处,似乎是头颅在哭泣和控诉。在《长恨歌》中,想象鼙鼓以舌头舔着大地。在《午夜削梨》中,梨核中藏着一口井。在《与李贺共饮》中,李贺的花雕竟然自觉地穿越唐宋元明清而注入“我”的酒杯。在《金龙禅寺》中,羊齿植物嚼着石阶。在《危崖上蹲有一只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鹰》中,“鹰”在高崖上独舞,奋力抓起地球向我心中的另一个星球掷去,成为精神上“孤独的王者”。
第二,节制的艺术。华兹华斯认为诗歌是在回忆之中诞生的,鲁迅在谈论自己创作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闻一多认为诗歌是戴着脚镣跳舞,虽然他谈论的是诗歌的韵律问题,但对诗人情绪与情感的处理,同样需要这样的特质。洛夫明确表示自己比较欣赏冷的诗。诗人在看这个世界时内心情绪激荡、情感热烈,然而总能对此加以节制,透彻看到世界的真相与本质。在苦难的汁水中浸润与成长的对人世抱着“悲悯情怀”的洛夫,在人生中年于越南战场再次目睹人间屠戮惨剧,必然激起内心的起伏波澜。然而,在《沙包刑场》中,诗歌的语调却是相当的冷静与平和,甚至似乎抱着一种事不关己冷眼旁观的态度,没有任何主观感情的参杂,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形成巨大反差,令读者沉静下来,直指灵魂深处。在《金龙禅寺》中,末尾是会心一笑的豁然开朗,是暗自喜悦与释怀。然而,诗歌转而抒写灯火的一盏盏亮起便戛然而止,诗人的情绪与感悟被掩藏遮蔽下来,形成了巨大的艺术空间,诗味更加浓烈。比起一些以抒情为主的诗人作品,洛夫的诗歌更讲究内在的深厚意蕴,思想与情感总是通过自我的感觉来表达,并且在表达的时候也是留有余地,不是将一切和盘托出,而是只说半句,留下半句没有说出,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与认识。这种艺术上的讲究来自于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歌,同时也来自于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歌是不讲主观抒情的,反而重视客观的呈现,一切都以理性而出之,洛夫的诗就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移植。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歌虽然以抒情诗为主,但这里的抒情是与叙事相对的,并不是说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容都是抒情,其表达方式也只有抒情。中国古典诗歌也很注重以意象的方式呈出诗意,思想、感觉、情感、认识、见解,都不可直接说出,并且也不可说完。即便像李白的诗,虽然有浪漫主义的情感化倾向,然而也是从自我出发的一种间接表达,也是没有说尽的。所以,洛夫诗歌以意象的方式讲究情感节制,以感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认知与思想,是相当成功的一种艺术探索。
三
九十年代后期,诗人以高龄自我放逐至遥远的加拿大,创作出3000行长诗《漂木》,见出诗人生命力的奔放与张扬,以及执着的不懈探索的精神。这首长诗标志着洛夫诗歌创作的一个新阶段,也代表了其诗歌写作所达到的新高度。它有着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博大的情怀,更加强大的想象力,更加空灵的语言,与早期的洛夫诗歌判然有别。它更加倾向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境界,实现了诗人自我创作历史上的两重超越,既超越了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歌,也超越了中国古典诗歌,而实现了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如果没有远渡重洋到加拿大生活的经历,如果没有自我放逐的过程与心态,如果没有把自我的人生当作一节漂木,诗人就不会有这样的一首长诗。它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提名,就是因为它的思想与艺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是从前的现代汉语长诗所难以相比的。
回顾中国新诗中西合璧的近百年历程,洛夫的出现和存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新诗寻找现代出路的艰难尝试,是当代诗歌史上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洛夫的诗歌可以为我们思考许多问题,提供重要的依据和启迪:在浩瀚如海、巍峨如山的中国诗歌传统之下,如何继承与创新;在东学西学并置争锋的背景下,如何吸收西方诗歌传统的有益因素;在时代剧变、诗歌地位急剧下降的情境下,如何实现现代诗歌的接受与传播。洛夫的诗之所以形成了当代中国诗歌的高峰之一,主要缘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世界、从世界回到中国大陆这样的人生历程所带来的见识广、体验深、感觉富,这是其大量杰出诗歌作品产生的基础。二是诗性情怀的拥有,让他的诗大都产生于灵感,而很少产生于思考,他放开了自我的心灵,放开了自我的感觉,所以他的感受往往是全新的,并且是独到而深刻的,这就是许多杰出诗篇产生的机运。三是注重积累,注重探索,没有重复他人,也少有重复自己。洛夫从事过多种多样的工作,从小逃难于战争,在孤岛上对抗战争,在越南战场上进行实地的战争;同时,他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相当熟悉,对于西方的现代派诗歌也相当了解,他从事西方诗歌与文学的翻译,也写了大量的散文,长期坚持书法操练,特别是后期几乎是以一个书法家的身份出现,在海内外举办了大量的书画艺术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对于他的写作,都是积累,都是探索。我们很难将他者与洛夫的诗歌进行比较,然而我们认为他的诗与散文也不在余光中之下,虽然后者更加丰富与多样,更加适合于大众阅读的需要,在民众生活与社会事务中有着更加广泛的影响。综上所述,在整个中国新诗史上,洛夫及其诗歌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