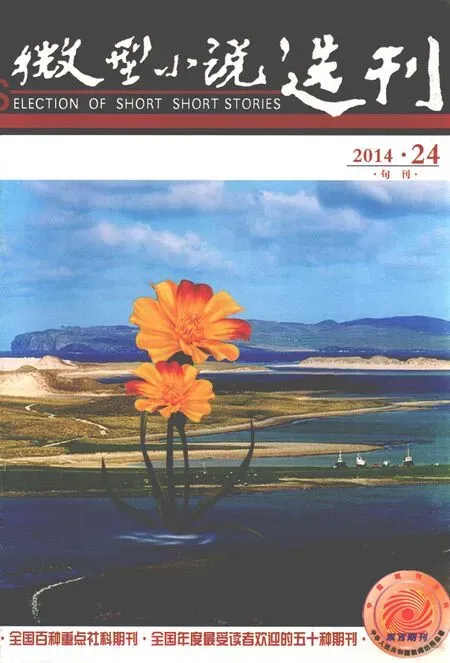幻术师
□【美】刘宇昆 著 陈楸帆 译
幻术师
□【美】刘宇昆 著 陈楸帆 译
我掂了掂小小真皮钱包的分量:轻,比我的希望轻多了。
“这是四柳村里所有剩下的金币了。”年长的安瑟伦说,“我们已经请过一队骑士,三个巫师,甚至一帮和尚。没一个能帮我们除掉格兰戴尔。拜托了,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也是最便宜的。我心里暗想。
但乞丐没有选择的权利。雷米王,一个清教徒,禁止了影子戏并关闭了所有剧院。我和学徒埃莉斯看着积蓄日渐缩水,知道别无选择,只能咽下昔日骄傲,成为一名赏金猎人。
要杀掉怪物已属不易:当你只是一名幻术师时则难度倍增。
“格兰戴尔有三个人脚踩着肩叠起来那么高。它是魔鬼的后代,在恐惧与悲伤中孕育。它有畸形的头,歪斜的脊椎,生锈匕首般污秽的牙,它的三只手臂不一样长。它晚上来掠走我们的孩子,留下的只有噩梦。”
我们跋涉穿越黑暗森林。我在脑中反复回味安瑟伦的话语,为即将到来的任务做足准备。
“师傅,我们怎么才能用幻术打败怪物?”埃莉斯问道,她美妙的嗓音中充满恐惧和怀疑。这能够模仿狮子怒吼或夜莺歌唱的嗓音,此时颤抖着。“我可只学过怎样发出讨喜的声音。”
“剑和火焰魔弹并不是唯一有杀伤力的东西。”我告诉她,“人与怪物同样,都会在心中最黑暗的恐惧成真时死去。”
她点头,下巴紧绷。她13岁了,不再是个孩子,能分辨出我的话什么时候只是安慰而非出自真心。
我指向路边,那里便突然出现一座茅屋,窗户发出温暖的光。透过雾气迷蒙的窗格,你可以看见一对夫妇在逗弄宝宝的剪影。我们静静地站着,凝视着完美的一幕。我毕竟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幻术师。
“谢谢你,师傅。”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挥一挥手,茅屋便消失。
2016年7月15日,从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市举行的第40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传来喜讯,中国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项目通过大会审议表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无疑为花山岩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奠定了一个国际基础,花山岩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站到了一个更高更大的平台上。如何利用申这个国际平台展现自身的价值和魅力,吸引更多的国际关注,反过来为自身的保护、传承与传播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是花山岩画对外译介承担的一个必要任务。但是反观花山岩画目前的对外译介情况,笔者却觉得不容乐观。
“坚持你的梦想,它便永远不死。”我告诉她,“现在继续上路。”
许多年前,一个婴儿狂野的哭声把我从温暖酒馆里的麦酒微醺中唤醒。循着那强劲的嗓音,我发现裹在毯子里的埃莉斯被抛弃在教堂的台阶上。我知道她很特别,拥有天赋。
我很欣慰自己仍能打动她,即便在她眼中,我已不再是无所不能。
树林逐渐变疏、穷尽。我们到了格兰戴尔筑巢的沼泽地。
“来战吧!”我朝雾气大喊,空气中充满腐烂植物的恶臭。
格兰戴尔在五十英尺开外的雾气中浮现。它的脸,覆盖着扭曲的皱纹和渗脓的疮口;它的眼睛,就像我在动物园中见过的笼中虎的双眼般血红。它死死盯着我,让人不寒而栗。
它靠着腿撑起身体,用三条胳膊敲打胸口,张开血盆大口,怒吼着向我冲来。
我挥动双手,一百个骑士步出森林,他们的长矛在我身后排成一列,形成一面利刺的坚墙。
格兰戴尔将腿扎入泥地,停下了。它继续将目光抬高,高过长矛,直到看见我的杰作。那是一条一百英尺长的龙,闪烁着祖母绿的荧光。它缓缓盘起身体,目光凶残地俯视着格兰戴尔。
我向格兰戴尔微笑,它只能选择逃跑。绝望黯淡了它的双眼,但它眼中又重燃起反抗与愤怒。它开始再次向我冲来。有时候仅靠幻术还远远不够。
“我很抱歉,埃莉斯。”我轻声说。她脸色煞白,眼睛闭得紧紧的。
突然间,另一阵嚎叫从远处传来,那是在沼泽深处。听起来更像是格兰戴尔在叫,只是更苍老,而且……更令人毛骨悚然。
在离我们只有十尺开外的地方,格兰戴尔站住了。它转身望着嚎叫传来的方向。
一个轮廓在迷雾中聚结成型:扭曲的脊椎、无用的肢体,衰老的面孔布满伤疤,一个长满西班牙苔藓般茂密长发的头。
格兰戴尔朝着远处的轮廓嚎叫,像是提出一个问题。
那个轮廓回应,我几乎能从她的嚎叫中认出词语—有悔恨、悲伤,以及找回曾经失落之物的喜悦。
当那轮廓再次隐入雾气之时,格兰戴尔开始奔向它。成对的嚎叫传来,一个古老而怀有母性,另一个年轻而深情,一起渐行渐远。然后,骤然间,嚎叫声停止了。
埃莉斯用力呼吸,她的脸因为长时间竭力发声而变得通红。“那里是悬崖。”
“干得漂亮。”
埃莉斯给我一个疲惫的笑容。“有时候梦想也能杀人。他也是个孤儿。”
我为爱丽丝的机智强大而高兴。我也为自己不再是最伟大的幻术师而忧伤。
(原载《科幻世界》 山西刘丹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