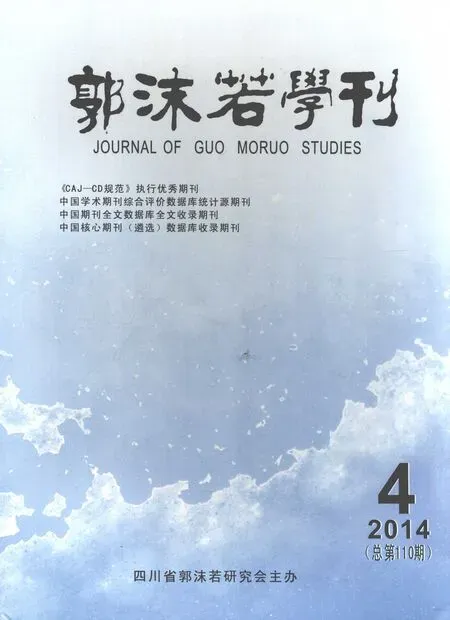重读《地球,我的母亲》
林荣松
(宁德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宁德352100)
重读《地球,我的母亲》
林荣松
(宁德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宁德352100)
《地球,我的母亲》是郭沫若诗歌的重要作品,以往解读立足于礼赞工农、劳动和创造,其实,最值得注意的是生态视域下人与地球的关系。地球博大的慈母胸怀,“我”发自内心的报恩心理,从中可以窥见人类与地球关系的未来图式,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热切期盼。
地球;母亲;“相亲”;“报恩”;生态情怀;悖论
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是诗集《女神》中的重要作品,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往解读该诗立足于礼赞工农、劳动和创造,其实,最值得注意的是生态视域下人与地球的关系,而这一层长期以来被忽略了。
一
置身于五四时代开放性文化结构之中,郭沫若的态度是别致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独到的理解和割舍不断的情感,但又不是固守的、学究式的推崇,既用传统文化“净化自己,充实自己,表现自己”,又能“融化一切外来之物于自我之中”,从而构建《地球,我的母亲》的生态文化立场。
中华传统文化不乏生态智慧。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多以儒家“天人合一”作为代表。“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旨归,也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眷顾,培育了中华民族亲近自然的文化心理和伦理目标。郭沫若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同时吸收了西方浪漫主义尊崇地球母亲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论中德文化书》等文中,多次谈到他的泛神论倾向滥觞于传统文化,坦言因为喜欢庄子才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接近”,才受泛神论思想的“牵引”。在他看来,泛神论提供了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理想境界,可以让人回到原始的“大同社会”。歌德鼓吹“以自然为慈母,以自然为女友,以自然为爱人,以自然为师傅”,郭沫若感同身受:“特别是对于自然的感念,纯然是以东方的情调为基音的,以她作为友人,作为爱人,作为母亲。”而以崇尚自然为重要特征的长江流域文化,特别是巴蜀文化,对郭沫若的精神个性给予了深刻的影响和发展的基础,加深了他对大自然执着的偏爱。故乡的两条河流沫水与若水,不仅成了他的名字,更融入到他的血脉之中。所有这一切,都成为郭沫若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源,写出《地球,我的母亲》绝非偶然。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最早真切感悟生命自由与自然尊严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强调“绝端的自主,绝端的自由”,由此激发出强烈好奇心和审美想象。郭沫若还是一位“重视人伦感情”的人,以“孝”为先思想深烙在他的意识深处,每提起父母莫不感激之至。正是这种立场与情感的交织,“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才能完美融合,人与地球之间的亲和关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地球,我的母亲》作为时代精神的宣泄与自我感情的释放,既契合了“劳工神圣”的五四潮流,又拓展了对地球的认知范围与体验程度,诠释了由自然彼岸回归自然之中的生态伦理命题。
二
郭沫若回忆《地球,我的母亲》的创作经过时说:“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去看书,突然受到了诗兴的袭击,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木屐)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在那样的状态中感受着诗的推荡、鼓舞,终于找到合适的诗句。”郭沫若以丰富的意象、奇妙的联想和饱满的情绪,描述了地球的慈母胸怀,“我”发自内心的报恩心理,字里行间荡漾着浓浓的亲情。诗人用一颗纯粹的心在呼喊,这显然要比说教性的文字感染力更强。
《地球,我的母亲》重新书写了人与地球的关系。人与地球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相亲”:人是地球之子,没有地球母亲无私的养育和呵护,就不可能有人类。地球还用“你的歌”“你的舞”“你给我的赠品”“特为安慰我的灵魂”。每念及此就会由衷希望:“地球,我的母亲!/我不愿在空中飞行,/我也不愿坐车,乘马,著袜,穿鞋,/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从“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到“我饮一杯水,/我知道那是你的乳,我的生命羹”,使“相亲”的画面充满了母子间才会有的亲情和温馨。第二个层面是“报恩”:“相亲”是“报恩”的基础,“报恩”是“相亲”的升华。“相亲”多了些情感的元素,“报恩”多了些道德的成分。“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报答你的深恩?”明白这一点,“表示我的孝心”才有了依附;作为“孝子”的“农人”和作为“宠子”的“工人”,连同“草木”“动物”,才会令人“羡慕”。第三个层面是“行动”。“报恩”不是摆设,关键在行动起来,像“田地里的农人,炭坑里的工人”用劳动来报答地球母亲的深恩。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血液来养我自己,养我兄弟姐妹们”;要做到这样,“我”不但要健强“体魄”,还要强健“灵魂”。从“相亲”,到“报恩”,再到“行动”,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情感的力量与逻辑的力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生态环境里,世界万物都是相互依赖,丝丝相扣的。自然是生命的物质载体,生命是自然的精神结晶。自然是人类存在的空间,人类是自然的存在物。对人类而言,地球尽到了母亲的责任。对地球而言,人类远未尽到“孝子”的责任。对于地球母亲,人类往往在掠夺式地开发,在浪费着各类资源,在污染和破坏着从地面到空间的环境。我们曾经健康美丽的地球母亲,怎堪如此重负、这般摧残。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只于此。地球是人类共有的永远的母亲,她的健康美丽事关人类的千秋万代。如果人类希望世世代代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家,就得首先保证地球母亲永葆青春、健健康康。所幸的是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不孝”的恶果,生态意识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保护地球、美化环境正在不懈努力。
三
郭沫若自称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从不客观地、静止地描写自然景物,相反,总是将自己的主观情感倾注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之成为自我表现的对象。从亲近自然,到效法自然,到超越自然,再到“没我”于自然,他在咏叹生命中感悟自然的伟大,在自然的启迪下联想到日月轮回、新陈代谢千秋万代。
郭沫若早年就研究过天体的形成和发展,对宇宙因何存在、为何变化发展的原因有过思考,虽然没有找到科学的答案,但这一经历促成和丰富了他的生态情怀。在给宗白华的信中他曾提及,《三叶集》通讯期间田汉从东京湾来博多湾小聚,有一天看到路旁有一堆嫩草,田汉脱了木屐跳入草丛。郭沫若马上说:“你爱他,何苦蹂躏他呢?”这种本能的反映,正是深植于心的生态情怀的最真实的流露。1978年郭沫若病重期间留下遗嘱:“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大寨曾是中国农业的一面旗帜,郭沫若对大寨有着特别的感情,把骨灰撒到大寨肥田不仅体现了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生命观,也使他的生态文化思想多了几分感人的成分。
郭沫若对远古文明充满无限向往,追怀“自由纯洁的原人”,羡慕“人类的幼年,那恬淡无为的太古”(《南风》)。从这个基点出发,他在晴朝中陶醉(《晴朝》),在春天里歌唱(《司春的女神歌》),预感到“春潮正涨”(《春潮》),憧憬着新芽萌发(《新芽》),漫步在清新的松林、平整的沙路和唱着歌的车夫构成的“平和”画面中(《晚步》),享受着“到处都是笑:海也在笑,/山也在笑,/太阳也在笑,/地球也在笑”(《光海》)。郭沫若没有满足于乐观的歌唱,《凤凰涅槃》已经带有生态预警的意味。梧桐枯槁、醴泉消歇的恶劣环境,逼迫凤凰集香木自焚以获重生,环境与生存的关系就是这么残酷。正是对皈依自然心有所感,又清醒地看到了这样的生态危机,他在《我们的花园》中呼吁:自然是“我们的花园”,需要我们自己来美化。郭沫若笔下尊重劳工与善待地球、人类诉求与生态保护互为呼应,从中可以窥见人类与地球关系的未来图式,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热切期盼。
毋庸讳言,五四时代出于启蒙和救亡的需要,过于夸大“人”的地位、作用和力量,从而导致对天地自然之道的忽略甚至无知。素有浪漫心性的郭沫若,在“生的颤抖”与“灵的喊叫”中,同样难免会因缺乏理性制约而压抑了自然。《地球,我的母亲》创作于1919年12月,此前两个月,郭沫若还写了一首同样以地球为题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诗中放声呼喊:“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把地球摧毁”。此后两个月,又有《天狗》一诗问世:“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要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短短数月时间,从“摧毁”到“相亲”“报恩”,再到“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如此矛盾的诉说,主要源于郭沫若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各种思潮纷至沓来,而他自己正处于思想发展的青春期,又宁愿做一个自我放逐的歌者,出现波动与彷徨的现象在所难免。《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和《天狗》一向被当成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的宣言书,但换个角度看,澎湃激情的背后折射出可怕的人本主义思想观念。对天地自然失了敬畏之心,人的主观意志就会无限膨胀。应该看到,郭沫若那一代知识分子还不具备真正的生态意识,没能预见人类将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困境,没能通过伦理反思唤起人类对自然责任的担当。郭沫若身上实际上存在这样的悖论:既呼唤生命从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突围,又向往在激烈的破坏中构建新的自然;因对“人”的强调获得了对生命的超越,但过于强调“人”又限制了思考的广阔性、深刻性和科学性。可见,人类摆脱人本主义观念绝非易事,生态文明的建设任重道远。
人类有权享有一个健康美丽的地球,地球同样拥有健康美丽的权利。人类在受益于地球的同时,必须扪心自问为她做了些什么。要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局限和思维定势,实现《地球,我的母亲》的期待目标,那么,从现在就开始,从每一个人做起,全身心投入地球生态的保护吧。
(责任编辑:王锦厚)
[1]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A].郭沫若研究资料(上)[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72.
[2]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J].创造周报,1923(3).
[3]郭沫若.自然底追怀[J].时事新报·星期学灯,1934(70).
[4]郭沫若.论诗三札[A].沫若文集第10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13.
[5]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I207.22
A
1003-7225(2014)04-0036-02
2014-04-15
林荣松,宁德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