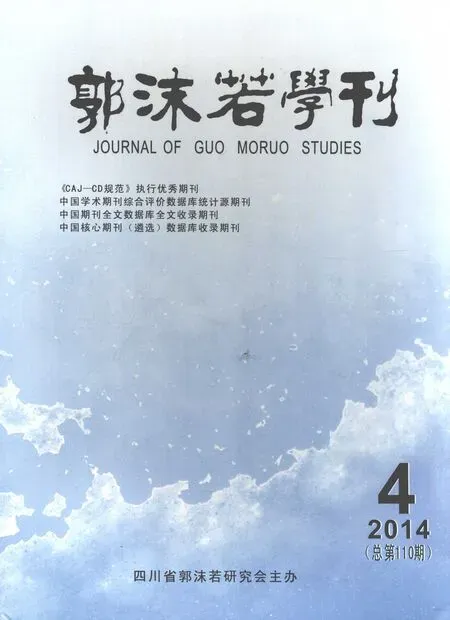学术视野下的《甲申三百年祭》研究
何刚
(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乐山614000)
学术视野下的《甲申三百年祭》研究
何刚
(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乐山614000)
《甲申三百年祭》与当时围绕明末史研究已然形成的学术语境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和衔接;抗战时期国共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往往以学术面相呈现,学术话语构成了双方建构各自革命意识形态时共同利用的思想资源和工具,学术的政治意图与政治的学术外衣紧紧的纠缠在一起,这在当时明末史研究和《甲申三百年祭》上得到鲜明体现;除了在国共双方的政治斗争中激起巨大影响之外,与现实政治似乎有一定距离的学界学人对《甲申三百年祭》同样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读。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学术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抗战时期刚一刊出,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国共双方为了各自的政治斗争和用途考量,在解读《甲申三百年祭》时有意凸显其某一方面的内容或主题,并加以选择性利用,构成双方在文化宣传战线上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围绕《甲申三百年祭》又出现过几轮评论和研究热潮:官方一如既往的延续过去的做法,将其视作新形势下执政党自身建设可资借鉴的历史教材,通过各种场合和公开文字阐发其现实警戒功能;学界则对郭沫若的撰写动机意图、《甲申三百年祭》的学术得失和价值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上述研究成果浩繁,论述详备,本文无意再作赘述。
本文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从当时学术发展理路的视角看《甲申三百年祭》与当时民国学术之关系,试图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研究补阙,并请方家指正。第一,众所周知,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之时,其主要精力在于先秦诸子研究。他之所以专门抽出时间选择明末历史进行研究,写成此文,固然缘于现实斗争的政治需要,但同时也和自晚清以来明末史研究的持续热潮有着紧密的联系,与之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思想与学术史渊源。例如,在明末历史问题上形成的,诸如南明政权覆灭、满清统治中原就是中国亡国等观念,构成了包括郭沫若在内的民国士人共同的思想资源。第二,当时国共双方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往往是以学术的面相呈现出来的,学术话语构成了双方建构各自意识形态时共同利用的思想资源和工具,这在围绕明末历史及其《甲申三百年祭》而起的“轩然大波”上有清晰的体现。学术的政治意图与政治的学术外衣的纠缠颇为注目。第三,《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除了在国共双方的政治斗争中激起巨大影响之外,该文在与现实政治似乎有一定距离的学界学人那里,是否也能得到他们的关注?他们又从《甲申三百年祭》那里解读出了什么呢?
一
在20世纪前半期的“史学革命”中,各派各家并起,争流竞进,“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沉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流播”,使中国史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具体到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再加之因应当时现实斗争和社会生活变迁的需要,同样取得了很大成就。就研究领域而言,如明末与南明史史料整理出版、明代东北地区及满族源流、以抗倭为主的明代中日关系史、郑和下西洋、明代中欧关系交往史等成为研究热点。其中,明末政治形势与明末农民战争研究更是热点中的热点。随着西方各种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被借鉴应用到中国史学,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史学受到有力冲击,过去延续已久的传统观点开始遭到“重新估定”和纠正,这在明末农民运动研究成果上有鲜明的体现。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草创时期,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用唯物史观对明末历史,特别是对明末农民运动进行分析,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看法。这些都构成了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时的基本学术语境。
随着二三十年代社会科学潮流的勃兴,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治史成为当时许多学人的共同旨趣。在明末史研究中,这一潮流表现得很明显。学者开始从整体上对明末的社会与政治形势进行阐述,从社会背景着重分析明季“流寇”兴起、明朝灭亡原因,从社会阶级性质及关系的角度分析明末农民运动的成败教训等。
关于明朝灭亡。
“贼亡人国”,“明朝之亡,亡于流寇”是尽人皆知的旧史之说。在三四十年代,也有人持类似的观点,认为:“亡国之惨酷莫如明,而明之,也曰流寇:以流寇之故而中原荒芜,以流寇之故而都城残破,以流寇之故而思宗殉国,以流寇之故而清人入关。”但大多数学者已经不满足于这一简单化且具情绪化的结论,认为对此必须要“作一客观的探讨”,找出它的“社会的基因”。学者们提出,明季流寇之所以猖獗,实际上是由当时时局所必然造成,因为“流寇既不是如一般史家所说的‘天生贱骨’,更不是什么‘飞将军从天而降’,他也是血肉之躯的人类,他的形式,更离不了当时社会环境的背景,所以我们要研究流寇之亡明,必得要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换句话说,我们要认识孕育流寇的母体”。他们从明朝社会组织、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明季之亡进行原因分析。例如,陈德昭在《明季之政治与社会》中总结道:“明季政治社会衰败之极,当时的若干现象真使人怵目惊心……旧的社会组织实在是历史进步的桎梏。地主的脱离生产,和土地耕种的零星分割,一面是社会贫困的本源,同时更使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停滞不进,以致坐等天灾人祸的摆布。”学者们通过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明朝“在当日虽无流寇满清,固亦不能免于亡也”。
其中,过去史家多称赞崇祯帝是一位聪明有为、励精图治的皇帝,于他“殉国”之君的末运表示同情。崇祯自己亦有“朕非亡国之君,臣尽亡国之臣”的话。《明季北略》亦有“明之所以失天下者,其故有四,而君之失德不与焉”之论。作为明末政治与社会机构的最高职掌者,崇祯帝是否真的与明亡无太多的干系呢?学者们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提出,要分析明季亡国的原因与责任,应将崇祯皇帝作为研究的中心,“自崇祯帝即位,以迄被难,中间有十七年之久,且即位之初,东北边事尚相持于今之锦州一带,后来攻陷北都之李自成,尚未创乱,假使崇祯帝挽救得宜,尚有可能,然终于不能挽救者,崇祯帝十七年中之措施,当然有很重的关系”。他们认同清初戴笠在编辑《流寇长篇》时的“自叙”——“主上则好察而不明,好佞而恶直,好小人而疑君子,好速效而无远计,好自大而耻下人,好自用而不能用人”,认为君臣都是明朝亡国的责任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崇祯有根本的错误,实为明季亡国的第一主因,具体表现为:流于以察察为明而使太监监审,宦官布列要地;擢用将相以个人好恶为标准,以致人才适得其反;“猜疑忍酷喜怒无常,予智自雄苛于责人等种种心理病态”等。
关于明末农民运动。
《明史·流贼传》有“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代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的说法,对明末“流寇”暴蛮惨虐的各种行状记载甚多。学者们多认为这些感性与想象的文字并不足信,应进行理性分析。他们首先认为,明末“流寇”属于贫农革命的性质,“而后来参加之士大夫及城市流氓,虽居领导地位,然其主张不外迎合此辈贫农之要求,其作用更在谋要求之实现”。同时,因为其后抗清反吴,部下归于南明,“尽屡经抗战,民族意识极为发达”,因此,于贫农革命性质之外兼有民族解放之意义。其次,明末“流寇”之兴起,实为当时社会情势所致。有人提出,当时的贪污政治是“制造流寇的源泉”,官民争地即土地兼并是“制造流寇的酵母”,经济财政的破产崩溃是“加速流寇的发展”。相似的,有人指出:“南居益所说的‘军民交困,嚣然丧其乐生之心,穷极思乱’的情形,自然是造成流寇的根本原因。其中最怵人心目的,就是在灾荒既起之后,而当时的士绅,还在乘灾荒和贫穷所构成的极端困苦的情况,加紧他们的横暴侵渔的活动;其结果,民间累积的怨恨,更催速了变乱的爆发。”
与前述基本上停留在“穷极思乱”的解读路径与层次不同,当时有一些人在自觉不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治史的过程中,努力尝试将唯物史观运用到明末农民运动研究之上。代表人物即是三十年代正“出入于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之间”,并“开始越出实验主义史学的门墙,走上了研治社会史”的吴晗。1934至1935年,吴晗相继发表《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与《明代之农民》两文。前文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指出,明末农民运动的兴起是社会“贫富两阶级悬殊”的结果,农民为了生存,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打倒旧日曾鱼肉他们的阶级”,晚明流寇的兴起是一个社会组织崩溃时必有的现象,如瓜熟蒂落一般;后文则对明代农民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农民税役负担过重,土地高度集中,“地主和贫农的关系也愈趋恶化”,农民叛乱自然会发生。
学者们结合中国历朝农民起义的特点规律,对明末农民运动失败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并重点谈到了革命队伍出现的“领袖之腐化及其内讧”和思想意识蜕化问题。例如,有人对起义队伍进京后骄傲腐化,内部相斗尤其是李岩被杀等事进行批评:“自成持身颇俭,而其他领袖入京师后,多得意忘形……刘宗敏等将则骄横非常,肆意耽乐,甚至士兵怀金,亦少斗志,故抗满第一战即遭大败。至牛金星谗杀李岩,则尤自坏栋梁,减损实力,以岩之声望而言,则使部众凝心,殆为事实。”有人总结道:“他们只是暴动者,而不是建设者。他们永久只是顾念着自己。他们散漫,没有理想,没有坚强的信心和毅力”,“当他们的势力日趋强大时,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的意识,就很快败坏下来。”
这一时期,涌现出诸如柳亚子、谢国桢、吴晗、王崇武等一批明末及南明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例如,抗战前期是柳亚子研究成果最为集中丰硕的时期,他倾心史料搜集整理,潜心研究,撰成《南明史纲初稿》(第一编),还有《南明后妃、宗藩传》、《江左少年夏完淳传》等十余篇(部)人物传记,以及多篇考证文章;谢国桢在1926年发表《明季奴变考》一文之后,历经数载访求书籍,于三十年代出相继出版有《晚明史籍考》(80万字、20卷)和《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论著。
可以看出,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与当时围绕明末农民运动研究已然形成的上述学术语境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和衔接,至少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其时形成的纪念甲申三百周年与明末史研究的学术热点,在史料搜集整理、史籍考证等方面形成的活跃学术氛围;二是摒弃过往用“寇”、“贼”等字眼对明末农民运动的感性描述,转而进行正面客观的深入分析;三是在分析明亡原因时,将崇祯帝作为重要着眼点,推翻过去崇祯“非亡国之君”的说法;四是分析明末农民运动失败原因,谈到了起义队伍堕落腐化的问题。必须指出,除了这些契合与衔接之外,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与前述明末史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和转向。笔者以为,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叙述重心的转移,即由过去对明末农民运动整体叙述,转而深入农民运动内部,以历史人物叙述为重点和主线,将明末史和农民运动叙述成为崇祯、李自成、李岩三位历史人物命运的“悲剧”诗史。正是这种以历史人物命运为主线、由外移入内的叙述策略,方才引起各方的关注与共鸣,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甲申三百年祭》虽然选取的是明末历史,是农民战争题材,但从本质上讲不是农民战争史研究,而是历史人物研究,应将其归入郭沫若四十年代坚持“以人民为本位”的历史人物研究的整个谱系和脉络之中。
二
《甲申三百年祭》所承载的政治现实功能是勿容置疑的。但是,它关注的是几百年前的一段旧史,出自一位文化学术大家,具有完整的学术形式和风格,何以能在国共思想文化战线上掀起“轩然大波”呢?其实,当时国共双方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往往是以学术的面相呈现出来的,这在围绕明末历史研究和《甲申三百年祭》上有清晰的体现。
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为了给其“剿匪”“攘外必先安内”等统治政策寻求历史依据,蒋介石找到了明末历史,强调当时中国与明末的相似性。1933年7月创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后,他多次对之发表讲话,声称“如不先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明朝之亡,可为殷鉴”。他说:
一方面抵御外侮,一方面势必至要分力剿匪,那就与从前明末的情形一样。当明末之时,一面陕西山西的土匪猖獗,他没有先去剿清,因之满清乘机入关。假使当时明朝只竭全力在山海关那边抗战,他何尝不能抵御外侮。可是后方的土匪李闯猖獗,等他打到了北京,结果只有亡国……不得不承认明朝之亡国不是亡于满清,而是亡于匪乱。现在我们的国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剿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如能够稳固自强,终究是挽救转来的。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步骤零乱,既要对内打土匪,同时又要对外御外侮,试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结果也只好重演一回明朝亡国的故事。
蒋介石此语既出,大批为其佐证、详加阐述的文章在各种出版物上涌现出来。它们将“流寇”与“共匪”“赤匪”直接等同在一起,借诬蔑明末农民起义来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讨论“治流寇之方法,以为剿赤匪之一助”,其哓哓之声十分刺耳。例如,《明代士大夫之矫激卑下及其误国的罪恶》一文称:“自九一八以来,暴日进逼于外,共匪猖獗于内,与明末外有满清的侵扰,内有流寇的纷乱,国家是同样地陷在风雨飘摇的境地;”持相似论点的文章还有《中国明代匪乱的总检阅》、《崇祯朝的“官”与“匪”》、《新流寇》等等。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于此十分忧惧,称:“近闻各地奸民,假借游击队名义,恃众横行,扰乱秩序,妨碍治安,种种弊害,不胜枚举。是未见困敌,先以自扰,殊失全民抗战之本意”,因而下令“禁止假借游击队名义”。所以,当时攻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术的各种文章又多了起来。其中,“反共专家”叶青的《关于游击战术》一文,将中共的游击战术和历代“流寇”的流寇主义结合起来,可谓代表。叶青称:“整个来说,这样的游击战术论实在是一种农民(精确说来是破产农民——流氓)意识底反映”,“这是由陈胜吴广经过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直到义和团一切被史家称为‘流寇’的农民战争经验之展开。”
与此同时,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展开的围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中,农民运动问题成为一个重要方面,“究竟在中国现在农运是否需要?农运与革命,是否有关?农民阶级是否为国民革命的基础阶级,他对于革命有何力量?”这些都是当时人们十分关心和热烈讨论的问题。同样的,这种现实的讨论自然也会转移到对“史”的分析之上,论战阵地如《新思潮》《文化批判》《新生命》《读书杂志》等均有这方面的文章。其中,陶希圣在《新生命》上连载《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一文,历述历史上许多失败的“由革命转变为剥削”的农民战争,根据这些“历史经验”断定:在中国革命中,游民无产者起不了作用,“这种革命的教训,在观察中国今日流寇的发展的时候,是不应当忘记的……从流氓散兵所集成的流寇上去讨社会主义的出路,是枉然的。”陶希圣此处显然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而发的。
所以,在整个30年代,围绕明末农民起义,名义上做学术文章,实际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人很多。他们均不约而同的将影射攻击的对象指向了中国共产党。这当然也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注意和反弹。1940年,翦伯赞连续发表《辽沈沦陷以后的明史》《论明代阉宦及阉党政治》等文,赞扬明朝军民对满族入侵的英勇抵抗,揭露明朝君臣昏庸和政治腐败招致引敌入室。这无疑是对借“流寇”之说的国民党政府有力针砭。1941年,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在上海出版的《知识与生活》发表《流贼二臣及其它》一文,一针见血的指出,封建史学家替地主官僚服务,自然要给予叛乱农民“流贼”的谥号。现在的中国革命已不同于宋明历代的农民战争,因为先进阶级的领导是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所以想做洪承畴或洪承畴的师爷帮闲清客们便要大大的冷落起来,于是不得不大骂先进势力了,尤之陶希圣,陈独秀,叶青,胡秋原诸公,便都不免要先先后后借流寇而骂到游击战,更乘势欲把一粪帚的污水洒到别人的头上去”。1943年,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刊物《群众》发表《明末农民运动研究》一文。该文分“崇祯时期”和“南明时期”两个阶段,对前后长达三十四年的明末农民战争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回顾,高度肯定其历史意义和李自成等农民领袖的功绩。而《甲申三百年祭》,从重庆新华日报社等围绕纪念明亡三百年的酝酿组织,到该文的连载出炉等,更鲜明体现了中共的政治反击目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在蒋介石国民政府一方,继续公开的将中共与“流寇”等同起来,显然是不合适的。在文化宣传和政治话语建构上,“抗战建国”、“民族复兴”成为了其最重要的关键词。为了与国民党内投降派的斗争,激励军民抗战信心,更为了维护其思想文化上的统治,他们有意将当时现实的中国与宋季明末的中国切割开来,强调今日之甲申非昔日之甲申,反对将二者相提并论,并提出,“今日全国奉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准绳,一切言论行动,皆以此为判别是非顺逆忠奸贤不肖的标准……即或有少数文人仍如明末无聊士大夫之所为,亦终必被全国唾弃”。
所以,《甲申三百年祭》刊出以后,国民党方面自然将郭沫若视作“如明末无聊士大夫”的代表,从“败亡主义”的角度,斥之为“败战亡国的思想之残渣”。对此,共产党和《新华日报》方面很快进行了反击,着眼点仍在学术之上。《甲申三百年祭》出版两天后,也就是3月26日,潘梓年就发表《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一文,从“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角度,抨击思想专制意图。潘梓年认为,学术思想自有规律,不应由政治力量从外面来加以干涉和束缚,不应以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为由,动辄对学术思想进行钳制、“纠正”,“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是把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区别开来的重要特征,也是战胜法西斯日寇建立新中国的必要条件。我们迫切需要有学术思想的自由。”
国民党方面继而组织的抨击也一改之初直白的政治语言,将自己的文字披上了学术讨论的外衣,大谈历史,试图在学术研究上将郭沫若击倒。这在叶青、黄一本等结集出版的《〈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这本小册子上得到体现。例如,黄义本就指责《甲申三百年祭》是“错误的史观与武断的史论”,“个人的悲剧即是民族的悲剧,本来是一种英雄史观,不合于惟物史观。不过郭氏的英雄史观,同时是兼有反叛史观与假使史观,所以又合乎惟物史观的口味了。”越客更摆出超然世外的学术姿态:“今天他们不纪念别的年份,偏纪念这亡国之年的甲申,他们自有他们的用意,这里并无心去追他们的用意,只是列举二三史料,仅以警惕我同胞。”
三
除了在国共双方的政治斗争领域激起巨大影响之外,《甲申三百年祭》在与现实政治似乎有一定距离的学界学人那里,是否也能得到他们的关注?他们又解读出了什么呢?
乍一看来,《甲申三百年祭》并未进入主流学界的视线,因为未见有主流学者对其进行评论,一些主流学术刊物也没有评介性的文字。然而,情况并非这么简单,未见有专门的评论,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对其进行关注。恰恰相反,笔者认为,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刊出后,应该是进入到了一般学界的学术视野,并带来很大震动。不仅如此,由于不同意郭沫若对明末清初历史及农民战争的全新论述,他们积极组织撰述和刊发相关文章,予以驳诘。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为例,1947年出版的第十二本上,就同时刊载了李光涛的《清太宗求款始末提要》《清入关前之真象》《记努尔哈赤之倡乱及萨尔浒之战》《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记崇祯四年南海岛大捷》《清太宗与三国演义》等6篇文章,后几本又相继有《刘綎征东考》《李如松东征考》《洪承畴背明始末》《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等文。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本文于此无意全面展现,这里仅以李光涛的两篇文章为例,或可见一斑。在《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一文中,作者用意主要是为了论证:“明末‘东事’与流贼为二大祸,‘东事’者,努尔哈赤之叛国也,流贼者,李自成张献忠辈也。二者并生,明廷左右支吾,卒至于亡”,“盖流贼实因‘东事’而蜂起,东事亦缘流贼而不救,明兵仅有可用者一股,顾左失右,援东西弊,此其所以亡也。”而在《清军入关之真象》中,作者认为,1642年“壬午虏变”之时,清军实力本已筋疲力尽,很难摇得动明朝这棵“大树”,“假使明末无流贼,或者崇祯十七年没有李自成之陷都,或者崇祯暂时地南迁,或者明朝更换一好人为帝,则是关外清国的命运能否可以长久自保,恐怕都成了问题”?在四十年代后半期,主流学界对明末历史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关注,确实很不寻常,应当是受到了特别的刺激才对。再加之李光涛等人所持之论与《甲申三百年祭》南辕北辙,成尖锐对立之势,文章虽未点名,但看得出,他们这一时期关注明末历史,集中刊文,当与《甲申三百年祭》此前掀起的“轩然大波”不无关系,其用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消解郭文的学术影响,以“拨乱反正”。
我们再以这一时期撰文最多的李光涛为例,他在40年代倾心于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在中央研究院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傅斯年的授意推助密不可分,而傅斯年的授意推助又与蒋介石的“询问”颇有干系。例如,对于自己研究明末农民起义,写作《明季流寇始末》一书,李光涛曾回忆道:“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傅孟真先生由美国回到南京,晋谒蒋总统于北极阁之临时官邸,当时共匪猖獗加紧危害中华民国,蒋总统有感于此,特向傅先生询及中国历代流贼(包括自汉朝以来)的史实究竟是怎样?所以傅先生就嘱光涛写了这篇《明季流寇始末》一文,于三十七年十一月完成。”
当然,除此之外,在当时一般的评论界和出版界,部分学人也关注到了《甲申三百年祭》。只是他们的关注和解读与国共双方都不同,他们既没有解读出“败亡主义”,并以此为调对“流寇”(明末的和现代的)大加鞭挞,也没有从中找出“革命胜利后不能骄傲”的历史教训。他们的解读恰恰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所忽略的。
比如,有人就敏锐的看到《甲申三百年祭》以李岩为中心,对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一问题进行的论述。1946年,孔另境主编的《新文学》杂志在第二期就刊载了《读〈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者就说:“郭先生这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真相,更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估量,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个人的感觉,则作者对于李岩的悲剧,认为永远值得回味,无宁是对知识份子在时代中作用,看得太独立了,李岩是代表中国知识份子的另一方面,历史上尽多李岩这种类型,现代的李岩,当然应该理解的是农民运动的本质是什么。”这位作者读出了郭沫若在书写中对李岩“悲剧”的用心,尽管他可能并不认同郭沫若就李岩在整个明末农民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分析,认为这“对知识分子在时代的作用,看的太独立了”。但是,他的解读可能是与郭沫若的写作意图心境最为接近的。
还有人整体肯定《甲申三百年祭》“搜集了许多正确的史料,用进步的,科学的观点,批判地把数百年来歪曲的历史纠正了”,如驳斥了封建“流寇”论者,把崇祯帝的真相客观地予以批判和暴露等,并从中解读出当时政治动员上的一个重要口号——“政治重于军事”的结论,认为郭沫若通过分析李自成失败的原因,“使我们懂得他在军事胜利以后,因为政治腐败分裂、谋杀,造成政治上的败失,而形成革命政权的崩溃,所以李自成便死于九宫山下;这里作者无异把他的失败,作为我们的殷鉴,用史实来证明‘政治重于军事’悬悬不解的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金性尧(笔名文载道)主编的《文史》杂志,在1945年7月的复刊第三期上开始转载《甲申三百年祭》,署名“鼎堂”。很快日军投降,《文史》因被划为“附逆刊物”而被取消,《甲申三百年祭》并未转载完毕。但是,即便如此,在发行量很少的沦陷区,《文史》的转载也扩大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响。例如,有人就是通过《文史》的转载才得以一睹《甲申三百年祭》的真容:“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这题自是去年早经在什么文化消息栏内见到了,正因是居敌区,无法入目,直到今年七月间的文史上转载,方才读到了一段。”
笔者认为,身处沦陷区的金性尧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郭沫若治学胆识的赏识,以及在明亡历史、明末农民战争等问题的认识上与郭沫若有相近之处。比如,早在1938年,金性尧就称赞郭沫若在“疑古辨伪”上的勇气和精神,认为“郭沫若先生从‘祖’字上证明了古人的‘生殖崇拜’,何尝不是违反了群情与旧说。王国维罗振玉之类即使有这样的主张,但决没有那样的勇气。而他们的思想因此也终于跳不出‘遗老’的泥沼”。对于明亡之责任,金性尧说:“‘流寇’自然也要负一部份。然而,当时的政府大员如马士英阮大钺诸公,一天到晚的只知道倾轧,挑拨与排挤,那罪恶,恐怕未必比‘流寇’来得轻。所以,与其痛责为饥寒的逼迫而掀起的农民暴动——‘流寇’,还不如咀咒那些丰衣足食,手握邦国大权而又苟安媚敌的朝廷命官来得公正!”所以,金性尧认为,如果只是一味的叫骂“流寇”长、“流寇”短的,而不去探究产生这种暴动的原因,甚至妄加征引,刻意挑剔,那么对于事实的真相,是永远没有什么裨益的。虽然金性尧未有对明末历史进行专门的研究,此处的论述也是针对汪精卫等人的言论而发,但是,明显可以看出,他对明亡历史,对“流寇”的认识,与后出的《甲申三百年祭》有许多的所见略同之处。正是这种所见略同促成了他对郭文的转载。
总之,《甲申三百年祭》本身承载着现实中亟需的政治功用,烙上深深的政治印迹,自问世以来即众说纷纭。如果从《甲申三百年祭》与当时民国学术之关系的这一新的视角对其进行再审视,可以看到:《甲申三百年祭》固然缘于现实斗争的政治需要,但同时也与当时围绕明末农民运动研究已然形成的学术语境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和衔接,同时也存在着从对明末农民运动的整体叙述,到深入农民运动内部,以历史人物为重心的叙述转向;围绕《甲申三百年祭》的前前后后可以看出,国共双方当时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往往是以学术的面相呈现出来的,学术话语构成了双方建构各自革命意识形态时共同利用的思想资源和工具,学术的政治意图与政治的学术外衣紧紧的纠缠在一起;《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除了在国共双方的政治斗争中激起巨大影响之外,同样在与现实政治似乎有一定距离的学界学人那里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读。
(责任编辑:廖久明)
注释:
①李光涛:《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1947年。据该本“本刊告白”知,李光涛此文曾刊载在该刊第十二本第一、二分合刊之上,于1945年在重庆出版,出版面世时间当在《甲申三百年祭》之后。当然,要指出的是,李光涛此文写作时间甚早,初稿于1937年夏成于南京北极阁,原名为“顺治元年正月至西据明地诸帅书稿跋”。由于初稿“以付印故,致沦陷战区,存亡不可知,兹所长傅孟真先生,嘱予再补写一篇”,所以,李光涛就记忆所及,并略事补充,于1943年夏再写于四川宜宾李庄古镇,并因原题目“见者不明瞭其内容”,将其改为“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
②《文史》创刊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停刊于三十四年七月,前后共出三期。《文史》是此前刚刚休刊的《古今》杂志的承续,如“撰稿人和内容大致和《古今》大同小异,有的还是《古今》存稿”。而《古今》系汪伪政府中一些担任要职的文人,如周黎庵、瞿兑之、徐一士、周作人等人在上海所创办。所以,《文史》被视为“附逆刊物”并不奇怪。比如,野草出版社1946年3月再版《甲申三百年祭》时,就称《文史》为“汉奸刊物”,其“窃将转载”《甲申三百年祭》“是不配的”。(参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野草出版社,1946年版,前言第1页)
③文载道:《关于历史的引用》,《华美》1935年第1卷第35期。金性尧此语是直接针对汪精卫而论的。汪精卫曾在《中央周报》发文,以所谓“明末流寇”比附、污蔑中共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说:“现在的游击队,是明末流寇的作法,用之于国内战争,或者可以颠覆政府,用之于对外作战,必不足以榰持强敌……所以明朝便亡于流寇。”(转引自高良佐:《汉奸汪精卫》,重庆求是出版社,1939年版,第8页)
[1]张荫麟.自序[A].东汉前中国史纲[M].青年书店,1944.
[2]祝实明.明季哀音录[M].交通书局,1942.
[3]陈德昭.明季之政治与社会[M].独立出版社,1942.
[4]薛农山.论明末的流寇[J].时代精神,1941,3(6).
[5]束世徵.明季流寇之成因[J].史学杂志,1929,1(3).
[6]赵正平.明季何以亡国[J].复兴月刊,1935,3(11).
[7](清)戴笠,吴乔.明末农民战争史料·流寇长编(上)[M].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8]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J].史学年报,1937,2(4).
[9]陈峰.20世纪30年代吴晗史学述论[J].史学理论研究,2003(2).
[10]吴晗.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J].大公报·史地周刊(第5、6期),1934年10月19、26日.
[11]吴晗.明代之农民[J].天津:益世报·史学(第11期、第13期),1935年10月1日、15日.
[12]张其昀.党史概要(第二册)[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
[13]众擎.流寇的性质与剿办赤匪的方法[J].铲共半月刊(第17、18期合刊),1931年7月.
[14]本俊.明代士大夫之矫激卑下及其误国的罪恶[I].汗血学刊(第2卷第3期),1933年12月.
[15]李奇流.中国明代匪乱的总检阅[J].汗血月刊(第2卷第3期),1933年12月.
[16]味辛.崇祯朝的“官”与“匪”[J].越风半月刊(第15期),1936年6月.
[17]新流寇[J].华年(第3卷第4期),1934年1月.
[18]蒋委员长通电禁止假借游击名义[J].民意周刊(第6期),1937年1月.
[19]叶青.关于游击战术[J].民族生命(第4期),1938年5月.
[20]克宣.农民运动的归趋[J].新生命(第6号)(民众运动专号),1928年9月.
[21]陶希圣.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J].新生命月刊合订本第3卷(下),1930.
[22]翦伯赞.辽沈沦陷以后的明史[J].中苏文化(第7卷第3期),1940年9月;论明代阉宦及阉党政治[J].读书月报(第2卷第7期),1940年10月.
[23]潘洛琏.流贼二臣及其它[J].知识与生活(第1卷第7期),1941年6月.
[24]陈家康.明末农民运动研究[J].群众(第8卷第1、2期),1943年1月.
[25]姜季辛.现代中国非宋季明末论[J].新政治(第6卷第3、4期),1941年8月;张九如.中国今日不是明末[J].中国社会(第5卷第2期),1939年1月.
[26]潘梓年.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N].新华日报,1944-03-26.
[27]黄义本.战败主义与思古悠情[J].民族正气(第2卷第4期),1944年4月.
[28]越客.甲申史料[J].民族正气(第2卷第4期),1944年4月.
[29]李光涛.清入关前之真象[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1947.
[30]李光涛.明季流寇始末·序[J].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一,1965年3月.
[31]陈鉴.读《甲申三百年祭》[J].新文学(第1卷第2期),1946年1月.
[32]边星.读《甲申三百年祭》后[J].综合(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
[33]金性尧.《文史》琐忆[A].星屋杂忆[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34]奴齐.读《甲申三百年祭》[J].书报(第1期),1945年11月.
[35]文载道.说到“流寇”[J].华美,1935,1(36).
I206
A
1003-7225(2014)04-0018-07
*本文为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项目“《甲申三百年祭》研究”(批准号:SC14E0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4-10-10
何刚(1976-),男,四川绵阳人,历史学博士,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和郭沫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