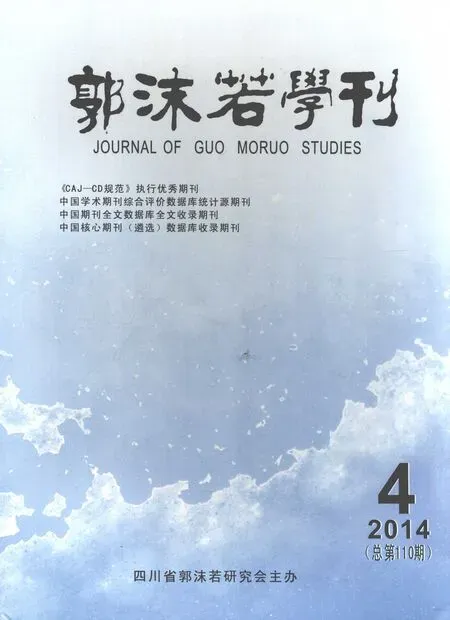《豕蹄》成书与“新文字”等史事
蔡震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北京100009)
《豕蹄》成书与“新文字”等史事
蔡震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北京100009)
《豕蹄》(上海不二书店1936年10月初版)习惯上被称作郭沫若的历史小说作品集,收录了他的六篇历史小说。但是实际上《豕蹄》还辑录了《初出夔门》等五篇自传散文,另有一首《献诗》。尽管郭沫若的作品集常常将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混编成集,但把历史小说和自传散文,再加一首诗作辑录为一个集子,还是有点“不搭界”的感觉。其原因,在《豕蹄·后记》中曾说到,关联到当时的一些史事。但《豕蹄》中的历史小说作品被收入小说集《地下的笑声》之后,这篇《后记》就被删掉了(以后的《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均如此)。《序》因另成一篇文章,即《从典型说起》,后来先后编入《沫若文集》第11卷,《郭沫若全集》第16卷。
《豕蹄·后记》中这样记述了这个作品集编辑出版的过程:
《豕蹄》,最初本是预定着用新旧文字对照着出版的。新文字已由李柯君苦心孤诣地翻译了出来。但据出版处的意见,说是新文字出版颇有困难,只得暂行抽了出来另印单行本,而把我去年下半年写的《自叙传》的一部分来补上。《自叙传》中所叙及的长兄橙坞,不幸在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已经病故,自北京一别后转瞬二十余年,未能再见一面便从此永别了。我之有今日全是出于我的长兄的栽培,不意毫未报答便从此不能再见了。含着眼泪补写这几行,聊把这后半部的《自叙传》作为纪念亡兄的花果。
这里提到的《豕蹄》的“新文字”已经翻译成了,并“预定着用新旧文字对照着出版”,是涉及到当时(1936年)国内文坛正在热烈讨论着的一件事情:实行拉丁化的新文字。郭沫若在年初时,就写过一篇文章《请大家学习新文字》,号召大家“赶快学习、赶快采用”新文字。不过文章发表在留日学生在东京办的一个刊物上。7月1日,郭沫若又与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陶行知、李公朴、鲁迅等140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提出:“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是值得向全国介绍的了。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意见”中建议施行的一个具体办法,就是用“新文字汉字对照”的办法编印书报。
郭沫若显然是身体力行,准备率先将自己的作品集以新旧两种文字对照出版了。7月10日,郭沫若与质文社的陈北鸥、任白戈、林林等人一起到横滨送友人,之后他们聚会讨论国内文坛的创作、国防文学、救亡与救穷的关系、采用拉丁化的新文字创作国防文学作品等问题。郭沫若告诉大家,他最近要出版的一部作品集将用“新旧文字对照着出版”。这部作品集就是《豕蹄》。所谓“新文字”,是指拉丁化拼写的汉字。
然而,从《豕蹄·后记》可知,出版社方面大概是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那毕竟是要增加成本的。并且一个文学作品集用新旧两种文字印制,岂不是有点像一本语言读本了。当然,拉丁化的新文字也没有能在社会上推行开来。而原计划以新旧两种文字印制出版的《豕蹄》,抽出新文字部分,仅剩下一半文字量,在篇幅上难以成书,自然要补充内容,于是,郭沫若选了之前一年写的几篇《自叙传》文章。
何以选了这几篇《自叙传》呢?郭沫若并非没有别的选择,即以历史小说而言,他将旧作《鹓鶵》《函谷关》《马克斯进文庙》(均作于20年代,但未曾收入作品集),以及新作《中国的勇士》(作于1936年3月,后以《齐勇士比武》为名收入《地下的笑声》)等辑录进来,岂不是更好!看来几篇《自叙传》的选择,主要是因为郭沫若恰在此时得知长兄郭开文病故的消息。
长兄郭开文是在郭沫若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郭沫若自谓:“除父母和沈先生外,大哥是影响我最深的一个人。”“我到后来多少有点成就,完全是我长兄赐予我的。”事实确实如此,仅就由郭开文决定,并资助其赴日本留学一事而言,那就深深影响到了郭沫若的一生。所以,在郭沫若笔下有关家人的文字中,提及郭开文之处也是最多的。《初出夔门》等五篇《自叙传》散文,恰好正是记述了郭沫若得长兄资助,赴日本留学的那一段经历。把这几篇散文补入《豕蹄》,以寄托对长兄去世的哀思,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豕蹄·后记》除了记述到成书过程中的这样一个曲折,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即,这是郭沫若在成为正式出版物的文字中第一次记到郭开文去世的日期:1936年6月25日。而有关这个日期,又涉及到需要讨论另外几则相关的史料:
抗战爆发回国后,郭沫若于1941年9月作有《五十年简谱》并发表出来,其中记到郭开文去世的一条谱文作:“民二五年(一九三六)五月七日长兄橙坞在家病故。”
《五十年简谱》以民国纪年系年,其月日当为公历日期,所以《五十年简谱》在以“民纪前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方式记到出生日期时,另注明为“阴历九月二十七日”。之后有其他若干条谱文涉及具体月日者,均为公历时间。依这一体例,《五十年简谱》中的“五月七日”,应为公历时间,那么郭开文去世的日期就有了两个不同说法。但稍做查考,可知“五月七日”应该是用了夏历纪年的日期,因为其对应的正是公历1936年6月25日,也就是《豕蹄·后记》中记到的时间。显然,《五十年简谱》关于郭开文去世一条谱文的时间记载是不合编撰体例的。
其实,若未注意到《豕蹄·后记》的文字与《五十年简谱》的记载有异,并不会意识到这之中有什么问题。所以事实上也一直没有人直接对此——郭开文去世的时间,或是《五十年简谱》谱文有无疏误——提出过疑问。但是,另外一则史料的出现,对此构成了质疑。那是1936年7月9日《成都快报》、《新新新闻》上同时刊登的一则内容相同的报道,题为《郭沫若兄郭橙坞逝世督署从优抚恤》。报道称“我部新闻译编社,善后督办公署秘书郭橙坞,原籍嘉定,系国内新文学家郭沫若胞兄,前因病告假返籍息养,久未告痊,兹悉郭氏已于昨日遽归道山,督署同事等闻耗极感悼惜。”
按照报道文字的语言逻辑,郭橙坞去世的时间是7月8日。查考到这一史料,并著文披露的作者也是这样认定的。这样一来,对于郭开文去世的时间,就需要再有一个确认了。
有另外一篇文献资料——郭沫若作《家祭文》,其中也记述到郭开文去世的情况:“长兄文以哀毁逾恒,已病殁于民国二十五年夏历五月七日。”
《家祭文》是郭沫若于1939年为父亲办理丧事并守丧在家期间所撰写。这样一篇文章中关于父母、长兄等家人生前身后种种情况的记述,当然会是十分仔细的。比之于1936年时身在海外与两年之后的1941年,郭沫若对于长兄去世日期的记述应该是最准确的(如果比对之间有所不同的话)。《家祭文》所记日期,正可以印证《豕蹄·后记》的记述,也恰好反证了《五十年简谱》纪年上的疏误。
那么《成都快报》《新新新闻》报道的日期又该如何看待呢?首先,这则报道本身是有缺陷的。作为新闻写作,一篇报道最基本的元素之一就是“时间”。报道一个人去世之事,应用准确直接的时间单位,而非间接的、需要推导出的时间概念(诸如昨日、前天等等)。其次,尽管该报道是出自报纸,两报是否为日报,并不清楚,更关键的是,即使两报为日报,也无法断定该报道是在成稿之后即刊发出来了。记者写稿与稿子刊发之间有时间差是很正常的,从关于郭开文逝世的报道仅是“豆腐块”样的一则文字可以推断,该报道应该是在成文后若干天才刊发出来的。因之,那个由报道文字“昨日”推断出的“7月8日”,实无必要作为郭开文去世日期的另一种说法。
关于以上几则史料的查考,是由《豕蹄·后记》延展出来的。再回到《豕蹄》这个作品集成集本身,不能不说留下一些遗憾:
将历史小说、传记散文、自由体诗这样三种不同文体的作品辑录成一个作品集,从编辑出版的专业角度说,显然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豕蹄》没有再版,甚至群益出版社成立之后,也未曾将《豕蹄》重新出版,与此大概不无关系(《豕蹄》中的历史小说以各自篇题辑入群益版的《地下的笑声》)。其后,郭沫若的历史小说陆续在日本、韩国都有了成集的译作,但没有一种译作选用《豕蹄》作翻译的底本(即使译本也沿用了《豕蹄》的书名)。
《豕蹄》在后来编辑《沫若文集》和《郭沫若全集》时,似乎也成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即,如何保留原集名,是放在小说作品卷,还是放在自传作品卷?因为这是编辑《沫若文集》和《郭沫若全集》的一条基本原则。其结果是,无论《沫若文集》还是《郭沫若全集》的小说作品卷均未保留这一集名,自传作品卷也未保留这一集名。《豕蹄》这一极有特点的集名,不复存在。
(责任编辑:彭邦本)
[1]请大家学习新文字[J].东京《东流》月刊(1936年2月第2卷第3期).
[2]上海:《文学丛报》月刊(1936年7月1日第4期).
[3]国防文学集谈·我的自述[J].东京《质文》月刊(1936年10月第2卷第1期).
[4]五十年简谱[J].《中苏文化》半月刊(1941年第9卷第2、3期合刊).
[5]周晓晴.郭沫若的长兄逝世以后[J].郭沫若学刊,1990(2).
[6]收入《德音录》,见《沙湾文史》1987年6月第3期.
2014-01-14
蔡震,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