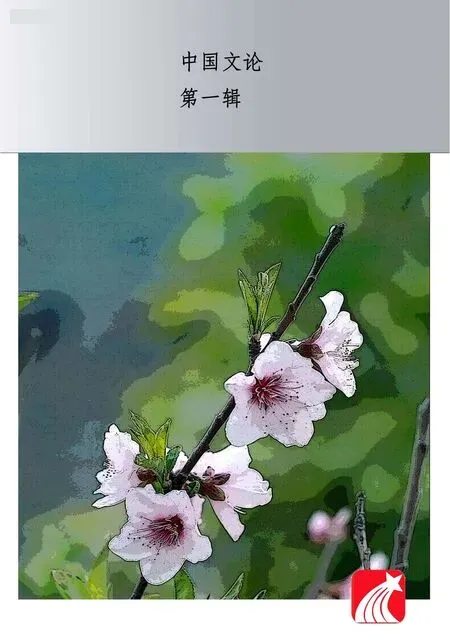“批评意象”刍议
高文强
●知音君子
“批评意象”刍议
高文强
“批评意象”是指存在于文学批评活动中,用于传达某种文学理念或批评观点的意象。它与传统意义上以塑造审美艺术形象为主要目的的“文学意象”在“立意”方向与“立象”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异。它是“意象批评”法的主要表现工具。对“批评意象”的深入研究,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拓展与创新都有一定意义。
意象;批评意象;文学意象;意象批评
“批评意象”是古代文论研究中出现极少的一个范畴,本文在此提出这一范畴进行讨论,其直接原因是受到古代文论研究中广为熟知的另一范畴——“意象批评”的启发。“意象批评”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基本方法,学术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关于这一批评方法的界定,有学者曾指出:“‘意象批评’法,就是指以具体的意象,表达抽象的理念,以揭示作者的风格所在。”“意象批评,是一种以意象为喻的文学批评方法。”从这些界定中不难看出,“意象批评”的主要特点,就是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借助意象来传达某种理念或观点,这一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应用得相当普遍。那么,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将存在于文学批评活动中,用于传达某种文学理念或批评观点的意象,称之为“批评意象”?这一颇具印象批评法提出的观点,从经验层面来看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欲使“批评意象”成为古代文论体系中的一个正式范畴,就有必要从学理层面对其内在之意义与外在之关系作一番辨析,而这正是本文欲解决的主要问题。观点是否正确,辨析是否合理,则有待各位专家的批评指正。
一、“批评意象”是一种什么“意象”?
“意象”之全部内涵若集合起来可是一个“大家族”,学术界至今也没能为这一“大家族”找到一个统一的、明确的界定。正如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所说:“意象是文学批评中最常见而意义又最难把握的术语之一。”本文在此并不想挑战这一难题,而只想厘清一个对“批评意象”研究颇为关键的问题:“批评意象”在这个“大家族”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
对“意象”内涵的界定,古今中外、不同学科间多矣。就不同学科来说,如哲学、心理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对“意象”内涵的界定便存在着较大差异。而从古今中外来看,在中国古代,就如其他众多范畴一样,“意象”范畴的内涵同样是多义而不确定的;中国现当代之“意象”理论,则多受西方“意象”观念之影响,与中国传统之“意象”观念又有所不同;而西方所谓“意象”理论,则是建立在我们将“image”翻译为“意象”这一基础之上,而同时该范畴还被翻译为“形象”、“表象”、“象征”等多种意思,因此西方所谓“意象”范畴的内涵自然复杂多变。对于“意象”范畴之内涵的上述复杂性,前人已有较多论述,本文在此不欲重复,只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意象”内涵做一个大致的归类,从而确定“批评意象”在其中的位置。
从前述“批评意象”的内涵可知,它主要是文学领域的一个范畴,因此,我们在讨论“意象”范畴时,基本限定在文学领域来谈(有时可能推至艺术领域),而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对“意象”范畴的界定,则不在我们归类之列。依据这一原则,从“意象”范畴在文学领域的历史流变来看,其内涵大致可以归为三类。
第一类为“尽意之象”。“意象”范畴的这一内涵源于“意象”一词的本义。在考察“意象”一词的形成过程时,人们一般都会追溯到《周易》时代。汪裕雄先生便曾认为:“易象即是意象。”特别是《易传·系辞》中所言“圣人立象以尽意”,更是被学界公认为“意象”一词内涵的源头,而其中“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这段话则被后人视为“意象”本义的经典解释。“意象”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在王充《论衡·乱龙》中首次出现时,其内涵就是此义。故本文将“意象”源于本义的内涵概括为“尽意之象”,即“用来表达某种意义的物象”。“意象”的这一内涵,时至今日,在各个领域依然运用得相当广泛。不过,此内涵之意义从古至今也并非一成没变。在早期,“意象”所尽之“意”,主要是指理性之观念,如“易象”所指便是如此。至迟在王弼《周易略例》论“象”、“意”关系时依然保持了这一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魏晋以后文学与艺术的不断自觉,“意象”范畴开始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其所尽之“意”,也逐步融入情感成分。可以说,这一转变直接促成了“意象”范畴其他内涵的形成。
第二类为“艺术形象”。“意象”的这一内涵最早出现在《文心雕龙》之中,刘勰“窥意象而运斤”的创作构思论,正是在“艺术形象”意义上运用“意象”范畴的。此后在古代文学和艺术领域,“意象”此内涵的运用也较为普遍。不过,对此内涵应用得更为普遍的则是在现代文学或艺术领域。现代文学理论或艺术理论一般认为,创作活动包括体验、构思和传达三个阶段,也就是说,创作过程一般是在体验的基础上,先在头脑中“形成主体和客体统一、现象与本质统一、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审美意象”,然后“经过艺术媒介或艺术语言等物质手段传达出来,就成为艺术作品的艺术形象”。刘勰所“窥”之“意象”,可以说就是经过构思在作者头脑形成的审美意象,“运斤”则是将头脑中的审美意象传达出来或者说物态化的过程。因此,作为“艺术形象”的“意象”又可以分为相互关联的两种:其一是构思时在头脑中形成的“审美意象”,其二则是将头脑中的审美意象物态化后存在于作品中的“审美意象”。
第三类为“艺术境界”。将“意象”视作艺术的最高境界甚至美的本质,是现代文学和美学研究中不少学者持有的观点。例如,顾祖钊先生的《论意象五种》中,便列有一种“至境意象”,“所谓至境意象,就是达到了艺术最高品味的意象”。叶朗先生在继承了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的意象理论后,提出“美在意象”的美学观,将“意象”视为了艺术美的本根所在。汪裕雄先生也曾提出审美意象是“审美心理的基元”的观点。如此等等。像上述先生这样将“意象”释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或艺术美的本质所在,已是当前学术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故我们在此将“意象”的这一内涵称为“艺术境界”。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领域,“意象”的这一内涵已与“意境”范畴的内涵基本一致。因此,在中国古代“意象”范畴的多元运用中,有时会与“意境”同义。大概这也是“意象”范畴令人难以琢磨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在文学艺术领域,“意象”的上述三类内涵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同时它们之间又并非毫无关联。其实从这三类内涵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意象理论发展的某种递进关系。不过,“意象”的三类内涵,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一直存活在文学和艺术理论领域之中,在不同的语境下,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通过上述分类,“批评意象”属于哪一类“意象”应该已不难分辨。“批评意象”作为在文学批评活动中传达某种文学理念或批评观点的“意象”,其最根本的目的是要传达“观念”,它既没有必须去塑造艺术形象的任务,也没有必须去创造审美至境的目标。因此,就“批评意象”的根本特征来看,显然它应属于第一类“意象”,也就是“尽意之象”。
二、“批评意象”与“文学意象”
存在于文学活动中的“意象”,在以前的研究中常被称为“文学意象”。“批评意象”同样也存在于文学活动之中,只不过不是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而是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由此,这里出现了提出“批评意象”范畴必然要面临的第二个颇为关键的问题:“批评意象”与“文学意象”到底什么关系?或者说,如果将存在于文学活动中的“批评意象”视为“文学意象”之一种,那么“批评意象”与其他“文学意象”又有什么不同?
对文学活动中的“意象”的研究,已是学术界非常普及的一个课题。不过,从已有的此类“文学意象”研究来看,基本都是围绕文学创作中的“意象”来展开研究的,诸如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柳”意象、现代诗歌中的“花”意象等等。因此,为了便于以下的叙述,我们暂且将此类“文学意象”称为“创作意象”,以区别于“批评意象”。那么,“批评意象”与一直以来人们研究的“文学意象”即“创作意象”到底有何不同?我们认为,两者的区别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两者“尽意”的方向不同。无论是“批评意象”,还是“创作意象”,作为“意象”之一种,它们都具有同样的基本功能——“立象以尽意”。不过,作为不同类别的意象,它们的“尽意”方向却并不完全一致。我们知道,“批评意象”之主要功能在于传达文学批评之观点,因此,其所尽之意多具理性色彩,甚至许多时候要传达的就是一种理论观点。如钟嵘《诗品》评谢灵运诗“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其所传之“意”则在“未足贬其高洁也”这一论断。严羽《沧浪诗话》“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的象喻,所传达则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之观点。虽然“批评意象”时而也会有情感成分的融入,有时也不乏审美形象的塑造,但这些都不能遮蔽它传达理论观点的基本特色。
“创作意象”则不同。作为文学创作中的基本元素,其功能主要在于创造艺术形象,也就是创造一个审美对象,或者说就是创造美,而其创造美的基本方式就是“情景交融”,故其所尽之“意”充满情感色彩。它“不是一种物理的实在,也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世界,而是一个完整的、充满意蕴、充满情趣的感性世界,也就是中国美学所说的情景相融的世界”。例如同为“月”意象,作为“创作意象”的“举头望明月”所传达的是思乡之情,而作为“批评意象”的“水中之月”所传达的却是诗味之理。因此,“达理”与“传情”代表了“批评意象”与“创作意象”两者“尽意”的不同方向,可以说这一差异正是“批评意象”区别于“创作意象”的主要因素之所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达理”与“传情”虽然代表了两种意象“尽意”的不同方向,但是任一“意象”在“尽意”的过程中,“理”与“情”又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创作意象”有时可能会借理表情,如宋诗中“意象”所传之理趣;“批评意象”有时也可能会以情传理,如《二十四诗品》中对各种风格“意象”的描述。但就两种意象“尽意”的终极方向而言,“理”、“情”之分还是比较明确的。
其次,两者“立象”的方式不同。与“尽意”的不同方向相关联,“批评意象”与“创作意象”在“立象”方式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创作意象”因其具有塑造审美形象、创造艺术至境的目标,以及“情景交融”的基本特征,故所立之象多源于客观景物,如“梅兰竹菊”、“日月山川”等,即使是人文景物,也常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如“舟桥亭台”、“空闺游子”等。这一“立象”方式显然符合“创作意象”结构中客观之景与主观之情相交融的基本要求。
“批评意象”由于所尽之意在于表达一种理论观念或批评观点,因此它并不将“情景交融”视为其“立象”的基本原则,而更重视如何借“象”去更好地“尽意”。因此,“批评意象”所立之象虽也较重视借助客观景物,但同时在人文内容的运用上,同样也非常重视,尤其是颇具主观色彩的文化内容被大量运用于“立象”。例如,严羽《沧浪诗话》中的“以禅喻诗”便是非常经典的例子,诸如“大乘”“小乘”、“临济”“曹洞”、“第一义”“正法眼”等一系列禅宗文化内容,都成为严羽构造“批评意象”的素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批评意象”还常常直接“借用”“创作意象”所创立的现成“意象”来传达它的文学观点。例如,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词人三境:“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在此,晏殊、柳永、辛弃疾三人词中的“创作意象”已转化为王国维的“批评意象”了。
“批评意象”与“创作意象”虽有上述不同,但是两者毕竟同属于“文学意象”,因此它们在“立象尽意”的基本特征方面还是具有共通性的,只是由于两者应用功能的差异,以及追求目标不同,才使两者所尽之意与所立之象存在一定的差异。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批评意象”作为“文学意象”中的另一类别,其与从前人们所认识的“文学意象”即“创作意象”在尽意之方向与立象之方式上确实存在一定差别。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批评意象”确是“意象”中的一个新的类别,并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
三、“批评意象”与“意象批评”
正如开篇所言,“批评意象”这一范畴的提出,最初灵感是来自“意象批评”,而且我们知道,“批评意象”还是“意象批评”这一方法实施的重要载体。如此我们不禁要问:“批评意象”作为实施载体在“意象批评”活动中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呢?这是我们提出“批评意象”范畴后必须回答的第三个关键问题。
“批评意象”是“意象批评”方法实施的重要工具,也是“意象批评”观点传达的主要载体,两者有着密切联系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批评意象”所发挥的功能与“意象批评”方法所具有的特征便是分不开的了。
“意象批评”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它的直观感悟式的批评方式,这一特点与作为批评对象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特征极其相似。中国古典文学讲究含蓄,讲究“言外之意”,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但这个“无穷之意”又是不能直接说出来的,若一语道破则了无余蕴,故只能靠感悟,靠暗示,靠创造意象来传送那个“意”。而“意象批评”所采取的批评方式与传统文学的创作方式极其相似,同样强调直观感悟,同样强调言外含蓄,同样通过创造意象来传达批评之“意”。这种方法不是用逻辑式的分析、演绎和解释,而是通过创造“批评意象”,引导人们与文学作品中的意象对接与融会,然后去感悟作品中所包含的意蕴。可以说,“意象批评”就是以艺术创造的方式感悟艺术创造。或者说,“意象式批评的本身,就通向艺术创造,或者说,即是艺术创造”。
从“意象批评”的这一特征我们不难看出,“批评意象”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连接批评与批评对象的一座桥梁,是沟通批评之“意”与作品之“意”的中介。这样一种以感悟对感悟,以“意象”接“意象”的批评方法,可以说有效地避免了理论批评可能出现的肢解审美经验完整性的弊端。
“意象批评”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特征是它对接受者的启悟式引导作用。文学批评的功能一方面是对文学作品做出合理的评价,另一方面还可以起到引导读者合理接受文学作品的作用。现代文学批评重视理论化与逻辑性,追求概念清晰、判断准确,力求结论明确而合理,对读者的引导具有明显的“说服”与“说教”色彩。“意象批评”以创造意象的方式传达批评之“意”,以艺术创造的方式感悟艺术创造,这实际上为引导读者在接受中进行再创造留下了很大空间。运用“意象批评”的批评者在批评活动中不是作为一个裁判者,而是作为一个启悟式的引导者,去引导读者在接受中进行再创造,而绝不越俎代庖。
“意象批评”的这一特征让我们看到,“批评意象”在引导读者接受艺术作品的过程中,同样发挥着再创造的中介和桥梁作用。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意象批评”以平等交流的方式引导读者的接受活动,是非常符合文学接受的这种多元特征的。
从上述分析可知,作为“意象批评”重要工具的“批评意象”,其在批评活动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与文学作品意象的对接中发挥着中介与桥梁的作用,使“意象批评”活动能较好地把握文学作品意象之意蕴;二是在启悟引导读者接受艺术作品过程中,同样发挥着中介与桥梁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帮助读者创造性地把握艺术作品的内在意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批评意象”作为古代文论已有研究中极少涉及的一个范畴,在今后的研究中适当予以关注是很有必要的,且对此范畴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通过对“批评意象”的研究,我们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进一步理解古代文学批评之方式与方法的独特品性;其二,长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从整体上看较偏重思想、观念、范畴等内容层面的研究,而较忽略批评文体、批评风格、批评语言等形式层面的研究,或许这也正是“批评意象”研究被长期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对“批评意象”的深入研究,也可补古代文论形式研究之不足。
高文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