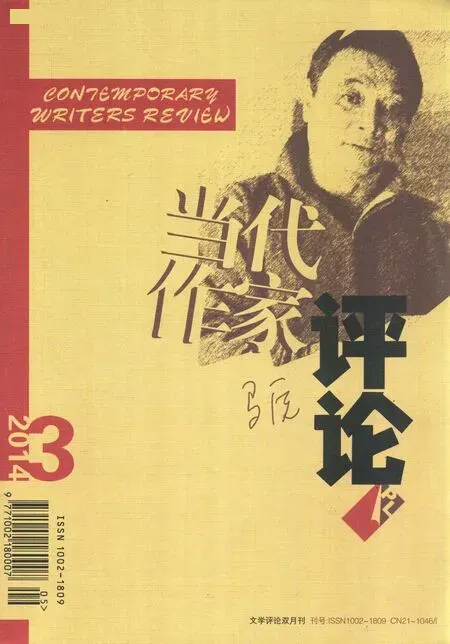多即是好:当代中国文学阅读与翻译
林丽君 (王美芳译)
如葛浩文所说,我与他合作翻译,虽然也有辛苦,但更多的是乐在其中。我们翻译中文小说,一般我先翻译第一稿,之后让他来改,改完之后我再读一遍,等到我们都满意之后才发给出版社。这是翻译小说,说到翻译诗歌,可能更复杂。下面我就从诗歌集《推开窗户》(Push Open theWindow
)里选出几个例子,予以说明。这部诗集收入几十位中国当代诗人,每人选了几首诗歌,但读者可以因小见大,从中看出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大概。我这个标题里的这个“多”字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当然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种是让更多的人读更多的中国诗歌,或者更多广义的中国文学。以《推开窗户》这本当代中国诗集的英译为参考,我们将讨论到以下问题:翻译、诗集收录,以及跨越文化及语言上的界限来阅读中国诗歌。我还将谈到诗集是如何收录到一起的,在编辑和处理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为什么说“多即是好”。还会用到双语的例子来阐释在平衡原文忠诚度和可读性之间的困难和作为一名译者的责任。此外,我也会谈到将中国文学译成英文的一些总体相关话题。
第一,诗集是如何收录到一起的,也就是说,选择要翻译的文本。这种诗集是在一些不太寻常的情况下收录到一起的。多年以来,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of the Arts,NEA)一直与世界各地多个国家进行合作编撰双语诗集。有两本诗集由这一计划支持出版,一本英语,一本非英语。所以就中国诗集而言,《推开窗户》是一本中英双语的版本;一本美国诗歌集将随之按英中双语的格式出版。在这里我不多说美国的版本,因为我也没在那本书的出版中起到什么作用。原始的中文诗歌都是由相当于NEA的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所指派的北京诗人王清平所选。在总数达五十位的诗人及其作品被选中后,中文的原文发到了我和我的合编者葛浩文手中。我们读了这些诗,并进行了新一轮的选择,主要是因为诗集无法收录每位诗人的每一首诗。不用说,选择过程一定会反映出我们自身的文学敏锐度和诗歌赏析能力,但我们一直都记得这本诗集决不应是“林丽君和葛浩文最喜欢的中国诗歌选集”。接下来我们又联系了遍布四大洲的可能合作的翻译者,他们分别来自美国、香港、中国、澳大利亚和英国,最终有四十三名译者签约同意翻译四十九位诗人的一百零六首诗歌。涉及如此之多译者的主要原因在于要保证声音和用词上的多样性。我们相信,更多的翻译者对于一本选集来说是好事,尤其是诗歌选集,我们也确保每位译者只翻译不超过两位诗人的作品。曾经有一位评论家抱怨过译者数量太多,应该只有一位译者为所有诗负责。我必须要说我们完全反对一位译者的做法。这里我要引述这一评论:
只有一位译者会更准确地理解过去五十年内中国诗歌的发展和变化。在这么多译者参与翻译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确定中国诗人能够看得懂的新的修辞技巧锦囊不是译者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呢?(《莱姆帕斯日报》)
这位评论家的说法很有问题。一是他评论的前提条件是在过去的五十年中诗歌,或者广义的文学,呈线性的发展变化趋势,二是认为大家可以通过阅读诗歌“看到”这些变化。文学作品阅读,至少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愉悦的感觉,而并非像我的很多学生那样是作为完成学科作业等要求的目的性行为。更糟的是,我在上述评论中读到的是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一种长期不变、不可动摇的不利看法。大多数读者好像都在不断地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以了解中国和中国社会,但同时他们却很少通过阅读海明威,或者T.C.波伊尔的作品去了解美国文化,或者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来了解哥伦比亚文化。但恐怕我们会一直看到这样的评论,直到有一天,英文读者能够拿起一本中文诗集,随手翻至一页就开始阅读。或者他们会出于小说本身去购买一本由中文翻译的小说,而不是因为这本书能够教给你一些关于中国的东西;尽管英文读者也许确实能够在阅读过程中学到一两样东西,但目的仍然是为了阅读本身。
但我对于这条评论的最大质疑还在于他声称一位译者来翻译的方法更好。一方面我并不否认任何一位译者都尽全力将作品翻译到最好,但我也注意到我自己以及其他译者都有一种趋势,那就是会偏好某些特定的字词或者句子结构。如果一位译者翻译全部一百零六首诗歌,那么可不太容易避免所有诗歌之间的相似性。
比其他文体都要更明显,诗歌的翻译是一种模仿,因为诗歌很大程度上是靠诗人的语言所创造出来的形象来建立自身的高度,因此翻译者相对于小说或者戏剧来说发挥的空间较小。此外,还要考虑到这是一部双语作品集,中文原文与英文翻译并列而置。尽管大家——出版商、NEA、译者和编辑,都希望作品能够尽可能广地被受众所接受,但我们也意识到有一些读者既懂中文又懂英文。结果就是,我们必须要找到最好的诗歌译文,一种能够为众多大师所赏读的译文。
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This is Beijing at4∶08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的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This is Beijing at4∶08
An ocean ofwaving hands
This is Beijing at4∶08
A shrill train whistle trailing off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
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Beijing Station’smajestic edifice
Convulseswithoutwarning
Shaken,I look out the window
Not knowing what’s going on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绒绳就在妈妈的手中
My heart shudders in pain,clearly it is
My mother’s needlework running me through
At this timemy heart transforms into a kite
A kite tethered to her hands
(食指作)
这里的翻译读起来还可以,同时也与原文结构完全一致,只有几处创新的选词。例如,“突然”我们可能更愿意翻译成“suddenly”或者“all of a sudden”,下一行也可翻译成“I look out the window in surprise or in shock”。但我们作为编者还是认同译者更具理解性的译法,译者显然认为如果是突然(sudden),那么一定是事先没有警告。而“吃惊”的译法同样也是理解性的,而不是字面上的直译;如果翻译成shaken,那么显然已经包括了shocked或者是surprised。而且,虽然“shaken”本身并不是“吃惊”最好的对应翻译,但选择“shaken”来翻译“吃惊”还能与诗歌的第二行的“抖动”形成呼应。
现在我们再来看另一首诗歌的翻译,编者与译者之间就这一翻译进行了多次激烈争论。
母羊和母牛
Nanny Goats,Cows
有一年
在山坡上,
我的心融化了,
在我的手掌上
在我捏碎的一粒羊粪里。
那原来是田埂的青草
路边的青草
我听见
自行车后架上
倒挂母羊的叫声
就像一个小女孩
在喊
“妈妈,妈妈……”
我的心融化了,
在空气里
在人世上
On the hillside one year
my heart dissolved,
in my palm
in the crumbling nuggets of goat dung
thatwas grass,green on the ridgeline,
green grass by the road.
Iheard a nanny goat
slung head down
from the rack of a bicycle
calling like a girl,
“Mama,Mama……”
My heart dissolved
into the empty air,
into this human earth.
(杨坚作)
对这个翻译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是结构上的变化;可以从中文原文与英语译文的对比中看出英文比中文少了几行。我个人并没有看出来将前两行缩短为一行有什么好处,无论是“One year/On the hillside”还是后面的“like a girl/calling”。后来我们发现原来那位译者本身也是一位诗人,他本来就不太喜欢那首诗的某些地方。换句话说,这位译者比诗人更知道怎么能写出一首好诗。当然,有的人会说,翻译者也应该像诗人一样用诗的破格来努力给出最好的翻译,我认为这样做的前提应该是在将翻译的英文回翻到中文的时候,发现与最初的原文差异不是太大。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译文翻译回来与原文对比的效果如何:
有一年在山坡上
我的心溶化了,
在我的手掌上
在粉碎的一粒粒羊粪里
那原来是草,田埂上的青青路边的青草
我听见一只母羊
倒挂
在自行车架上
像一个女孩一样在喊,
“妈妈,妈妈……”
我的心溶化
成空的空气
入这个人的世界(土地)
于是就“融化”的翻译问题与译者有了另外一次更长的争论,我称之为“melt还是dissolve”的问题。我们查过很多本不同的汉英字典,“融化”的定义都是 melt不是 dissolve;在译者的版本里出现的dissolve是指水的特点。只要看一下这两个词,差别就很明显了,但无论我们怎么说就是无法说服这位译者,后来他告诉我们他的共同翻译人是一位中文母语者,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编者中也有一位中国人的事实。我们与译者反复协商,但最后决定把这个例子看作是古老的忠实度与可读性之间的对立问题而让它顺其自然;读者在看到这些诗歌的时候可以自行评判。但是我最反对的还是译者将中文原文的“空气”翻译成“empty air”,将“人世”翻译成“human earth”。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无法说服这位译者改变想法,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重新译回中文的时候就有了“成空的空气”。最后,我们决定不再继续这种讨论,或者说争论,一方面因为译者拒绝听我们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愿意让读者看到更多的翻译方法。
这种趋势在翻译者当中并不少见。最近我正巧看到两个有些过分(也很有趣)的例子:第一个例子,翻译者在主角的名字中看到“雄”,就决定称他为“Manly”(意为男子气概的,雄性的),不是外号而是名字。英语母语者会将这看作是一个可接受的名字吗?比如说,白瑞德不叫Rhett Butler,而叫Manly。那么大家能想象出来Scarlett O’Hara(斯佳丽·奥哈拉)追在后面大声说“噢,Manly,请不要走”吗?我怀疑会不会有英文的读者会认真地看待这样一个角色或者这样一本小说。在个人层面上,翻译者又会不会为她的儿子起这样的名字?如果不会,那么她凭什么认为在中文小说里的一个角色叫这样的名字就完全没有问题呢?另一个例子是一位译者将一位女性角色的名字“阿芳”翻译成Chrysanthemum(菊花),后来他还缩写成了Chrissy,作为一种昵称。当我看到这位译者从阿芳一下子跳到“菊花”或者“小菊”时,我真地是无语了。如果说上面Manly的例子是将中文的特殊化,那么我们在这个例子中看到的就是特殊化和过于内化中文文本的一种结合。一方面,我还没有在美国或者加拿大遇到过有女孩叫Chrysanthemum这样的名字;另一方面,将Chrysanthemum缩写为Chrissy则把一个中国人的角色变成了一个美国女孩。
既然已经将我的翻译者同伴让大家如此细致地检查,那我必须要再强调一下从中文译成英文非常有难度,而且任何足够勇敢和傻气去接受这一任务的人都会受到我最高的尊敬。让我再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难度有多大。当汉译英的问题出现时,有一些人会立即提到中文与英文之间的差别,比如句子结构、语法、时态和数字上的差异等。当然这些会造成一定的难度,比如很简单的句子“他提着礼物去看朋友”,翻译者起码要了解提了多少礼物。再比如我最喜欢的一首诗中有这样几句: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栖。
这首诗中有多少只鸟向南飞?一只,几只还是很多只?这有差别吗?也许并没有,但英文这种语言本身就要求翻译者在一个和一个以上之间区别开来。这一句话有的读者理解为一群鸟,象征着曹操希望聚集在他周围的人都是智者和能人。但不能理解成一只独鸟吗?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鸟呢?有的人说是喜鹊,有的人又说是乌鸦。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喜鹊和乌鸦可是代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象征含义的。
但是与另外一些由于中文写作风格特征所形成的不经调整就不成文的翻译相比,这些都是小问题。
第一点就是重复。一般来说,中文写作中可以出现较多的重复,事实上甚至鼓励重复的出现。这里有两个例子,是从我最近翻译的毕飞宇的《推拿》一书中所看到的:
(1)都红对男人们很失望,对女人们也一样地很失望。
Du Hong was disappointed in men and she was similarly disappointed in women.
英文的编辑很可能会由于重复而说这句话翻译得很糟。要避免这种重复我们可以用以下的两种翻法:
Du Hong was disappointed in men and women alike.
Du Hong was inordinately disappointed in people,both men and women.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翻译?我们要不要来个投票?
第二个例子也是来自于毕飞宇的《推拿》:
(2)沙复明出来了。他不想出来。
Sha Fuming came out.He didn’t want to come out.
这个英文翻译得不光重复,听起来也很差劲。似乎可改为:
Sha Fuming came out,even though he didn’t feel like it.
Sha Fuming came out,with reluctance.
还有其他的建议吗?你更喜欢哪一个?
中文写作的另外一个对翻译极具挑战性的重要特征就是习语的使用。
还是《推拿》里的例子:
(3)羊肉不膻还能叫羊肉吗?不膻还值得挂羊头卖狗肉吗?
字面翻译:You can’t call itmutton if it’s not gamy.If it’s not gamy then it doesn’t deserve to be sold at a place selling dog meat as mutton with a sheep’s head hung up to deceive the customers.
有几个原因使得这句话特别地难。第一,两句话之间的逻辑关系:真羊肉一定膻;如果不膻就不是羊肉。这很清楚。但第二句话中的“不膻”是指什么?看起来好像是说如果不膻就不是羊肉,这也是它不值钱的原因。但作者又用了习语表达:挂羊头卖狗肉。让我们暂时先不去想怎么翻译最好,也不去想怎么就从羊肉的膻转成了羊头。暗含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不是羊肉,就不能卖成羊肉。足够简单了。但我们还要去处理第二句话,并将羊肉与将狗肉当羊肉卖的商店联系起来。这样当然要由翻译者来决定如何处理这个习语。是不是应该把它翻译得让英文读者知道这是一个中文习语呢?如果能够找到我们是不是应该用英文中对应的习语?
与习语的翻译相关的是那些已经是陈词滥调的表达法。是不是中文中这样的一个陈词滥调就应该翻译成英文中的另一个陈词滥调呢?
(4)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a)Once bitten,twice shy.或者
(b)Once bitten by a snake,you’ll be afraid of a rope for ten years.
(5)船到桥头自然直。
(a)The boat/ship would right itself when it gets to the bridge.或者
(b)We’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we get to it.
有的人可能会说(b)——这句英文习语非常好,因为它能够保留原文中所提到的桥;也有人可能喜欢(a),因为它更忠实原文,也更生动,能进一步告诉英文读者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像这样的习语很难翻译,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都需要以一种相对习语化的方法来进行翻译,同时也因为这里习语都需要经过更细致的考虑以避免那些不必要的认为中文很奇怪的暗示,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这也引出了另外一个对于翻译者来说重要的任务和挑战。中国翻译者无一例外地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需要决定译文在英文中是如何理解的。主要有三个层面:一、完全内化以便让译文读起来就好像本来就是用英文写出来的;二、保留中文里的原汁原味,尽可能让译文听起来是从外语翻译来的;三、介于两者之间,译文中保留一定的中文痕迹而又不失可读性。对于你们当中熟知翻译理论的人,你们应该知道这些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不断提出的或者翻译家们讨论的问题。总的来说,这不是什么新问题。但让这个话题值得一再讨论的原因是英文和中文之间差异本来就很大。如果是从西班牙语或者法语翻译成英语,那么在文化和宗教上共同的传统会让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容易得多。从中文到英文的话就困难多了;比如怎么将“缘分”或者“老实”翻译成英文?除了要很好地将这样的概念传达给英文读者,翻译者还必须要很小心不让中文或者中国文化看起来很奇怪。我认为,翻译,就像所有其他跨文化呈现形式一样,是一种矛盾的尝试;文本的独特性要加以保留,但是单独字词又不能在文本或文化中显得太过独特,或者干脆成了一种讽刺画,这会让这种独特性成为主题公园里的标志,游客都靠这个来区别文化之间的差异。
从我上面所谈到的这些可以看出,翻译者在每天坐下来让另一种语言的读者可以读到一部作品时所面临的挑战很多。事实上,这些挑战的数量太多而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我会在这里再提一点,而这一点大多都来自那些能够看懂原文又恰好懂得译文的读者。很多读者好像都有这样的一种幻象,认为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都只有一种文本。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我提到的曹操的诗。在我还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时候,我总是将这句诗“乌鹊南飞”理解成只有一只鸟,我就像那只孤独的鸟一样找不到栖息的枝头。而我并不在意这到底是一只喜鹊还是乌鸦。对我来说,鸟的形象就足够我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毕竟是我对这首诗的理解,而当我阅读并赏析这首诗的时候,这首诗是我一个人的。没有人与我争论,我相信你们当中读过这首诗或者其他诗歌的人也都有你们自己的解读。
但到了翻译问题上一切就都不一样了。读者常常关心译文有没有完全传达原文,或者是不是失去了在原文中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因为译文,尤其是汉译英,对译者理解度的要求相当高。要是翻译者搞错了,读者看到的和作者原意不同怎么办?当然翻译也会犯错,就像我前面的例子中所说的那样,但如果翻译者愿意让其作品由其他人先读一下,尤其是中文母语者先来读一下,那么这些错误很容易就能改正过来。但读者关心的并不是这个层面上的错误,而是他们觉得很难明确表达的东西,只能问“你怎么知道你理解得对呢?”事实上,这些读者已经认同他们对于一部电影或者音乐作品有着不同的反应。
今天我提到的最后一点要问大家几个问题:什么是文学?文学是不是商品?我们是不是其实觉得作者是为自己写作?如果作品不出版,或不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读到,那么为什么还要写作?如果是为了这样的目的,那么凭什么我们会觉得像小说这样的文学作品在以另一种语言出版时那么神圣不可更改?有很多很多次,我都数不过来,我们这些翻译者因为改变而受到批评,尽管这些批评大多数都来自于出版社的编辑们。但无论是谁先开始的这种改变,对出于可读性的考虑而作出的调整大家一直都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有的人称之为迎合国外读者,还有人干脆将之看作是一种文化侵略。但是,汽车制造商或者快餐店改变产品来迎合不同市场却从来都不是问题。我知道这种说法听起来简直相当于异端邪教,因为文学应该比汽车或者汉堡的层次高得多,但正如我前面问到的,小说难道不是一种商品吗?它的作者和出版商都希望能够将小说卖给更多的人。而谈到中国文学的问题,我们——作者、出版商和译者——都希望看到作品能够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境内的人去阅读和欣赏。这也是我说的另一种“多即是好”。
(责任编辑 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