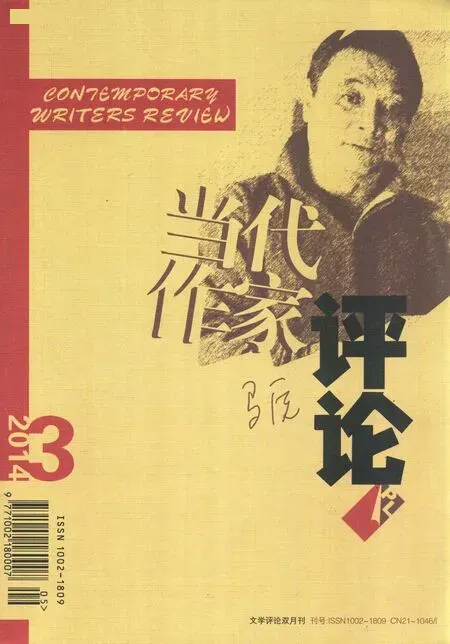风景叙事与小说主体的现代性理念流变
——以新时期到新世纪的西部边地小说为中心
金春平

——以新时期到新世纪的西部边地小说为中心
金春平
自然风景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叙事客体,从《诗经》中的“比”、“兴”肇始,到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文学达到风景抒写的高峰,风景一直是古代作家“文以载道”的具象工具,“天人合一”、“物我交融”、“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均表现出自然客体和文学主体趋于融合的审美诉求。“五四”时期以来,现代性作为中国文学的价值轴心,风景走出诗歌和散文的抒情领域,逐步融入以叙事为本质属性的小说结构,并成为现代小说叙事空间中的重要元素,承载着文学主体对现代性理念“认同”与“分化”的艺术表现功能。但世纪之交以来的中国文学,在“风景死亡”的喟叹声中,在日常生活、欲望表达、网络快感、价值重建等主题的遮蔽下,风景的抒情与风景的叙写,不仅无法被大众接受者的阅读审美所期待,也无法成为当代许多中东部地区作家传达个体化思想和解构性理念的有效艺术形式。在此小说理念下,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中国西部边地小说当中,自然风景叙事不仅一直是其最为重要的叙事主题,充当着文本主客体间性的关系中介,而且还通过文学主体对自然风景的隐喻、转喻、提喻、象征、写实等艺术手法的加工,呈现出与文学主潮发展“迎应”与“悖离”的曲线图谱,从而使得西部边地小说的自然风景叙事,超越了古代文学风景描写“自然与人同化”的单一关系模式而趋于多元化。文学主体对自然风景的观照、审视与改造,使西部边地小说在文学主流的“边缘”处,在“边地”这一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明的共存语境下,成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生态主义等文学思潮生成与演绎的文化场域,也形成了文学主体现代性认同与批判互为参照、互为补充的多元化认知模式。
文学风景叙事中的现代性内涵
在人类文明的创造过程中,人与不同区域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方式的差异,孕育出了多元化的文明形态,“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同时,在人类从大自然争取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中,更为高级的人文环境也逐渐形成。正因如此,“人地环境”和“人文环境”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内容。现代性本质上是对人类自我力量的张扬,是驱除自然之神对人类奴役的反前现代性的理念思维和认知哲学。同时,现代性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体精神力量,也将“民主”、“科学”、“理性”作为中国文学的元话语和核心概念,民主解决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科学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理性解决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但现代性作为外源性的历史潮流和理念体系,其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偏颇之处在于,因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政治改造的迫切需求,文学对“民主”投之以极大的热情,并对“民主”概念所引申和辐射的个体价值(启蒙主义)、民族独立(革命主义)、国家建设(左翼主义)等文学主题进行经典化塑造,文学主体借“民主”这一概念将话语客体指向了人文环境(社会、历史、人性)当中群体的“人”;文学同样也对“理性”这一话语核心进行了本土化构建,并以此作为反叛传统文化束缚,批判国民精神劣根,重建现代人格内涵的理想工具,并由此引申出了“社会批判”、“文明批判”、“国民性批判”、“政治批判”等文学主题,文学通过“理性”这一现代思维概念,将话语客体指向了文化蒙蔽、人性蒙蔽、历史蒙蔽中个体的“人”;但对“科学”这一现代性内涵要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涉猎不足,科学固然包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从准确、可验证性并能达到普遍公认的角度讲,科学一词指自然科学”,它所解决的恰是主体之“人”与客体“自然”的关系认识论。古代文学当中的风景抒写,绝大多数都是主客体的审美融合诉求,追求“无我之境”乃是风景描写的最高境界。而对于以现代性为价值核心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风景描写已经脱离了“物我交融”的单一审美功能,转化为凸显“个体之我”的有效参照,文学通过对“自然风景”的主体化叙事,所传达的恰是现代性所关注的对“人”的“主体性”的重新发现、对“人”的内涵的突显、丰富和审视,主体和客体的间性关系,即文学主体审视自然客体的方式,文学主体和自然客体的关系模式构建途径,正是风景叙事所蕴含的现代性价值所在。
风景叙事当中的现代性内涵,归根到底是文学主体的现代性内涵,“现代性的核心是个体主体性”,“个体的生成可以看做是现代性的标志”。现代性发生之后,个人的主体意识开始复苏,在对自然万物进行观照的同时,审美的、对抗的、象征的、隐喻的关系开始生成,主体之“人”与客体“自然”的关系模式也渐趋多样化,它们既可以作为促进人类活动的背景空间,也可以作为与人类活动相背离的异化力量。尤其是我国,由于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反差极大,不同地域文学主体对自然的审美观照态度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姿态。
中国内陆的自然地理基本是“西高东低”的阶梯状。西部边地恒久而悠远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也正是在这样迥异的自然环境当中孕育和成型的。西部边地的地理特征,既形成了中国边地文化板块中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现代文明、后现代文明相交融的文化格局,还作用于西部作家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成了西部文学所独有的地域精神样态和自然美学特征。但纵观西部边地小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部地区的自然物象进入小说是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潮和不同类型作家的文化心态紧密关联的,正如李兴阳所说,西部当代小说基本经历了一个“从异域性文化想象到重新发现”的过程。我认为,如果说“异域性想象”更多承载的是西部边地文学跻身主流文学的叙事策略和地域资本,是西部边地作家群体崛起时刻意标榜“西部边地”特征的文学抒写智慧,是充分利用了“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的接受美学心理,并大有“妖魔化”和“神秘化”的“过度渲染”倾向,那么,“重新发现”所带来的自然景物叙事的多元面貌,已成为通过小说叙事的方式,实现文学主体对“边地空间”“现代性”认知和演绎的文学场域,负载着更多对现代性所推崇的“人”的内涵的丰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边地自然景物进入小说,当中贯穿着自然风景被“刻意强调”的主体性建构。
与现代性在中国新时期文化语境中的发生相关,边地作家对自然风景的书写,基本经历了一个从“人化自然”到“异化自然”再到“生命自然”的嬗变过程。这种自然风景叙事的主体性“生成”与“隐退”的线索,一方面反映出自然风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影响因子,对西部作家创作心理和创作意识的深层影响,是他们挥之不去的一个创作情结;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部作家在与主流文化潮流的遥相呼应中,自然意识从刻意强调,到本土意识的复苏,再到人类关怀意识觉醒的前卫与先锋。因为“人化自然”和“异化自然”是西部作家以地域化的方式,对文学现代性主潮进行的先锋性应接和前卫性反思,而“生命自然”、“生态意识”则是边地作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患意识,在文化理念方式上的先觉反映,这三个方面不仅成就了西部边地小说在同时期文学主潮中带有“审美批判式”的艺术理念构造,还导引出超越地域层面的对现代性丰富内涵的多元认知模式。
风景的“发现”与“审美现代性”
对于意外闯入西部边地的作家来说,自然风景显然不仅是小说叙事的背景空间,而且承载着对启蒙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审美现代性”内涵,并形成了自然客体与文学主体之间的“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模式。新时期之初,启蒙主义思潮复苏,续接起了“五四”启蒙大旗,追求“人”的价值,追求自由、民主、科学,对封建传统文化、传统帝王之制遗毒进行了全民性的反思和批判,即“理性现代性”的建设重新拉开帷幕;同时,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又亟待进行现代化的建设,特别是进行物质层面的建设,改变原有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满足人民物质需求和生活需求的市场经济体制,即“感性现代性”的建设成为全民竞争的动力。但在中国特殊的现实情境中,感性现代性与理性现代性建设的同步却出现了偏颇,即感性现代性(物质现代性)不仅成为国家的主导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成为全民的集体生活诉求,世俗现代性获得了极大的认同和强化。但“人”的欲望得到合理释放的同时,也沦为了“物”的奴隶,“人”刚从传统文化和政治桎梏的“不自由”当中解放出来,又陷入“世俗”和“物欲”的“不自由”当中,理性现代性(二次启蒙)的建设还未完成,就在不经意间被“感性现代性”和“世俗现代性”所击垮,理性启蒙悄然隐退。对于坚守启蒙大旗的知识分子来说,面对“世俗”四壁陈列而抗争,却又如此悲壮和孤独,当他们将目光转向前现代文明聚集之地的西北大地之时,他们发现了别样的“风景”。西部边地自然风景的发现,让这些长期身处和浸淫于东部现代都市文明,但又深受现代文明负面文化伤害的知识分子,获得了普遍的归根之感,其代表包括张承志、红柯、冯苓植、杨志军、王蒙等。这些坚守启蒙大旗的知识精英,由于理想受挫、信仰受阻或政治磨难而漂泊旅途,在寻觅精神家园的过程中,他们意外地闯入神秘而广袤的大西北,西北奇特的自然物象重新激发出被现代文明负面因素(政治信仰、世俗困扰、信仰坍塌、自我迷失)渐将湮灭的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让他们能够站在超脱于“感性”和“理性”的形而下层面,进行“反思”和“超越”型的批判,对现代性的负面性进行平衡和制约,对自己的启蒙信仰重新寻求坚守的理由和信心,对现代性的异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并试图重建“主体之人”的“神性”。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西部自然风景所具有的不仅是“人化”的美学内涵,还具有“神性”的神秘光环;不仅与这些闯入西部者本身所秉持的理想主义的家园期待意外契合,而且,西部自然物象无疑成为这些闯入者们寻求思想启迪、完善人格、寻求家园的最佳启蒙之神。自然物象在这样的审美视域中,不仅被有意强调,凸显出鲜明的西部边地特征;而且往往具有了精神导师的作用,具备了“人格化”和“神圣化”的意味,成为构建文学主体“审美现代性”的绝佳客体,发挥着疗治现代文明伤害的抚慰作用,成为这些精神流浪者和文明反叛者追溯人类、民族、人性本真的精神渠道。
西部自然所引发的主体心理与世俗的“疏离感”和精神“超脱感”,以及对人的“神性”和生的“超越”的生存体验和艺术诉求,不仅是新时期闯入型作家创作的深层心理动机,而且那些原始情状的西部自然,也成为他们驰骋想象、忧怀古今和演绎生死的叙事空间客体,并在文学主体的现代性批判和审美构建中,使西部边地小说的自然叙事呈现出鲜明的浪漫化色彩。
浪漫主义从其起源来说,就承载着对理性王国的反叛,并将个体的独立和自由作为价值核心。在西部边地小说的浪漫型自然风景叙事中,自然往往是被人格化和审美化的,他们不仅是西部地域自然物象的写实呈现,而且被负载了诸多的象征隐喻含义,成为文化重建和人格重建的动力之源。表现在小说主题上,就是审美主体出于“文化寻根”和“价值重建”的心理诉求,将西部自然升华为启蒙主义者身处现代世俗困境和异化情境中“精神导师”的象征体系。在这个象征体系中,自然物象不仅是国家崛起和民族振兴的隐喻,同时也是流浪者生命回归大地的母性之居。尤其是西部作家为了与新时期陷入失落境地的理性启蒙主潮相应接,西部自然物象常按照作者的审美心理倾向,有意识地朝大写之“人”的精神气质和人生哲思的方向加以移情和拟人,以此彰显出一种民族精神重建与文化体系复苏的导向。那么自然物象就不仅成为与作品中的人物相并峙的叙事客体和特定地域民族本质力量的审美镜像,而且成为西部闯入者浪漫想象和文化传达的审美空间。因此,这类西部自然的主体化叙事,就既具有现实性的实指性,又具有了超越性的文化反思性,即现代性批判的“审美现代性”。这种自然景物呈现的“实”与象征含义的“虚”相结合的叙事方式,不仅是西部自然物象参与文本结构、文学主体进行价值构建的特殊策略,也是在启蒙主义思潮失落、世俗文化侵袭背景下,西部边地小说力图通过浪漫主义的艺术方式,捍卫“人”的“神性”、“独立”和“自由”的决绝反抗。
风景的“日常”与“社会现代性”
对于绝大多数西部本土作家而言,西部自然物象在他们的观照视野中并非是“唯美”与“浪漫”的,而是“狰狞”与“暴烈”的,是与主体性形成彼此“相异”的外在客体,在文本中可视为外在“主体”。这种“相异”关系甚至是“对抗”关系,蕴含着现代性的另一维度,即“社会现代性”。
社会现代性,既包括了物质感官层面的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欲望的释放、个体需要的合法等,即“源于工业与科学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胜利”,还包括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性催生的和赖以存在的政治实体,它相对于朝代国家而言。传统国家是朝代国家,其合法性在于神意,君主不是以民族代表的身份而是以神的名义进行统治。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在于民意,国家是以民族利益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这是理性精神在政治领域的实现。”社会现代性,既要求以现代的科学精神改造阻碍社会进步的外在客体,包括大自然,甚至将大自然改造为“人”的奴隶,将神驱逐下神坛,让“人”成为万物之主宰,形成“人文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同时,还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让“民族”和“人民”成为创造历史、推动时代、建设国家的主体,形成新的“民族国家主义”和“人民本位主义”。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民族国家主义,都是启蒙主义者所推崇和向往的价值模态。
对于西部本土作家来说,他们分别从“反抗自然”和“人化自然”两个维度来展开,前者以物质现代性的建设为旨归,后者以民族现代性的重建为目标。自然环境是一个特定民族的“形影不离的身体”,是孕育特定民族人群的大地之母。但在他们的审美观照中,大自然并非总是以和蔼慈祥的面目出现,而是有着狰狞惨烈的一面。辽阔的西部地区,有着崇山峻岭、漫天风沙、土壤贫瘠的地理特征,整体上属于干旱、半干旱或荒漠、半荒漠的不适宜人类生存状态,“高、寒、旱”成为了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的典型特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西部人不可能像中东部地区的民众那样可以不必考虑自然灾害的随时降临,只需要一心一意考虑如何获取丰收,而是不得不将人怎样存活、怎样征服自然求得生机作为首要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体验过西部自然肆虐的本土作家而言,他们往往将西部人艰难的生存境遇的根源,归结为不可更改的西部自然世界的狰狞与恶劣,“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与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西部地区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不仅影响着西部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方式,而且也渗透进了他们的集体意识形态和无意识文化心理等方面。西部乡土所发生的悲欢离合,西部乡土所蕴含的精神伟力,西部乡土所造就的奇风异俗,以及西北人的集体性道德伦理、精神面貌、人格意志等,往往都是西部特殊自然环境的逼迫使然。因此,反抗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就成为西部边地小说自然叙事当中所蕴含的社会现代性理念。唯有如此,才是西部地区现代性转换的首要步伐,也唯有如此,才是西部民众解脱苦难、获得物质解放的当务之急。在了一容、雪漠、石舒清、陈继明等作家笔下,源于自然地理的恶劣而导致的物质匮乏,源于自然景观的狰狞而导致的生命脆弱,都蕴含着西部作家基于西部本土地域的现实处境而做出的社会现代性诉求,“广袤的西部地区,由于自然的恶劣、地域的封闭、市场经济的滞后,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向往成为西部乡土现代性转换的首要任务”,也就是说,只有破除了对自然风景的浪漫化想象,回归到真实的西部现实,才是切近西部现实本土、实现现代化改造的必经之路。因此,反抗自然,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反抗前现代”、反抗“荒蛮”、“落后”的地域景观,就成为西部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文学表征。
人与自然的对抗,还表现为“人化自然”,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非审美主体的趋同性改造,而是表现为在对抗性当中凸显“人”的主体地位。这种人与自然的异己性进入小说就呈现为一种对立性自然叙事,即自然物象所扮演的角色与前述类型相反,它充当的是一种压迫性力量。这种自然叙事类型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突出“人”的内在力量,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物象叙事。其叙事模式基本表现为,人被放置于一个广阔的自然空间当中,人的求生与自然的压迫呈现为对立状态,最终目的是观察人的生命力量在自然压迫下的嬗变和震荡。这种对立型的自然叙事,不仅表现了作家对自然和人类相异性的思考,更重要的在于凸显人在生命绝境中的内在力量或人性本真,自然在这里所充当的是炼狱的角色,对人性力量的强调才是文学的最终旨归。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西部边地小说中,这个“人”往往不仅是一个“个体”,更多时候是“民族”群体和“国家”群体的象征。人化自然,表现为将自然视为主体重生的毁灭性力量,人在这种涅槃中获得新生。在西部边地小说中,常表现为将具有民族色彩和国家色彩的意象,如黄河、长江、瀑布、草原、高原、雷电、雪崩等等,作为突显“人”的力量、“民族”更新、“国家”重建的外在客体,在文学主体和客体的对照中,将“毁灭性”与“革命性”进行转喻,将“死亡”的力量与“生命”的力量进行换喻,最终在文本的叙事角色中,凸显出“人民”和“民族”改造社会、创造历史、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主体角色。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叙事策略与上述反抗自然的叙事主旨其实是殊途同归,不仅是西部作家在现代性思潮的引领之下,所做出的重铸民族之魂与重建人性主体的一个地域性的思想呼应与文学响应,而且也是对西部边地自然地理条件下所造就的西部民众原初民族根性的一次发现与弘扬,是一种探索地域自然与民族性情内在关系的文学思考。
因此,在本土型西部作家的审美视界中,人在感受大自然的暴烈与严酷,在体验生存艰难的同时,也铸就了西部人长期的与恶劣环境斗争的忧患意识和坚韧气质。狰狞的西部自然物象不仅在文学层面上破除了对西部异域的唯美化想象,还原出一个较为本真的西部世界,营造出一个富有边地特色的区域文学风貌,而且在自然压迫与人的反抗中,凸显出了人的生存悲剧与反抗的悲壮,而这个英雄式的“人”,这个承担了太多时代苦难和政治磨难的“民族”和“国家”,恰恰符合社会现代性所进行的民族国家更新和现代政治重建的集体诉求。
风景的“主体”与“反现代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西部边地小说创作中,都是以“人”为旨归的。在浪漫化的自然叙事中,自然与人的关系呈现出的是正面化的“审美自然”,当中更多的投射了作家的一种人格重建的文化隐喻色彩,一种对现代性异化的反思和批判主题;在对立型的自然叙事中,自然成为人类生存的威胁对立面,戕害着人的生命和尊严,阻碍着物质社会的进步,横亘在民族国家重建的快行道上。因此,无论是审美现代性对“人”的“神性”的复苏,还是社会现代性对大写之“人”的“力量”的挖掘,价值轴心永远是“人”,并导引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科学技术主义、现代理性王国,人类成为主体,自然完全是臣服于主体的叙事客体。世纪之交以来,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特别是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对现代工业文明弊端的矫正,对中国语境下“人定胜天”等行动与口号的批判,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的新型哲学伦理模式开始出现——生态中心主义。因为,一味追求现代性的诸多弊端开始显露:全球雾霾、资源枯竭、自然破坏,虽然审美现代性(即反思和超越层面的现代性)从现代性发生之初就进行着制衡和警策,但它只能起到一种反制的效用,是一套辩证逻辑,本身并不是一套新的思维体系。随着现代性异化日益成为大众所失望的图景,亟待构建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以张扬生态平等的生态中心主义孕育而生。它认为,人类对自然的奴役、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最终换来的是大自然的报复——生态恶化、动物灭绝、灾害频发,等等,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在自然价值观上,人与自然之间并没有固定不变的界限,应该否定相对于非人自然的人类价值尺度的至上性与唯一性,应该消除所谓的“人”的主体性,而将人与自然置于平等的主体性位置,使其在生态平衡当中实现互补与共赢,这一文化理念也常被视为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难能可贵的是,西部作家先于中东部作家率先构建起了这种文学主客体关系,体现为他们秉持着“反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在小说中,不是将自然神秘化和神圣化,也不是将自然妖魔化和审丑化,而是在“生态和谐”和“生命中心”的层面,对人与自然在生态层面进行探讨。陈继明、雪漠、郭雪波、杨志军、乌热尔图、铁穆尔等作家,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中,首先确立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和谐与对应,并由此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拓展性和追溯性反思,最终将造成生态恶化的人、历史和社会都纳入了反思的范畴,从而导引出“文化的生态破坏”才是造成“自然的生态破坏”的根源这一理路。因此,西部生态型自然叙事,就不仅仅体现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上,还包含了一切自然性的人与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和谐,比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生命本性的“和谐”,并确立了带有“生命中心主义”倾向的新型自然叙事文学理念。
由此观之,生态和谐的观念一直存在于西部关注自然的作家的文化思考中,只不过由于特定时代的不同审美需求,西部自然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隐喻色彩和文化理念内涵。尤其是由于工业化进程而引发生态危机之后,中东部作家才有意识地接触、关注,并试图推波助澜之时,西部作家早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各自的思考与探索,西部文学的“先锋性”和“超越性”由此也可以得到明证。在生态文学视野中,西部自然在小说中的出现,一改之前浪漫型自然叙事的精神象征性风格,将自然置于人类之上的不对等状态,也一改将自然作为人类生存对立面的基本关系框架。因为以上两种关系框架,自然本身是从属的,甚至是被忽略的,“人”的精神主体性升华成为唯一的主题。而在生态文学的理念中,生命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人此时也被看作是自然生态环境循环链中的一个环节。从这一意义上讲,西部边地小说的忧患意识已经从对个体的人的忧患,延伸到了对整个世界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忧患。这种生存忧患意识在西部生态小说中不仅得到了深化,而且以其新的文化姿态,拥有了世界性眼光,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西部边地小说其实一直在默默而孤寂地引领着中国文学发展的前沿。当然,也不得不承认,西部作家的生态叙事相较于西方纯粹意义上的生态作品还有较大的距离,生态理念支配下的生态作品的成熟之作毕竟也是有限的,绝大多数西部作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还停留于潜意识或无意识层面,而远未达到自觉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边地小说生态叙事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结 语
西部作家无论是对自然风景所蕴藏的力感美学的体验和沉浸,还是将西部风物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力来观照人在其逼仄之下的生存状态,抑或是将自然景观作为生态大概念来表达对生命的尊重与忧思,其共同特点是,西部作家总是将大自然作为一个永恒的创作主题,赋予其多样化的文化内涵和人格内涵,正如韩子勇所说:“就自然而言,没有哪块地方像这里一样,自然的参与、自然的色彩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和制约如此直截了当地突现在历史生活的表象与深层。有时候,自然的‘故事’整节整节地被载入人的活动历史。”尽管西部作家赋予自然的文化内涵有所不同,有的是作为生存感悟和思想升华的契机客体,有的是作为塑造人格和锤炼气质的物象载体,但构成西部文学本色的首要因素仍然是其自然风景,“西部未来的文学不仅应该而且可能对中国未来的文学做出特殊的重大的贡献。……这个贡献不一定表现在在这块土地上产生的作家、作品对其他地区而言有多么的出类拔萃,而是以西部独特的地理地貌、民情民俗、历史和现实、自然和人、生和死、理想和幻想、成功和毁灭、痛苦和欢乐、卑污和崇高作了审美化的提供和丰富”,并且这些西部自然物象经过西部作家的艺术策略进入文学,最终形成了西部边地小说特有的自然主体化叙事特征。在这个文学世界中,自然物象具备了人的某种精神气质或精神力量,并参与着小说文类的文本叙事,甚至作为人物故事之上的主体而出现在文本中。这种对自然的观照与审视,其实质是对人类精神关系形态的一种文化探寻,是西部边地的自然地理特征和西部作家之间形成的相互勾连和塑造的关系互动,是人和自然由现实关系向精神关系转化后在文学领域内的一种艺术反映和体现。但从根本上来说,西部作家面对自然景物时审美心理和叙事方式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蕴含着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西部作家对现代性的多维理解和认知,其中,既有超越同时代的制约、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异化的“审美现代性”,也有适应民族国家重建和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现代性”,更有着超越于现代性层面而具有世界性因素的“反现代性”的“生态中心主义”,西部作家也在客观地域环境和主体自觉构建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十分普遍的“自然意识”,完成了文学主体对自然景物的现代性认知模态构建,掣制着“风景消亡”的文学命运。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项目“当代大众的文学生活情态研究”(项目编号:11ZHB007)、江苏省高校社科重点项目“当代大众的文学审美素养调查研究”(项目编号:2010ZDIXM047)、山西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网络时代的文学审美转型研究”(项目编号:QN-201401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韩春燕)
金春平,文学博士,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