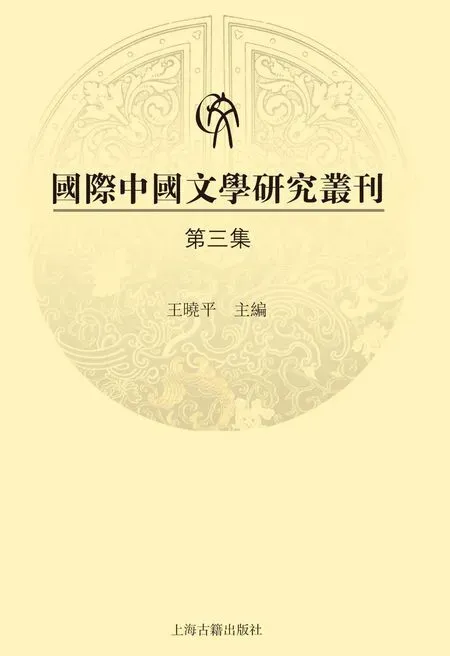翻譯出版與中日學術交流
——以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爲中心(下)
郝 蕊
翻譯出版與中日學術交流——以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爲中心(下)
郝 蕊
二
前面提到,據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中記録,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有鄭震節譯本和王古魯全譯本之外還有一個譯本,即江俠庵(1875—1951)譯《南北戲曲源流考》。因爲青木的《中國近世戲曲史》是將他1926年所作《自昆曲至皮黄調之推移》和1927年所作《南北戲曲源流考》兩篇文章加以整合,在此基礎上用了一年時間寫成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稱江譯本爲《中國近世戲曲史》雛形譯本也不爲過。
1.江譯本
青木正兒作《南北戲曲源流考》是在1927年,據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中記載,江譯本初版是在1938年10月,由長沙商務印書館印行,另據之後學者們的考證事實上江譯本已於1928年即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就當時的資訊傳播速度和出版發行狀況來看,是否足可以説明江譯本翻譯出版速度之快了呢?
譯者江俠庵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由兩廣總督府舉辦選送出洋留學生考試之時被録取官費留日,攻讀法政科。1925年夏,他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聘他爲特約日文翻譯。據《中國目録學家辭典》記載:“江俠庵,近人,生平不詳。著目録學著作《先秦經籍考》,193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筆者曾盡力查找關於江俠庵的其他資訊資料及研究專長,遺憾的是很難找到,他編譯的《先秦經籍考》引起了我的注意,該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出版,並於1990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作爲中外文化要籍影印叢書出版發行,2010年3月又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再版上下精裝兩册。筆者下載該書發現江俠庵在凡例中自云“本書著者非一人,大率東邦碩學名儒。終身研究所得之結晶品。至於地理考察,且有萬里裹糧,長期踏勘。而後著書者,與率爾操觚者回異”。《先秦經籍考》裏面收録、翻譯了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武内義雄、本田成之、小島佑馬、小川琢治、倉石武四郎等著民國年間日本學者關於先秦經籍的研究文章41篇,按專題分爲:總論類、周易類、尚書類、毛詩類、兩戴記類、春秋三傳類、四書類、孝經爾雅類、諸學類、地理及傳記類、雜考類等11類。附録倉石武四郎《淮南子考》、武内義雄《百衲本史記考》、《桓譚新論考》等。
從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選取篇目來看,他視野寬闊,集當時日本漢學家研究的主要成果於一書,可以概見當時日本學者對中國典籍研究之大概,對當時中國學術界無疑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直至今日仍對學術研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我們僅從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譯《南北戲曲源流考》等可以看出,他要借助日本學者的研究狀況開啓我國學者以科學整理學故之風氣。他在《先秦經籍考》序中寫道:
吾人未用科學以考古。古代之書。多由傳説和假託。因之不能不考證其著作時代之背景。及其變化之原因。欲考證之。不能不利用科學。——而吾國學者以科學整理學故者。其風氣尚未展開。
當時我國學界正處於由傳統向近代轉型,他將西方先進的學術研究方法借助日本先行範式快速介紹到了我國,他要用譯介推動我國學術研究近代化的進程。正是因爲他有極高的鑒賞力和厚重的文學功底,使他能慧眼識金,率先看到了青木正兒《南北戲曲源流考》的價值,並在短時間内將它翻譯出版。雖然筆者没能考證到江譯本《南北戲曲源流考》所帶來的影響力有多大,但是,現在除了我們知道192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江譯本之外,還可看到1938年長沙商務印書館和1965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再版的江俠庵譯《南北戲曲源流考》,這是不是就可以證明江譯本存在的價值了呢?
2.鄭譯本
《中國近世戲曲史》是青木正兒于1930年2月完成由弘文堂刊行,鄭震在短時間内於1931年上半年就完成了《中國近世戲曲史》的節譯本,1933年3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發行。在節譯本完成等待出版發行之前,鄭震又於1931年5、6月份在《現代文學評論》第2期發表了《關於中國近世戲曲史》一文,介紹了原著和節譯的情況。他以:“足足費去了一星期的光陰,我才把這部書日文的中國近世戲曲史續完。”爲文章開頭,緊接着便將青木正兒原著五篇的梗概作一介紹:第一篇是寫南北曲的由來。先敍述了宋以前的戲曲發達概況,繼而寫南北曲的起源和南北曲的分歧,一直到元朝的中末葉爲止。第二篇是寫南戲復興期。雖從元之中葉説起,可是明以前的南戲,除永樂大典本戲文三種外,其餘只列有書名,並未敍其内容。述及明代雜劇,非常詳細。第三篇是寫“昆曲的昌盛期”。這部分前前後後,足足寫了四百餘頁,可以説是全書的最精彩處。也是作者的最得意之作。第四篇是寫從昆劇到皮黄戲的推移。詳述了皮黄戲的勃興和昆曲的衰落。第五篇是餘論,也可以説是補遺。最後以“曲學書目舉要”作殿軍。
鄭震對出自異幫人之手的《中國近世戲曲史》評價極高,他認爲讀了這一部戲曲史,即不讀宋元戲曲史,對於中國歷來戲曲界的全盤情形,也可得着一個概念。他説:“我們謹就這簡單的目録來看,即可以知道那是怎樣的一部巨著。以一個異邦的人,能夠做這樣有系統的研究,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難怪乎作者前前後後要費二十年的功夫(據作者自序裏所説),才完成這部作品。”
鄭震歸納出了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的六大特點:第一,全書的收材豐富。第二,編法按照年代,有很整齊的系統。第三,本書名是《近世戲曲史》,而於明以前的戲曲,也有相當的論述,更追溯到宋以前的戲曲的遠源,使讀者對於中國全般的戲曲史有相當的瞭解。第四,書中各處部分的考證——如關於戲劇作者的正誤,戲劇本事的出處等,有許多都相當的有意義。第五,關於樂曲之逐代的變革,有相當的説明,可以使讀者約略知道古來舞臺上演奏的大概。第六,全部書的結構,繁簡適中,犯着“得此事彼”之病處殊少。
鄭震在讚賞之餘,並未對這位元異邦作者認識上、觀點上的錯誤採取姑息的態度,而是直言不諱、一針見血地指了出來。此外他還指出了該書的偏於一面、疏忽、遺漏、説法上的欠缺等不足,尤其是關於青木正兒對每篇作品所作的評語,鄭震認爲:
作者青木先生,是一個資産階級的學者,一切的資産階級學者對於歷史嬗變的法則,都是盲目的,作者自然也不能例外。所以在這一點上作者没有説明,我們也不必對於作者加以怎樣的苛責。
本屬於敍述每篇作品的梗概之後,並附以歷來批評者的評語——這一點在我認爲是絲毫都没有附加的必要。因爲中國歷來批評者的批評文章,純粹是用主觀的感情,並不包括客觀的真理在内。這一種批評,最容易導人入錯誤的門徑。
當今學者稱鄭震的評論方式爲“階級分析的方法”,認爲:“譯者對作品内容的評論,往往着眼於階級分析的方法,這在當時的戲曲評論中還是比較少見的。”鄭震的階級分析觀使他對青木正兒所寫作品評語持不贊成的態度,這也是鄭譯本把原著五篇删爲三篇、對原著的考證材料和前人評語大量删減的原因所在。
鄭震節譯《中國近世戲曲史》,更在於他對以戲曲爲代表的俗文學所持的態度,他曾列舉了中國歷代戲曲中“糙”的五種類型,儘管如此,他卻依然急於將青木正兒的《中國近世戲曲史》公諸於世,這是因爲他看到了戲曲等俗文學的價值,他認爲:“最後我要説的便是中國過去的戲劇,究竟是一個民族意識上的一種遺留品,雖然它是那樣的乏味,而用歷史的眼光看來,卻自有它文藝上的價值。”這正是他文學研究的歷史觀和審美觀,更符合民族主義文藝理論即“反階級鬬争理論,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的實質。
鄭震對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的譯介行爲有他獨特的方法,《關於中國近世戲曲史》一文,是他節譯本的鋪墊。鄭譯本及前期的造勢文章對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的傳播無疑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鄭譯本本身起到的作用並不大,原因在於:一方面鄭譯本是節譯並非全譯;另一方面,幾乎就和鄭震同時,王古魯也開始翻譯《中國近世戲曲史》。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王古魯的全譯本,雖然當時尚未採用“譯著”(是1958年作家出版社再版時採用的),但是,已經有了“著”的成分,它的出版只比鄭譯本晚3年,鄭譯本的影響無法和王譯本相比。但是,不能否認鄭譯本曾經産生過的影響,董每戡先生于1944年寫《説“角抵”“奇戲”》一文時,就引用了鄭譯本。鄭譯本的作用更在於它着眼於原作的快速傳播,採取節譯的策略,且在節譯本出版發行之前,又寫文章在《現代文學評論》第二期上發表《關於中國近世戲曲史》、又在第三期上堪布《曲學書目舉要》,加速了《中國近世戲曲史》的交流速度。
鄭震所借助的《現代文學評論》雜誌,當時它的傳播力和影響力究竟有多大呢?《現代文學評論》由李贊華編輯,以中外文學的介紹和評論爲主,同時也刊有文學創作,是一個有一定民族主義文藝傾向的刊物。該雜誌1931年4月10日在上海創刊,由現代書局發行。中國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是繼三民主義文藝運動之後,1930年6月開始出現,由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陳立夫、陳果夫支持上海六一社提倡的,所以《現代文學評論》由國民黨省、市黨部主辦、控制。因爲它當年創刊當年停刊,只出版了4期,因而被現代學界所忽視,事實上它是“民族主義文學”的主力刊物之一。“鄭震的《關於中國近世戲曲史》一文被中國戲曲研究界引用至今。”所以,《關於中國近世戲曲史》和《曲學書目舉要》的傳播不容小視。
鄭譯本起到了使《中國近世戲曲史》連同他的作者青木正兒引起學界關注的作用。鄭震採取節譯的翻譯策略,並在譯本出版前借助雜誌的傳播力推出介紹文章,他的這一連續作法源於他急於把明清戲曲史問世的消息儘早公諸於世。鄭震是古典文學研究名家,他十分清楚我國戲曲史研究狀況,以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爲開山之作,之後的中國戲曲史研究正如顧頡剛所説:
七八年前,我讀王静安先生的《宋元戲曲史》時,便想繼續他的工作,做成一部《明清戲曲史》。但明清兩代戲曲材料太多了,不容易整理出一個頭緒來;加以我的學問的嗜好早已改變了方向,更不能分心搜集戲劇的資料。因此,我這個希望至今還只是一個空想。
顧頡剛代表了當時學界的想法,很多學者把明清戲曲史作爲課題曾努力與嘗試但均未成功。基於當時的社會背景,鄭震爲了能夠讓人們儘早看到這一願望的實現,才採取了介紹、節譯的策略吧,這是鄭震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實施對譯文選擇的典型實例。當人們高度評價王譯本這一傑作時,也不能忘記鄭譯本完成的使命。
青木正兒于1930年2月發表《中國近世戲曲史》,中國學界馬上就有了反應,9月25日陳子展撰文《青木正兒的〈支那近世戲曲史〉》,發表在當年出版的《現代文學》雜誌上,對《中國近世戲曲史》的章節和内容作了介紹,讚譽此書“不能不算是敍述中國近代戲曲之變遷的第一部好書”,尤其是乾隆以後的戲曲史,很爲詳盡精當。據説鄭震和陳子展是朋友關係,他向陳氏求序,陳便將三年前寫的《青木正兒的〈支那近世戲曲史〉》,稍作修改成爲了鄭譯本陳序。
3.王譯本
幾乎和鄭震同時王古魯也開始翻譯《中國近世戲曲史》,王譯本1931年7月譯成,1936年2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推出初版。
王古魯對《中國近世戲曲史》的翻譯是成功的。王譯本在當時就受到學術界很高的讚譽,吴梅評價説,王古魯“舉青木君徵引諸籍,無不一一檢校。舟車所至,曾不輟業,書中附載參考各條,是正原文,闕功甚巨。——此又可爲青木之諍友焉”。
譯者王古魯在商務印書館的中譯本中增入“參考”近30處,附録2項。“參考”收入了許多重要戲曲史料,有的是爲了彌補原著在徵引文獻方面的不足,也有的是爲了糾正著者的錯誤,此外,他還對原著作了必要的補充與修正,並附録他自己的《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之蔣孝〈舊南九宫譜〉》與《蔣孝〈舊編南九宫譜〉與沈〈南九宫十三調曲譜〉》考證文章兩篇。
王古魯的初譯本用他自己的話説:
我翻譯此書,時間極爲短促,加以分量極多,譯時精神或有失照顧之處,所以不敢自信完善。不過我可以説對於原著頗忠實,凡盡我力可以爲此書助者,必設法覓得資料。如上述之抄録《舊南九宫譜》,以及覓得原著所覓者《鞠通生小傳》之類。(小傳全文附刊入本書第十章爲參考。)並且我還發見原著所引用之文頗有誤解原文之處若干點,我就我所知範圍,亦爲之施注及添加參考文(當然大部分所增的參考,不全是校正原書錯誤之點,而系供讀者便覽之用的。)一方使讀者不致以譌傳譌,一方希望原著者
對於原著再版時一爲訂正,俾此書益臻完善。
這都反映了譯者嚴謹的治學態度。有人説王古魯是最合適翻譯《中國近世戲曲史》的人選。吴梅在《中國近世戲曲史》序中説“古魯遊學日本久,語言文字,盡通癥結,譯成是書,載更寒暑”,表明了其語言方面的純熟;他以(附録一)《國立北京圖書館所藏之蔣孝舊南九宫譜》與(附録二)《蔣孝舊編南九宫譜與沈璟南南九宫十三調曲譜》兩篇文章顯示了他的學術水準,説明他只不過選擇了這種寓著於譯的獨特著述方式,王古魯的著譯方式也爲翻譯研究提供了真實素材。
作者青木正兒本人也對王譯本很滿意。他在爲郭虚中譯《中國文學發凡》(原題《支那文學概説》,商務印書館,1936年)所作自序中説:“曾著《中國近世戲曲史》,流世已久,顧者無幾,然而,中國則出鄭王兩家譯本,可見其不棄也。”“真乎德不孤必有鄰矣”。該書翻譯的成功並不僅僅表現在王古魯先生忠實于原著,將作者的意見準確、妥帖地翻譯出來,更爲重要的是,他没有停留在譯的階段,而是憑着自己對戲曲史的嫺熟,糾正了原著中的不少錯誤,補充了原著中所缺的一些材料,並在書中增加了參考和附録兩部分内容。
王譯本在1936年商務印書館初版的基礎上又經過了1954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刊行的“增補修訂本”、1956年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重印之後,譯者再作校補,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題署爲“青木正兒原著,王古魯譯著”。針對這一做法,他解釋爲:
改稱“譯著”而不稱“譯”。這不獨因爲我所蒐所附的資料和文字,約占原著全書分量的三分之一左右,適當與否,未便讓原著者代負此責;而且一如上文所述,我的修訂增補情形,更已逸出單純翻譯範圍,改用此二字,表示本人亦負一部分責任。
全書有五篇十六章三十二節。他兩次訂正,訂正了原譯的一些錯誤,並根據新的文獻資料,重編了《曲學書目舉要》,補入了《奢摩他室藏曲待價目》等。
因爲翻譯該書的關係,王古魯還和作者青木正兒在學術上的切磋也隨之開始。李慶編注的《東瀛遺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一書,共收録了王古魯致青木正兒的書信37封,披露了許多珍貴的資料。對於譯書過程中學術問題的探討,王古魯也有記述:
一面將我發見他的錯誤各點,去函告知。他的復信,虚心地接受我的意見,並且還承認這一點錯誤的指出,使得他的“論點根本顛覆”,殷殷詢問曾否替他訂正。最初我拘泥於“引文固可一本所引之書原文更正,著者的斷語,則似未便代加修正”的見解,在1936年本中並没有提出修正的意見。等到接得復信之後,又以業已付印,只能在重版時再斟酌如何修正方法。
他們二人的書信往來,即使我們看到了王古魯“可爲青木之諍友焉”,也顯露出青木正兒這位日本中國戲曲研究學界“一言九鼎”大家難得的謙虚與真誠。兩人不僅在該書中譯本再版過程中進行通信聯繫,相互討論切磋,其後還曾在日本有過愉快的面談,兩個人的來往一直持續了20多年。
小 結
生態翻譯學是近十年來中國原創、具有國際視野的翻譯理論,是翻譯研究的一個新視角。“翻譯生態環境的構成要素包含了源語、原文和譯語系統,是譯者和譯文生存狀態的整體環境”。自2001年發軔到2004年《翻譯適應選擇論》的出版,胡庚申論證和構建了一個以“譯者爲中心的‘翻譯=適應+選擇’的理論範式”。其理論認爲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託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本篇借助這一理論,揭示圍繞《中國近世戲曲史》在“翻譯——傳播——接受——影響”四大環節組成的完整翻譯生態鏈中整體/關聯的互動,揭示出江俠庵、鄭震等人爲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在中國的傳播所做出的貢獻。
本文應用生態翻譯學理論揭示《中國近世戲曲史》翻譯傳播的過程,其目的不只限於青木正兒一本《中國近世戲曲史》在中國的影響,而是要展現王國維和青木正兒以及京都學派、青木正兒和王古魯等中日學者間直接的、間接的學術交流,他們和江俠庵、鄭震等共同爲中國近代戲曲研究這一文學領域的構建奠定了又一塊基石。生態翻譯學理論也許對過分强調譯者主體性是一個反撥,它强調譯者如何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和譯者如何進行選擇性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翻譯適應選擇性理論有利於譯者積極性的發揮,但譯者是翻譯活動中最活躍的因素,這一點仍不容忽視,所以筆者在本文第二部分仍舊採用“譯者主體性”的説法,我覺得生態翻譯學理論當進一步延伸到源文本的成書過程,也就是本文的第一部分,那麽就可以將中外文學學術交流的一個相對完整過程展現出來了。
所謂“學術”是指系統專門的學問,是對存在物及其規律的學科化論證。圍繞《中國近世戲曲史》的翻譯出版,可以看出青木正兒與王國維、王古魯等人之間的的交流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學術交流,這一史實的形成可以説源自王國維,他的作用無可替代,中外真正的雙向交流始于羅振玉、柯劭忞、王國維等人,尤以王國維爲代表。正如馬信芳所言:“而王國維身處清末民初史料大發現的時代,兼具精通數門外語、諳熟西方哲學、與處於學術前沿的中外一流學者密切交流的優勢,因而在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等眾多新學術領域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王國維、王古魯踐行了中外學術交流,是成功的經驗,他們爲我們今天的學術交流提供了範式。江俠庵、鄭震等人雖稱不上成功、範式,但至少不容否認他們對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在中國傳播起到的積極作用,是戲曲學術交流的先例。考證這一段史實,我們會發現學者之間相似的學術背景(包含譯者)對學術交流有積極推動作用。
王國維戲曲研究的現代學術風貌,是後來的研究者都能感受到的,他外引西學而内接幹嘉之學,在文學思想上“則上承莊禪的個體價值關懷傳統,而康得、叔本華(尤其後者)爲他所心儀則是這種價值關懷的一個延伸。”王國維受康得、叔本華思想影響來自于他日語老師的引導,王國維在《静庵文集續編自序》中回憶説:“是時社中教師爲日本文學士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學。余一日見田岡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康得)、叔本華之哲學者,心甚喜之。顧文字睽隔,自以爲終身無讀二氏之書之日矣。”
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繼承了日本明治維新前期學者的研究理念。黄仕忠認爲明治時期的中國戲曲研究,層次豐富,脉絡清晰,涉及面寬廣,他認爲:“而森槐南、幸田露伴、笹川種郎等人,超越了日本江户儒學和明治漢學,把中國小説戲曲之研究,帶入近代學術之行列,成爲中國俗文學研究的一個嶄新起點,也成爲王國維曲學研究的先導。”可以説王國維所接受的是明治維新前期“日本學者對中國戲曲已經完成了全面而豐富的介紹,基本問題的梳理,並以西方文學的觀念,拓展了中國文學的概念與内涵,使得戲曲作爲一個獨立的門類得到人們普遍的認同。”這一先進文學理念,並在此基礎上創“二重證據法”。
羅振玉稱王國維的學術思想爲“東西洋學術”。青木正兒的恩師狩野直喜有着和王國維相似的學術背景,王國維稱他爲一代“儒宗”,思想上歸宗於儒學,他於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學習時和藤田豐八是同學,接受的是島田篁村的考據學教育。狩野直喜對中國哲學的研究繼承了島田篁村合注疏、義理、考證三者爲一的學問精神,正如小島佑馬所説:“在東京大學篁村老師教過的學生爲數不少,但繼承和發展了其考據學的只有狩野老師一人。”他兼通西學,熟稔英語和法語。
王國維和狩野直喜同受明治維新前期日本學者西方文學觀念下拓寬中國文學概念和内涵思想的影響,在此,我們所要强調的是他們的西方文學概念和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結合,都得益于清代樸學。
王國維和狩野直喜的學術交流爲人們所稱頌,他們的學術思想極大地影響着青木正兒,引導他走上了中國戲曲研究之路,青木正兒的學術理念集中體現在《中國近世戲曲史》中,它和王古魯爲代表的中國譯者産生思想上的碰撞,從而出現了王古魯和青木正兒等人新一輪的交流,成就了青木正兒戲曲思想在中國的快速傳播。徐雁平稱王國維和日本戲曲領域學術交流是“清代的考據之學和歐洲的東方學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正是在相似的學術背景之下,中日之間的學術交流變得更有可能、更有成效。”在此,我們要説他們具有帶動力,有滾雪球效應。如果説以王國維爲中心展開的中日學術交流爲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起到了基石作用,那麽,由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的翻譯出版,可以説爲王國維中國戲曲研究領域的構建夯實了基礎。
考證圍繞《中國近世戲曲史》翻譯出版的一些細節過程,可以爲中外學術交流尋求到範式。如果説王譯本《中國近世戲曲史》的多次再版是其成功標誌的話,那麽鄭譯本如按照生態翻譯學裏所説的“事後追懲”原則,它很快被王譯本所替代,也早已被人們所淡忘,可以説這是“適者生存”的結果。在我國近現代史上從晚清到“五四”,在走上西化進而到現代化的過程中,翻譯活動一直都佔據着文學最核心的位置,這期間翻譯價值取向曾發生過急劇轉變,出現了林譯“前譽後毁”的現象。“五四”期間林紓成爲批判的對象,之後文學翻譯標準轉向以貼近原文爲翻譯的最高標準。無疑,1931年當鄭譯本完成時,中國文學翻譯已經不再是張之洞《勸學篇》中所説的“可以補吾闕者之用”,中國文學而是已經結束了啓蒙邁入了現代,文學翻譯需要的是王古魯式的譯著,即中外文學學術交流下的文學翻譯策略,其過程需要切磋、互補等程式加以完善。從這個意義上説,鄭譯本未能流傳實屬必然,但是,無論從譯者、還是學者角度來説,鄭震竭盡全力快速將國外的研究成果公諸於世這點上來説,他對中外學術交流起到了推動作用,鄭震的初衷和着眼於中外學術交流的睿智是今天我們不應忘記的。
(作者爲天津師範大學外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