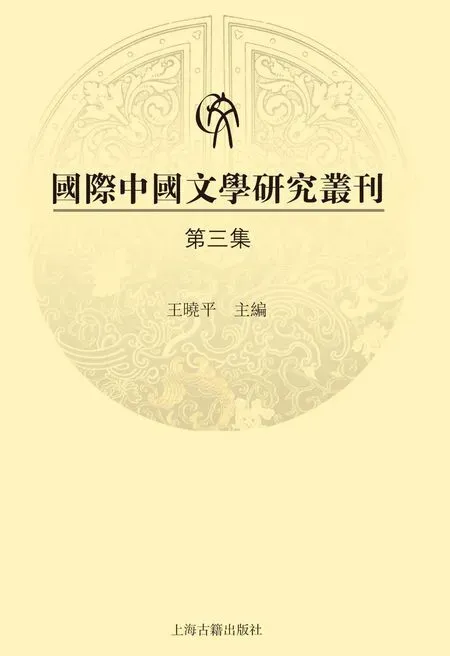津田左右吉的《論語》勘僞
張士傑
津田左右吉的《論語》勘僞
張士傑
近代日本處於古今東西文化與學術交匯、激蕩的漩渦之中。一些日本學者積極地運用西方近代學術觀念和方法,重新審視傳統文化。同時,也從本民族立場出發,重新解讀中國典籍,用力於構建近代文化。王曉平先生曾指出,“日本人對中國的研究與中國自身的學術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導這門學問的根本課題,是島國日本如何面對大陸中國。……盡管它們有時與中國本土學問面臨着同一對象,然而兩者卻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質和價值”。近代日本中國學如此,《論語》學亦然。
在日本學者熱衷研讀的中國典籍中,《論語》是極重要的一部。近代《論語》研究論着數量繁多,其中有二部著作被著名中國思想研究專家金谷治贊爲“現代《論語》研究之白眉”,即武内義雄《論語之研究》與津田左右吉《論語和孔子之思想》。二者均借助文獻批評的研究手段,對《論語》原典施以質疑和勘僞工作。前者的文獻批評是在篇目層面上進行的,後者則深入文本細部,在章句層面上,對孔子語録材料進行真僞勘定。
那麽,對於《論語》,津田左右吉到底勘僞了什麽?又是怎樣勘僞的?最終勘僞出了什麽?其是非如何?得失幾許?其實質又是如何?筆者懷揣如此疑問,擬就津田的《論語》勘僞做一細緻剖解和分析,以考其特質,辨其是非,論其實質。
一、津田左右吉其人其學
津田左右吉(Tsuda Saukichi,1873—1961)是活躍於日本大正、昭和時期的代表性史學家、思想史家,在日本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研究方面著述甚豐,於學界民間影響極大。世稱其學爲“津田學”、“津田史學”。津田中國學的一個顯著特徵,在於他對中國思想文化,尤其是對儒家思想的批判。
《論語和孔子之思想》是津田中國思想研究的第三部長篇力作,也是其《論語》研究的集成之作和代表性論著。全書由“緒言”、“世傳孔子之語”、“論語及孔子之語的傳承”、“論語的形態及内容”、“論語的成書軌跡”、“論語和儒家之學”、“結語:論語研究的方法及態度”共七部分構成,大體用功於甄别孔子語録材料的真僞,籍以考察孔子思想。
對於津田的《論語》研究,中日兩國學界都有一定的關注。大體而言,可以分爲以下三類。
第一,肯定與贊譽。金谷治、宫崎市定的觀點較具代表性。金谷盛贊津田的《論語和孔子之思想》,將其與武内義雄《論語之研究》並稱爲近代日本《論語》研究的翹楚。宫崎認爲,津田《論語》學具有疑古派“急於破邪而略於顯正”的特質,並將疑古派的長處發揮到極致。此外,津田關於儒教及中國思想的批判受到大正民主主義支持者以及戰後民主化立場人士的贊同。由此,可以管窺津田《論語》及中國思想研究在日本學界和公眾中的影響情況。
第二,審視其研究的文化屬性。子安宣邦的觀點較具代表性。子安認爲,津田左右吉的中國思想研究不限於思想史研究的範疇,也是對中國思想文化做出評價,並指出其研究的“目的就在於對以往的或同時代的中國學研究加以批判和解構”,並作爲“本土主義者”以固有的日本文化批判外來的中國文化。
第三,對其施以文化歷史批評。我國學者嚴紹璗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嚴先生指出,津田左右吉“接受了白鳥庫吉的疑古觀念,並加以發展”,“對於中國文化則抱着極其冷漠的態度,持一種全盤否定的觀點”,“已經顯現出從批判主義滑向虚無主義的全面否定的徵兆”。嚴先生弟子劉萍從“懷疑主義的近代學術方法”、“批判主義的文化觀念”、“民族主義的思想立場”三個方面對津田的《論語》研究施以高度概括和歷史文化批評。
概而言之,對於津田的《論語》研究以及中國思想文化研究,贊譽者有之,批評者有之。然而,三種觀點各自成説,似乎也都頗具合理的一面。考慮到特定社會背景中孔子《論語》被歪曲利用於服務皇權政治的情況,金谷、宫崎的觀點是有其合理性的。子安宣邦將津田中國學定性爲“解構”及“文化批判”,頗具學術意義。嚴紹璗、劉萍在日本中國學的學術視閾中進行歷史文化批評,十分可貴。
津田的《論語》研究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學術文化現象綜合體,由《論語》學、西方學術思潮、日本民族文化三位一體而成,是在古今東西文化觀念與學術思潮激蕩、融匯之中的日本學術文化發生新變的一個典型,比較如實地反映出近代日本《論語》學的某些特徵,體現着當時日本人解讀和認知《論語》的思路、方式及特質。
面對這樣一個研究對象,仁仁智智也就不足爲奇了。然而,筆者以爲,必須在日本中國學和中日比較文化研究的學術視野中認真汲取前賢業績,綜合運用文本細讀與歷史文化批評相結合的研究手段,既要精準把握津田《論語》研究的思路、方法、結論以及論證,又要客觀剖析其真正的研究目的、態度以及効果。唯其如此,我們才能夠形成一個客觀、科學而全面的認識。鑑於此,筆者擬對津田《論語》研究的文本進行精細解讀與分析,對其研究方法、論證過程以及結論的是非得失加以考量、評騭,並進而對其内在特質予以審視和批評。
二、勘僞之思路
津田認爲,《論語》是解明孔子思想、儒家思想乃至中國思想的鎖鑰,但其中所録的孔子語録材料頗可懷疑。他在研讀《論語》時發現,孔子語録之間在思想上有着自相矛盾或相牴牾之處,而且也間雜非儒思想成分。於是,津田心中生出兩個疑問:其一,《論語》所録孔子之語是否可以全盤相信?其二,是否可以依據《論語》所録孔子之語來認識孔子及孔子思想。他認爲,必須對《論語》施以近代學術式的文獻批評,以審定其中孔子語録材料的真實性。他在《論語和孔子之思想》一書的“結語”中寫道:
將非孔子的言説僞飾成孔子語録,將後世言論假託於孔子,這實際上是對孔子的輕慢和玷污,也掩蓋、遮蔽了真正的孔子人格和思想。如欲尊重孔子,瞭解孔子思想,則務須除去僞飾、揭開遮蔽,再現真正之孔子。這才是仰孔子爲宗師的儒家的責任。儒者若尊孔子爲宗師,則此爲必須之要務。
由此可知三點信息:第一,津田儼然以儒者自居,標榜尊崇孔子;第二,津田對《論語》中孔子語録材料的真實性懷有疑問;第三,津田主張還原孔子言論和思想。
津田梳理了前人關於《論語》真僞之辨的研究,認爲歷來學者的考辨大致有二個特點:其一,多用功於考察某篇之真僞;其二,主要通過考察稱謂、行文等體例,推斷各篇的編定者及年代,而並未對内容、思想做真僞判斷。對此,津田頗爲不滿。在他看來,此類研究大抵是在儒家立場上進行的。所謂儒家立場,即是將儒家思想視爲絶對,奉之爲道德、政治的不易準繩,並將其作爲自己的主張,排斥、否定其他思想。在此種立場上,儒者將《論語》視若經典,奉爲圭臬,不敢對原文有絲毫置疑,因此也就不可能對其中孔子語録材料的真實性做出理性的懷疑和批判,更遑論對思想與内容進行質疑了。津田認爲這樣的研究思路與手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此種研究的結論認爲某篇可信、某篇有疑,卻無法解釋一篇内部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問題;第二,未與儒家思想演變的歷史相對照,以致未能於可疑之處質疑,也未能剔除後世改作和僞託的成分。他認爲只有除去後世的假託和僞飾,才能認識真正的孔子人格和思想。因此,津田的《論語》文獻批評著眼於兩點:一是孔子語録材料,二是儒家思想演進的軌跡。即參照儒家思想演進軌跡勘定孔子語録材料的真僞,以還原真正的孔子人格和思想。
首先,津田在語録材料的層面上作真僞判斷。
關於《論語》真僞問題,自崔述以來聚訟已久。崔述、伊藤仁齋、市村瓚次郎皆以各篇爲單位考察真僞,如某篇中有一二處可疑,則往往因之懷疑全篇。武内義雄析解二十篇的同時,也指出每一篇的末尾幾章不可輕信。若從解構的角度來看,東壁、仁齋將《論語》解構至篇,武内有解構諸篇的傾向。津田索性打破篇目的規限,在章、句的層面上施以考察。津田《論語》真僞之辨的對象是孔子之語。因此,他考察的焦點並非《論語》一書,也非《論語》諸篇,而是孔子語録材料本身。於是,他撇開《論語》整體的真實性問題,也不止步於對各篇的真僞考辨,而是深入章句層面,對書中所記孔子語録材料逐條考量、推斷。這種思路具有一定的科學性,既不迷信《論語》本文,也不因一章一句而否定全篇,但也有一定局限性,即可能割裂語録材料間的關係以致做出誤判。
其次,津田的文獻批評是在與儒家思想史的相互參照中進行的。
津田認爲,文獻批評應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本文批判”,二是“高等批判”。“本文批判”,即通過考校異本、參照他書,勘正原典中的誤字、脱字、衍字等,明確句讀,以獲得正確的文本。例如,津田注意到《荀子》中可見較强的引文意識,體例亦十分規範,若有引用則以“曾子曰”、“傳曰”、“道經曰”、“孔子曰”等明確標示。“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同見於《論語·憲問》和《荀子·勸學篇》,兩者辭句全然一致,但《荀子》中未標明“孔子曰”,津田由是判定此章並非引自《論語》,而是荀子自言。所謂“高等批判”,要在“本文批判”的基礎上進行,即參照思想史演進軌跡,以印證語録材料的真實性。具體而言,他把孔子語録材料置於思想史中加以比照、考量,從内容、思想上推斷語録材料的年代、出處等情況,若發現某條語録材料與《孟子》、《荀子》相同或近似,即試圖厘定其間關係,從而判定該條語録材料是否真屬孔子,抑或是後世僞託、改作。例如,津田認爲,《論語》中“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等章中隱含王道思想與異姓革命説的成分,當歸屬於孟子。又如,津田認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等章中,禮樂被賦以政治意義,應是以荀子禮樂説爲背景才能産生的。
以上兩點之外,津田還從内容出發,認爲一些語録材料偏離《論語》和孔子思想的基調,應當屬於道家思想、隱遁思想的範疇。例如,“憲問”篇中“賢者辟世”、“泰伯”篇中“無道則隱”、“微子”篇“長沮、桀溺耦而耕”章中“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等中顯見隱遁思想。又如,“微子”篇中的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以及“憲問”篇中石門、晨門等故事中顯見道家思想,而與儒家學説相左。
此外,津田也將社會發展演進的歷史作爲判斷《論語》中孔子語録材料形成年代的依據。例如,津田認爲,“堯曰”篇中“興滅國,繼絶世”、“爲政”篇中“繼周者”、子路篇中“如有王者”等語録材料應當是在周室名存實亡、興替漸顯的社會時代背景中才可能出現的,因而判定這些語録材料的形成時期爲戰國末期。
通過諸如此類的勘定,津田將《論語》中的孔子語録材料作爲客觀研究對象加以懷疑,並參照思想史以及社會發展狀況,施以文獻批評以辨析真僞。他在勘僞過程中,將爲數不少的語録材料從孔子名下剥離出去,或歸於《孟子》、《荀子》,或納入《詩經》、《尚書》、《易經》、《孝經》等,或劃給道家等等,内容涉及仁、聖、禮、樂、孝、隱逸等方面。就孔學範疇而言,津田的勘僞主要集中於“禮”和“仁”相關語録材料。
三、勘僞禮學相關語録材料
津田借審定語録材料真僞之名,將部分禮學相關語録材料從孔子名下剥離。這主要反映於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津田認爲《論語》中禮樂並提之處並非真正的孔子之言。他認爲:雖然《孟子》中也可見禮樂並提的現象,但將二者置於同等重要地位的則是荀子的禮樂論。據此,津田判定“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論語·先進》)、“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論語·子路》)、“文之以禮樂”(《論語·憲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同前)、“樂節禮樂”(同前)、“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興於《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等並非真正的孔子之言,另如冉有所言“如其禮樂”章(《論語·先進》)、宰我所言“三年之喪”章(《論語·陽貨》)也應歸於《荀子》。
第二,津田認爲《論語》中將禮、樂與政治相關聯的語録材料並非真正的孔子之言。他認爲,爲禮樂賦以政治意義、將禮樂與正名相關聯、文飾禮樂等禮樂政治觀念源自《荀子》“禮樂篇”、“樂論篇”,如“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論語·子路》)、“文之以禮樂”(《論語·憲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同前)、“文之以禮樂”(《論語·憲問》)等應是後世據《荀子》僞作後竄入,並假託於孔子的。
第三,津田認爲《論語》中關於禮、樂規制與政治地位相符的語録材料並非真正的孔子之言。如“八佾”篇“八佾舞于庭”章、“季氏旅于泰山”章、管仲不知禮章皆本于《荀子》“富國篇”、“禮論篇”。
第四,津田認爲,《論語》“鄉黨”篇中多處關於孔子守禮的記録應當是取自《禮記》的。如“賓不顧”、“立不中門”、“不履閾”、“執圭鞠躬如”、“足縮如如”、“迅雷風烈必變”等徑取“曲禮”、“玉藻”、“少儀”諸篇原句,另有多章是依據《禮記》中的觀念改作而成。津田認爲,《禮記》的這些篇章大致成書於西漢時代,所記内容或出現於先秦末期,因此,“鄉黨”篇中關於孔子守禮的行爲記録源自先秦末期的相關材料。
第五,津田認爲《論語》中關於儀禮、演禮的語録材料並非真正的孔子之言。他認爲,“八佾”篇中“林放問禮之本”章强調“禮”的精神,説明此章應出現於儀禮形式完備之後,當是先秦末期産物。
第六,津田認爲《論語》中言及三代之禮的語録材料並非真正的孔子之言。津田認爲,三代禮制之不同多見於西漢著述,而孟子則殊少言及禮樂,荀子也似未曾論及先王之禮因王朝而變遷,因此斷定“爲政”篇中“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章、“衛靈公”篇“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章、“八佾”篇“哀公問社於宰我”章等,言及三代之禮不同的語録材料應當出現于荀子之後。
第七,津田以禮樂並提爲依據,將“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劃歸荀子。此章宗旨在於孔子强調禮的精神内涵。津田否定此章,亦即否定孔子對禮的精神内涵的重視。
我們知道,孔子面對禮崩樂壞的時代情勢,主張恢復周禮,以維護社會秩序。具體而言,孔子提倡禮治,提倡恢復西周儀禮法度,提倡正名,即按照周禮的法度規範行爲,重視禮的精神内涵,認爲禮的形式可以改變,還在日常生活中守禮。這些是孔子禮學的内容,在《論語》中都有體現。然而,如上所述,津田否定了很多與禮相關的語録材料。如此一來,孔子禮學中的禮治、禮樂、正名、儀禮法度、禮的形式與精神内涵等觀念和主張遭到悉數否定,孔子禮學也就在津田所謂文獻批評的猛烈攻擊下遭到瓦解和否定。
四、勘僞仁學相關語録材料
津田在審定《論語》中孔子語録材料真僞的名義下,將部分禮學相關語録材料從孔子名下剥離。這主要是從以下三方面展開的:
第一,津田判定部分仁政、德治相關語録材料的思想來源是孟子的王道思想和異姓革命論。例如,他認爲“近者悦,遠者來”(《論語·子路》)、“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同前)、“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等語録材料中所表現出的施行仁政以歸服四方之民的觀念源自孟子的王道思想。又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論語·子路》)、“吾其爲東周乎”(《論語·陽貨》)等、“繼周者”(《論語·爲政》)等語録材料中隱含孟子的革命思想。津田認爲,這些語録材料自然不是真正的孔子之言,而是後世依據孟子思想僞作,並假託於孔子的。
第二,津田將部分與禮樂相關的語録材料判定給荀子。例如,在津田看來,“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章中禮樂並稱,而且禮樂被擡高至幾乎等同於仁的高度,而這種觀念是在荀子禮樂思想盛行之後才能産生的,因此理當歸屬於荀子。
第三,將部分語録材料肢解,分别判給孟子、荀子。津田認爲,“克己復禮爲仁”(《論語·顔淵》)並非真正的孔子之言。在他看來,此章中隱含“性”的思想,應是來自於孟子性論;而且,“禮”被擡至略同於“仁”的高度,因此必然與重禮的荀子有關。孔子主張“克己”、“複禮”以“爲仁”,即認爲“克己復禮”是實行仁的方法。但津田將其肢解後,分給了孟子、荀子。
我們知道,仁學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提倡的仁,首先是社會倫理概念,包含孝、悌、忠、信、恭、寬、敏、慧、敬等細目。孔子主張仁政,是仁學在政治思想範疇的體現。這兩點是孔子仁學體系最主要的構成部分。津田對“克己復禮爲仁”(《論語·顔淵》)以及仁政、德治相關語録材料的否定,實質上是從倫理道德與政治思想這兩個極爲重要的範疇上瓦解、否定孔子的仁學體系。
五、勘僞之是非
津田標榜用科學的、學術的方法研究《論語》,但其論證過程中的主觀臆斷、牽强附會以及結論的荒謬都是顯而易見的。要言之,其謬誤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顛倒先後,錯亂源流。先秦儒學思想發展、演變的軌跡十分清晰。孔子是源,孟荀是流。孔子學説是孟子、荀子學説的來源,孟子、荀子是孔子學説的繼承者和發揚者。此爲學界定讞,不易之史實。津田將孔子之言判給孟子、荀子,其謬之甚,不言自明。例如,“克己復禮爲仁”(《論語·顔淵》)是孔學的一個重要觀念。孟子的性論、荀子的隆禮論是受此啓發的。津田反説此句是後世參照孟荀思想僞作並假託於孔子的,而且也没有給出什麽根據,完全是主觀臆斷,不可信憑。又如,禮樂制度先於孔子就已經存在,但西周末年以來“禮崩樂壞”,禮流於形式,乃至儀禮法度也未被正確運用。孔子主張“爲國以禮”,主張“正名”以貫徹“禮治”,主張“齊之以禮”以使禮下及于庶民。津田以荀子的禮樂説較爲完備爲依據,認定孔子關於禮治、禮制、禮樂並提、三代之禮等方面語録材料源自《荀子》,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再如,孔子將仁貫徹於政治思想中,主張德治,認爲施行仁政可以使“近者悦,遠者來”(《論語·子路》)。這種仁政、德治觀念是孟子仁政論的理論根源。津田反而判定“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等源自孟子,顯然不當。
第二,割裂語録材料之間的關係,以致未能讀懂原文。例如,津田從“繼周者”(《論語·爲政》)、“吾其爲東周乎”(《論語·陽貨》)二則的字面意義做出臆測,認爲此二則出現于周室衰微之際。這種推斷是比較隨意的,也並不妥當。“繼周者”是孔子對子張“十世可知也”(《論語·爲政》)的回答,孔子對三代之禮因循變化進行審視和思考之後,對禮的形式演變做出一種推測。“吾其爲東周乎”(《論語·陽貨》)中,孔子的本旨在于恢復周禮,而非取周室而代之。這兩句語録材料與異姓革命思想本無關聯。津田無視上下文脉和原文本意,僅依字面便妄下臆斷,認爲其中暗含異姓革命思想,是太過於牽强附會的。
第三,削古人之足,適今人之履。例如,津田從引文體例的角度發出觀點,認爲“古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爲己”屬於《荀子》。這種思路頗具近代學術意識,不過其結論未必如此。嚴格標明引文出處,是近代的做法,荀子時代尚未有如此嚴格的學術規範,即便荀子也並非處處用心於此。何況,荀子以孔子之學爲宗,必定已將孔子的一些言語爛熟於胸,以至於隨口説出而渾然不覺。津田以近代學術思維臆斷兩千年前的古人,有削足適履之嫌。
第四,對社會時代發展情況的認知有誤。例如,津田判定“繼周者”、“吾其爲東周乎”二則應出現于戰國末期。其判斷的根據在於,只有在群雄並起稱霸、王室奄奄一息的戰國末期,才較有可能萌生取代周室的看法。此二則語録中是否含有革命思想,已于上文有過論述。而且,禮樂崩壞、王室衰微的狀況早在西周末年已然出現,而非戰國末期才有。津田對社會狀況的把握不準確,也是導致其做出誤判的一個原因。
以上略説津田的四點錯誤,第一點是其對思想學説發展規律的無視和對思想史實的歪曲,第二、三點是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教條式運用,第四點是由對社會歷史的錯誤認知而生出的誤判。要言之,津田對孔子禮學、仁學以及天命思想等方面相關語録材料的否定,滿是主觀臆斷的成分和牽强附會之語,是經不起推敲的。除卻道家思想、隱遁思想相關材料的裁定尚有一定合理成分之外,並無多少值得肯定的地方。津田標榜對《論語》進行“學術的”研究,實則相悖甚遠。
六、勘僞之實質
綜上可知,津田以文獻批評的手段,將《論語》中的部分孔子語録材料予以否定。然而,津田所做勘僞的用意卻不止於此,而是别有他意的。
首先,否定《論語》。在津田“論語學”中,不少語録材料被勘定爲非孔子之言。禮樂思想成熟于荀子,則與禮樂相關的材料大抵屬於荀子。王道思想、革命思想是由孟子宣導,則與王道、革命思想相關的材料理應劃歸孟子。凡此種種,類推可知。以要言之,津田將《論語》中與《孟子》《荀子》《易》《詩經》《尚書》等典籍相同、相似、相近、相關的孔子語録材料一一摘出,經過一番分析之後,便判定《論語》中的這些語録材料都不是真正的孔子之言,或者是由那幾種典籍中抽出、改作而假託於孔子的,或者是與那幾種典籍中的材料同樣引自其他文獻。另外,津田認爲,《論語》的宗旨在於言道德、政治,即言人之應爲之事,因此言及“天”、“命”的語録材料也非真正的孔子之言。如此,津田將《論語》中與其他先秦典籍有關的孔子語録材料悉數否定,内容涉及禮、樂、仁、孝、天命、隱逸等方面。這些材料被剔除之後,《論語》幾近被否。
其次,瓦解孔學體系。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實質上,津田對孔子語録材料的否定就是對孔子學説體系的瓦解和否定。仁學、禮學是孔子思想體系的兩個基本範疇。禮學是孔子思想的出發點,仁學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津田否定禮學、仁學,即是從孔子學説的核心範疇和根本層面上否定孔子學説。孔子仁學、禮學既屬於倫理道德範疇,也體現於政治思想方面。津田認爲孔子學説體系由道德與政治兩方面構成。他對禮學、仁學的批判在倫理道德和政治觀念兩個層面上都有體現,這就等於是從整體上否定孔子學説體系。
最後,抹殺中國思想文化之於日本的影響。津田將孔子思想視爲解讀中國思想的關鍵一環,正如其“前言”中所言:
欲知中國之思想,必先知儒家思想;欲知儒家思想,必先明孔子思想;欲明孔子思想,必先研讀《論語》。
由此可知:第一,津田將《論語》定位爲解明孔子思想、儒家思想乃至中國思想的鎖鑰;第二,津田標榜其研讀《論語》的目的在於解明孔子思想、儒家思想乃至中國思想。如此一來,在津田構建的中國思想文化研究中,《論語》研究被置於核心範疇和根本位置。因此,《論語》研究的結論如何便關係到津田對中國思想文化的核心認知,《論語》的歷史地位和文獻價值也就成爲關涉中國思想文化地位和價值的重大問題。在津田中國學的範疇中,否定《論語》,就相當於從核心層面上否定中國思想文化。如此,日本文化中的中國影響就蕩然無存了。
以上三點,由否定《論語》語録材料出發,進而瓦解孔學體系,從而抹殺中國文化之於日本的影響。這正是津田《論語》勘僞的實質所在。
津田著此書時,刻意避免漢字、漢語詞匯的使用。他在“前言”中説到,
我素來主張少用支那文字,此書也務求如此書寫。唯習練未足,故致駁雜不純。然日本之固有名詞則應盡用假名。
這一段話,或許正可旁證他的真正用意。順便一言,津田的努力并未如其所願。觀其書中,漢字與漢語詞匯仍然不少。他不得不承認完全放棄漢字是不可能的,但他認爲是自己習練不足所致。其實非也。我們知道,日語的片假名改自漢字的偏旁部首,平假名是由草體漢字變形而來。因此,即便津田全部釆用假名書寫,也無法脱離中國的文字與文化。可以説,津田若要徹底斬斷與中國文化的關係,那就只有一言不發,一字不寫,甚至連一點思考都不能有。
七、結 語
典籍的成書一般是一個歷史過程,因此,其間混雜後世成分的可能性較大。津田以是否符合儒家思想爲基準判斷語録材料真實性的思路和做法是較爲合理的,但其論證過程中頗多主觀臆斷的成分以及顛倒源流的謬誤,這與其所標榜的科學精神相去甚遠。而且,其結論也經不起推敲。嚴紹璗曾指出津田左右吉受白鳥庫吉中國文化否定論影響而滑向虚無主義,是有道理的。津田集中否定孔子禮學、仁學相關語録材料,又旁及孝、樂、天命等方面,實質上是將孔子學説的核心範疇和若干重要理論構成部分進行徹底的否定,是對孔子學説體系的瓦解。雖然,津田表面上説《論語》中的孔子語録材料大部可靠,但他自己也一定知道那無非是一句空乏的謊言罷了。同樣,津田所謂的尊重孔子、還原孔子也只不過是一個幌子而已。他的真正目的在於否定《論語》中的孔子之言,進而否定孔子思想。在津田中國學的範疇中,《論語》和孔子思想被定位爲中國思想文化的核心和關鍵。那麽,否定了孔子之言和孔子思想,就等於在核心層面和關鍵部位否定了中國思想文化。
津田對《論語》和孔子思想乃至中國思想文化的極力批判和否定,其實是事出有因的。從明治政府頒佈《教育敕語》,到井上哲次郎撰《敕語衍義》宣揚忠君觀念,再到服部宇之吉鼓吹孔子教,20世紀上半葉的日本一直彌漫着盜用儒學以服務於皇權政治的濃厚陰霾。孔子和儒學遭到綁架,並被推爲皇權論的“教主”和理論源泉。從這種意義上説,津田對《論語》及孔子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實質上是對皇權論者的批判和否定,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然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津田的謬誤是確確實實的。
王曉平先生曾指出,“日本人對中國的研究與中國自身的學術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導這門學問的根本課題,是島國日本如何面對大陸中國。……儘管它們有時與中國本土學問面臨着同一物件,然而兩者卻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質和價值”。日本學者的中國研究天然地歸屬於日本學術範疇,其根本目的在於如何面對中國大陸,在於構建日本的學術和文化。津田左右吉否定《論語》和孔子思想,就是要將《論語》對日本千餘年的影響歷史攔腰斬斷,將《論語》之於日本文化的影響關係一筆勾銷。其實質在於,剔除中國思想文化元素之後,構建日本民族本位的近代文化。
(作者爲大連外國語大學日本語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本文爲2012年度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日本近代的民族意識與《論語》研究”L12DZX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