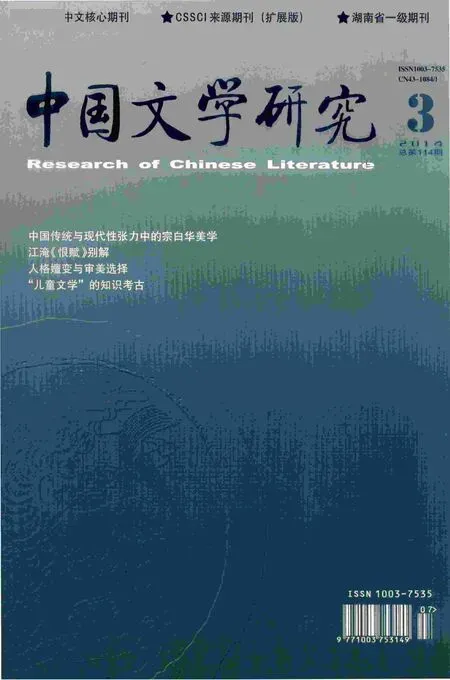面向世界的敞开与自我救赎之路:解读莫言长篇小说《蛙》
王亚平
(湖北科技学院教育学院 湖北 咸宁 437100)
在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的诸多作品之中,长篇小说《蛙》的异质性惹人注意。这部小说一改莫言往日汪洋恣肆,瑰丽磅薄的文风,转而呈现出严肃内敛的面貌,以一种平静中见波澜的方式,演绎“讲故事的人”的抱负和情怀。这也难怪,作为一部向建国六十周年献礼的作品,莫言对这部号称“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的小说所寄予的厚望也是可以想见的,正如小说封面勒口所写的:“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由此,他出人意料地将笔触伸向了“波澜起伏的生育史”,以“生育”这个话题来贯穿了整个共和国的历史。现在看来,《蛙》的意义突出地表现在,它一方面写的是历史和现实,从文化革命到计划生育,以及当下目迷五色的生活,呈现了极为广阔的现实空间;但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小说,触及了时下非常流行的生命政治的理论话题,彰显出既敏感又微妙的深意。
一、“计划生育”的文化政治
众所周知,自八十年来启蒙主义叙述以来,中国作家往往将创作聚焦对准反人道的国共内战、建国后的大饥荒和文革的残酷暴力之上,以求在对这些“恶魔性因素”的历史控诉中获得某种主体性的位置。但莫言的《蛙》却讲述了当代史上一个更为晚近的话题,这就是“计划生育”。围绕生育的话题,来梳理并贯穿六十年来的当代史。生育无疑是当代中国的“大事件”,围绕生育,前三十年以“人多力量大”相号召掀起了一股生育高峰,而后三十年则以“只生一个好”的政策开创了生育管制的历史。当然从长远来看,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作为解决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减少的资源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出生率方面具有巨大的历史功绩,当然其政策带来的残酷性也是有目共睹的。一方面是人口的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又是生育权的持续剥夺,这种两难的处境,使得计划生育政策成为一个异常复杂和尖锐的问题。
计划生育也是多年以来,在文学领域内隐而不彰的话题。从毛泽东时代后期,到新时期,甚至一直延续至今,“计划生育”都是饱受争议的一项政策,尤其是在海外,更是广受诟病。因为在西方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视野看来,每一个体都应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而生育权作为这种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利的一部分,也是任何人都不可剥夺的。而且另一方面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圣的,这其中也包括尚未出生的生命,所以“堕胎”也是西方一个富有争议的伦理话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计划生育”及其所连带的一些让人不寒而栗的灾难性事件,毫无疑问地被视为对生命权力的践踏,而围绕“计划生育”展开的一种福柯式的“全景监狱”的社会监督模式,也被当作当代中国威权社会的一个佐证,也就是说,从一种绝对的人道主义,或是生命政治的角度来看,“计划生育”几乎成为了红色恐怖、共产专制的一部分。
生命政治的议题,是一个普世的议题。莫言通过小说《蛙》中对生命政治理论的演绎,成功地将计划生育的话题与国际流行议题结合了起来,从而将中国的问题国际化。作为一位在国际范围内拥有广泛稳定读者群的作者,这样的举措也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小说家,每一部新作都势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读者的注意。由此,将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国故事,用普世化的语言方式讲述出来,才是他惯用的手法。当然在《蛙》中,莫言并没有对其简单地“妖魔化”,而一味控诉,而是对生命,对历史,有一种更复杂更深沉的思考。
二、寓言写作与矛盾心态
《蛙》中集中塑造了姑姑这样一个乡村女医生的典型。这是一个内涵复杂的人物形象,既是农村中先进的现代医学的代表,又是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集中表征。这种双重特质决定了这是一个带有“寓言”意义的人物。一方面她作为一个助产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作为先进接生技术的掌握者,是对传统的“接生婆”某种进步的体现,或者说在一种传统与现代的视野里体现了某种现代性,因此也是生命权利的一种张扬和保护。但另一方面,她作为一位“老左”,革命理想的坚定捍卫者(也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愚忠分子”),在“计划生育”实施的年代,她又扮演了生命权利践踏者的角色。姑姑形象从正面走向反面,实际上也是当代历史,或者说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从正面走向反面的过程。社会主义挽救民族于危亡,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个体生命的安放建构了一个场所(避免了个体生命的流离失所),这种现代性恰恰体现在对个体生命的保护之上,然而紧接着,社会主义实践又以历史合理性的名义,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从而也展开了对个体生命的残酷剥夺,毫不留情地扼杀。就像“计划生育”的历史目的所展示,为了未来人口的有效管理,未来人们生命权利的呵护,需要对现阶段人们的生命予以践踏,而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也需要以这种历史的合目的性,通过指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远景”将现代性激进化,来克服现实的某种焦虑和不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姑姑”所掌管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实际上都是在现代性的名义上展开的,以现代性为名,我给予了你生命,同样以现代性的名义,我也可以剥夺你的生命,这是“姑姑”从颇为强悍地,成活率极高的“接生”、“助产”,到毫不留情地“引产”、“堕胎”,双手沾满鲜血的杀戮这一曲折故事的最大逻辑支撑。
无论如何,“计划生育”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性技术实践,它其实类似于福柯意义上的社会“治理术”,“治理被定义为处理事情的正确方式——不是为了导向公共善的形式(如法学家的文本所言),而是为了一种对每一项有待治理的事情来说都‘便利’的目的。这意味着多种特定的目标:比如,治理必须保证尽可能大量的财富被生产出来,必须保证给人民提供了足够的谋生手段,必须保证人口的增殖,等等。”而在福柯看来,“人口似乎超越所有其他东西,成为治理的最终目的”。“人口是需要的主体,欲望(aspiration)的主体,但同时也是治理手中的对象,面对治理,人口知道自身想要什么,但对治理对它所做的一切一无所知。存在于每一个组成人口的个人意识层次的利益(interest),还有被认为属于整个人口利益的利益(不管构成人口的每个个人的特定利益和欲望是什么),这就是人口治理的新目标和根本手段:一种新艺术,或在某种程度上一系列绝对新颖的手法和技术,诞生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看“计划生育”,以及围绕它展开的一系列话语形式,这些包括助产、接生、避孕、结扎、人流、引产等等,这些无疑都是现代的技术形式,都是服务于人口治理的。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主权和国家利益,以国家和整个社会为思考出发点的社会主义政权,必然将人口治理和国家安全,即安全、人口、治理这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思考。因此,从一种国家主义的层面来看,“计划生育”的伟大意义是不容抹杀的,通过国家的组织,根本的目的是要使得每一个人的生活更有意义,生命更有价值,所谓“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实践也证明,计划生育三十年中国整整少生了四亿多人,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这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然而,从个体生命政治的角度来看,国家主义的“计划生育”所包含的生命戕害又是触目惊心的,小说中写到的“喝药不夺瓶,上吊不抢绳”,其实都是现实生活的写照,甚至是农村大墙上赤裸裸的标语,而围绕“计划生育”展开的拆房、打人、罚款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的事实。因此,如何更为复杂辩证地看待计划生育的方式,也应该是我们更为复杂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历史的方式,也是我们如何复杂地看待现代性本身的方式。
这种复杂性在小说中表现为叙述者“我”在对“姑姑”的态度上的矛盾处。虽然说,小说是以客观而略带冷漠的笔法进行叙述,但这一展现却是出之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视角,这就使得小说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张力。一方面是不带感情的描写,一方面是叙述者“我”的参与其中,情感和理智上的错位,常令叙述者“我”处于一种游移不定之中。这种态度上的暧昧,正表明了作者对“计划生育”所表征的“生命政治”的复杂态度。于焉不难看出“计划生育”话语的复杂性的一面:其虽残忍而充满血腥,但并非毫无道理;其虽是一种针对个体的压制,但于国家在特定时代的的发展却是必不可少。
事实上,即使是在西方,“生命政治”的议题也一直以来备受“自由主义”的挑战。福柯曾指出:“这些问题(即生命政治的问题——引注)不能摆脱政治合理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它们显现和酝酿了其迫切性。在此,‘自由主义’进入了这个画面。因为正是和自由主义相关,这些问题才开始具备一种挑战的面貌。在一个急切地要求尊重法律
主体和确保个人进取的体制中,‘人口’这一现象,连同它的一些特定效应和问题,当如何解释?人口,将以何种名义,根据哪些规则来对待?”在福柯看来,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其实是对真正问题的掩盖。不论是“生命政治”,还是“自由主义”,都涉及“人口”的管理这一问题,其自柏拉图以来即已存在。福柯以他的研究试图告诉我们,“自由主义”虽表现出对治理过度的批判,但其仍旧是“一种实践”,要把自由主义当作“使治理实践变得合理化的一种原则和方法。”这样来看,“计划生命”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明显,换言之,对于“计划生育”的理解只有放在“人口”管理的框架内,而不是同自由主义对立的角度,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有效的阐释。莫言以他的态度上的含混表明了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因而也就不仅仅是道德上的简单判断所能打发得了的。
三、历史与现实
莫言的小说,很多都是以建国后的历史作为背景,他的小说有很强的历史感。这在《蛙》中仍旧如此。尽管他对建国后特别是“文革”前后的这段历史念兹在兹,但他并不是要借叙述和想象的力量展开对历史的批判。他是在借对历史的叙述,达到同历史的和解。这种意图在他这部现实主义之作中仍有延续,并没有因为文体和风格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他的小说,与其说充满历史感和对历史的尖锐批判,不如说暗含指向现实的反讽。这是阅读莫言的小说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说,莫言对“姑姑”形象的矛盾态度是作者对那段历史的复杂态度的表征的话,一旦笔触转向现实时,他的态度则变得明朗起来,其小说所具有的批判性也于焉显现。小说的后半部分,已从历史回到了当下。小说表现的重心也明显有所转移。此时,饱含负罪感的姑姑已经产生了某种宗教般的皈依倾向,她依然痛苦地活着是要为自己的过往而赎罪,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实际上体现出了某种对当代历史的超然姿态,及其意欲达成历史和解的意味。但是颇令人玩味的是,小说最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生命政治化”的形式,即资本对个体生命权力的掌控,牛蛙公司,即“代孕中心”围绕生殖、生育,生命的再造与重生,围绕商业、利润和资本的运作展开的对个体生命的重新侵占,颇为触目惊心地反映了当下“新意识形态”的社会生活。小说的现实指向性很强。
事实上,就如“姑姑”的忏悔反被资本主义的商业所利用,叙述者“我”的忏悔其实也很有限并极富反讽意味。“姑姑”在迷幻状态下想象并被制造出的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泥娃娃形象,并不仅仅止于供“姑姑”忏悔,终还是成为市场上供人挑选膜拜的商品。而叙述者“我”对代孕妈妈陈眉的态度上的两可和矛盾,也正表明叙述者“我”的虚伪。“我”虽洞晓“代孕中心”的存在,但却不管不顾,甚至纵容不孕的妻子找人替我“代孕”;“我”虽对陈眉代“我”怀孕有乱伦和违法的自责,但在心里却极希望这样一个孩子的降生;故而一面装出立意要让陈眉引产的决定,一旦时机成熟又以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来为自己开脱。在这里,针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实质上是以商业的逻辑表现出来;其与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以国家的名义实行计划生育的逻辑这一行为,不同之处又表现在哪里?对于那段已逝的历史,我们可以以国家的名义为个人的言行赎罪,可对于当下自己参与其中的现实,对于这一自己从中获利的商业逻辑,叙述者又该如何评判呢?可见,叙述者虽然表现出批判现实的意识,但其实很虚弱。
四、结语
莫言这部小说,从毛时代的“人多力量大”,到改革时代的“只生一个好”,再到当下富人“包二奶”、“生二胎”,围绕“计划生育”实施的三十多年当代史,既一以贯之地讲述了莫言本人较为热衷的生殖、生育的话题,又奇迹般地契合了当代欧洲非常流行的生命政治的理论热潮。从福柯到阿甘本,从动物权利到环保低碳,“生命政治”几乎成了甚嚣尘上的后现代伦理学的重要表征,也成了保守欧洲的最后价值观的“救命稻草”。在这个意义上,莫言用“他者”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也算是在用一种他人可以理解的方式“阐释”中国,这算是他对“诺贝尔”的投怀送抱,或者至少是暗送秋波吧!
这一努力,在小说中则表现为虚构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日本作家衫谷的存在。《蛙》的故事主干实际上是写给衫谷的五封信,小说则变成了夹带在书信里面的“附件”,甚至在第五封信中,他还附带了一个完整的话剧剧本;这虽是作者形式探索的一贯表现,但却实实在在透露出其内在的意识形态色彩。叙事人“我”万足,小跑,或者“蝌蚪”,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通过给日本文学前辈衫谷义人写信,以交谈和倾诉的方式,牵出历史过往和历史中的人物、故事,他人的际遇和悲欢离合,历史的沉重感和现实的沧桑感。这样一种叙述及其缺席的“他者”式的存在,毋宁说正代表一种凝视和审慎的目光,他既是在审视“奇观”“落后”的中国,也是在对知识分子“我”的拷问,而也正因为这一目光的存在,令叙述者“我”反躬自省,时刻不敢怠慢。在这里,衫谷的身份很重要,他的存在,实际上成为了叙述者“我”走向自我救赎的必要通道。救赎来自异域,而不是中国内部。如果从象征或寓言的角度再去解读,这一自我救赎之路毋宁说可视之为面向西方世界的敞开。通向西方的救赎,与获得西方的认可并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之间的距离,虽不可以道里计,但却是相通且能跨越的。莫言以他的获奖这一事实,证明了这点。
〔1〕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2〕米歇尔·福柯.治理术〔A〕.汪民安、陈永国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上)〔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3〕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A〕.汪民安主编.福柯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