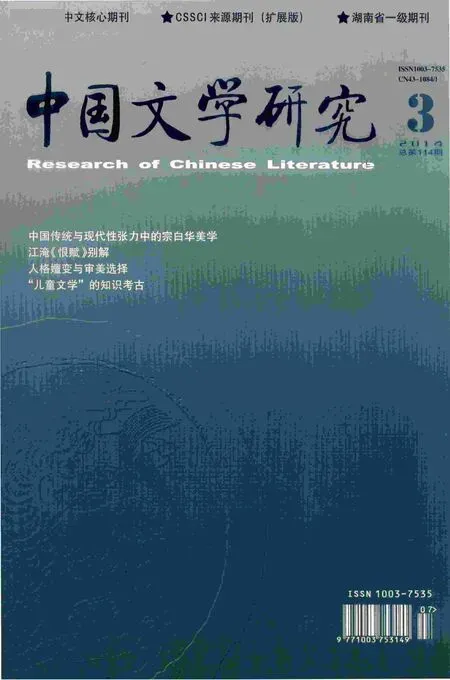论《呐喊》中“真的人”的形象演变
蒋永国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上海 200433;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鲁迅“真的人”的观念渊源于留日时期,它在《呐喊》中演变成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并体现出人物形象间的关联。但学术界并未对此进行有效而细致的梳理,这影响了《呐喊》中的各篇小说的跨文化研究和互文性解读,从而削弱了《呐喊》的艺术整体性。因此,对鲁迅“真的人”的渊源及其在《呐喊》中的形象演变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一、“真的人”的渊源
讨论“真的人”的文化渊源要从《破恶声论》谈起。《破恶声论》是鲁迅留日时期一篇未写完的文章,文中提倡“真的人”,认为“真的人”是“纯白”之人。鲁迅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伪士”是指“浇季士夫”,因为他们“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即是说“伪士”被功利所饰,只剩躯壳,真心灵和真看法丧失。这种真心灵和真看法在文中就是鲁迅所说的“白心”,田刚认为这样的词汇源自《庄子》,指出“庄子是人性自然论者,他反对与自然人性相对立的‘机心’或知识世界,并把这视为人性的异化。因此,在《庄子》一书中,类似‘纯白’、‘纯素’、‘朴素’之意的词比比皆是,他把得道之人称为‘素土’,其用意也在于此。而在对于自然人性的崇尚和道德拯救的承担这两个方面,鲁迅无疑从《庄子》中得到了潜在而又丰富的启示。”鲁迅认为真性情是“迷信”之人具有的品质,他们纯洁,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因而“迷信可存”。鲁迅在此要建构的真性情、纯粹和怀着童稚之心的人是“内曜者”和“心声者”,“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也。”“恶声”是“伪诈”之声,所以鲁迅要破“恶声”。“五·四”时期鲁迅在翻译爱罗先珂的童话时,屡屡在译后记把他比作上面所谈的“真的人”。《〈狭的笼〉译后附记》中说到诗人幼稚优美而纯洁的心,《〈池边〉译后附记》中又说:“他不像宣传家,煽动家;他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也为了非他族类的不幸者而叹息。”这些言论和《破恶声论》中所述并无很大差异,那说明鲁迅在“五·四”时期继承了留日时期的这种想法。
《破恶声论》还谈到“真的人”和“超人”间的关系。在谈到“伪士当去,迷信可存”后,鲁迅说:“至尼佉氏,则刺取达尔文进化之说,掊击景教,别说超人。虽云据科学为根,而宗教与幻想之臭味不脱,则其主张,特为易信仰,而非灭信仰昭然矣。”鲁迅说尼采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攻击基督教,提出别开生面的“超人”学说,尼采不是剿灭信仰,而是建立新信仰。此处所言“超人”是从根底上摆脱基督教仪式、教条和教规的新人种,他首先是“真的人”,然后才能是“超人”。“超人”是“真的人”发展的最高状态,是建立了自我、具有创造性和价值维度的人。鲁迅此前所写的《文化偏至论》也肯定了“超人”,在《摩罗诗力说》中大力颂扬的摩罗诗人亦是“超人”在文学上的表达,他们是“抱诚守真”的精神界战士,所以其诗歌能“撄人心”。鲁迅当时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对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超人”寄寓很大的希望,但鲁迅改造了尼采“超人”的蔑视民众的激进立场,把“纯白”和“超人”融合起来,“真的人”是“超人”形成的起点,“超人”又是“真的人”演进的高端。
《新生》的流产是鲁迅归国后长期沉默的重要原因,但当一定的历史机缘到来,鲁迅的文艺梦又一次反弹,而在日本所形成的文化思想也随着走进了鲁迅的文学世界。因此,“真的人”的观念就成为鲁迅《呐喊》中的人物形象的思想根基之一。那么,“真的人”在《呐喊》中怎样通过文学形象演进?
二、“真的人”的高端呈现
《呐喊》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这样说:“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这里的“真的人”相对吃人而言,不吃人并一味要好就是“真的人”。“吃人”在此象征封建礼教,“吃人的人”就是利用封建礼教和被封建礼教毒害的人。“不吃人的人”就是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获得了人的基本自由,成为一个真实而淳朴的人。由此来看,“真的人”是不被因袭的道德所束,真实、纯洁,有主体自由。《狂人日记》第十二节最后一句再一次说道:“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是要进一步说明“真的人”不被外在和传统势力左右。中国背负了因袭的重担,很多人被传统所奴役,丧失主体性,所以不见“真的人”。日本的增田涉、伊藤虎丸和丸尾常喜都把这里的“难见”解释成“没有脸见”。丸尾常喜对增田涉提出的这个观点进行了周密的考证,他从词典和古代文献以及白话文的用例中说明,古代的“难见”是“不容易见到”,白话文中的意思更接近“没有脸见到”,并从《狂人日记》中透露出的耻辱意识角度证明增田涉的说法。他又据鲁迅“五·四”时期撰写的《随感录四十一》把“真的人”解释为“人”、“人类”和“世界人”,这里讲的“人类”是指通过改革其生存方式,由“类猿人”变成“人”。丸尾常喜的解读很有价值,但太偏重字面意义,把“耻”意识做了放大处理。“耻”其实是因封建礼教造就的人觉醒后具有的,所以难见觉醒的人。因而,“真的人”则是指在这样的封建礼教下觉醒的人,是鲁迅据尼采思想发展来的具有改革和创新意识的人。《狂人日记》的“狂人”看清了封建礼教的弊害,他破除了内心的“黮暗”,远离了世人的“伪诈”,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个真性情的人。因此,“狂人”首先是“纯白”之人,再是觉醒的先驱者形象,这样就带有了尼采“超人”的痕迹,故“狂人”作为“真的人”演进的高端在小说中出现。
继《狂人日记》之后,《药》中又塑造了夏瑜这个先驱者形象,夏瑜明显不是“浇季之士”,不唯功利是尚,而是铁屋中惊醒的革命前驱,是“真的人”的又一高端呈现。《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也有“狂人”或者“超人”之影,小说的叙述把N先生限定在革命的视域内,再借辫子问题批评中国革命。N先生有狂气,脾气乖张,时常生闲气,说不通世故的话,发不合时宜之论。N先生是真实的存在,是一位觉醒的思想启蒙者和知识分子,这又是鲁迅“超人”的另一种表达。他们其实都是“真的人”发展而来,带有尼采“超人”的影子。尼采的“超人”把民众踩在脚下,他说:“对于许多人你不应伸手的,只应给之以巴掌:而且我希望你掌上多有钩爪。”这里的许多人基本是庸众的代名词,由此可见尼采的激进立场。鲁迅在《呐喊》时期明显怀疑尼采的这种“超人”思想,他于《随感录四十一》中说“超人”太渺茫就是证据,他期望造出尤近圆满的人类是不渺茫的“真的人”。与此相对应,《狂人日记》、《药》和《头发的故事》等小说就把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矛盾呈现出来。启蒙者、先驱者和知识分子作为“超人”的一面是民族的希望,然而他们无法把他们的思想传递给民众,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天才或“超人”存在的土壤,即“纯白”之人的存在,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要有《破恶声论》所说的真性情之民众。因此,《狂人日记》中要呼吁“救救孩子”,《药》在结尾要把夏瑜和华小栓的坟茔放在一起。
从《狂人日记》到《药》再到《头发的故事》,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这是鲁迅反思“真的人”演进到高端存在的问题,也是对尼采“超人”的深度怀疑。这个怀疑使鲁迅把希望回归到“未有天才之前”即“真的人”身上,这就出现了《呐喊》中一系列脱去“超人”面影的“真的人”形象。
三、“真的人”的回归民众
鲁迅通过《狂人日记》、《药》和《头发的故事》等小说对“真的人”的高端存在进行了深度反思,但他怕苦的寂寞传染给青年,而且那时的主将又不主张消极,所以他需要和民众贴心,这成为“真的人”在《呐喊》中回归民众的内驱力。
首先要讨论《一件小事》。这篇小说情节简单,叙述坐车人“我”看到一个人力车夫的善举。故事一开始就说了“我”高高在上的姿态,当这件事发生后,车夫和“我”就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我”反思自己,拉下架子。这让“我”质疑自己一天天看不起人,最终车夫的宽厚、正直和无私使“我”仰视。冯雪峰在分析此小说时,说人力车夫的行为和品质对“我”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这篇小说赞美劳动人民,是鲁迅在《呐喊》中塑造人物形象的一次重要视野转移。正象冯雪峰所分析的那样,人力车夫的优秀品质对“我”产生了行动上和道德上的冲击,而不是像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孔乙己等普通民众那样让“我”绝望。
《一件小事》仍然是鲁迅早期思想的延续和变异。鲁迅在17岁之前于绍兴全面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1898年去南京接触了进化论,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了解和学习了很多欧洲的哲学、文艺和文学知识,热衷于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施蒂纳、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对拜伦、雪莱等摩罗诗人大力颂扬,称他们为为“精神界战士”。从《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可看出,鲁迅是用“超人”和“精神界战士”对抗中国传统中的“不撄人心”的和合文化,先驱式的“超人”和“旨归在动作”的“精神界战士”批斗和合文化造就的“圣贤”和“隐士”。这个思想在回国后走向了沉寂,直到“五·四”时期,鲁迅才以文学的样态进行了复苏。狂人、夏瑜等先驱者和阿Q、孔乙己、华老栓、陈士成等麻木愚弱的国民形成对抗性关系,鲁迅逐渐意识到先驱者的文化优势。先驱者或者启蒙者在这个预设中高人一等,这就是鲁迅在《一件小事》中说的“我”一天天看不起人。当这个坏脾气在遭遇人力车夫的冲击时,原来被鲁迅所批判的国民在一刹那间光芒四射。这样,鲁迅就拉近了先驱者和国民的距离。
人力车夫表面上看对“我”形成道德冲击力,但本质上是对生命尊重给“我”造成的震撼力。传统的中国是个暴君治下的国家,人的生命从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我”在思想上中了这样的毒,车夫的行为让“我”戒毒。只有把他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平等来看的人,才具有对生命的热爱和同情。人力车夫是普通的劳动者,他的朴实是他尊重生命的基点。鲁迅在劳动者中看到的人力车夫是“真的人”,他真实面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敢于承担责任,不像“浇季士夫”唯功利是尚,他“灵觉”尚存,良心未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寄希望于孩子,现在却又意外发现普通劳动者的真善美。从孩子到普通劳动者,体现了鲁迅的希望向普通国民转移。可是他无法看到更多这样的人,他的视域下还多是被奴役的国民,他的视野又回到了童真时期。
《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和《社戏》承接了鲁迅这样的回归。《故乡》中的少年闰土是“真的人”的代表,鲁迅通过写景及童趣来表现: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鲁迅用了几个特别应该注意的词,“深蓝”给人的是静穆而高贵的感觉,也是自然的颜色;“金黄”是收获的象征,和下面一望无际碧绿的西瓜地形成互释的景象结构;“圆月”是中国最传统的意象,寓美好圆满之意。这样的描述确立了少年闰土自然淳朴的形象。闰土在雪地里帮“我”捕鸟,在西瓜地里刺猹,展现了他的聪明伶俐,至于说到走路人摘一个瓜吃的问题,又暗示了乡土人家道德的纯正。“我”和少年闰土间的情谊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之上,少年的天真烂漫让人体会到人生的美好,少年闰土是“真的人”,“我”正是和“真的人”建立了美好的友情而在分别时大哭一场。小说通过少年闰土和成年闰土的比较凸现少年闰土的淳朴自然、真实聪明。少年闰土清水流淌,成年闰土浊流蔓延。一声“老爷”让纯正情谊随风而去,让真实美好的少年形象灰飞烟灭。在一个充斥着杨二嫂这样的“末人”世界里,又加上兵、匪、官、绅的逼迫,少年闰土必然走向成年闰土,而下降成农民“末人”。在小说的结尾,鲁迅把希望又寄托在“我”的侄儿宏儿和水生之间,比“救救孩子”来得更加温馨和富有人情味,鲁迅激愤的力度在这个地方减弱,他用深情的笔触塑造了宏儿和水生之间的未来时。“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成为童真人性的隐喻,和第一次的出现形成回还。这让人想起尼采的“永远回还”,人性的真善美其实在不同的辈分之间也是这样的。当人被异化时,就会出现《狂人日记》中所说的“难见真的人”,只有打破束缚,从儿童的阶段起就保持人的本性,人才可望成为“真的人”。尼采的人的精神由骆驼到狮子再到孩婴的过程,正是一个这样的“永远回还”过程。鲁迅寄希望于孩子很可能是受到尼采这个思想的影响,当然和李贽“童心说”也相似。
《兔和猫》弘扬了兔的天真烂漫,表达了对践踏生命的黑猫的憎恨。兔在这里是“真的人”的比喻。《鸭的喜剧》歌颂爱罗先珂纯洁善良,鞭挞驱逐他的强权者。由是看到,鲁迅的这两篇小说依然具有“真的人”的文化底色。
《社戏》在艺术结构上与《故乡》极其相似,是现在的成熟和过去的童年之间的对比结构。这是一种艺术策略,鲁迅要赞扬美好和童真的人。“‘我’回忆中的世界是一个儿童的世界,那个世界是美的,成年后的‘我’对都市戏剧的不满就是在儿时这个经验世界基础上形成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经验的世界,没有这样一颗童心做基础,他对这样的都市戏剧是感受不到不满的。他可能同周围那些都市观众同样迷恋于这样的演出。《故乡》的结构是《社戏》结构的转化形式。‘我’在回忆中储存了儿时与闰土的关系,他现在对故乡现实的不满,实际是在儿时感受的基础上发生的。如果没有儿时与闰土的交往,‘我’对闰土也无所谓满与不满了。”王富仁认为《故乡》的结构是《社戏》结构的转化形式。从创作时间的先后来看,《故乡》创作于1921年1月,发表于当年5月,而《社戏》创作于1922年10月,发表于当年12月,所以应该说《社戏》结构是《故乡》结构的转化形式。《社戏》起源于“我”对京戏瞒和骗的不满,于是就回想起儿时在绍兴看地方戏的情景。绍兴戏在此处和京戏形成有所偏重的两级结构,回忆儿时在乡间看戏就成为“我”自然的情感书写逻辑。和“我”一起玩的乡下小伙伴天然纯朴,不受束缚,没有那么多长幼尊卑观念,是源于乡野的“真的人”。鲁迅没有浓墨书写看戏,而是怀着浓情蜜意写了回来在船上煮蚕豆吃的情景。“我”喜欢乡野之趣及生存于这样的民间文化之上的真性情人,“我”很在意与性情自然淳朴的乡下孩子之间其乐融融的时刻,因为这里没有瞒和骗,摇船、赛船、看戏、煮豆,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那样天真活泼。这个世界是童真的世界,没有成人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我”在这里找到了精神的皈依,这个皈依是对“真的人”的渴望。
与《故乡》比较,《社戏》的转化在于具体内容的变更,其实质并无很大变化,都是通过对童真世界的怀念来抛却被传统习俗力量异化的人世。小说想在这样的两级结构中肯定了“真的人”,以“真的人”来对视成年闰土、杨二嫂这样的非“真的人”。
四、结语
“真的人”形象在《呐喊》中从高端呈现到回归民众,经历了从“狂人”、夏瑜、N先生到人力车夫、少年闰土、儿时玩伴的过程。“狂人”、夏瑜、N先生有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解构的倾向,但在这种高端的呈现中暗示了鲁迅对启蒙者、先驱者和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矛盾的深度反思,这个反思使“真的人”形象回归民众和童真。从“救救孩子”到人力车夫再到少年闰土、兔、爱罗先珂和故乡儿时看戏的伙伴,就是鲁迅向我们展现的“真的人”形象的环形回归路线。这个回归并不是否定启蒙者、先驱者和知识分子,而是要说明他们的存在首先要是“真的人”。在鲁迅看来,中国民众已经被异化,丧失了人的本真。“狂人”式的先驱者、启蒙者和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显得有些不着地气,所以第一要务是“立人”,只有通过“立人”,“沙聚之邦”才能转入人国。这里蕴含的深层逻辑是,暴露封建礼教的弊害,引起国人的注意,同时造就“真的人”,为启蒙者的出现打好民众基础,这才有“立国”的基点。
《呐喊》中“真的人”形象演变是上面所言鲁迅深层文化逻辑的文学化表达,这暗示了《呐喊》中各篇小说之人物形象的内在逻辑关系。鲁迅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中确保了《呐喊》的艺术整体性。
〔注释〕
①冯光廉也曾在研究鲁迅小说时说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超人”在鲁迅小说中大抵只是换了一个“真的人”的名称而已,并且还注释说这两个概念内涵上也存在差异(见鲁迅小说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327.),但他没有具体分析它们的关系。
〔1〕鲁迅.鲁迅全集(第 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田刚.《庄子》与鲁迅早期思想〔J〕.鲁迅研究月刊,2003(4).
〔3〕鲁迅.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4〕参见周作人:瓜豆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参见〔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M〕.秦弓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德〕尼采著,徐梵澄译.苏鲁支语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8〕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参见冯雪峰.鲁迅的文学道路〔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0〕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