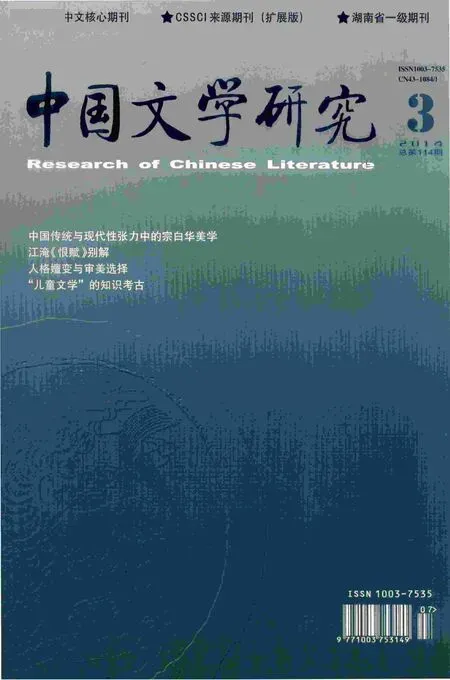革命、知识分子与个人主义的魅影:解读延安时期的萧军
王 俊
(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13)
当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党的文艺政策的形式成为延安文艺创作的最高指导原则,并建构起相对完善的规范机制时,对于一大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最后投奔延安解放区的左翼作家而言,他们必须要对自我的身份进行更为清晰的界定。与丁玲、艾青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接受思想改造,从知识分子、作家、党员和革命干部等多重角色间的游移到逐渐以党员/革命干部的角色来定位自我不同,1940年代的萧军与延安革命政权/毛泽东话语始终保持着某种限度的游离性。如果说在1942年之后丁玲、艾青等人响应党的召唤积极地改造自己,那么萧军则一直不愿放下“这可怜的‘自己’最后一块盾牌”,希望保有一个思想者、作家的特殊身份,以便成就一个新英雄主义者为解放人类而战斗的政治蓝图。萧军在延安解放区的一系列经历,既反映出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与革命政权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也极为微妙地揭示了身为左翼作家/革命作家的萧军思想中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成分。
一、“为人类而战斗”
造成萧军与延安人民政权之间若即若离关系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以鲁迅弟子自居的姿态、对鲁迅思想的阐释与继承。在1939年,还未举家奔赴延安之前,萧军已经意识到:“我本身应该是:鲁迅现实战斗主义的承继者……”到达延安之后,更是以鲁迅的学生和继承者自居。在萧军延安时期的日记中,鲁迅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之一。有时候他认为“在文学、精神上鲁迅先生是我唯一的先生”,试图把鲁迅的精神和毛泽东的政治理想融合为一,或者想将列宁与鲁迅合二为一,立志在文学上“做一个鲁迅式的,列宁式的战斗者”。在他内心最爱的三个人中,鲁迅被排到首位。有时候又以一种宗教的情绪崇拜着鲁迅,“(鲁迅)是我生平唯一所崇拜的中国人,没有什么人,能感动我如此地深,如此地长久,如此获得我毫无保留的崇敬”。有时候将鲁迅视作自己的精神之父,直言是“中国鲁迅这转轴人底承继者”,只有自己才能继承和发扬鲁迅的精神。有时候又视鲁迅为知音和最信赖的人。有时候透露出想超越鲁迅的想法,认为鲁迅代表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自己代表的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当处于逆境时,又常以鲁迅来砥砺自己,要将《鲁迅全集》作为自己的终身读物,来洗练和培育自己的灵魂。在延安,他积极参与成立鲁迅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两辑《鲁迅研究丛刊》,还经常布道式的将鲁迅的石膏像赠送给友人,以期能够广布鲁迅的精神。在关于鲁迅后期的思想究竟是一种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革命者的思想转变,还是对早期的革命思想的发展,萧军与胡乔木的分歧与争执,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萧军对鲁迅思想的阐释权的争夺。延安的一些崇拜鲁迅的年轻人甚至将其视作鲁迅的替身,连革命政权也赋予他“鲁迅死后唯一的旗手的地位”。不过,与中国共产党试图将鲁迅塑造成主动地靠拢乃至认同革命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的形象稍有不同,萧军则反客为主,强调党应该主动学习鲁迅的思想。在批评一些党员借党的关系为自己谋私利时,他主张“中国的党员应以鲁迅的书作为日常教科书”。他甚至强调鲁迅遗产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希望包括革命政权的高层领导人在内的每一个中共党员与非党员都能读懂鲁迅,并继承鲁迅的精神。在他看来,鲁迅的精神是一种毫不妥协的“为人类而战斗的精神”。而这种战斗精神的终极目的是使人摆脱做奴隶的地位。毛泽东、张闻天等着重强调的是鲁迅对敌——日本、国民党、托洛茨基派等——斗争的一面,萧军强调的是鲁迅的双向作战——对外(对敌人)与对内(对自我、对同一阵营)。在阐述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的目的时,他特意强调延安的“革命”和“抗战”中还存在“错误,不良的倾向,落后意识底残留等等”,因此也更需要“更深和更韧性的强力的东西来和它战斗”,鲁迅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正提供了这样一种强力。“为人类而战斗”的鲁迅精神成为萧军生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立足点。在他延安时期的日记中,“战斗”是又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尤其是在身处逆境时,常常会出现“我一生将要战斗到我停止呼吸底一天”,“一个战斗的兵士似的战斗着”,“战斗即是真理”等自我砥砺的表述。
鲁迅的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的最佳体现是他的杂文。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将鲁迅杂文所代表的战斗精神视为对(革命体制)外/对敌人的批判武器,而不赋予其对内批判的价值和功能。而萧军(包括胡风)强调的是鲁迅“横”站的意义,既重视鲁迅杂文所代表的对革命社会外部/对敌人的批判,又重视其对革命本身/对内的批判。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之后,萧军还专门撰文强调“我们不独需要杂文,而且很迫切”,作为“思想战斗中最犀利的武器”,杂文犹如两面刃口的剑:“一面是斩击敌人,一面却应该是为割离自己底疮瘤……”在《棲迟录二章》、《艺术家的勇气——棲迟录之三》、《论“文武之道”》、《论“遵命”》、《说“吉利话”》、《作家前面的坑》、《“胜利”以后怎样呢?》、《论“终身大事”》、《续论“终身大事”》等杂文中,萧军都批评了延安存在的诸多问题,这其中也包括部分党员和革命干部的不良作风。在其延安时期的日记中,很多文字与其说是日记,毋宁说是带有诛心之论的萧军式的杂文。事实上,对鲁迅的战斗精神解读上的契合与分歧也决定了萧军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之间的亲疏关系。
二、“爱”与“耐”
正是因为坚持“为人类而战斗”的精神,萧军在延安始终将自我定位为一位鲁迅式的批判性知识分子,总是秉承一种基于尊重和关怀个体生命尊严的批判立场。在日记中他大胆地宣称自己永远以一个人类的“控诉者、监督者、见证者、改变者”的姿态,在保持自我独立的同时,“反抗那些能残害人的事和物”。他将自己比作堂吉诃德,要替“一些小小者伸冤”,“要决然地担当起人类保护者监督者的担子”。有时又颇带有悲壮意味地宣称:“我不愿说我是上帝,但我愿说我是人类被残害的公证者,控诉者。”同时,他又要做一个人类的“拾荒者”与“拓荒者”,将那些被革命的无知所遗弃或者残害的人重新拾回革命的队伍中。比如对延安解放区仍然满腹牢骚的青年人,萧军认为领导者应当给他们“真诚的同情和尊重”,而不是采取严厉斥责等粗暴态度。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在战斗中犯过错误的革命同志,也宜用尊敬的态度对待。与那些始终呆在“保险柜”里“逞英雄的英雄们”相比,他们毕竟受到了血与火的“试炼”。总之,对于革命队伍中的同志,要多“爱”——尊重和同情——与“耐”——说服、教育和理解。他还呼吁对延安未成年的孩子多一点关爱。尤其是在各个机关做勤务的“小鬼”,他们正当的权利与合理的诉求不应被漠视,更不应当用奴隶式的态度对待这些未成年人。1941年11月,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的萧军向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提交“设立正规小鬼学校”的提议案。1942年7、8月份,萧军多次找在机关服务的小鬼们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处境和思想状况。他计划将来创作一篇关于抗战时期的小鬼们的童话。1942年11月8日,因为不满“文抗”总务部指导员程追打骂小勤务员,萧军与程追发生了冲突,甚至还打伤了后者。因为这件事,他被边区法院判刑6个月,缓刑两年。
最典型地体现萧军的“爱与耐”精神的是他对待王实味的态度。在1942年5月22日举行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萧军公开宣称王实味对革命政权的批评还是出自于“革命立场”。他内心并不认同将王实味视作敌人的做法。1942年6月2日,听说王实味要主动退党,萧军认为这一行为对党对王实味都不利。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充满同情地写到:“从一个党员立场来看他,他这是不对的事,从一个‘人’的立场来看他,那是应该同情。”同一天,他还为如何处理王实味的事情专门找到毛泽东。萧军向毛泽东明确表示,自己既不同意王实味的一些做法,也不同意当下对王实味的处置方法。在出席两天后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第二次对王实味的斗争大会上,萧军将批判者粗暴打断王实味发言的行为视为“像一群恶狗似的,伸出嘴巴向他围攻了……这简直是一种阴谋!”他忍不住站起来要求大会主席让王实味把话说完。会后,萧军向人表达了对这种批判方式的不满,又被人向“文抗”党组织汇报,并直接招致了中央研究院发出8个团体签名、108人署名的抗议书,要求他赔礼道歉。在1942年6月29日的日记中,他依然坚定地认为“王实味绝不是一个‘托派’”。而此时的王实味已经被延安文艺界认为是“政治上的敌人,文艺界的敌人”,被文抗理事会开出会籍,被称为“托派王实味”。同年10月2日、22日和12月15日,与萧军没有交往的王实味却突然三次“来访”。虽然三次见面留给萧军的印象不佳,甚至最后一次见面时王实味已经被开除党籍、被组织上认定“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但萧军仍然认为“他不是个托派”。萧军甚至还告诉王实味要学会与一些不良人事进行“韧性战斗”。1943年1月13日的日记中,对于已经盖棺定论的王实味事件,萧军谨慎地表示了怀疑,认为这种处置方法不是“正路”。乃至到了这一年4月15日,他将中央研究院当初对王实味的批判视为“诬良为盗”的行径;6月29日,他又将对王实味的批判视作“栽赃移证”。等到了1944年重读王实味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时,萧军还是认为找不出王实味作为托派和特务的根据。事实上,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对延安社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等现象的批判,与萧军“准备反攻一切丑恶的力量”的“勇气”是相契合的。在萧军的日记中,他多次以革命的立场批判党内的不良现象。
当然,萧军所倡导的“爱”与“耐”也包含了拆解革命体制下的等级秩序,建立人人平等关系的期待。在两性关系上,他主张从最基本的人性出发,给个体的生命欲求以合理的尊重。当听到一个女同志因为夫妻生活不和谐而主动提出离婚的时候,萧军反倒感到欢喜,因为他终于“听到了女人们正面的,本质的敢于提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这才是真正的大大小小的进步的征候(症候)”。他进而批评男性的专制、嫉妒、自私、暴力等“恶德”对女性造成的伤害,甚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自我,认为在自己身上同样存在这些“恶德”。在和家人“下放”到边区农村时,听说了几个农村妇女因不幸的婚姻而有谋杀亲夫之嫌,萧军认为她们原本是买卖婚姻的牺牲品,“从全盘‘人’底观点来看,她们是无罪的”。
萧军的“爱与耐”与战斗精神,均表现出萧军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怀。他要捍卫的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个体所应具有的生命的尊严与权利,包括独立、自由与解放。正如他强调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中……一个做为‘人’底尊严是不应该失落的”。这正是林毓生所说的以“对人的尊严的肯定与坚持”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人的尊严则来自个人至高无上与自身的、不可化约的(irreducible)价值。”“人的存在本身乃是目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任何政府、社会组织或别人的手段或工具。”这也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严格地说,萧军的思想并非纯粹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立场。因为他并不反对个人为了革命而作出应有的牺牲,但前提是必须尊重个人的尊严,个人作出牺牲的终极目的也是使更多的人作为有尊严的人而存在。在他看来,这样的革命才是“一种真正的人性底解放和提高”。
三、“家族以外的人”
对个体尊严的坚持让萧军始终将自我定位为一个坚持独立的现代文化人/知识分子/作家。在1939年5月15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文人们总要附属于一个阶级,作歌颂的喇叭手,总要附属一种不正的力量把自己抬起来,是很少有着仗着自己艺术能力的自觉,可怜!”“文艺靠着政治力量捧场,决不会有好的收获。政治应消极地辅助,还应该让作家自己行路。”他将自己比喻成一颗穿越庸流星群的独立的彗星。他将那些用文学阐释政治概念的作家称为“江湖医生”,他们的创作只能是一种“乞丐行为”〕。“行乞”显然是一种失去尊严的生命存在。
1940年到达延安之后,坚持个体的尊严也成为他界定自我和革命政权之关系的重要支点。比如,他认为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更要注意“勿甘心丧掉自己的人格和独立的精神,变为浅薄的软骨病者或装甲的乌龟”。他甚至暗示,革命政权不应当像旧的统治阶级那样将知识分子视作门客。
对个体的尊严和自由的坚持还典型地表现在萧军和党的关系上。据萧军的妻子王德芬回忆,1940年代初,毛泽东曾经劝萧军入党,但萧军拒绝了。他认为自己身上的“个人自由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太重,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是受不了束缚的,最好还是留在党外。事实上,在入党的问题上,萧军在思想上经历过反复的斗争。1941年7月28日,听到组织部征求艾青入党的消息时,他也有了入党的冲动,但马上又否决了这一念想。他自称“我不能有任何锁链,那会毁灭了我自由突击的天才,蒙蔽了自己”。8 月 1 日,甚至设想入党后自己会很快升到高位,但又会“庸俗了自己”,“在文学上毁灭了自己”,并决计“我还是在文学上行走吧”。8 月 8 日,友人劝他入党,他认为现在还不需要,并给出“我是不应和任什么(人)‘结婚’的”理由。8 月 12 日,在和毛泽东、陈云谈到入党问题时,他再次以婚姻为喻:“我是不乐意结婚的女人。”1942 年 5 月 24 日,当友人问他何时入党时,他回答:“我要走自己的路,为了不杀死我自己。”在目睹了王实味受到批判后,他更是决定“一生决不加入任何党派,以文学为生”,一个作家不一定非要入党才能革命。到这一年的9月份,他又生出自己爱从事政治军事工作,却间接地从事了文学工作的感慨。不过一想到自己决不被人领导,所以决定还是走“自己的(文学)路”。9 月 17 日,他告诉吴奚如:“我决不想做个党员。”10月23日,因为主编的《文艺月报》被停刊,他又生出“绝对是不能为任何一个党员的”想法。10 月 25 日,在与朋友们的交谈中,他表示从事文学创作的话,自己就不会入党,“入党我就完全从事政权工作”。是否入党取决于是否对革命更有利。但内心却又以自己的价值还没有被党所真正了解,而仍坚持走文学的道路。到了11月份他又计划找毛泽东谈入党的事情,甚至极为自信地认为自己入党会给党带来一股新的血液和新的气氛,入党可以更好地战斗,“传布鲁迅的影响”。不过马上又吐露“但我还不乐意为一个党人却是真的”。当妻子劝他入党时,他自比花果山上的孙猴子,既不愿做弼马温,也不愿做陪唐僧西天取经的孙悟空,他要尽可能地逃开“金箍咒”(。到了1943年5月1日,把《共产党宣言》又读了一遍后,他坦承自己时时都有做一个党员的冲动,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对延安“抢救运动”中滥用私刑的不满,他甚至生出“无论如何我不能做一个党员”的想法。
1944年3月初,正和妻女在延安农村过着“下放生活”的萧军主动向人表明自己愿意回到延安,目的就是“准备入党”。他的这一想法连听的人都感到吃惊。回到延安后,萧军主动向党校副校长彭真提出入党的要求。当彭真告诉他,入党就要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的时候,他再次选择了继续留在党外。此后,刘白羽、胡乔木、彭真等人又先后跟他商谈入党的问题,他还是觉得无法遵守党的纪律而决定留在党外。1948年在东北解放区,他的入党申请已经被批准,但是因为《文化报》事件而遭到批判,被定性为“反苏反共反人民分子”,成为阶级敌人,致使他始终没有过上组织生活,成为所谓“家族以外的人”。
萧军将自己和党的关系比作一对恋人,他爱她却不能嫁给她。一方面,他明确表示拥护党,认为它代表进步的力量。同时,他又在一些党员的身上尤其是自己所接触到的“一般所谓政治文化人”身上发现官僚主义、市侩主义、过左的政治倾向等,这反倒使他以一种不能同流合污的姿态拒绝成为他们的同类。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在一个众声合唱的队伍中,他们对于那些发出不同的声音始终要么纠正,要么消除。萧军认为自己的独奏或者噪音对于整个合唱队的“革命进行曲”是无害的,“甚至是必要和精彩的”。只是因为这独奏或噪音“缺乏(对)高度革命音乐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就不被容纳和理解。与丁玲等党员作家将党员、革命干部和作家等角色统一于一身不同,萧军倾向于将这些角色分开看。在这一点上他和王实味的观点类似,认为作家和政治家是不同的,“他(指作家——笔者注)不能任命,也不能借光,更不能以别人底牺牲铸成‘自己的’成功”。尤其是当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何其芳、周立波、舒群等党员作家纷纷发表文章主张“必须改造自己”时,他看到作为党员的作家要自己割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要“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缴纳一切武装”,作家的身份要绝对地服从于党员的身份;党员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中央的立场”。这对他而言意味着作家特殊性的泯灭。他特意将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中引用考茨基的一段话摘抄在日记中,以示这种特殊性的重要性:“知识分子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他个人的能力,他个人的信念。他只凭靠自己个人的品质,才可获得相当的意义。因此,在他看来,自己个性表现底完全自由,是顺利工作的第一个条件。”他坚持将作家、党员和革命干部的身份分开,“工作时就是个工作人员,写作时就是作家,作党员时就是个党员。对于工作要求效率,对于作家要求艺术完整性,对于党员要求纪律执行”。他认为政治家注重的是眼前的功力,思想者关注的是未来,艺术家看重的是历史。他更希望保持一个思想者和作家的身份。尤其是经过抢救运动,他看到的是政治工作者的“功利性、辩论性、无情性”,这些从文学家的角度观之,全是病态的表现。他抱有的是一种通过文学来影响、监督、改造或指导政治的启蒙主义的文学立场。显然保有知识分子/作家的个体性/独立性、创作的充分自由和作品本身的独特魅力是萧军最终选择做党这个“家族以外的人”的主要原因。
萧军与一些党员作家和党员干部之间发生的冲突使他对党抱有一种疏离感,但他又从大局出发抱着维护党的态度。1943年6月份的日记中,两次记载了党外人士向他抱怨党内存在的不良风气时,他都劝说对方“把整个党的态度要和个别党员分开”,“把个别党员不正的行为意识应与党基本的态度分开”。他甚至要求这些党外人士能够理解部分党员的苦衷,要反省自己。正是出于爱护党甚至帮助党的目的,他又将对党内不正之风的批评视作一种真正的革命行为,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革命责任与义务。过高的自信与过度的自傲——自认为是个战略指导者、具备马克思、列宁、鲁迅、托尔斯泰等人的部分伟大品质、有释迦牟尼、耶稣、摩西、默罕默德等对人类的负责精神,让他产生“我对中国共产党起了改造火种的作用”。他甚至认为自己应该以无产阶级为立场、以共产主义为目的而担负起批评各个党派的任务。这也决定了他时时刻刻挣扎在入/不入党的矛盾斗争之中。
试图保有作家的特殊性而最终选择做“家族以外的人”,并不意味着萧军要走纯文学的道路。事实上,他也承认自己“是一个政治性最浓的作家”。萧军的政治性不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性,而是他将文学、创作本身视为“更大的政治”。他自视甚高,“我始终是文学中的‘王’”,“建设一个文学的国,和建立一个真正的国一样,它是应该不受任何谁的,某种力量的压迫干涉,虽然他可以有权利批判。”在综合了《联共党史》、《圣经》、鲁迅、列宁、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的思想后,这位文学的“王”又提出要在文学的理想国中建立自己的精神体系:新英雄主义和新希腊思想。按照萧军的解释,所谓的新英雄主义最核心的要素是:为人类(以示与“为自己”的旧英雄主义的区别)、争取第一、强健自我、敢作敢为、不断战斗、敬爱同志、敌友分明。尽管他对新希腊思想的解释比较模糊,但从只言片语中大致可以推出,新希腊思想的核心是培养一个获得充分解放而高度发达的个体。无论是新英雄主义,还是新希腊思想,萧军都将起点放置于个体身上,从个体/个人走向集体/阶级/党,最后走向人类大解放。人类的大解放意味着每一个体都获得了充分的解放。因为追求的终极目的是人类解放,萧军甚至将自己的新英雄主义和新希腊思想视作与共产主义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更新阶段的发展”。因此他宣称自己既是共产主义者,又是新英雄主义者。这也是他所理解的“最浓的政治性”。总体而言,萧军的文学理想还是典型的启蒙主义。他是通过文学来实现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体系,最终的目的还是改造国民性,只不过新英雄主义和新希腊思想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在萧军的文学思想中,人永远都是目的而非工具。小而言之,文学是关注人的生命尊严,大而言之,文学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他并不否定人的阶级属性,但反对将人的阶级属性化约为一种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工具。在1943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第三代》中的第三、四、五、六、七部以及第八部的部分章节中,萧军似乎表现出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有意疏离。在这部表现东北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小说中,他没有将农民的反抗升华为集体意识的觉醒。《八月的乡村》中陈柱司令、铁鹰队长等对革命有着明确认识的人没有出现,只有类似于唐老疙疸的村民:优柔寡断的王大辫子,善良乐观的林青,朴实憨厚的宋七月兄弟,曾参加过义和团的井泉龙,血气方刚的土匪刘元等。这些农民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反抗意识也更接近于路翎的“人格力量自发性内因论”,而非一般左翼文学中的阶级意识。小说的结尾也没有被设计成农民彻底觉醒,在革命者的带领下冲向地主之家的经典画面。当有人从左翼文学正统的立场来批评这部小说时,萧军反倒认为自己的立场是:“从最高度的‘人生’看人的。”显然,“最高度的‘人生’”是超越了阶级意识的人类意识,他也有意识地用关注个体的生命尊严的立场取代了阶级的立场。在1948年3月9日的日记中批评一出名为《血海深仇》的话剧公式化、脸谱化,其源头是《白毛女》,“我最讨厌这戏(指《白毛女》——笔者注)的”。在1949年7月2日的日记中批评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艺术上的失败之作,“她(指丁玲——笔者注)的艺术才能被僵化的政治理念牺牲了”。当作家和作品变成简约化的工具而存在的话,也就很难“用艺术的深度来擒住永恒的人性”。
四、结语
1940年12月17日晚上,萧军在给胡风的信中提到在延安的好处:“第一不愁吃穿居住;第二不必跑警报;第三不会有意外的‘横灾’,夜间可以不闩门安安稳稳睡觉。”但他又马上说:“不过,我还是觉得没有在这里生下根,总想要跑跑,虽然明知道没地方可跑,而且目前不能跑,也不需要跑。有的(一)些人一到这里就生根了,而且预备发芽下去……”因为将自己定位为“战斗的士兵”,要严格地站在工农大众和共产党基本政策的立场上,和一切不良风气作斗争,再加上其嫉恶如仇和过于耿直的个性,萧军与许多作家乃至与不同的机关单位之间都曾经发生过摩擦。在延安时期的日记中,他多次表达了离开延安的冲动。在延安无法找到归宿感的萧军,在一位研究者眼中更像是一个“永远的精神流浪汉”。精神上永远的流浪意味着个体拒绝加入到秩序中去,拒绝成为秩序中一个被给定位置的局内人。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也意味着他永远无法“长大”——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蜕变为党的战士。萧军自己的话也许揭示了他内心的一份执念:“我是集体主义前提下,一个顽强的无害他人的‘个人主义者’。”显然,无论他如何宣称自己可以做一个“非党的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的作家”,如何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萧军割舍不掉的还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存在的自由与尊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永远作自己的主人,自己的战士”〔1〕(P395)。
〔1〕萧军.萧军全集·第19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2〕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3〕萧军.两本书:“前记”(一)〔N〕.解放日报,1941-10-13(4).
〔4〕萧军.萧军全集·第11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5〕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N〕.解放日报,1942-4-8(4).
〔6〕萧军.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N〕.解放日报,1941-10-21(4).
〔7〕萧军.论“终身大事”〔N〕.解放日报,1942-3-25(4).
〔8〕林毓生.鲁迅个人主义的性质与含意——兼论“国民性”问题〔J〕.二十一世纪,1992(8).
〔9〕林毓生.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A〕.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10〕王德芬.我和萧军风雨50年〔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11〕萧军.萧军全集·第 20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12〕丁玲.丁玲全集·第7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3〕钱理群.天地玄黄〔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