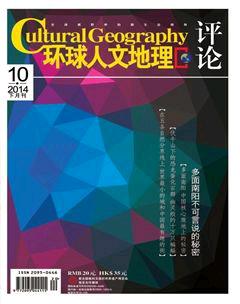浅析吉林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发展形势
李嘉平
摘 要:八十年代至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通过比较吉林大学现当代文学学者的研究著述,探讨前后变化的各个方面,以及对造成变化的诸般因素进行分析。
关键词:吉林大学;现当代文学;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作为文化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领域,文学事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与文学创作的勃兴相呼应,文学研究也有了巨大的变化。本校文学院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本文将通过对八十年代至今本校现当代文学学者的部分著述的探讨,探讨时间前后的差异和造成差异的因素。
老一辈的学者们,大多非常重视写作的完整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地方:一是在对作品力图进行全方位的评述,对作品的情节、人物形象、思想内容等方面,都希望做到面面俱到。例如在刘柏青教授的《<子夜>的成就》一文中[1],作者便从情节、人物、思想价值等三个方面依次对《子夜》的成就进行阐述。二是在对作家、学者的评述中,常常致力于围绕所评述的人物建构体系。例如在刘中树与张福贵教授合作的《论鲁迅辩证思维的逻辑系统》[2]中,两位作者将鲁迅的思想进行整理,建构起了既带有鲁迅个人特色又与马克思主义共通的思维体系,在建构这个体系的过程中尤其注重其矛盾统一的特点。三是特别注重对作家、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具体而言也就是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意义。例如在金训敏教授的《论鲁迅的“拿来主义”》[3]一文中,三个章节中有两个即为探讨“拿来主义”之产生背景和现实启示,而内容约占全文一半。
老一辈学者们的这些特点,可以在许多先贤身上寻得滥觞。追求对作品的各方面进行面面俱到的评述,不正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吗?在有机整体论中,亚里士多德就将文学作品看做由多种成分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他为悲剧设定了六种要素,作为评述悲剧的标准。在后世无数学者的文学评论中,都可以寻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子。然而,正如同文艺复兴后西方人对亚里士多德文艺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趋向僵化[4]一样,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的对于完整评述作品的努力,也时常忽略了作品作为整体的有机性,体现在具体评述中,就时常表现为形式上千篇一律,以及社会功能完全凌驾于艺术价值之上等现象。
而围绕人物建构思想体系的努力,也可以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中寻得某些源头。建构完备的圣人,在圣人身上构筑现实伦理与形而上学为一体的理论体系,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特点。如文王、周公、孔子等圣人,其道德与政治理念,和天道相通,形成了庞大的体系。而建构人物的努力,与当代西方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相结合、碰撞的过程中,产生了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一种现象:圍绕“现代”作家的建构。这里的两个关键词是“现代”和“作家”,区别了这种建构与前代的差异:这种建构并不是一种在回溯过往遥远的历史中完成的虚设,所处时间就是现代;对象并非是贵族、士人、教育家等,而是职业性相对明显很多的作家。简单来说,部分作家(像鲁迅和郭沫若等)在他人的评述中有时变成了思想家乃至哲学家。这种改变,必然是受到了当时文化权力和现实价值需要(比如发挥文化楷模的教化作用)的推动而形成的。然而我们不禁要多问一句,为何思想体系的建构就是文化权力和现实价值发挥所需要的?是不是因为建构体系,就是制造着拉开外围与权力的距离的宫殿呢?
重视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意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所讲的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相呼应,致力于探究现实与文学的因果关系,在这种努力下,研究实践常常更集中于文艺社会学领域。
总体来说,老一辈学者们的著述,相比于今天专业的科研作品,更加注重叙述知识和完整评述,重视现实与文学的一致性。这个总体的情形和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方的文学研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不过,也正如西方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发生了重大转向,当代学者的文学研究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其内容也与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学研究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将研究转向作品本身,并且相对于之前的“完整”,日趋细化,寻求作品其他社会思潮的联系。毕竟我们的文学研究就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步步发展的,就是整个现代化,也是以西方发展为蓝本。西方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益感受到人在世界中的尴尬处境,这一点深刻体现在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中。同样,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者们在处理作家作品与世界的关系时,也转向了对人的关怀。这些变化,必然也在本校的现当代文学学者身上体现出来。
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外的各种社会思潮对作品进行研究,不太注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整体性”,在当代是普遍的。在白杨教授的《<第九个寡妇>:原型意象与讲述方式》[5]中,作者运用西方的原型批评方法,对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评述,从情节模式、人物、环境的意象分析中探讨象征意义。这种变化显示出文学日益凸显的独立性。文学不单是政治的宣传方式,也不是哲学的载体,也不是社会学的实验工具。情况反了过来:文学的创作和译介在思想解放的环境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空间,而文学所向人展示的广度和深度也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先前的研究方法已根本无法应用于这些雨后春笋(其实也无法对“雨前”和“雨中”的无数作品进行有益的研究)。因此,借助各种社会思想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和解读便是一种必然,换句话讲,文学成为了被伦理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诸多学科进行阐释和解读的对象,而不再处于附属品的地位。
当人们看到文学的无尽的深度和广度,也就随之认识到了:文学作品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与文学作品的无限可能性相比,作家成为了带有很大局限性的存在。因此,作家在研究中也就逐渐成为了次要的存在。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围绕作家或研究者进行思想体系的建构,对于文学自身的发展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而且也会落于空疏,也不可能展现“真实”的作者)。文学毕竟不是思想,更多需要感受而非认识。研究作者,说到底还是应该从阅读文学作品和寻求与作者的共鸣出发。而感受是片面的,作家与读者(研究者)不可能完全契合(这也表明围绕作家建构思想体系是不可行的)。因此,研究作家的努力,也就转向了对作家精神世界中的某个方面进行的深入探讨。在王学谦教授《反传统——自由意志的高峰体验》(与张福贵教授合作)等文章中[6],作者从鲁迅的反理性观念的角度入手,探究鲁迅思想与意志哲学、存在主义等和反理性话题密切相关的思想的关系,进而讨论鲁迅所描写的人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是从单个方面研究读者,但是只要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自然也就具备了广度。
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当代学者与过去相比(当然,并不是先前的学者就忽略了人本身,只是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往往不得不将人文关怀搁置一边),在文学研究中更为重视人文关怀,尤其是对人在世界中的孤独、扭曲、异化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也是一个普遍现象。例如在张福贵教授的《人性主题的畸形呈现》和《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中[7],作者从张资平小说中的性爱题材中探讨个人解放、男女权力、两性关系异化和社会对人的压抑等在现当代日益突出的问题。人文关怀对文学而言,不仅与其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且也是文学作为人文学科所应承担的道德义务。一切的存在,包括文学在内,都具有伦理性。伦理性是文学维系于现实世界的桥梁之一:毕竟,文学的流传与发展,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它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的伦理功能;反过来讲从文学的超越性的、形而上的价值看,如果没有具体的价值体现,广大读者也就失去了登堂入室的必要途径。有不少类似于“为文学而文学”的观念,诸如创作上的唯美主义和阅读研究的享乐主义等。不可否认这些观念是严肃的,但是正因为认识到它们是严肃的,我们才得以看到:它们的实质,就是将文学看做封闭的存在。但事实上,没有任何文学能在自我封闭中(也不存在自我封闭的文学)生生不息。重视文学学科的道德责任,在提倡个性解放的今天,应该是需要得到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