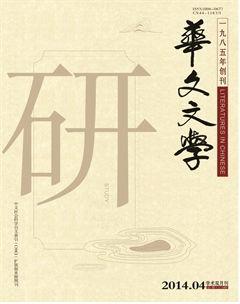肌质·节奏·抒情空间:现代汉诗感知形式初探
关天林
摘要:“肌质”指词语间的组织,“节奏”指肌质组织衍生的律动,“抒情空间”即情意脉络的动态布局。一首诗便是三层构架互动而成的有机整体。本文并不意在归纳一些“诗法”、“诗型”或追溯形式的历史变迁,而集中以古典诗歌美学为参照,通过由肌质到抒情空间的结构分析,展示现代汉诗美学形态的趋向,为开拓新路的现代汉诗提供一个观照的角度。现代汉诗重复探索语言肌质,寻求自身成为开放、可塑、富张力的经验载体。这种运动姿态仍是抒情的节奏,同时也是体验的、“遭遇”的节奏。现代汉诗是古典诗歌这舞台的延伸和改造,但舞者的舞姿却已跃进了新的演出空间,其开发新感知形式的“经验”对当今汉诗的创作和分析有一定借鉴作用。
关键词:现代汉诗;感知形式;肌质;节奏;抒情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4)4-0061-10真正的作品不存在于确定的形式,而存在于一连串试图迫近它的努力。①
——伊塔罗·卡尔维诺《给下一轮
太平盛世的备忘录》
诗并不载什么道,除非这个“道”是解释为自我整体的感性活动。②
——李英豪《论现代诗之张力》
创新作品指出新的发展趋势,经典则把已有可能性发展至极致。③
——陈国球《文学结构与文学进程——
布拉格学派文学史理论评介》
古人诗格诗境,无不备矣。若不能自开一境,便与古人全似,亦只是床上安床,屋上架屋耳,空同是也。④
——方东树《昭昧詹言》
一、引言
本文涉及对现代汉诗抒情形式、经验方式的梳理,主要思路是以肌质、节奏和抒情空间三层规模各异而环环相扣的分析媒介为经,以一系列诗作为纬,以古典诗歌美学为参照系,务求展示出现代汉诗作为感知形式和古典诗歌传统后的一种新兴诗体的特质与可塑性。限于学力、材料和篇幅,本文追求较深切的刻画与呈显,而非理论化的综合和概括。另外,由于是共时层面上的研究,故不采追溯发生和发展的历时角度。
本文之作,实源于一些论述的启发,包括奚密《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视现代汉诗为重整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新有机体,在文化身份、语言观念、结构意识等方面探讨现代汉诗对古典诗学的继承与转化;高友工在《唐诗的魅力》一书以及《中国语言文字对诗歌的影响》、《律诗的美学》等文章从语言法则、节奏形式等方面对中国内在化、心象化的古典抒情美典作出仔细梳理;葛兆光《汉字的魔方》立足关键现象,剖析中国古典诗歌图式的形成,论证了宋诗与白话诗在更新诗歌语言的思维上的共通性;罗青《论白话诗》认为白话写诗保留汉字本身特性,阐扬抒情传统,其文法的分析性又有助开拓新领域;叶维廉《中国现代诗的语言问题》分析诗歌语言变化所带来的对传统手法的“现代”转化;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对诗作为有别于陈述语言的造型语言所创造的特殊经验方式与有机生命形式的强调;桑塔耶那(Georg Santayana)视美为感知现象客观化的积极判断过程,又重视形式启导出感知客体的作用;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以现象学方法追随诗歌由私密空间趋向未定空间的存有;尼尔迈纳(Miner, E.)《比较诗学》认为抒情诗本根是共时呈现,抒情符码是强化共时呈现的手段,这套符码存在于作品、诗人观念、读者和历史里,其变化可用于文学史的考察,个别诗人也有不同强化风格;还有布拉格学派紧扣文学结构与文学进程的辩证关系的文学史理论。
有赖以上种种启导,本文打算针对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汉诗的转折和转型这一棘手的问题,再做一些功夫。当然,本文只能算是表层的、起步的探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本文的材料范围。第一,分析对象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作为主。第二,由于想引用全诗而篇幅又有限,这些诗作大部分都是几行到十几行的短诗。第三,分析对象之中没有什么名作,只为方便说明现象,点出其大体趋向,此外,不用名作或能减少先入为主的定见,有助我们更直接地投入对作品的感知。第四,历史上有所谓白话诗、自由诗、小诗、格律诗、象征诗和现代诗等区分,形式上有格律诗和自由诗之分野,语言上又可分为追求精细,如朱自清所谓“增进文字尊严”的象征派诗,⑤以及标榜大众化和口语尊严的诗——种种分期分类和背后的问题,本文都会暂且悬置,把焦点放在现代汉诗的基础感知形式之上。
二、古典诗歌美学的化境:王维《终南别业》
本文会先分析王维的一首家传户晓的名作《终南别业》,藉此建立一个关于中国古典诗学的参照面。只选一首诗作代表,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本文重点只在通过初步的对照,把握后起的美学形态,暂不涉及转换内部的历史现象的交错脉络,故只能集中一首而且必然是读者熟悉的一首分析,以提供论述基础,方便下文,稍稍把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符码定型下来。
除此之外,分析这首诗也有种种理由。作为律诗,它既显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典型的独立存在之坚实性和内向性,又处处有所超越,在严密的架构中指向更大的感通境界,即某种天人合一、周游往复的圆转运动。它让我们感到,律诗,以至中国古典诗学本身,是以言语道断的“道体”所蕴涵和保证的。当然,选析它并不表示只有它达致化境。至于为何采用律诗,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闻一多说紧凑、精严的律诗与西方的十四行同为最佳抒情诗体,辨清律诗不但得见中国诗之真精神,也得见中国人均衡、浑括、圆满之理想人格;⑥朱光潜指唐以后的词曲都是律诗化身,后者影响甚至波及散文;⑦用高友工的说法,就是因为抒情精神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主题,律诗则以一种“意的形构”体现了抒情精神的理想境界。⑧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综合历来一些赏析,⑨大抵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化律为古、化律为意,即重视其“化”;一个是化中合度,即重视其“度”。从事态发展的角度看来,此诗的转合其实仍很明晰,基本是直叙,另一面是态度的逐步显现。另外,从“主题─评论”的句法观点看,此诗不但每联上下句存在张力,每联之间也隐含张力。⑩如次联,上句引起期待,下句竟以“胜事”带过,而且“空自知”,自我消解;颈联,上句由时到空,由行而止,下句由空到时,由止而动,看似对映,实际上已化被动为“心与物游”的自由。在整首诗中,首联是意愿实现,颔联却是实现后的复杂心理,其中不无孤独的遗憾,颈联相当于突破了困境,又代表了意志真正的体现,尾联一方面连接颈联,也可说是前三联的涵摄与超越:事出无常,心也付诸偶然。于此可见此诗流动与张力之“度”,但这种绵密中见弹性的互动局面也可反过来说明此诗突破了诗联的锁链的浑然意态。
全诗最瞩目的颈联,直接把握了一种圆足的姿态,提掇了直线开展局面,而进入横向扩延的生命力。若说首两联还是多少有点概念化的事件,此联便是纯粹的体验,也是感通的发生源,容许不断回溯重演;道境、化机,便是从这意义上说的。更难得的是,此联没有像一固化形象突出于全诗之上。这一生动的动作,始终是那悠然自得的主体的演出一部分。主体只是直道出自身的体验而不经意显示了体验中最鲜活悠久的内质。这首诗既是追忆,又是生活态度的宣示,主体只是分享他是怎样体验生活的。分享到五六句可说已很圆满了,于尾联补写一笔,就像是志得意满时的余裕的表现。
尾联也是“意体”化生的一部分,然而,颈联才是律诗最不像律诗的“化机”,尾联无可避免标志着律诗的格局。它在一气回荡上尽了它的本份,而律诗讲的正是本份,“位”,而同时又容许“势”的变化。此诗的突破除了流水行云一样的高古浑然之态,便是不断重回那体验最丰盈的发生源的势。此势减少了律诗由固定旋律、平仄安排而造成的封闭感,而转成开展流动的局面,又形成一定的逆流,让整个过程最真切的“意义”汇集凝止。“一气相生,不分转合,而转合自分”,{11}此诗还律诗以变化莫测,又还变化莫测以律诗。
高友工认为抒情美典就是一种内化心象的形构,诗人成为其中的间架和原动力,但由于自我无处不在,诗人反退隐到诗外,只剩下客观化的内在心境,就像以心眼观察内景,时间亦收缩为此时此刻。{12}据此,高友工指这首诗牢牢地支配了一个必能回归的理想世界的中心,一种内景自足地通过诗人意志屹立起来。{13}诚然,王维此诗有把内在心境孤立起来的趋势,但也保存展布的趋势。内景没有成为一种架构,而是始终保持“当前时刻”的动态。
王维的诗被称为“诗中有画”,很大程度是因为其“无我之境”。丰富的画意是以自然造化而非人物为基础的,但在诗中要求彻底无我却又不可能,充其量只是抒情主体不占重心,或处于相对淡静的位置。“我”的轻重显隐位置之差异便造成种种意境。{14}王维此诗的无我之境毕竟也是营造出来的,营造之迹虽被减至最浅,但全面贯彻的无我之境也倒映出摄受的心眼无处不在。这是悖论,但不代表失败,抒情主体是无法绕过的,但它却可能承载无我的体验,或者说,无我的体验也可能反照深情的目光。从无我与有我境地的自在共生的关系这角度看,王维不单驾驭了形式,也超越了它,可谓“嗒然遗其身”。
总之,此诗深入律诗的外形和心象的图式而创造出生气盎然的特殊经验形式,正如纪昀所说,是经过绚丽的平淡,是盛唐诗的“归墟”。{15}朱光潜引“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代表六朝律诗初兴时尚巧丽、求尖新的时代精神,{16}“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便可说是律诗的反璞归真。
但当把这浑然流动的生命形式分出了转合、析出了法则,它便有可能约化为新的图式,这首诗便可能成为以后诸多膺品的间架和原动力。中国艺术的极境是自在俯仰的游,而不是观,游出于观,又把观提升至气或意的境界。但若主体本身没有自在浑厚之气/意作原动力,所谓游观,终是画框。更重要的是,读者的理想鉴赏状态也是游观,如徒具虚形,感知反而局促,然而经典化或定型化的抒情符码尚存,便容易令观者产生认同错觉,其实他们可能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地处身狭窄的画廊。
三、现代汉诗感知运动的基本轮廓
有了王维那么一首无懈可击的作品做制高点,好像让下文的分析有点为难。其实不然,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律诗,和现代汉诗虽不能截然二分,但两者毕竟处于两种文化意识、美学观点和创作体制之下,现代汉诗实际上是另觅起点,正如奚密所言,历史地看,现代汉诗的成就是在于“另辟蹊径”。{17}
我们可先用两首诗勾勒现代汉诗感知形式的轮廓。李长之,是文艺批评家,也是诗人。他在《语言之直观性与文艺创作》指出艺术的本质是在幻想力的统制中,通过艺术工具和手段,表现一种内在体验,也让读者观众感受到这体验;艺术家孜孜以求的表现的“直观性”,便是幻想纳入活泼逼真而指向确定的活动。内在体验并不是纯粹的,它必然受表现工具制约,对诗人来说,语言文字便是他必须通过的体验。{18}语言的直观性在于唤起种种情调,启示情境和内在事件,创造一个与我们情感生活相回荡的生动幻象;{19}除了由情调唤起直观的诗,也有由直观唤起情调的诗。{20}那么,以下的一首《雨水》是如何通过语言唤起内在体验的?情调与直观如何互相感召?
院子里泥泞着,33/小小的一方水,33/来一个微雨的滴,331/便努力着作出沦漪。422/水纹缓缓的扩张,232/它也许正在幻想322/处在清净的宽广的233/小溪。2{21}
在诗行旁标示“音顿”有助初步的观察:第一到第三行是稳定进行的感官描述,统觉在形成并唤起了情调——“滴”字尾突显了“小小的”一方泥水所作的“小小的”挣扎。此后音顿上一直相异相从。最后那个2是跨行出来的,33相续的一段暗示着无限的开展可能。“宽广”形容小溪,也代表幻想的扩展;“清净”在发音和意义上都意味着稳定平和,“宽广”却包含拓开的力度和胸襟。小溪二字虽是尽处,韵脚也回到最初的“滴”,彷佛应和着沦漪最后消失的结局,但我们知道直观持续唤起的情调已唤起了新的直观。虽然幻想不能无限制地延伸,正如院子仍是院子,一方水不能化身万千,但情境经过再协调而添上一层流动性;最后的直观形象同时包含了观者的同情之眼、挣扎的涟漪,以及理想中的、自由开放的小溪。
王维的诗当然是通过了语言的内在事件,但其存在也是一种直达核心、内外俱化的姿态。语言的体验以完成和保持“意”的优位性为本旨,既“立象以尽意”,又“得意忘言”。《雨水》没有这种圆融,它由始至终都在通过语言,我们看到语言逐渐获得直观性并尽力与之保持透明而充实的联系的那道痕迹:在语言中(一方水),“幻想”被召唤,语言继而在幻想的召唤下召唤出一件活泼而有确定指向的内在事件(小溪)。《终南别业》的生动在于言语道断后的澄明,《雨水》则因留下了一连串感召的语言事件而鲜活。
我们可再看另一首诗以进一步观察那语言体验的特质。这首诗在题材和情调上都和《雨水》大相径庭。
陈湖《马路口》{22}
西北风霸住马路口,3/古老的城缩一团觳悚,2/裸女广告留音机的歌1/唤不住路人的伫足。2
柏油路像死蛇翻白,2/冷月漫布一层忧郁,2/中年绅士像丧家狗3/把脖子钻到皮领里。3
夜游女也困守残火,2/警察失了盛世的高傲!2/从远方:一排又一排2/西北风试新磨的刃。1
我们可以注意标示在旁的“煞尾”,另外还有跨行的安排。“煞尾”不外三种,普遍地说,一字尾较突兀有力,二字尾最常见而有道白味道,三字尾带点摇曳的吟唱腔。其中以相续节拍迎向那个“刃”字的发展最特异。诗的另一规律是每段三四行实际上都是一句的跨行,每段也因此可分成前后两半。这种跨行规律引起我们对第三四行的悬宕变化效果的注意。
诗的首两行可说是一种双向运动。一方面是由“马路口”到整座古城的扩大,一方面则是古城“一团觳悚”的收缩,共同突显西北风的肆虐与宰制,产生了整座古城瑟缩起来的错觉。第一段也奠下了前半段以静态为主,后半段强调动态的模式。关键是第三段,整首诗的对位结构已完成,每段的每一行、前半后半,均互相映照,逐步推演。由路口到路上到困守,是时间的推演也是空间趋于封闭。警察本是在街上最富行动力的,但只以毫无动词的一行总结,与困守无异,暴虐的力量已可谓彻底包围。这些结构趋势加起来,就是这个古城颓唐下去,坐以待毙。最后那三四行的跨行是最明显的,张力也是最强的,“一排一排”的霍霍刀声彷佛都聚于那个“刃”字之上。
《雨水》和《马路口》所营造出的某种感知空间,在短小的范围内缓缓展开,时刻隐藏着变量,又贯彻着一种前驱力,寻找着感知空间最丰盈的完成时机。《马路口》较结构化,前驱力和变量的关系更复杂,结尾也是一种过渡的、戏剧性的、屏息以待的凝止。
奚密借分析废名的《街头》直指现代汉诗的本质,认为除了形式和意象,现代汉诗真正和传统诗学拉开距离的是感性与对诗之为诗的理解:诗是由某种自发以至偶然触机开展出来的感知过程,有时甚至是发掘自我和世界的认知媒介,讲求读者积极地参与意义创造;而传统诗歌却往往以人和宇宙的交感共鸣为终极指向或框架,讲求的是作者读者共同的学养与文化背景。{23}在以上两首诗,我们同样需要参与它们的语言运动,进行各层次的感知。
勾勒出现代汉诗感知运动的基本轮廓后,便可进一步从肌质、节奏与抒情空间三方面展露现代汉诗感知形式的生成。然三者互相牵连,不可能把其中一项完全抽离出来作独立分析,因此以下各部分例析只是在侧重点上不同。
四、经验中途:肌质的震颤
刘勰《文心雕龙》在《附会》一篇力言“统绪”的贯通、“义脉”的流动,以求把“绸迭”之“情数”生动地统合起来,既提出“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这样的大原则,复注意到单位的经营,说“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又言“悬识凑理,节文自会”。周振甫解释“凑理”为肌肉纹理,这两句即表示“能够深切认识文章的肌肉纹理,然后章节结构自会合理”。{24}
门罗(Monroe C. Beardsley)《美学》明言有两种审美形态,一是构架(structure),即作品主要部分之间规模较大的联系,二是肌质(texture),即次要部分之间规模较小的联系。{25}高友工在分析近体诗语言结构时便充分调动了这两层观念,指出肌质作为词语间局部的相互影响如何组成左右大局的构架。例如他认为语法限定了词之间的可能范围,也可能把肌质的更多可能降低,近体诗进一步减少语法虚词,句法关系更弱,歧义更常见;{26}又指唐诗的名词,趋向性质而非事物,加上句法宽散,肌质成为主要因素,名词并列时,它们便自然进入肌质的多重关系,系词介入则可突显某种关系,触发相对方向的反应。{27}在以下诗作,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局部的词语组织如何左右诗意的构成。
覃权《悼玛林》{28}
在夜里舞蹈出阳光的/那女孩已死了/听着她轻灵之步音/渐入睡乡的/那片土地/也随之死了/死了
(1968/3/1)
这是一首悼亡诗,但它哀悼的不单是死亡,还有死者与生者之间的独特而富生命力的联系。诗不断迫近这个双重失去的事实,而始终无法释怀。根据句意,我们可以把全诗分为三部分,而各以“死了”终结,像是连续出现的三个音:首两行是突如其来的尖音,次四行是延缓的低音,最后二字是轻轻一触,却袅袅难消的尾声。
在第一音和第二音之间,瞬息印象扩展,造成几乎是脚尖与大地的强烈对比,以及一种浮沤没入无限寂静的效果。在两个“死了”之间,张力布局已提升。另一发展是从视觉、听觉到视听皆杳。诗并没有达致最终的清醒,而在紧接敲出的“死了”的确认里止于浓郁的迷惘。
此诗很短,不但诗行少,实际上也只由三句组成,但我们不但不会觉得快速顺流而下,反而像卷进了回旋与回旋之间那样沉重纡缓。这表面上是因为分行造成的拖沓,更深一层其实是重复出现的“死了”构成了肌质关系,其回荡支配着全诗凝滞的语调和凄迷的气氛。我们再看覃权的另外两首更短的诗,只有三行,但肌质元素也更明显。
《日落》
太阳轻踩着云朵下来/到远方的海/沐浴去了
(1968/10/13)
这首诗有点颠覆了日落的惯常印象,在一“来”一“去”之间,出落得异常轻巧。先以“轻踩”“云朵”的细节逼近,再由近而远,进入“离去”的阶段,也稍稍进入想象的领域。这三段“舞步”,实际上只是由全诗唯一的动作“踩”所牵动。“到”传递着余力,“去了”的动态比“浴沐”更能承接前两行而展现了观者出神眺望的姿势。至于“海”,作为来去之间的一个瞩目的单音顿,就像两个连锁舞蹈动作中间轻触式的一点——如果说“来”“到”“去了”贯穿了动作,全诗的轻巧便押于“海”。
《无题六》
屋是向晚/窗是夕照/你是暂息的云
(1975/8/15)
我们首先想到,如果不逆置,换成“向晚是屋/夕照是窗”,就显得太滑易、太机智。事实上,不逆置会令诗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命意不明朗,反而像一种文字的布局,失去了张力。因为逆置,首二行蕴蓄着把空间时间化的拉力,于是“你”这个要“暂息”的特异存在所产生的张力就更大。诗中由大至小的发展都被背后那力量的争持掩盖了。通过几乎是全体性的肌质调动,我们得到的不是一重套一重的画面,而是对抗的过程:在有限时间中撑持出空间。
施蛰存提倡有“完美肌理”的“现代诗形”,本旨是在“坠入了西洋旧体诗的传统”,讲究“韵法”和“时节”的诗风以外另辟新路,追求内容与形式更自然也更富反射性和综合性的密切关系。{29}他的一系列“意象抒情诗”便可说是某种实践,以下专析《蛏子》一诗如何通过肌质营造出含蓄而流动的“诗形”。
夜的极司斐尔公园,/满是缄默的蛏子。/在月光的海水里,/投露了纤瘦的素足,/来来往往地/浮沉在荇藻上。{30}
这首诗以一个“夜”字开始。“夜”字的份量在独自和“极司斐尔公园”这长词组对峙的情况下突显出来。表面上公园是主语,夜不过是修饰成分,但单音节词与六音节词的不对称却引向另一些语法可能。第一,它们处于并置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夜显得格外重,极司斐尔公园则显得格外大,如此两者方可保持平衡。第二,以夜为行首,亦予人绝对感,“极司斐尔公园”便是夜所囊括的范围,极言夜之无遗——夜于是反成主语。试想如果把两者颠倒,后置的夜便仅变成时间标识。“的”字某种程度上只是掩眼法,它和“极司斐尔公园”一样,都贯注和传递着空间化之力。
作为张力的单元,第一行只代表了主语之一端,还有待于第二行的谓语,把上一行的力具体化。缄默不但指向蛏子,也指向夜。缄默之缄,无论在原义与发音上都比“沉默”之沉更有力。我们可以说,夜就是一只缄默的蛏子,是空间化与形象化的能量储存器。
如果说首二行是集束,末四行便是解散。这个分成四行的长句缺乏关键的主语:谁在海水里投露素足?素足属有者为何人/物?当然,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将蛏子视为主语,但更重要的是,在遗落主语后,直线联系的链条便让位于联系过程中途的丰盈现象。这四行虽然仍是一个过程,但却不是单线直下,而是带着重叠之迹层层揭露:先是海水一层,继而是素足,来往浮沉的动势也是一层,最后是荇藻:一层保持最低动态的底色。我们看到,随着节奏的舒放,处于不稳定语法状态的语言也转化为一种现象语言,它们不是跟随着现象,而是本身就携带着现象,与现象同步呈显。但与古典诗不同,它的这种明澈性更多是动态的包摄,而不是静态的包含;我们看到的不是圆足的镜头的完成,不如说是镜头的生成;悬置性与连续性并存,始终传递着一种经验的震颤。
五、摇曳生变:节奏的弹性与容量
从以上例析可见,肌质局部的组织及其相互作用所带来的,实际上是节奏的问题——字词之间的拉扯、分行与跨行、句的长短分合——在覃权的三首诗中,或带出轻巧的跳跃感,或拉动沉缓的哀音,或紧张地移向内在空间;至于施诗,在类似古典诗境的明澈背后导引着一道敏锐而柔韧的潜流。
罗大刚的《永夜》,在那夜的静境的底色上,和施诗有微妙的一致,唯《永夜》引起我们更多遐思。其经验的错综连结,其持续性与广延性更舒放的交互表现,足以进一步揭示现代汉诗节奏运动的性质。
梦在无梦的梦中/知道跋涉的重量么/悄悄地落在林外的/流星而已/古代行脚僧人/一一闭目远去/当我们怀归的时候/我们是鱼/夜在盲人眼里/莲华开遍大千世界{31}
第一行一层套一层,看似位置陈述,其实却是一层生一层,因为问题不在有多少个梦,而是在梦与无梦之间摇曳的节奏。如此理解,则下一行的疑问才显得是必然之问,才显出惶然的情绪。
重量之问荡开二象:流星与行脚僧人。流星本自悄悄,强调其落处在林外,便觉一瞬的悄悄也是空间的寂寥——跋涉本不只是时间问题;行脚僧人比流星的脚步落实,但闭目远去又是一种梦中摸索的姿态,不为留下任何痕迹,反而觉得他们同样是流星——历史时空的流星。惶然正来自这样一种时间空间的包围。
伴随这二象而来的,除了惶然的背景,也有第七八行的启悟时刻:跋涉只是归程,于无梦与梦之间,我们都是鱼。而“当……”这条件句所下启的还有一整个相生相扣的情境。夜在盲人眼里,鱼在莲花池中,本就辐射出丰富的想象空间,若开启“夜”一字动词的机能,则能揉结最后三行,成一灵动的流程:所谓跋涉、归去,其实也是浑忘,如鱼“夜”入了盲人眼中的大千世界。诗的前六行基本上是意象映带编织的过程,到最后三行,则已超越意象的跳接,而进入意象之网在万花筒似的镜头下变化增生的状态。
这首诗佳胜处既在意象过渡相生,造成疏淡流丽的意境,也在惶惑的蜕变、渡让、卸下、解脱之后,仍保持游进新境之势。全诗若以句意来分,是很整齐地以两行为一段落的,但这只是表面的节律,更深在的经验节奏绵密蕴藉地流变开拓。若我们只看到与古典诗境界相缘的“相忘江湖”“色空”等“讯息”,我们也就遗下了那“永夜”、那整体体验之迹,亦即诗本身。
《永夜》的节奏是在绵密的生变中徐徐形成的,冯至《在海水浴场》组诗三首则在整齐的形式里摇曳生姿。{32}
浪来了,你跳入海中,/浪平了,又从海中跳起,/跳在平板的船儿上,/唱着你故乡的歌曲。
浴衣衬着你的肌肤,/金发披在你的双肩,/岩石为着你含了愁容,/潮水为着你充满疯癫。
我可是在什么地方/好像是见过你的情郎?/他夜间在阴森的林里望着树疏处的星星叹息!
第一段轻快流畅,第二段连续出现四个“你”,句式两两叠加,像雕塑工夫,第三段蓦然闯入思绪,带到反差极大的形象和姿态,形成富张力的情节;彷佛有两个世界存在,且同时在“我”身上交通叠合。连续用韵也与这演进相映,加强紧张推展的情态;由响亮音(方、郎)顿入纤细音(里、息),亦是戏剧性的变化。
组诗第二首《沙中》首二行属于总概,由“深吻”到向空中伸手,由“懒”到“暖”,都是缓慢的深情表现,直到昨天的“玉体”现身,稍一过渡,便趋至一系列快速而激烈的动作,与之前的缓慢甚至庄严形成强烈反差。从节奏的激变上暗示了幻想凌越了清醒的灵魂。
风吹着发,又长了一分,/苦闷也增了一寸;/雄浑无边的大海,/它怎管人的困顿!
那边是悲切的军笳,/树林里蝉声像火焰;/波浪把一座太阳/闪化作星光万点。
远远的归帆/告我新闻一件:/“有只船儿葬在海心,/在一个凄清的夜半!”
至于第三首,每次双行总是一种较远距的跳动,而且和上两首一样,最后一段逸出了两段式,变成四行顺下,而此四行又均是前两段富张力的扩展。最后两行倒装,强调时段,其实也等于点出在海这个辽远的空间,消息总是姗姗来迟,不幸事件可能已在前两段的中途发生。最后一段不是单纯的延展和跳跃的结果,它通过深化而成了全诗核心。那凄清的夜半是翌日黄昏的震央。
三首诗都以海为场景。海给予诗人的除了幻想、回忆和外在事件,还有与外在世界的联系;海浪、滩岸都是变化不测的模型,都是诗中抒情空间的基本特质,但三首诗共通的形态,也表现了诗人建立抒情空间的自觉与控制。与《永夜》的温柔渐进相比,《在海水浴场》的节奏无疑较激动,有一定不可测知性,由散漫到紧张,由周旋到直泻,但都是最后一段出现突破,以此统合全诗,外在事件的介入终被结构纳入,甚至如第三首那样,积极地担当了类似船锚的重心。其次,四行的节式也是诗不致支离涣散的另一“锁链”,诗人利用了四行这种相对闭合的体式层次,安排顿挫灵动的诗意,保留了结实的推展力量又予以弹性,就像骨骼加上关节和肌腱,能容纳更大幅度的运动、更具对抗性的情境。
如果说《永夜》以其柔韧的意象生变“流”进了辐散、开放的抒情空间,《在海水浴场》则在浪涛似的体式冲击下切入了富戏剧张力的抒情空间。
六、动态的涵摄:作为舞台的抒情空间的开拓
上文已展示了现代汉诗在组织上的流动性、弹性和张力,我们有必要对整体组织作更全面的观照,以掌握现代汉诗感知运动背后的基本姿态与动力。
关于“抒情空间”,在分析程序上既自上文之肌质和节奏延伸、深化而来,其用法也需在此作一些解释。苏珊朗格分析音乐感知形式时,认为除了“音乐时间”,还有“音乐空间”,即“第二幻象”,两者同样都是经过艺术转化的虚拟“造型”。在音乐作品中,空间感知像回音一样时间虚幻序列的展布而呈现,是时间感知的延伸属性,又为后者创造多一个维度。{33}
诗固然包含虚拟的时间序列,也同样在运动的展布中投映出空间的维度,但诗的实际情况较特殊,它的材质是有音也有义的词语。正如上文所示,节奏既是词语和语象的组织,它便不只有表面上的时间性推展行进,也有多层的造型和多向的运动,以形成足以涵摄时间感知的空间感知模型。从语言角度看,以精炼的文言书写的古典诗歌,倾向内敛含蓄,至于现代汉诗,以本于口语的白话或语体文为主要构成单位,虽同为汉语一脉,却有古典诗歌所不显的向外包孕的延展性、屈折性。现代汉诗在适当承接文言遗产的同时,继续开发白话那分析漫衍的维度,实际上便是把近体诗旋律化的空间转化为一种节奏化、动力化的空间。以下是陈敬容《哲人与猫》:{34}
雨锁住了黄昏的窗,
/让白日静静凋残吧,
/我的石室冷而寂寥,
/雨如细珠轻滚着屋瓦。
来呵,猫儿,温静的友伴,/来伏在我胸前,让我拍着你,/听我心的湖水还波动着吗,/和着雨,斜斜的秋夜雨。
可是我的灯呢,灯呢,/我要一盏青色的灯/青色而明净,如夜中星点;/石室染上黄昏的颜色了,/不怕迷失吗,猫儿,/瞧雨在窗上做了疏斜的帘幕。
来呵,这儿我找到你的双瞳,/恰像是两粒青色灯焰,/青色而明净,如夜中星点,/射着我,用你温柔的凝视;/我的眼中满贮着疑虑吧,/因为雨,因为黄昏。
让幻想带着离奇的幽香,/在屋角扑摇着羽翅——/摇出夜:白的月,/蓝色的安息……
去吧,猫儿,同着我/和我的影子,去月色铺下的/水晶舞场,在碧润草原上,/林木静静舞蹈着,/时光踏着无声的拍子。
此诗注目处首先有两点。一是时间上从下雨的黄昏移至雨息的夜,二是空间上从室内到月光下的草原舞场;空间的转移是后出的,以入夜为前提,但时间的进程中,其实已充满了空间化的趋势。黄昏代表一种必然的时段,偶然的雨却把它锁起来慢慢消磨,黄昏变成一种固定的“石室”;而黄昏所象征的白日的凋残,则进一步变成一幅在石室中的画。对抒情主体来说,这段凋残的时间缓慢、沉重、寂寞,甚至危险,需要友伴慰藉;“我”和“猫”相视相守,前者不但在猫眼中找一盏灯,也找到夜中星点,照出了自己的疑虑。时间的变换被描绘成空间事件,空间事件又开始内化并自行发展,缓慢和沉重的情调终在“摇”这轻巧的动作下开始化解,时间的威胁露出了有限而无伤的边界。
意象穿织与空间布置密不可分,然而更关键的是从中引出的姿态也在演变。面对某种被时间固化的通道所困的危机,抒情主体最先选择了另一种固化去抵抗。“胸前”便象征一种凝缩的内在空间,而与猫的沟通则是私密化的通道。直到在与猫的互动中静观自身满贮的疑虑,较平静从容的态度才显现出来。除了由被动到主动、由焦虑到从容的转变,抒情主体也同时在建立一种融贯内与外、私密与广远的新关系。猫眼中的星光,寂静的心湖等意象都能暗示这种新关系的形成。
这首诗首尾两段对照鲜明,呈现了由重重闭锁到一步步开阔的节奏。凋残是命定的,舞蹈却是自发的自由的。凋残可说是以雨为喻的一把时光之锁,这也解释了为何雨如细珠这个普通的比喻能制造摇憾心弦的威胁感——它在极富闭固感的石室顶上“响起”。在尾声,一声“去吧”,身姿已全然不同,解脱和融入是同一件事,而且不只是融入另一个新的空间,也是不断从原有空间出去。空间的疆界在出就是入、入就是出的动作中消解了。时间的种种意象锁链逆反成轻盈无声的拍子。
这首诗说的是展开新的动力、新的空间的可能,为被时间宰制的空间赋予生成的力量,而最后不是其中一方被压倒,而是互相涵容:内与外、闭与开、日与夜、视与听、时与空。这种效果可说全由空间意象的独特编织节奏所达致;这节奏虽持续变密而保持舒展余地。我们在以下两首周定一的诗里则看到另一些不同的情境和动作:
《窗外桃花》{35}
家乡的门外小河有座荒洲,/我曾想归去种满桃花。/于是梦里几度花开花谢,/醒来向朝云书一笔颜色。/记起古代诗人画出的一个世界,/他的桃源应不在“尘嚣外”。/古城自有风沙中的春信,/我打开今年第一扇南窗。
这首诗最后留下了一个异常有力的确信的动作,几乎反讽式地质疑着前段种种,但反过来看,它又是连着前段遐想的“梦”和“画”才有力的。首先,末二行才揭出身在古城风沙之中,珍视和渴想因而变得实在,突然充满分量,也因此,明知风沙包围仍推开窗的动作才有力;其次,之前虽也有动作,但不外想象、造梦,或古人的绘画内容,如今是真正的动作:真正由内伸延向外,打开了方向。
此诗以两行为一组,发展上类似传统的起承转合结构,但反讽结构以及脱离心境营构到暗示介入现实的推移,都是和古典诗迥异的地方。此诗一直在酝酿由内向外的力,因此当典型的轻倩笔触转化到凝重坚稳,气脉仍是贯穿,最终亦具说服力地展示出信念的来历。
《游凋敝的万牲园》{36}
鸵鸟迈着孤傲的步伐,/毫不理会同一栏内的鸸鹋。/小鳄鱼的梦泡在浅水里,/像哭累了的迷路孩子。/只有猴儿们的兴致还好,/争抢投来的劣质花生米。/可是跟游人相对无言时,/也毕竟打了个呵欠。/狮熊虎豹都成了标本,/生命似早已各归其位。/游人不用为它们埋怨了,/可哀的是这一室静静的午后之影。
此诗可分为三节,每节四行。第一节的拟人化描写是偏于静态的,第二节一开始是动态,却急转直下,第三节复杂一点,“标本”和“生命”组成矛盾,“归”的概念也是反用,前两行可说是总括地反写凋敝;至于后两行又是一反,一直隐匿的观者现身,但关顾的已非园中动物,而是自己的处境——视线向外,本是游动物园的惯性,突然收回来,便发现自己也在一室中困守,和可哀的动物没本质区别,是凋敝的一部分;游人不游,题目也构成反讽了。与此突发的内省相应,最后一行音顿较多,且较多长音顿,格外沉重缓长。
更有趣的是这游人和之前那些动物的认同情感。他为它们埋怨什么?他是否赞同鸵鸟的高傲,同时想到其自欺?同情新一代?嘲笑现实的小丑?真正珍贵的已变成标本,社会充斥庸俗?那自困之局可能是基于游者的批判,当然更深一层是自觉到不能置身事外;凋敝的园景和凋敝的人境不是隔离的。
第一节分别描述,左顾右盼;第二节集中一景,出现转折;第三节密集翻合,自觉一种“元处境”。节奏形态由有序推展到急转,再到交错起伏,重量越来越沉,而且也凝聚了一种引力,终由“元处境”涵摄了之前的一系列场景。
不论是陈诗或周诗,我们都在那经历重重营构的抒情空间里找到一个统合性的动作、姿势和情境,而更重要的是,这逐步撑持出来的抒情空间并没有推出一个超脱的、凝固的终点,它由始至终都是一种运动的主体,承载着自身持续下来的动力和变化争持的姿势,所谓统合性,并不意味着闭合,而是在动态意义最丰盈最集中时某种舞台空间的呈现——与其说现代汉诗开发了某种形式,还不如说它开拓了一个让形式保持生发力量的舞台空间。
七、遭遇现实:形式的许诺
现代汉诗依然开发着一种内在化、心象化的抒情美学,但其抒情符码是变换了;现代汉诗在固有的抒情美学的局面之内更新了其定义——真正的更新必涉及在内部发生的转化。单从本文的例子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两种感知趋势:在遭遇的背后营造化解与融和的空间,或推展出戏剧性的僵持情境;沉浸于经验潜流生成,或在经验的涤荡里寻找突破口;内向的、近于音乐化而趋向超脱的,或充满介入动力的、戏剧化以至雕塑化的——这当然只是异彩纷呈的现代汉诗之一斑,但无论何种趋势,它都不是晶莹圆润,有形而上保证的自足胜景了,它从语言的经验出发,经历一次又一次节奏的浮动与凝定,规划一个富张力的、始终生成的载体。
高友工说,深深浸淫在抒情境界的古典诗人虽相信那悬置起来的内在世界自有独立而不能磨灭的意义,“现实总俟于一侧,在抒情时刻过后再度席卷诗人。时间和空间的两轴再次成为一加诸诗人身上的参证格式,诗人须重为其视境定坐标,努力与外在世界重做接触。”能否将这种遭遇现实时所造成的紧张与不安重新“熔铸成一和谐之整体,或转成强烈的冲突,几可作为探测诗人意识深度的一个标准。”{37}换言之,遭遇在诗外。诗本身则是超脱遭遇并融化之的结晶,诗人在现实时空的钟摆中不断重复回到虚静的瞬间开辟永恒的经验,自设感知时空,这也是古典诗形式的绝对性、纯粹性所在。现代汉诗的形式却恰恰是与现实的遭遇本身,它的力量所在不是化合、回返与悬置,而是保持遭遇,并且内置之、展开之、深化之,同时又始终贯彻一种作为遭遇现实的突触与转机的节奏。现代汉诗正以此节奏承诺了对充满生机而不可测知的现实遭遇的承担力,开拓了另一种标榜流动、开放、介入、遭遇的意识深度的标准。
对于这种遭遇现实的承载力,瑞恰兹对两种经验结构或审美结构的区分是值得参考的:第一种经验结构,是由单层的、同一方向的冲动组成一次互相协调的、完整的反应;另一种则通过驳杂以至对立的冲动,扩大反应的基础,创造更丰富有力的经验的平衡状态。{38}我们可以说,前者贴近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主流情况,后者则是现代汉诗所形塑开发的,不得不基于第一种经验结构,又不得不超出其反应模式。瑞恰兹还指出,在后者,“我们不是被导向某一特定的方向……而是通过许多道路,同时地、有连贯地对事物作出反应”,{39}那些复杂以至对立的冲动通过形式的手段被唤醒,又通过形式元素的组织得到解放;冲突领域更广阔,其可塑性也更强,更能接受诗人的控制。{40}经验本身也许无法分析,但其所以被唤醒、解放与组织的节奏形式,却可作一定程度的把握和解释。本文便是为了呈现一种经验结构重新整合的过程;因这种整合,现代汉诗获得更广阔的反应道路。
王佐良有言:形式实际上意味作家把握世界的方式和程度。{41}古典诗歌如是,现代汉诗如是。与现实的接触与互动是形式的一个源头,唯形式必经创造和运用,并藉此许诺更富生命力的运动、更多样地寻找意义内烁外发的过程,以及更具承担力的体态。现代汉诗所锻炼的形式,便是蕴含着向现实开放的生成张力的柔韧节奏;它是抒情节奏,更是经验的节奏、体验的节奏、遭遇的节奏,其成果值得我们进一步回顾和继承发扬。
① 伊塔罗·卡尔维诺:《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吴潜诚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06页。
② 李英豪:《论现代诗之张力》,张汉良、萧萧编《现代诗导读(理论、史料、批评篇)》,台北:故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89页。
③ K. K. Leonard CHAN(陈国球). LITERARY STRUCTURE AND LITERARY PROCESS: PRAGUE SCHOOL'S THEORY OF LITERARY HISTORY(文学结构与文学进程——布拉格学派文学史理论评介). 王守常、汪晖、陈平原主编《学人(第二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60页。原意为Mojmir Grygar提出:“even a less successful work can sometimes indicate new developmental possibilities, while the value of 'completing and culminating a developmental tendency' is reserved to artistically perfect and mature works”。陈国球引申为“An innovative work starts a certain developmental tendency whereas a 'classic'work makes the given developmental possibility fully apparent.”
④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15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49页。
⑤ 朱自清:《诗的形式》,《新诗杂话》,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5页。
⑥ 闻一多:《律诗底研究》,孙觉正、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十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第159-166页。十多年后,闻一多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在西南联大教授唐诗时说:“七绝当是诗的精华,诗中之诗,是唐诗发展的最高也是最后的形式。……传统看法认为五律是唐诗的重要成就,我觉得还欠考虑。”(郑临川述评:《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⑦ 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第154页。
⑧ 参看高友工《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试论中国艺术精神》二文。(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⑨ 可参看“搜韵网”(http://sou-yun.com)关于王维《终南别业》的辑评。
⑩ 参看曹逢甫《从主题—评论的观点看唐宋诗的句法与赏析》,《中外文学》1988年第17卷第1期。
{11} 王文霈编:《历代诗评注读本》,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314页。
{12} 高友工:《小令在诗传统中的地位》,《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第279-280页。
{13} 高友工:《律诗的美学》,《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第250页。
{14} 邝龑子:《由“无我之境”到“诗中有画”:抒情主体之道》,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编辑委员会编《人文中国学报》第17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5} 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30-931页。
{17} 奚密:《中文版自序》,《现代汉诗》,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页。
{18}{19}{20} 李长之:《李长之文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85页;第490页;第496页。
{21} 李长之:《李长之文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22} 《文学导报》1936年1卷1期,第22页。
{23} 奚密:《现代汉诗》,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6页。
{24}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5页。
{25} Monroe C. Beardsley. Aesthetics: Problem in the Philosophy of Criticism.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 Inc, 1981: 168-169.
{26}{27} 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诗语的结构主义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5-76页;第52、86页;第37-38页。
{28} 覃权:《远去》,自费出版,1973年。转引自“香港文化数据库:覃权诗钞”: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hk/2011/03/blog-post_2302.html。其他两首均录于此。(2013年9月26日)
{29} 施蛰存:《文艺独白: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1933年4卷1期,第7页。
{30} 施蛰存:《意象抒情诗:夏日小景》,《现代》1932年1卷2期,第229页。
{31} 《新诗》1936年第1期,第57-58页。
{32} 冯至著,韩耀成等编:《冯至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0页。
{33} Susanne K. Langer. Feeling and For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3:117-118.
{34} 蓝棣之编选:《九叶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9页。
{35}{36} 杜运燮、张同道编选:《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287页。
{37} 高友工:《中国叙述传统中的抒情境界——〈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读法》,《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第293页。
{38}{39}{40} 瑞恰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想象》,伍甫等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02-303页;第304页;第297-298页。
{41} 张大农:《诗评与译诗——与王佐良教授一席谈》,王佐良《中楼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Texture means the organization of words; rhythm refers to rhythmic movements of the textual organization; lyrical space is the dynamic layout of the affective context. A poem is an organic unity of these three layers. This article will not summarize its poetic method or poetic form or retrospect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its form. Instead, it will use the aesthetics of classical poetry as reference, and through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of textural-lyrical space, uncover the aesthetic tendenc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so as to propose a new perspective for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its development. Modern Chinese poetry repeatedly investigates the texture of language in order to become an open, plastic and tensional experience carrier. This moving posture is a lyrical rhythm but at the same time a ryhthm of experience and encounter. Modern Chinese poetry is an extension and also a reformation of classical poetry in a new space. Its experience of new perceptive forms has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writing and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poetry, perceptive form, texture, rhythm, lyrical 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