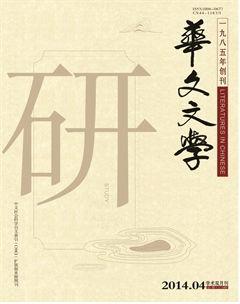论台湾文学场域中的政治和市场因素
张诵圣
摘要: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台湾文学受中国现代文学影响至深,这种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本文结合台湾文学的发展形态,着重探讨了延续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的政治和市场因素,如何在台湾文学场域中获得了复苏并发生了新变。
关键词:台湾文学;主流文学;政治因素;通俗文学;市场因素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4)4-0018-07
一、1949年以后台湾文坛的复苏
(1)文坛复苏
在台湾紧接着1949年之后的那些年里,政治威权控制合法的文学话语的努力,是通过值得信赖的文化参与者和一种半自治的文化场域的管理法的中介实施的。可以肯定的是,在党国的严密监管下,政治力量渗透了文学生产领域的所有机构(学校、出版工业以及媒体),以及绝大多数平民活动的领域,然而,随着岛内向着一种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稳步前行之际,文化生产领域却依然停留在准自治的状态。
1949年之后的台湾文化场域源自特殊的历史状况,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国民党当局强制的语言政策,这一政策意味着那些不能说汉语的本土台湾人基本上没有机会在文学领域获得成功,因而受到信任的外省籍作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不过,在这些文学参与者显露出的倾向于顺从的同时,他们也对避免过度的政治影响有着极大的兴趣,他们探索他们有限的自治,试图在外在的各种要求中开拓出一种相对自由的创造空间,然而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伪装的策略被他们自己整合到文学场域的功能规则中去了。
一些例子可以证明,一种半自治的文化场域确实存在,并且政治力量在一般领域力量中的作用力是经由场域的运行规则间接实现的。例如,与一般的印象相反,在1951至1956年间,一些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的年度奖获得者是台湾人,包括廖清秀、钟理和和李荣春①。很显然,即便是在紧接着1949年之后的那些年里,单一的政治认可并不能保证文坛中的成员,在摆脱了外在的政治束缚之后,文坛还有它自己的法则——而文学上的成功则取决于对两套规则的固守。
对这种双重强制的制度的一种更加积极的贡献,就在于它的外表的非政治文类的发展和证明是大众的并终究推动文学生态朝着更加自治的方向发展的美学实践,一起贴上“纯文学”的标签,这些新事物被授予了政治合法性的微妙要素,如一些成功地利用了一种潜在的中国中心主题。
当市场和大众传媒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快速发展的时候,文坛自治的一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值得讨论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出版工业的兴起和副刊的繁荣,带去了从战前和战时中国大陆的中心城市——包括那些日本人占领的城市,在那里文学活动免受在其他地方遭到的剧烈变化,大部分保留了战前的商业模式——留下的遗产,1980年代在台湾文学场域中兴起的上海热足以证明这种血亲关系。
不过,在它的早期,“文坛”无疑面临着相当大的限制。“文坛”一词意味着一种精致文化、“中国现代知识界”、有着优雅品位的男女、有声望的要人以及据说在投身充满生气的活动方面有着超常天赋的形象②,这一形象与布迪厄宣称的“艺术家拥有的吸引力和迷人之处与其说是艺术本身,不如说是艺术家的生活方式,艺术家式的生活”相对应。尽管外省人文学参与者的“文坛”魅力在1949年以后的台湾已经复苏,它必定会带有它从国内战争的废墟中再生的特质,因此它与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上海文坛有着显著的差别,这一点在李欧梵的著作《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中有着生动的描绘。
编辑家及作家林海音在1984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文坛剪影》,在台湾再次浮现的文坛,其核心形象恰好传递出这个文学场域的特殊情形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回忆录的条目证明了1950年的杂志和副刊既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同时文坛也主要是为国民党赞助的文化项目所支撑,然而,政治印记沾染并有效地弥漫着一种精致的、动情的、公然的非政治气氛,这种气氛重新界定了“纯文学”的特征。毫无疑问,林海音那一代的文学参与者都参与了在威权统治下象征着知识分子生活的一种斗争,为了理解他们主体性上升的自然和必要,以及在一种温和的、和谐的文学共同体中感伤的创作风格,人们不得不对1950年代文学生产的体制环境作进一步的探究。
(2)战争模式及其遗产
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很难想像在1950年代台湾的文学环境与抗战时期中国大陆的文学环境是何等的相似,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建立起来的文学生产的“集体主义范式”——这种范式既在解放区也在国统区盛行——事实上也带到了台湾并在1949年之后得到了很好的延续。查尔斯·劳林(Charles A. Laughlin)在他的文章《文化生产的战场:战争年代中国的文学动员》中,讨论了文学生产的状况因抗战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使以往的美学标准和生产模式不再站得住脚,并加速了他们被生产的集体主义模式置换,以往的文学成就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且无可争议地——使中国新文学受到了战争的负面影响,文章也讨论了这种影响是如何在后来的民国时期阻止了像现代主义这样的艺术倾向的发展。在劳林的文章中,视角的转换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因为它提示我们,战争期间文化生产模式的发展在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的文学建构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伴随着向集体主义模式的转变,一些过去占支配地位的出版工业都市中心即使不是彻底消散,也是衰竭了。为了适应战争的特殊要求,新的规则建立了,这些规则包括:由军方掌控的文学活动组织化;密切作家和他们新的最常使用的题材——在前线的战士——的联系;以及自愿参与文学动员。
战时的集体主义模式在1949年后的台湾已经在形态上有所改变。台湾学者郑明娳在《当代台湾文艺政策的发展、影响与检讨》一文中,确立了早期政策的三个组成部分:党(国民党),由张道藩主其事;军队,由蒋经国的得力助手王升将军主其事;蒋介石本人。很显然,当蒋介石的传统主义和精神领导为台湾文化和文学话语定了调之后,在凌驾于文学生产之上的体制控制方面,党和军队通常掌握着支配权。
然而,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薄弱,导致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政策迅速退化为中国中心修辞学和新传统主义的道德主义。比如,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者赞成的阶级仇恨,国民党的右翼理论家大肆鼓吹主张与生俱来的人性善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仁心”成为文化官僚手中的感伤修辞学。这种鼓励知识分子回避诸如赤裸裸描写社会经济问题、讨论“阶级”禁忌等议题的消极战略,最终事与愿违,特别是在1970年代反霸权的乡土文学运动中尤其明显。另一方面,这些更易于受国民党意识形态灌输影响的人发展了他们的保守主义观点,这些观点在占据主流位置的文化参与者那里广泛流行。
文学体制的战争模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1950年代,当国民党当局为即将来临的与共产主义的战争做准备的时候,动员的推动力来自大多数有影响的文学机构,中国文艺家协会——也就是1938年抗战时成立的文协——是一个典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当战争的威胁逐渐消散,作为文化政策首要目的的积极动员衰竭了,尽管如此,组织框架还是适当地保留了下来,以便有助于完成诸如在文化生产的意识形态内容之上维持控制,安抚和同化文学界的潜在反对者(如不合时宜的台湾本土作家),以及教导学龄青年的任务。于是战争模式的重要元素保留了下来,包括政府对“文化赞同”的积极精神的强调。
很难在执政的国民党和军队对文化事务的介入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不过一般认为,党和军队在决定政府文化政策方向的重要观点上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力量角逐③。可以确定的是,在抗战和国内战争时期,从事文化活动的准军事组织既具有军队的军事经验,同时也具有一种可将文化事务组织化的组织结构,而且,台湾文学界高比例的军中作家也常常被用来作为——至少在“军中文艺运动”,一种被认为是受到蒋经国保护的总政战部主任王升领导的特殊的积极倡议——成功的证明④。
然而,在军中文艺运动成功的背后,还有特殊的历史条件。两场连续不断的战争导致了人口大规模流离失所,许多来自传统中上层家庭的青年人和青少年男女,为了寻找在他们受到战争蹂躏和敌人占领的家乡失去了的教育机会,离开家乡考入政府资助的、军事化管理的中学⑤。这些流亡学生中的一部分最终加入了军队并在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撤退来台。这些年轻的,相对来说受过良好教育的军人,大部分有着上层社会的家庭背景,他们居住在台湾的眷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次文化。那些在1980年代声誉鹊起的婴儿潮世代作家中的大多数,都是在眷村成长的外省第二代——这份遗产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们的成功,并且这种成功也部分地来自他们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界有着良好的关系,其时第一代军中作家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与可能的预期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军队展示了一种“开明”,并在文化事务上超越了所有实用主义领导风格,对于军队中的年轻作家来说这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对西方影响的容忍是这种半自由姿态的一部分,这也解释了军中作家何以在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早期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扮演了非常活跃的角色,一方面是忠诚和爱国,另一方面是风格的先锋派和创造性的自由挥洒,这两者的有趣混合使这些作家在政治和文化合法性的较量中居于边缘。在政策制定的更高层面,王升将军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正如郑明娳在她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是在1978年,当王升力图中止乡土文学论战所引发的政治混乱时,他的讲话还是以一种几乎是自由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为底线。王升强调国家安全是文化政策的底线,结果,一种结合了外在的实用主义和内在的强势控制的政策,就成为蒋经国时代(大致从1970年代早期至1980年代后期)——一个政治保守、市场化、中产阶级文学都快速增长的时期——软威权统治的特征。
总之,肇始于1950年代后期经过1960年代和1970年代,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生产的集体主义模式,相继受到提倡现代主义和乡土文学的精英同仁杂志的挑战,这种挑战在1970年代中期很快发展为富有战斗性的反对力量,本土文化——对国民党建立的文化霸权而言是一种真正的威胁——于焉形成。也许有人提出,国民党在乡土文学论战后成功地重获文学界的控制权要归功于痖弦——一位年轻时代来自军中的现代主义诗人——在1977年正主编《联合报》副刊并在1980年代一跃而为文学媒体的领袖。事实上,在戒严期的后期,随着显而易见的政治检查制度的松弛,社会富裕程度的增长,以及媒体独立性的增强,战前大陆中心城市的市民模式开始主导台湾的文化生产,当副刊以及相关的文学出版工业成功地盗用国民党支持的官方文化以从一种日益商业化的环境中获利之时,它们也从1949年后早期阶段的一些动员策略和组织结构中获益。同样地,负责分配公共资源给文化参与者的官方机构——如“文建会”和“文化中心”——在后戒严期的台湾这样一个更特殊化、更分化、更专业化的文化环境中,在文艺的价值和功能方面不可避免地继承了一些早期的观念。本书余下的大部分章节将致力于描述当代台湾文学发展——作为一种伴随着向(重新)令人神往的受市场和自由社会支配的市民模式缓慢进步而不断消除集体主义文化建构的过程——的特性。
二、政治因素的非官方线索:
文学中的民族主义—道德主义话语
彼得·柏格(Peter Burger)关于文学“体制”的概念直接关注形成那种体制形态的话语,以及目前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化领域——包括台湾——流行的特殊的话语,那是一种有效的政治话语,但并没有被赋予一种政策含义,更确切地说,它由我所说的“非官方政治因素”,柏格所称的“关于艺术或文学的一般观念”,以及“能决定参与文学主体的外貌”的“霸权范畴”的存在所组成。作为这种范畴中的一个例子,他引证了自十八世纪后期以来在欧洲盛行的艺术自主,这种艺术自主暗含“艺术已经从社会生活的现实中解放出来,有目的的、理性的思考并不适合这片已经创造出的天地”。
中国现代社会中的“霸权范畴”看上去恰恰相反,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常常担心在文学使命中注入了过多的社会功能如道德教化、政治效用以及增强社会健康等,更为特别的是,大约在整个上个世纪,文学被当作了一种民族主义—道德主义话语以帮助强化民族观念和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如同常常被看到的那样,坚信文学的社会功效既能提高地位又能增进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文学活动的利害关系,与此同时,民族主义—道德主义的修辞学很容易得到专制的中国政府的支持,反讽的是,专制的中国政府的文化政策总是将知识分子阶层置于自己的有效控制之下。
在文学界,即便是直接的政治控制让位给市场力量之后,民族主义—道德主义的话语依然存在。在台湾,它在高度政治化的乡土文学和本土文学运动中重获生命,尽管它出于民粹的要求,但在两种运动背后关于文学观念论的这个话语,与当代台湾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的现实在根本上是不一致的。不论是自由主义运动还是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运动,民族主义—道德主义话语在论及文学艺术时被赋予的政治合法性原则特权,不断地与更“真正的文化”合法原则——这个原则在台湾日趋自治的文学界以竞争为基础——发生冲突。
(1)文学想象和民国时期的现代文坛
李欧梵在他197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开头两章中,揭示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存在于文学说教的知识分子话语和文化生产的市场化倾向现实之间的一种潜在张力。李欧梵引用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位渴望从事文学工作的年轻人写给文学杂志编辑的,很有典型性:
我想做一点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我选定了文艺。我想借文艺来声讨社会的黑暗,人类的痛苦,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描写未来的光明。
在评价这种充满年轻人激情的天真而又真诚的表达时,李欧梵认为尽管文学作为一种“对人类社会有益”的媒体的概念是普遍的,但在现代中国的早期,受梁启超和鲁迅的影响,专业责任的观念更加明确,因此更强调它的民族的一面。“五四”一代人在他们的文字中把他们自己当作“社会改革者和国家良心的发言人”,这完全符合“五四”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思想”。
然而,在这种表面的一致性背后,在年轻人的使命感和吸引他来到其中的文坛现实之间,有一种明确的不协调。李欧梵描绘了一种由时尚引导的文坛,这一文坛看上去沉浸于以政治进步和现代开放观念自夸的西方的洋派,而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力量系统在发挥作用:一种在年轻门徒的使命感背后,另一种则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中国的主要城市中的现代都市“文学竞技场”的形式背后。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改革和强化民族的手段,和西方相关联的创伤遭遇需要文化的复兴,这提供了一种向着“现代写作人”进步的光晕,与此同时呼唤传统的霸权话语——这种话语能够加强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健康,而它被认为是文学的主要功能;另一方面,市场力量是在现代文学体制、出版工业、以及它日益增长的不关心政治、非意识形态奉献的参与者建立背后的主要动力。这后一种市场驱动力量的系统构成了主要动力并形成了文化场域的一般风貌⑥。
李欧梵的论述也许是关于抗战前中国——那时的中国已经在自治、形成对它自己在文学霸权话语的盗用和侵蚀标准上施加压力的能力上达到了一种坚实的程度——现代文学领域的第一次学术成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似非而是的方式:说教的民族主义—道德主义话语和享乐主义国际化/西方化因素(华丽的文风、波希米亚生活方式、伪先锋主义等)在建构当代文学想像时结合了起来——两者都是抗战前正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的文化领域中的有机组成。
(2)“殖民现代性”和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
在知识分子文学话语和实际操作之间的不协调也在1920年代中期开始的台湾新文学历史中有所体现,台湾的殖民地处境和它经历的特殊的现代化类型或许更扩大了这种歧异,这也是施淑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首与体》中的中心论题,在这篇文章中,她集中探讨了1930年代台湾现代化的兴起和“颓废”文学。
施淑论述了这种文学中的“颓废”是建立在新确立的时间和空间方向的基础之上,而这个新方向又是由有效地改变了都市中台湾作家认识图式的“殖民现代性”所确立的,日本殖民当局在1896年将格林威治时间引入台湾,当台湾的工业、教育系统和政府官僚体制都已经开始现代化的时候,这是调整统一民众生活的手段之一。施淑同时还指出与花费大量时间深入了解不同的时间体系相比,台湾的城市空间转换看上去对台湾作家的意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殖民者运用传统的日本空间处理原则全面彻底地重新设计和重建首府台北,这座城市和环绕它的群山、河流因此具有了一种精致的象征结构的味道⑦,传递着日本天皇的帝国优雅和崇高力量,这一切都成为了现代性的物质表象:
台湾作家和他们小说中的那些在1930年代早期受过日本殖民教育并生活在具有新城市景象的台北——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中心舞台——的人物一起成长,与此相伴的是日本的殖民统治和自己历史的丧失。除了无所不知却难以捉摸的帝国君权,直接给他们提供一种新的空间想像的是有着明显的现代风的街景、商店的橱窗、以及消磨时光的娱乐场所,像沥青铺就的道路,环形交叉枢纽的开放空间,百货商店,咖啡馆,电影院,当然,在所有这些场所中还包括移植的时髦:日式游乐场,歌舞伎,横笛表演,俳句,樱花等等;它们散发出一种只属于殖民宗主国日本的美的味道。
到1930年代中期,日本风味的城市景象在台湾小说中具有了一种新的意义。此时,许多台湾作家既有在日本学习的也有新近从日本返回的,台湾的现代化城市空间唤起了他们对日本大都市如东京这样的“第二故乡”的怀旧心理,失落感和羡慕感成为想像的重要资源,而在风格上也形成了一种“浪漫的,中产阶级颓废的”文学⑧。
在这种浪漫的“现代”文学流布之前刚刚开始并受到它的殖民地地位所限制的时候,台湾在1920年代就已经产生出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话语——这一点和中国大陆有着惊人的相似。最初通过赖和和张我军的中介,台湾知识分子了解到“五四”运动中的文学概念和写作情形,在1930年代,与大陆紧密的联系松弛了,不过“左”与“右”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日本继续刺激着文学上的政治化知识分子话语,因而,当“颓废的”现代主义作品在1930年代中期出现在台湾的文学舞台上的时候,左翼和右翼的知识分子都表达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指责这些现代主义作家纵情声色,并且丧失了台湾新文学“启蒙民众和实现社会改革”的目标。
于是,施淑文章的重大贡献,就在于它注意到文学发展受到了回望日本的怀旧心理的激发,以及对1930年代台湾的殖民地现代城市景象的反应,这使台湾的文学史变得复杂,它加强了那种我们熟悉的存在于一种持续的民族主义—道德主义话语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张力,注意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和其他的殖民地遗产。
(3)都市背景下的传统文人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
大陆学者陈思和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要注意另一个重要的现象:政治和文化术语的合法性可能已经实际上互为养料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献祭仪式中合为一体。陈思和在1990年代中期写了一系列文章探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问题,他提出三种基本方向:朝向政治中心的方向(庙堂意识)、仿效西方的启蒙传统(广场意识)以及最新发展出的专业主义(岗位意识)。
与我们的讨论相关的是陈思和文章的第二部分“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这一部分处理的是“五四”一代具有启蒙思想的公共知识分子与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大众文化(现代、都市)错综复杂(两者既具有竞争性又互相缠绕)的关系。从本质上讲,陈思和认为中国现代都市通俗小说——主要归结为创作于1910年代和1920年代之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二十世纪早期由在前一个时代受过政治和道德的保守教育的精英以激进的方式重建文化领域的一种副产品,这些精英先是在晚清的帝国改良中遭到失败,接着又发现他们自己被排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外,而这场运动主要是由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主导,他们从西方输入知识体系并成为这种知识的参与者。不过,在接下来的反动的民国政府统治下,这个群体开始承担掌控现代都市文化生产的各种手段包括报纸、杂志、图片、影像制品的责任,并成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生产的第一代。当具有启蒙思想的“五四”“新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文学用来批评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时候,这些保守的绅士阶层的艺术家则坚持残余的世界视角和不断试图大肆渲染主题特征,这些特征将与政府和公众分享的公共欲望包含其中,他们创作的通俗的、中等阶级的文学常常模仿和谐仿进步的、在“五四”运动中获得了较高文化地位的新文学。在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在都市文化空间、争取相同的读者群等方面不断斗争,当民族主义—道德主义话语在他们的作品中同时出现的时候,由于从散布在出版工业和大众媒体的参与者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力量,保守群体的那种更传统主义的、娱乐倾向的姿态就在市场中获得了一种实质性的优势。
陈思和以1930年代在《时报》连载并受到商业促进的巴金的小说《激流》为难得的例外——“五四”文学获得通俗性成功的例证。然而,从不同的角度看,在某种程度上讲巴金小说中的家庭罗曼司特征比大多数其他“五四”作品更接近感伤的情节剧,这就有可能把他们同时发生的向较高和中等读者的诉求,归结于一种发生在民族主义—道德主义冲动和通俗趣味之间的快乐趋同。我们也许认为这种新程式在各种都市艺术形式(小说、戏剧和电影)——这些兴盛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形式成为一种更早的、更传统的通俗文体鸳鸯蝴蝶体的替代——中的出现更可能是一个例外,由徐■、徐速和王蓝等作家创作的“历史罗曼司”小说能在1949年之后的台湾和香港风行一时,如同1950年代台湾大量生产的主流文学作品一样,毫无疑问地继承了这一极其可行的程式。
因此,陈思和研究的最精彩之处就在于对这样一些重要现象的考察,如早期阶段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生产和流通背后的历史和社会因素,1930年代和1940年代当市场扩张的时候高层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灰色地带,以及由民族主义—道德主义话语以它对文体科层无处不在的高压正统力量扮演的永远有迷惑力的角色。
三、基本结论
中国现代社会中的文学场域典型地受到政治合法性要求(既受到当局也受到民族主义—道德主义话语的认可)和文化合法性要求(受到市场——至少是在过渡的意义上——的认可)的制约,并且,其特性还受到持续的同化作用,以及受到市场倾向支配的文化产品生产、奉献、传播合法性的文化通俗化(庸俗化)要求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或“新文学”)在其产生的时候即深置于一般权力领域的政治斗争并受到杰出的改良知识分子梁启超和鲁迅的推动,他们的“五四”门徒,通过毫不夸张地说是“接管”和改革杂志、主要报纸的副刊和原先出版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公司——《小说月报》、《学灯》和商务印书馆——将新文学提升到主流的位置。与此同时,文化场域伴随着依托商业性生存的作品如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派)的衰落,科层化地建立起来。
当中国现代社会中的所有高层文化的现代形式倾向于从西方引进的时候,处于过渡期的受过传统教育的写作者发现他们的文化资本突然贬值了。受西方影响的文学风格逐渐取代了传统形式(或将之推到了边缘)。这种价值重估还产生了另一个明显的效果,正如陈思和在他的文章中所提到的,二十世纪早期原先传统绅士家族的后代成为出现在中国商业化都市市场的通俗文学的生产者和参与者,在一种较小的程度上,这种现象在1949年后的台湾再次出现,比如,出身绅士家族的作家高阳、南宫博,在传统国学方面极其博学,他们写的历史小说就运用了前现代方言小说特定的总体特征和叙事惯例,目的是使作品赢得大众——当然也导致了在确立风格科层时少受尊敬。明确的市场走向使这些作品仍然能赢得学术社群中更传统的部门的关注,然而对于大部分而言,应用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阐释框架,具有不断更新、引进高层文化概念的倾向。
除了一些例外,学者们对于文学生产中的市场力量相当轻视,结果是,在高层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灰色地带,风格的交融,以及在资本发展的过渡阶段支配文学市场的“中等阶级”趣味,很少有合适的称呼,甚至在深受尊敬的学者如前面提到的李欧梵、施淑和陈思和的研究中,尽管他们对于文学生产的矛盾因素作出了深具辨别力的观察,但主要关注的还是高层文化(如李欧梵对“五四”民族主义精神气质的提及;施淑对现代主义美学感性的关注;陈思和对“民间”文学价值重新认识后的肯定),总的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成果中赋予高层文化术语以特权导致了对诸如风格科层的变化和文学与阅读大众互动关系等情形的忽略,比如,探讨一些“五四”文学何以具有“通俗”面的自身原因,就很少成为细致的批评的焦点,与此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世间事的“过度合法化”、娱乐的中产阶级文学散落在本土或引进的高层文化范畴⑨,直到1990年代,市场已经在台湾海峡两岸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活中成为一种不可否认的力量之后,对“通俗文化”的分析才获得了它自身合法性的一种确定的身份,并对修订文学研究的某些观点产生了作用。
不过,市场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由于各自宣示了改革开放时期和后期戒严时期的到来,因了“大裂变”而突然出现,在现代时期——无论是在革命前的中国还是殖民地的台湾——市场已经是一种重要的复杂因素,在文化生产的政治反对原则和文化合法性之间共处和冲突、竞争和妥协中,起主导作用。正如已经讨论过的那样,直接的政府干预和一种民族主义—道德主义知识分子话语,在将一种政治合法性的控制原则强加给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方面互相补充,布迪厄把这个叫做“科层化的他治原则”,因为它按照源自一种对文学领域而言是外部行为——社会的一般权力领域——的标准来赋予价值。
在现代中国,当政府对文化生产的控制最为强势的时候,民族主义—道德主义话语可能会对政府有利,不过它也可能被政治挑战者或社会改良者利用来促进反霸权运动,在政府干预较少和自治的文化场域茁壮成长之时,民族主义—道德主义话语甚至可能越是矛盾,就越是被场域自身的运行法则缓慢而又吃力地调解。在1949年后的台湾早期,当文化参与者遭遇因政治和市场因素互动而培育出极其多变和模棱两可的形势,当受到尊重的学者——尤其是移居西方的学者——在文学献祭中拥有特殊的权威的时候,这种复杂性就成为主导。
① 获奖的小说有:廖清秀的《恩仇血泪记》(1952)、李荣春的《祖国与同胞》(1953)和钟理和的《笠山农场》(1956)。
② 参阅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特别是第一章《文学界的出现》和第二章《文坛和文人现象》。
② 根据对王鼎钧的访谈。王鼎钧是一位作家和退休的文化官员,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他曾在“中国广播公司”和国民党经营的文学杂志《幼狮文艺》工作。
④ 著名的军中作家包括痖弦、洛夫、朱西宁和段彩华。
⑤ 参阅王鼎钧写于1990年代的自传《昨日的云》和《怒目少年》,他亲身经历的那些事件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例证。
⑥ 这并不是说政治、意识形态和派系斗争就不存在了,如周扬和鲁迅之间的恩恩怨怨。
⑦ 关于日本殖民“权力”在台北建筑风格上的象征体现,可参阅杰森·郭(Jason C. Kuo)的《战后台湾的艺术和文化政治》第二章。
⑧ 在同一篇文章《首与体——日据时代台湾小说中的颓废意识的起源》中,施淑描绘了台湾小说中的一种新型知识分子形态,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日本留学或刚刚从日本归来,心怀对日本都市的乡愁。这种“文化上的双乡”意味深长地将这些知识分子从他们的那些将自己奉献给社会改革的前任者那里分离出来。
⑨ 评论家对张爱玲的过度关注是证明这一点的最好例证。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它主要出现在女评论家(周蕾、邱贵芬)——她们更能善待张爱玲作品中的大众因素——的笔下。
(责任编辑:庄园)
Abstract: Taiwan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s reflected in many way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emphatically explores how the political and market factors inherited from the tradi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re revived and transformed in Taiwan literary field.
Key words: Taiwan literature, mainstream literature, political factors, popular literature, market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