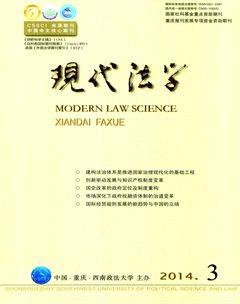国际民商事合同中的默示选法问题研究
刘仁山++黄志慧
摘 要:
在国际民商事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尊重当事人默示选法的意图,得到国内法与国际条约层面的广泛接受。但当事人默示选法在理论上还存在诸多争论。当事人的默示选法应当是对当事人业已存在的默示选法意图之认定,而不是对其选法意图的推定或假设,而且,当事人的默示选法在本质上是明示选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实践中,据以确定默示选法的因素包括仲裁(法院)选择条款、相关交易中的法律选择条款、在合同中“提及”或“并入”某国法律以及标准格式合同等。在认定当事人的默示选法时,应将上述指示因素以及合同和案件的整体情况综合起来一并考量。现有条约和国内法实践表明,对于默示选法的证明要求问题,各国尚未形成一致做法。我们应该在承认当事人默示选法的前提下,一方面要严格默示选法的证明要求,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默示选法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相关难题。
关键词:意思自治;默示选法;法律适用
中图分类号:DF97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4.05.13
意思自治原则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民商事合同(以下简称“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但在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问题上,尤其是国际合同当事人以默示方式选择适用法律(以下简称“默示选法”)及其效力问题,各国间仍存在甚为明显的差异。
对于默示选法,无论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中著名的合同自体法(the proper law of the contract)规则,还是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中的合同法律适用制度,均予认可。
关于英国、德国、法国等国默示选法的认可问题,参见:Gralf-Peter Calliess. Rome Regulation: Commentary on the European Rules of the Conflict of Laws[M].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11: 59. 另外,本文之所以分别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作为普通法系代表国家和成文法系代表国家的考察对象,是因为从相关国内法实践而言,普通法系的英国对于国际合同领域默示选法问题的实践,既开国际合同法律适用问题解决之先河,也不断影响着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就是其实践逐渐为相关国际条约所吸纳。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吸纳相关普通法规则的同时,在具体问题的实践上也有着较为鲜明的特点。在条约法领域,无论是1980年《欧共体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罗马公约》),还是2008年《欧盟关于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条例》(以下简称《罗马条例Ⅰ》),抑或是1994年《美洲国家间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墨西哥公约》)以及2012年《海牙国际合同法律选择原则》(以下简称《海牙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其他一些涉及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公约,如1955年《关于有体动产国际买卖法律适用公约》(第2条)、1986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7条)也均认可当事人的默示选法。《海牙原则》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针对国际合同一般法律适用问题而制定的示范法,尽管其并不具备法律拘束力,但作为一项比较法上的产物,其仍能反映两大法系在国际合同法律适用领域有关意思自治原则上的相互折中,也代表了国际合同法律适用领域意思自治原则的晚近发展。(参见:刘仁山. 国际合同法律适用中“意思自治原则”的晚近发展——《海牙国际合同法律选择原则》述评[J].环球法律评论,2013,(6):146.),均有原则性认可之规定。
从现有国际条约的实践看,《罗马公约》与《罗马条例I》无疑反映了大陆法系国家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统一化方面的晚近成就,《墨西哥公约》则可被视为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地区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上的统一化成果,而《海牙原则》则反映出代表世界各主要法律体系国家之间关于合同法律适用规则协调的最新进展,因此,本文将以上述条约及条约法文件作为国际条约法实践的考察对象。各国的理论及实践表明,默示选法所涉及的问题,首先是应否承认默示选法方式及效力问题[1]。除此之外,理论上主要涉及默示选法的性质与归类问题,而实践中主要涉及的则是确认当事人默示选法意图的指示因素以及默示选法意图的证明要求问题。
对于应否承认默示选法方式问题,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尽管也有分歧,但多倾向于承认该方式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100条之规定。(参见:中国国际私法学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M]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2;许军珂. 国际私法上的意思自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58.);我国现有立法实践明确采取的是否定态度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条。,但晚近司法实践似乎又有转向有限认可之势。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8条第2款。 因此,为求证认可默示选法方式之正当性,厘清实践中默示选法所产生的相关疑难问题,对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疑是必要的。
一、默示选法的理论争议:性质与归类
即使从上述认可默示选法的国家及相关条约法实践看,对于默示选法相关问题的争论也从未平息。其中,默示选法的性质及归类问题,往往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一)默示选法的性质问题
在根据意思自治原则确定国际合同争议准据法的过程中,法院(或仲裁庭)往往可能需要对当事人以默示方式表示的选法意图予以认定,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争议解决机构这一认定行为本身的性质呢?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实质上涉及对意思自治原则遵守的限度问题,进而也直接关系到承认合同当事人默示选法的正当性问题。
具体而言,争议解决机构对当事人以默示方式表达的选法意图之认定,到底是一种确认行为——对当事人已经存在但未能明示表达的真实意思所进行的确认?还是一种推定或假设行为——对当事人可能存在的选法意思所进行的推定或假设?简言之,根据当事人默示选法确定准据法,究竟是对合同当事人已经存在的选法意思表示确认的结果,还是对合同当事人仅仅可能存在的意思表示进行推定或假设的结果?对此问题,学界存在明显分歧。endprint
一类观点认为,默示选法中的“默示意思”,与所谓的“推定意思”或“假设意思”是存在区别的。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私法承认的当事人默示选法,系指契约准据法无明白约定时,就契约、文字、内容、性质等确定当事人有无“默示意思”(tacit intention, implied intention)。另外,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除了包括当事人明示以及默示的意思表示之外,还包括在无法发现当事人的默示意思表示时,由法官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推定或假设”(presumed intention or hypothetical intention)。换言之,是指在无法确认当事人的默示意思之时,法官得依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根据契约的客观事实或法定的硬性标准确立契约的准据法,从而使得法官利用这些事实或标准来推定适用于契约的准据法[2]。李浩培先生认为,假定的选择不能认为是默示选择,因为所谓假设,是指当事人如果认为有选择法律的必要将会作出的选择。亦即所谓假设的选择,实际上是在当事人并未选择法律的情况下,由法官代为作出的选择[3] 。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对“默示意思之认定”与“推定意思”、“假定意思”进行区分甚为困难,因为从实践来看,在确定合同准据法的过程中,无论在措辞上还是在表述上,这些概念往往可能互为通用[4]。如果当事人的意思能从“合同的条款和性质”及“案件的总体情况”得以证实,则其到底是认定当事人的默示选法意思,还是推定或假定当事人的默示选法意思?上述问题并非泾渭分明。英国学者戴蒙德(Diamond)教授甚至认为,无论是默示选法还是推定选法,均是在当事人未对法律选择问题作出任何意思表示之时,由法院决定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受特定法律的支配[5]。简言之,默示选法与推定选法,实质上都是由法院代替当事人作出的法律选择,并非当事人真实的选法意思。
本文认为,对于默示选法的认定,应将其界定为对当事人已经存在但未能明示表达的真实意思所进行的确认,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从默示选法的发展历程来看,以“假定意思”(presumed intention, hypothetical intention)、“推定意思”(inferred intention)作为确定默示选法依据的方法及实践,并以此作为默示选法理论(the doctrine of implied choice of law)的内涵,一直饱受批评或质疑。
默示选法理论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提出的所谓默示自体法(implied proper law of the contract),就是根据合同当事人的“假定意思”来决定的[4]104。而且,“假定意思”在该阶段也从未被认为是对当事人选法意图的虚构。也正因为准许对当事人选法意图的假定,这种默示自体法理论才得以活跃和发展。但从以“假定意思”作为确定默示选法的依据之初起,欧洲大陆包括皮耶特(Pillet)、尼波耶特(Niboyet)、齐特尔曼(Zitelmann)在内的国际私法学者就对该理论及方法持怀疑态度[1]8。到20世纪50年代,“假定意思”这一概念就被认为是虚幻的。一些学者认为,试图通过确定当事人假定的共同意思并以此为依据来决定合同准据法,显然是虚假和荒谬的,因为当事人在合同中隐形的共同意思之事实,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纯粹是虚构的[6]。到20世纪80年代,“推定意思”取代“假定意思”这一概念,成为合同自体法中确定默示选法的关键要素。对此,有学者认为,尽管较之“假定意思”而言,将“推定意思”作为默示选法的认定依据是一种可喜的转变,但依然存在缺陷[1] 7-8。
以“假定意思”或“推定意思”作为默示选法的认定依据,之所以在理论上受到诸多批评,主要因为它有悖于默示选法的真实含义。承认或认可合同当事人的默示选法,应以当事人确实存在真实的选法意思为前提。但由于这种真实意思并没有以明示的方式表现出来,才有对当事人的默示选法进行认定之需要。
第二,有关默示选法的现行实践表明,默示选法是争议解决机构对当事人未能明示表达的真实意思所进行的认定,而不是对当事人可能存在的选法意思所进行的推定或假设。如《罗马公约》的解释报告认为,即便合同中并不存在明示的法律选择,当事人的默示选择也必须是真实的。这种默示选择既可以从合同的条款推演而出,也可以从缔约环境(contractual environment)方面得出。该解释报告进一步强调,《罗马公约》第3条关于默示选法的规定应理解为:在当事人并没有基于明确的选法意图而可能作出法律选择时,不允许法院认定当事人有默示选法意图。在当事人没有明确默示选法之意思时,合同的准据法应根据《罗马公约》第4条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来决定[7]。
因此,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将默示选法的性质界定为对合同当事人之间已经存在但未能明示表达的真实意思所进行的确认,既是意思自治原则本身在法律选择方式上的具体要求,也是争议解决机构遵守意思自治原则的必然结果。
(二)默示选法的归类问题
默示选法的归类,即是要明确国际合同当事人的默示选法究竟是属于客观选法(即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一种形式,还是属于当事人明示选法的特殊表现形式。
对于国际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理论及实践一般遵循包括明示选法与默示选法在内的意思自治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之适用秩序。具体而言,就是首先适用当事人以明示方式或以默示方式选择的法律,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下,则适用依客观标准确定的与合同有真实和实质联系的法律。在这种“三阶层式”(the tripartite tiers)的选法方法中,默示选法与客观选法之间的界限甚为模糊[1]1。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当事人的默示选法究竟是合同自体法中客观选法的一种形式,还是合同自体法中明示选法的特殊表现?
对此,一种观点认为,默示选法应属客观选法范畴。如福康布里杰(Falconbridge)认为,所谓的“推定意思”,只不过是确定与交易有最真实联系国家之法律,其实是合同自体法的一种司法模式[1]8。英国学者诺斯(North)也认为,合同自体法理论中的默示选法只不过是可能的客观选法的范例而已,其可以使得“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确定变得相对容易[8]。加拿大学者泰特雷(Tetley)同样反对对当事人的默示意思进行推定:合同准据法的确定,从明示选法直接到最密切联系原则而不包括默示选法的路径是可取的,因为默示选法所依据的事实仅适用于确定最密切联系地[9]。显然,这类观点是将对默示选法的确定等同于对最密切联系地法的确定,亦即将默示选法与客观选法进行了合并。endprint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默示选法是明示选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如澳大利亚学者尼核(Nygh)曾明确指出,默示选法应被吸纳为明示选法的一种“子类型”(subcategory)[4]106。所谓的“推定意思”与“默示意思”都构成非明示选择(unexpressed choice)的方式,两者之间的微妙区分可以从推定意思和真实意思方面得出。尼核进一步认为,只有在当事人作出真实选择,而且这种真实的选择并非通过明确的法律选择条款表现出来时,才应被纳入默示选法的范畴[4]108。
本文认为,鉴于默示选法与明示选法在功能上的高度契合性,应该将默示选法归类为明示选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其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上述将默示选法归为客观选法范畴的观点,实际上否认默示选法作为一种选法方法本身的独立性。这种“合并说”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裂痕:从理论上讲,合同自体法的阶层式结构,决定了客观选法只有在当事人不存在默示选法意思时才可能被启用。在实践中,如果将默示选法意图的确认与客观选法方法合并,就会导致当事人可能存在的默示选法意图被人为地抹杀。即在当事人没有明示选法的情况下,这种合并式做法可能导致两种情况产生:一是对当事人是否存在默示选法意图进行确认这一必经程序,争议解决机构置之不顾,直接运用客观选法方法确定合同准据法;二是争议解决机构将依据默示选法意图确定合同准据法的过程与依据客观方法确定合同准据法的过程混同。这两种情况的一个共同点是:争议解决机构所确定的准据法,要么与当事人业已隐形选择的法律相去甚远,要么在法律适用结果上完全背离公平合理原则。这种合并式做法,表面上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争议解决机构未能注意到客观选法方法的依据与确认默示选法的依据二者间所存在的本质区别,实质上是没有充分考量默示选法的内在价值。同时,也是对默示选法在当今国际合同领域实践之真实状况的漠视。
第二,之所以将默示选法理解为明示选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对默示选法进行认定之前提,是合同当事人之间已经存在真实的选法意思,这正是意思自治原则得以产生效力并需要争议解决机构予以确认的条件,这与明示选法的内在要求在本质上是高度契合的。其二,于国际合同的当事人而言,其甚为关注的结果之一就是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当事人以合同形式来约定权利义务关系,初衷也在于此。合同领域的基本政策是保护当事人的期望,当然也包括对法律适用的期望。
关于当事人在合同领域法律适用期望的保护,参见:Eugene F. Scoles. Conflict of Laws[M].4th ed. St. Paul: Thomson West, 2004: 947.因此,将默示选法理解为明示选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与合同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目标是一致的。其三,实践中有判例支持这种观点。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其审理的Akai Pty Ltd v. Peoples Insurance Co Ltd.案中,法院中的多数意见认为,默示选法应该是明示选法的一种类型。
该案涉及当事人之间有关信用保单(credit insurance policy)的争议。谢勒(Sheller)法官和米格 (Meagher)法官均认为,无论是合同中的法院选择条款,抑或是与合同相关交易中的明示法律选择条款,其均可以表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真实意图,法院也应当认可其效力。(参见:Akai Pty Ltd v. Peoples Insurance Co Ltd,(1996)188 C L R 418.) 在立法实践方面,包括《罗马条例Ⅰ》和《海牙原则》在内的诸多国际法律文件,也是将国际合同中的默示选法与明示选法一并以意思自治原则的形式加以规定。
《罗马条例Ⅰ》第3条第1款规定,合同由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支配。选择必须是明示的,或者通过合同条款、案件情况予以阐明。《海牙原则》第4条规定:一项法律选择,或法律选择的任何调整,必须明示或显然明显地从合同的条款或情况得出。
二、默示选法的确定:基于对相关实践的考察
从相关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具体实践来看,争议解决机构对默示选法的确定,往往依赖于对相关指示因素(indicators)和案件的综合考量。这里所牵涉的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予以关注的:其一,在确定默示选法所依据的主要指示因素上,各国具体实践如何?其二,在确认默示选法过程中,如何解决当事人默示选法意图的证明问题?这也正是本文考察相关国内法与国际法实践的动因所在。
(一)确定默示选法的指示因素
既有实践表明,将仲裁或法院选择条款、相关交易中的法律选择条款、在合同中“提及”或“并入”某国法律、标准格式合同等作为确定默示选法的指示因素,是较为常见的做法。但这些因素中没有任何一项可以对当事人默示意思之确定起决定性作用。
1.仲裁(法院)选择条款
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仲裁地或管辖法院,即意味着选择了仲裁地法或法院地法,此即所谓衡量当事人默示选法意图的仲裁(法院)选择条款。《罗马公约》制定以前,除英国以外,这一实践就已在欧洲国家广泛存在,只不过对该指示因素的衡量,在不同国家及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4]116-118。
在1968年Tzortzis v. Monark LineA/B案中, 萨姆(Salmon)法官认为,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当事人选择在英格兰仲裁,即可无需迟疑地推断案件应适用英格兰法律。
就该案所涉及的事实来看,合同除了在仲裁条款上约定于伦敦进行仲裁外,其与英国无任何实质联系,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认为,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提供了高于其他任何指示因素之认定条件,从而使得作为仲裁地的英格兰之法律应为支配合同的准据法。(参见:Court of Appeal (Civil Division),Tzortzis v. Monark LineA/B,judgment of 24 January 1968,1 All ER(1968),949. )但在1970年的Compagnie Tunisienne de Navigation SA v. Compagnie d Armement Maritime SA案中, 英格兰法院开始降低仲裁和法院选择条款在确定默示选法意图中的权重。上议院(House of Lords)莫里斯(Morris)法官认为,将有关争议置于特定国家进行仲裁的协议,并不必然能够推定对该仲裁地国家法律的适用。当然,同案法官威伯弗斯(Wilberforce)发表的少数意见仍旧认为,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视为当事人已经选择仲裁地法律作为合同准据法的重要指示因素。尤其是在合同中可能存在不同国籍的当事人或者一系列的交易时,仲裁条款将会是唯一明确的指示。endprint
该案涉及一个由法国的船主和突尼斯的租船人在法国订立之合同。该合同约定将350000吨石油由突尼斯的一个港口运往另一个港口,运费在法国进行支付。双方当事人在租船合同中约定由合同产生之争议在伦敦仲裁解决。除了当事人约定在伦敦进行仲裁,该合同与英格兰并无任何联系,上议院认为,尽管租船合同中包含了合同受船旗国法支配的条款,但由于被用于石油运输的船舶同时保有多个旗国,因而该条款不能得以适用,上议院最终认定合同的准据法应该是法国法而非英格兰法律。(参见: House of Lords.Compagnie dArmement Maritime S.A. Appellants v. Compagnie Tunisienne de Navigation S.A. Respondents([1970] 3 W.L.R. 389)[EB/OL].(1970-07-14)[2014-02-10].http://law.queensu.ca/international/globalLawProgramsAtTheBISC/courseInfo/courseOutlineMaterials2012/internationalCommercialArbitration/CompagniedArmementMaritime.pdf.)
对于英格兰法院的上述做法,《罗马公约》及《罗马条例Ⅰ》的起草者均持赞同态度。《罗马公约》的解释报告指出,部分欧洲国家审理的案件表明,当事人对特定法院的选择,即是以一种非常确定的方式来表示愿意使其合同受法院地法支配,尽管这种认定常会受到合同其他条款和案件整体情况的制约。《罗马条例Ⅰ》规定,当事人之间协议授予某一成员国内一个或多个法院或仲裁庭以排他性管辖权来解决合同项下的争议,应被作为决定法律选择是否已获明确证实的一项因素加以考虑。
《罗马条例Ⅰ》详述12:“当事人之间有关将合同争议交由某成员国的一个或多个法院专属管辖的协议,应作为确定是否进行了明示法律选择的考虑因素之一。”上述实践无疑是对英国普通法规则——“选择了法院就选择了法律”(qui elegit judicem elegit jus),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
但与《罗马公约》及《罗马条例Ⅰ》不同的是,《海牙原则》对于合同中管辖权条款的态度是:当事人之间有关授予法院或仲裁庭管辖权以解决合同争议的协议,其自身并不等同于一项法律选择。
《海牙原则》第4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授予法院或仲裁庭管辖权以解决合同下争议之协议并不能等同于一项法律选择协议。”无独有偶,在《海牙原则》之前制定的《墨西哥公约》第7条,也采取了类似的否定式表述。即合同中的法院选择协议,并不能必然构成对合同准据法的选择。
《墨西哥公约》第7条规定:“合同受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支配,当事人对这种选择的协议必须明示或在没有明示协议的情况下,必须结合当事人的行为及合同的其他条款作为整体而明确得出。默示选择时,当事人选择特定法院并不必然表示选择了准据法。”当然,对于《墨西哥公约》的做法,学界有两种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墨西哥公约》实际上允许将当事人对特定法院的选择认定为对法院地法的默示选择。即尽管《墨西哥公约》采取了否定式表述方式,但是在效果上,公约实际上接受了普通法中“选择了法院即选择了法律”之推定[10]。另一种观点认为,《墨西哥公约》表明,其并不接受对法院的选择即是对合同准据法的选择之推定[10]107。
显然,对于上述否定式表述的规定,理论上已经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解读,这就使得利用法院或仲裁机构确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图时可能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选择法院也不意味着选择了法律的观点,也并没有否认确定选法意图时应该考虑选择争议解决机构的重要性。为此,本文认为,为实现条约法解释上的一致性,不妨采取这样的举措:如果合同中有关于特定国家的争议解决机构的排他性管辖协议,以解决因合同产生的或与合同相关的争议,该管辖协议虽然并不能明确证实当事人已选择该国法律,但在依据其他因素来确定当事人的默示选法时,这种管辖协议可以作为一个相对重要的指示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管辖协议作为一项最直接的双边协议,可以确保当事人只会在选定的法域而不是其他法域进行诉讼或仲裁。换言之,从法律选择的角度来看,排他性管辖条款的价值,在于它实际上附加了当事人之间在合同项下的消极义务(negative obligation,即合同违约等情形),这无疑可视为当事人共同的默示意思[11]。
2.相关交易中的法律选择条款
以相关交易中明示的法律选择条款来认定当事人的默示选法,主要分两种情况:其一,以相同当事人之间在先前的系列交易中存在的明示选法,来推定当前合同的准据法;其二,以不同当事人之间在与合同相关的交易中存在的明示选法,来推定合同的准据法[12]。依据英国普通法长期以来积淀之实践,以当事人之间先前交易或相关交易中的明示选法为依据,来确定因疏忽而未进行法律选择的本次交易的准据法,这一做法通常被认为是合理的[13]。
一般而言,在不存在明示法律选择时,法院能够以当事人先前交易中所选择的法律为依据来判断当前合同的准据法。对于这一来自普通法的规则,《罗马公约》和《罗马条例Ⅰ》的态度是不同的。《罗马公约》对该规则是认可的,公约的解释报告认为,相同当事人之间先前系列交易中已作的明示法律选择,在特定情况下可作为默示选法的指示因素[7]17。但《罗马条例Ⅰ》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疑惑的,从《罗马条例Ⅰ》的详述20和21来看,其似乎隐含着先前系列交易或相关交易中的明示选法,可以作为推定条例第4条第4款规定的确定合同准据法的一种方法。
《罗马条例Ⅰ》详述20指出:“如果合同与本条例第4条第1款、第2款所指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显然具有更密切联系,则‘避让条款应规定适用该另一国家的法律。为确定该国家,还应考虑该合同是否与其他一个或多个合同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详述21指出:“未选择法律时,如果准据法既不能根据将合同归入特定合同种类的方法确定,又不能确指实施特征性履行的当事人的惯常居所地国法,则合同由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支配。在确定该国家时,还应考虑该合同是否与其他一个或多个合同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模糊的表述,导致法院在根据条例第3条第1款所规定的指示因素来确定默示选法时产生困惑。对此,有学者认为,《罗马条例Ⅰ》的详述20、21应被理解为:在具备默示选法的条件时,应当依据建立在意思自治原则基础之上的默示选法而非客观选法方法来确定合同的准据法[1]20-21。endprint
但《罗马公约》和《罗马条例Ⅰ》均未对“与合同相关的交易”予以明确。在这一问题上,作为《罗马公约》缔约国的英国却有较为独特的实践。在1982年Broken Hill Pty v. Xenakis案中,法院认为,如果当事人在主合同中已作出明确法律选择,就可以据此来认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也作出同样的法律选择,以此来确定该保证合同的准据法。而且,这种方法可以在不同类型的合同中适用,而不限于主合同与保证合同。
该案所涉及的主债务合同和保证合同的当事人并不相同:主债务合同的当事人约定了适用于合同的准据法,而保证合同的当事人并未约定相应的准据法。法院认为,承担担保责任的保证人与承担主债务责任的主债务人在清偿主债务的意图上是一致的,故而调整保证合同的准据法应该与调整主债务合同的准据法相同。(参见:Queens Bench Division (Commercial Court),Broken Hill Pty v. Xenakis judgment of5 February,1982,2 Lloyds Rep.(1982),304 et seq.)在随后的Bank of Baroda v. Vysya Bank Ltd案中,法院不仅遵守了这一规则,而且将与合同相关的交易扩展至开证行和卖方(信用证的受益人)之间的合同以及承兑行和买方之间的合同。
在该案中,货物买卖合同的当事人约定用跟单信用证方式支付货款,这种支付方式使信用证的开出行和承兑行也牵涉到该货物买卖中,曼斯(Manse)法官由此认为,开证行和卖方(信用证的受益人)之间的合同以及承兑行和买方之间的合同,应该受同一法律支配。(参见:Queens Bench Division (Commercial Court),Bank of Baroda v. Vaisya Bank Ltd,judgment of 13 December 1993,2 Lloyds Rep.(1994),87 et seq.)
以相关交易中的法律选择来推定合同当事人的默示选法,虽然英国在特定案件中的实践有其合理性,但本文认为,不应将其绝对化。从确保当事人真实意思实现的目的来考虑,根据当事人在相关交易中的法律选择条款来确定默示选法意图时,务必考虑案件的整体情况。
3.“援引”或“并入”某国法律
当事人在合同中“援引(reference)”某一特定国家的法律,或者将特定国家的法律规则“并入”(incorporation)合同,这也是实践中出现的与默示选法之确定相关的问题。对此,部分国家是予以区别对待的[12]1572,但从《罗马公约》的解释报告看,公约一方面将二者同等对待,作为确认当事人可能选择特定国家法律的指示因素;另一方面,公约充分认可该指示因素作为确认当事人默示选法的依据。在当事人于合同中提及诸如《法国民法典》这类众所周知的法律时,尤其如此。
当然,合同当事人“援引”或“并入”某国法律的行为,到底意味着当事人意欲让已经选择的相关准据法来支配整个合同,还是仅仅意味着当事人将外国法的一些规定并入合同作为合同条款?对此,无论是对当事人选择法律意图的推定,还是对当事人选择法律意图的确认,均存在解释上的问题[14]。对于该问题,戴蒙德(Diamond)教授的态度是甚为明确的:“在当事人不仅仅提及了法国民法典,并且同时存在其他明确的指示因素指向法国法,诸如合同使用法语作成、运用法国法的技术性表达、提及《法国民法典》的其他相关条款以及其他法国法等情形,法院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当事人意欲适用法国法。”[15]
因此,从《罗马公约》的实践及相关理论观点看,即使合同当事人有“援引”或“并入”事实,在确认当事人默示选法意图时,仍必须结合合同条款和案件其他情况予以综合考虑。
4.标准格式合同
当事人如果选择了某一特定标准格式合同但未明示选择某一法律,是否可以认定当事人有使该合同受某一特定法律体系支配的意图?对实践中这一较为常见的问题,《罗马公约》的态度是肯定的。从《罗马公约》的规定看,如果交易是通过某一特定且众所周知的格式合同完成的,法院就能够认定当事人所选择的准据法。因此,根据《罗马公约》的要求,在伦敦违约的再保险合同,即意味着该应适用英格兰法律[12]1574。
《罗马公约》的上述态度与英国的实践是一致的。在Amin Rasheed Shipping Corp v. Kuwait Insurance Co案中,当事人在合同中使用了劳埃德保险单(Lloyds policy),法院面临的问题是应适用科威特还是英格兰的法律,最终法院判定合同应受英格兰法律的支配。
该案涉及在迪拜营业的利比亚公司为其货船向科威特保险公司投保的再保险合同,该保单根据英国劳埃德海上保险的标准格式合同订立。保单中并未明示约定准据法,但法院认为,当事人有以英国海商保险法为其权利义务之依据的意图,依据《罗马公约》之规定,当事人在伦敦市场经由经纪人所定之再保险合同,默示选择了英国法为合同准据法。(参见:House of Lords,Amin Rasheed Shipping Corp v. Kuwait Insurance Co,judgment of 7July 1983,AC (1984),50 et seq.)对此,迪普洛克勋爵(Lord Diplock)认为,除非通过援引英格兰的法律以及英格兰海商方面的司法政策,否则不可能解释为何英格兰法律或规定可以决定合同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 但他同时也认为,当事人选择劳埃德海事保险标准合同,即意味着规范该标准格式合同的英格兰法律可作为唯一的法律体系支配该合同[4]115。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将标准格式合同作为确定默示选法的一项指示因素,大多适用于租船和海上保险等特殊法律领域,在一般国际商事实践中并不常见。 但即使是在这些特殊领域内,若当事人在标准格式合同的准据法问题上保持沉默,法院就不得单纯依据标准格式合同来确定合同准据法[16]。endprint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以上述四种指示因素确定当事人默示选法的实践之考察,并不意味着确定当事人默示选法的指示因素仅局限于上述常见情形。无论在何种情形下确定当事人的默示选法意图,均存在一个关键问题——是应当对上述各指示因素进行综合衡量,还是应当将上述一种或多种指示因素与案件的其他情况结合起来予以综合考量?从现有实践来看,在通常情况下,法院可以通过所有的指示因素来探寻当事人已经作出的真实的法律选择[17]。这即意味着法院除考虑上述列举的指示因素以外,还应当对合同其他条款及案件的情况加以综合考虑。
在确定当事人的默示选法时,法院应考虑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其包括合同的协商过程、当事人在共同关系中建立的一致性和惯例、商业上所有权转移的关税、当事人随后的行为。(参见: Mikhail R. Badykov. The Russian Civil Code and the Rome Convention: Implied Choice of the Governing Law[J].Review of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Law,2008,(33): 187.)
(二)对默示选法的证明要求问题
前述确定当事人的默示选法方法,需要综合考量案件中诸多指示因素及案件其他情况。而且,为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默示选法的标准必须是相当严格的。但继而产生的问题是,对当事人默示选法予以证明的要求如何?即当事人默示选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证明,选法意图方可最终得到认定?从相关条约法与国内法实践看,各国在默示选法证明要求方面的差异也甚为明显。
1.条约法实践
在默示选法的证明问题上,相关代表性国际条约的实践表明,对于当事人默示选法之证明所要求的程度,各条约似乎处于一种徘徊状态。
对于当事人默示选法的意图,《罗马公约》要求应以“合理的确定性”(reasonable certainty)来阐明(第3条第1款)。公约的解释报告进一步认为,不允许法院在当事人可能作出但并没有明确意图之时,推定当事人已作出法律选择。这里所谓默示选法能够以“合理的确定性”被阐明,是一个同时涉及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有学者认为,《罗马公约》中“合理的确定性”之要求表明,法院对默示选法的认定,应当结合商业需要及实际。亦即法院的认定结论,必须是如同一个理智的和经验丰富的商人得出的结论。换言之,这种要求的潜在含义是,法院需要将自己置于商业理性的平台上,并以此为基础来决定对事实之衡量是否足以确定当事人选择特定法律的意图[18]。
对当事人默示选法的证明要求问题,是否应进行更为精确之界定?《罗马条例Ⅰ》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回答。相对于《罗马公约》而言,《罗马条例Ⅰ》对于默示选法的证明要求是有所不同的。在《罗马条例Ⅰ》的起草过程中,欧盟委员会特别提及了德国和英格兰法院所采取的较为直接的方法,即在默示选法意图和纯属假定的选法意图之间划定界限。因此,《罗马条例Ⅰ》第3条第1款要求,“一项默示的法律选择能够明确地从合同的条款及案件的情况被证明”(clearly demonstrated by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o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对此,有学者认为,相较于《罗马公约》,《罗马条例Ⅰ》显然提高了默示选法被明确证明之要求,即对默示选法完成了从《罗马公约》下的“合理的确定性标准”(reasonable certainty test)到《罗马条例Ⅰ》下的“明确的证明性标准”(clearly demonstrated test)之转变。英国学者布瑞格斯(Briggs)认为,这种显著的变化,实际上是欧盟委员会试图改变英格兰和德国法院所乐于接受的做法,并对英国、德国与不轻易接受默示选法的法国在实践上之差异予以调和[19]。
但也有学者认为,《罗马条例Ⅰ》规定的这种较高“证明”要求,可能招致不必要的程序问题[20]。为此,《墨西哥公约》并未对当事人默示选法规定严格的证明标准。荣格(Juenger)因此认为,《墨西哥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的默示选法,实际上赋予了法官和仲裁员相当灵活的自由裁量权。该条所提到的“当事人的行为”、“合同的条款”,已经足以允许裁判者依据“默示意思”来实现其意欲达成的结果之目的[10]388。
上述默示选法的证明要求问题,显然引起了《海牙原则》工作组的重视。工作组认为,应在有限情形下承认当事人的默示选法。为此,在对不同标准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工作组出于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并鼓励当事人明确选择合同准据法之考虑,采用了要求默示选法意图应从“合同的条款或案件情况中清楚表明”(appear clearly from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tract or the circumstances)之措辞。
关于该问题,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工作组的意见中有详细说明。(参见:Consolidated Version of Preparatory Work Leading to the Draft Hague Principles on the 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EB/OL].(2012-10-01)[2014-05-12].http://www.hcch.net/upload/wop/contracts_2012pd01e.pdf.)对于起草过程中很多专家建议的“明显清楚地”(manifestly clear)、“明确的”(evident from)之措辞,均因其涉及程序性的证明要求而被否定。
也有学者认为,当事人的默示选法能够被“明确地证实或阐明”(clearly established or clearly demonstrated),是一种立场较为折中的措辞,在赋予当事人默示选法以效力与确保合同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方面,该措辞维系了较好的平衡。(参见:Brooke Adelf Marshall. Reconsidering the Proper Law of the Contract[J].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102,(13): 14.)endprint
从《罗马条约》到《罗马条例I》对默示选法证明要求的提高,到《墨西哥公约》主要交由争议解决机构裁判,再到《海牙原则》的中庸要求,这些都表明,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认可默示选法的宗旨,就是要在坚持意思自治原则的前提下,公平且有效地解决合同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如果对默示选法证明要求过高而导致新的程序问题,显然与当事人有效解决争议的期望是相悖的。而且,确认默示选法,仅仅只是在解决合同争议法律适用过程中遵循相关原则的一个阶段或者环节而已。合同争议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除了可以依据意思自治原则外,还可以依据包括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内的其他以客观方法表现的原则。因此,如果因默示选法的证明要求而导致合同准据法确定的拖延,不仅无益于合同争议纠纷的有效解决,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
2.国内法实践
从普通法系和成文法系部分代表国家的实践看,各国对于默示选法的证明要求问题,同样存在较大分歧。从依据管辖权条款确认默示选法的意图这一实践中,便可见全豹。
英国的判例规则一直坚持,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某一特定国家法院管辖的约定,表明当事人有适用该特定国家法律的明显意图。但英国的实践也表明,在该规则的实施过程中,法院地法往往被优先适用。其主要表现为:含有法院选择条款的绝大多数合同案件,最终都被认定为当事人有选择适用法院地法之意图[21]。而且,英国在实践中采用任意性冲突法 (facultative choice of law) 理论,依据该理论,如果没有任何一方当事人提出适用其意欲适用的合同准据法,法院将会排他性地依据英国的法律来裁判案件[22]。亦即从证明要求来讲,采用任意性冲突法理论所确定的当事人之默示选法,无须过多综合考量案件情况。哈特雷(Hartley)教授也认为,依据任意性冲突法理论,只要当事人在诉讼中没有主张援引外国法,就可以认为其已默示选择法院地法。因为当事人进行法律选择的初衷是为了其自身的利益,在双方当事人均未要求适用外国法的情况下,法院仍执意适用外国法是荒谬的。即如果没有任何一方当事人提出其所选择的准据法,英格兰法院将会认为当事人已经默示选择适用英格兰法律[22]291。显然,在证明当事人默示选法意图方面,对于这种特殊的默示选法,法院并不需要过多依赖合同的条款及案件的其他情况。
作为大陆法系代表国家之一的德国,在确定《罗马公约》下当事人默示选法意图问题上,却因实践中的不一致而饱受批评。但长期以来,德国法院一直认为,当事人对特定国家法院或仲裁庭的选择即构成对该特定国家法律的选择适用。总体而言,德国法院关于默示选法的证明之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真实性选择的要求上,即对于当事人的默示选法,应该依据合同条款和案件情况能够得到明确证实。当然,大多数案件表明,在当事人请求的情况下,法院积极地将当事人的默示选法推定为法院地法。德国的这类实践,得到同属大陆法系的瑞士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追随,这些国家也将法院选择条款和仲裁条款作为当事人默示选法中最为重要的指示因素[21]309。
以合同中存在的法院或仲裁庭条款来认定当事人意欲使该合同受法院地或仲裁地法律的支配之做法,法国法院在实践中同样予以认可[21]308-309。根据梅耶(Mayer)等学者的考察,相当部分的法国判例对当事人默示选法的认定,往往依据的是合同中的法院或仲裁庭条款[23]。但与德国和英国法院的实践相比,对于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意图的确定,法国法院则以其异常严格的证明要求而著称。法国法院通常认为,依据法院或仲裁庭条款来确定当事人(对法院或仲裁地法)的默示选择,应该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得到充分且合理的确定性证明。而且,与前述英格兰法院的做法不同的是,法国最高法院曾经指出,在合同案件中,下级法院有义务提醒当事人法律选择这一问题,除非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作出了适用法院地法的明示选择[23]346。
总之,前述代表性条约法的实践表明,尽管相关合同法律适用的国际公约均对默示选法作出了规定,但由于措辞和表述上的差异,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都对各公约所规定的默示选法之确定作了多种解读。但是,对于当事人的默示选法之证明要求,从《罗马公约》下“合理的确定性标准”转向《罗马条例Ⅰ》下的“明确的证明性标准”,以及《墨西哥公约》与《海牙原则》均要求“必须能够从合同的条文(当事人的行为)及合同条款整体上得出”,且均特别强调合同中的法院(仲裁庭)选择协议并不等于当事人已就合同本身选择了适用的准据法,这些都表明,在默示选法的确定标准问题上,要求综合考虑案件的整体情况,强调当事人选法意图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已成基本态势。前述国内法实践表明,各国对默示选法的确定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以英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对默示选法之确定,法官所考虑的因素以及相关证明要求均有所不同。以法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对当事人默示选法之确定,却施以严格的证明要求,其目的在于确保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实现。
三、默示选法的实施:认可理由与实践难题
由于默示选法在实践中存在证明困难,而且在证明的要求上目前尚未形成一致做法,所以有学者认为,应摒弃任何形式的默示选法,只保留明示的法律选择和当事人未选择法律时准据法确定的客观方法。这种认识无疑使得意思自治原则面临严峻挑战,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当事人法律选择不明确或未作法律选择时,即便采用客观选法方法来确定合同准据法,也并不能确保合同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目标之实现。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国际私法领域所有的法律适用原则中,法律适用结果不确定性的缺陷,并不为默示选择法律方式所独有;另一方面,在目前各国对默示选法均有相应限制的情况下——要求必须在十分明显或确定的条件下才能认定合同当事人的默示选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法律适用结果的公正性与合理性[24]。而且,实践中当事人的默示选法得到法院认可之情形并非鲜见。
仅就我国而言,如广东省高院2004年审理的“深圳市华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汕头市国际货运代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涉及本国人对适用本国法的沉默,武汉海事法院2001年审理的“汽船相互保险协会(百慕大)有限公司与蓝贝壳航运有限公司船舶保险合同保险费纠纷案”涉及专业当事人对格式化选法条款的沉默,深圳中院2002年审理的“开平味事达调味品有限公司与鹰田食品(深圳)有限公司、银鹰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涉及担保合同附属于主合同,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本文对默示选法的内因予以探讨,其实践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认可默示选法之同时,对于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疑难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endprint
(一)默示选法的认可理由
从前述考察可知,默示选法有着坚实的判例法基础,可以说,默示选法的确立是判例法长久以来演化之结果。尽管有学者建议,没有必要背负英国判例法进化过程的历史包袱,应将当事人自主原则限定在明示选法之情形[13]174。但是,就立法实践而言,即使缔约国中大陆法系国家占多数的欧共体《罗马公约》及其转化后的欧盟《罗马条例Ⅰ》,其关于默示选法之规定,也均对前述英国普通法规则予以继承和吸纳。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海牙原则》及美洲国家间的《墨西哥公约》中,默示选法也同样占有一席之地。为此,本文认为,从意思自治原则的历史起源、实践需求及发展态势来看,作为已经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选法方式,默示选法还应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明确的认可。
其一,从历史起源来看,意思自治原则得到合同当事人自觉或不自觉的遵守,最初就是以当事人的默示选法方式而得以表现的。“意思自治说” 作为合同法律适用的一种理论,可以追溯至15世纪后期注释法学派的代表者诺忽斯·柯迪乌斯(Rochus Curtius)所提出的观点。柯迪乌斯认为,之所以要适用合同缔结地法,是因为当事人已默示地同意适用该法[25]。直至16世纪,法国学者杜摩兰(Dumoulin)才在柯迪乌斯学说的基础之上,较为明确地提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事实上,在著名的“加内夫妇财产案”中,杜摩兰也是将夫妻财产制问题识别为一种合同,从而将夫妻财产问题作为合同问题,适用当事人默示选择的缔约地法律。
1525年,有人就加内夫妇夫妻财产制问题请教杜摩兰,问他是否有可能避免适用该夫妇各项财产所在地的习惯规则
。杜摩兰表示赞成对全部财产适用加内夫妇结婚时的共同住所地——巴黎的习惯规则。其理由是,夫妻财产制应该被视为一种默示合同,可以认为,夫妇双方已经将该合同置于其婚姻住所地法的支配之下。(参见:保罗·拉加德,亨利·巴蒂福尔. 国际私法总论[M].陈洪武,等,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310.)可以说,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默示选法是合同领域意思自治原则的主要表现形式[26]。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前述默示选法应归类为明示选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之论断。因而,就当事人真实选法意思的实现而言,默示选法是不可或缺的。而且,
无论是明示选法还是默示选法,根本目的都是要在国际合同领域更好地贯彻意思自治原则,以实现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进而使合同受当事人所希望适用的准据法支配。因此,默示选法所体现出的价值与理念,与明示选法是一致的。
其二,从实践需求而言,承认默示选法,有助于避免在当事人未明示选法的情况下,法院或仲裁庭径直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或“特征性履行原则”来确定合同准据法,从而有助于避免对当事人业已表达的法律选择意愿发生忽视或曲解之情形。特别是在当事人由于受法律专业知识和经验所限,时常不能准确表达合同受某种法律支配之意愿
德国学者沃尔夫指出:“明白订立应当适用的法律是不很常见的。这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当契约是由法律顾问帮助订立的时候,或者在订约当事人使用特殊的契约格式(这种格式大多数是由法学家们起草的)的时候,才会发生。”(参见:马丁·沃尔夫. 国际私法[M].李浩培,汤宗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67.)
,而通过对合同条款或者案件的其他情况加以综合考虑,当事人默示选法的真实意图又能得以确定的情形下,如果法院或仲裁机构径以客观方法来确定适用于合同的准据法,不仅会有悖合同当事人的预期,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加剧合同法律适用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为了真正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满足实践之客观需求,根据当事人的默示意思确定合同准据法是必要的。
其三,从发展态势观之,默示选法作为当事人明示选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与明示选法共存,并共同构成完整的意思自治原则体系,是当今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客观结果。从理论上讲,早在合同自体法的主观论阶段,合同自体法就包括当事人明示选法及默示选法。在The King v. International Trustee for the Protection of Bondholders案中,阿特肯法官(Lord Atkin)明确指出,合同自体法是指当事人意图适用的法律,当事人的意图将由其在合同中所表示的意图来决定,如果有这种意图的话,那将是明确的;如果没有明确表示的意图,这个意图将由法院根据合同条款和有关情况来推断。(参见:The King v. International Trustee for the Protection of Bondholders,[1937] A. C. 500,529.) 这种共存的客观性表现就是,在诸多有关合同法律适用的国内立法及国际条约中,默示选法与明示选法一并得到广泛接受[27]。当然,这些立法均要求,为反映当事人法律选择的真实意图,对当事人默示选法之确定,必须摒弃法官的主观臆断。因此,如果我们将默示选法的性质界定为对当事人未能明示表达的真实意思所进行之认定,而不是对当事人选法意图的假定或假设,在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前提下,承认默示选法并不会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带来扭曲。
总之,在合同领域对默示选法予以回避之做法,既表明我们还未充分认识到默示选法在国际合同领域可以发挥的独特作用,也反映出我们实质上还未认识到默示选法在确定合同准据法方面所蕴含的积极的价值意义。
(二)默示选法的实践难题
前述表明,对于默示选法问题,主要条约法实践及国内法实践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应否承认默示选法的问题,而是在承认默示选法的前提下,如何确保对当事人默示选法意图之认定的客观与公正性问题。为此,进一步明晰并处理好默示选法在实践中的相关难题,就尤为必要。
第一,提高法律适用确定性与避免法律适用的“法院地法主义”问题。对于默示选法问题,似乎存在两个极端:一是如部分学者所认为的,默示选法容易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28],因而,对意思自治原则的贯彻,应局限于承认合同当事人明示选法的方式;另一极端却是,在确保法律适用确定性的外衣下,默示选法往往成为受案法院频繁适用法院地法的藉口。这不仅与意思自治原则的本质相悖,还与国际私法的目标格格不入。endprint
仅从提高法律适用确定性或者仅从避免法院地法主义这两个单一角度出发,对上述观点的合理性应予肯定。但是,影响法律适用确定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默示选法仅是其中一隅;同样,导致法院地法主义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大量法院地法倾向的实践表明,默示选法与法院地法主义的因果关系似乎甚为勉强。这是我们客观看待提高法律适用确定性与避免法律适用的“法院地法主义”问题的前提性认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国际合同当事人已经约定有管辖权条款的情况下,合同争议发生后,当事人更为关注的是争议解决的效率问题[29]。从这个意义上讲,既然当事人选择特定法域的争议解决机构且争议为该机构所受理,从管辖依据的角度而言,不能否认合同与争议解决机构的法域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在这种特定条件下,如果综合考虑合同条款及合同争议的整体情况,仍可以将当事人的默示选法认定为法院地法,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当事人的预期。
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法院地法能否适用,而在于法院不能仅凭少量或偶然的指示因素或案情情况便将当事人的默示选法认定为法院地法。
第二,对默示选法的认可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问题。前述合同中的标准格式、管辖权选择条款和采用特定国家法律用语等,往往是确定默示选法的指示因素,而根据这些指示因素所确认适用的,往往是西方法制发达国家的法律。由此产生的顾虑是,如果贸然承认默示选法,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当事人造成不利影响。
前述认定默示选法意图的实践表明,尽管从判例法角度而言,合同中的法院(仲裁)选择条款、“提及”或“并入”某国法律以及标准格式合同等,均可能成为确定当事人默示选法的重要指示因素,但在很多情况下,上述指示因素只是确定当事人默示选法的考量因素之一,法院通常应将案件的其他情况结合起来以确定当事人的默示选法。换言之,对当事人默示选法之确定,上述指示因素中的单独一项,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包括标准格式条款在内的这些指示因素中的任何一项,尽管在认定当事人默示选法中有其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但还不足以构成默示选法实施的障碍。
另一方面,根据格式合同等因素所确定适用的所谓法制发达国家之法律,对发展中国家当事人可能不利。但这到底是由默示选法带来的后果,还是国际民商事交流的历史使然?其本身所反映出来的,不是要不要承认默示选法的问题,而是国际民商事新秩序构建中另一更深层次的问题。
第三,默示选法与最密切联系地法在实施中的分界问题。前述对默示选法的认定要求所出现的日益严格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对当事人选法表意的真实性与客观性要求上,这就要求法院在确认默示选法的过程中,除了依据相关指示因素外,还应综合考虑合同的条款和案件的其他情况。这样就产生了应如何对默示选法与所谓最密切联系地法确定的分界问题。
当然,与最密切联系地法原则相比,承认默示选法的宗旨在于,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出发,使合同争议得到符合当事人意愿的解决。因此,尽管在确定默示选法的过程中,除前述指示因素外,要求综合考虑合同条款及案件整体情况,不免使得默示选法之确定与合同最密切联系地法之认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但需要明确的是,默示选法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最大区别在于:在默示选法的确定过程中,争议解决机构对合同相关因素与情况的考量,出发点在于确保当事人真实选法意图的实现,而且,争议解决机构主要是将与当事人的主观意志有关的行为因素作为确定其默示选择法律意图的依据。因为与当事人主观意志有关的行为因素,往往是当事人选择法律心理活动的表现,因而只有这类因素所外化的相关行为才可以被认为符合严格意义上的“意思自治”[24]65。在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准据法的过程中,争议解决机构更为关注的是与合同、当事人及案件整体情况有关的各类客观因素。亦即争议解决机构只有在不存在当事人明示或默示选法意图的相关指示因素的情况下,才能根据相关客观因素来确定与合同争议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第四,默示选法的确定是否需要告知并得到当事人的认可问题。即争议解决机构在最终认定当事人的“默示选法”之后,是否应将之告知当事人并得到当事人的认可问题。对此,本文认为, 为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进一步明晰默示选法与最密切联系原则在确定合同准据法之中的界限,争议解决机构对默示选法的确定需要告知并得到当事人的认可。
既然默示选法是对合同当事人之间已经存在但未能明示表达的真实意思所进行的确认,而且在实践中,默示选法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案件的整体情况,以便充分证实默示选法意图的真实性与客观性,那么,争议解决机构所确定的默示选法,就应该是当事人真实选法意思的体现。但由于默示选法的确定往往涉及事实的证明程度问题, 因而,在默示选法认定的具体实践中,依旧难以避免争议解决机构所确定的“默示选法”并非体现当事人真实选法意图之可能。由此,要求争议解决机构将所确定的“默示选法”告知当事人,并赋予当事人对该“默示选法”提出异议的权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讲,争议解决机构将其确定的“默示选法”告知并得到当事人的认可,既是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尊重,也是遵守意思自治原则的表现;从实践上讲,这种做法充分体现了默示选法与客观选法方法在确定合同准据法时的区别所在。因为争议解决机构根据包括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内的客观方法确定合同准据法,除了要在判决或裁决中说明理由外,并不需要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当然,争议以调解方式解决的除外)。
四、结语:当事人潜在选法表意之实现途径
当事人的默示选法,已经从最初的作为国际合同领域意思自治原则的萌芽形态,逐步成为当今践行意思自治原则的一种特殊形式。从理论上讲,承认默示选法并厘清相关实践问题,有利于明晰意思自治原则与客观选法方法之间的界限;从实践上讲,在当事人虽未明示选法但存在默示选法意图的情形下,承认默示选法,也有利于避免法院径直以特征性履行方法或最密切联系原则来确定合同准据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默示选法的确定,既有赖于争议解决机构对特定指示因素的考量,也有赖于争议解决机构对合同条款和案件其他情况的综合考量,这样虽有可能会加剧默示选法证明的复杂性,但对于默示选法的最终认定而言,在避免武断结果之产生方面,无疑具有积极意义。endprint
对于国际合同当事人的默示选法问题,各国理论与实践虽然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但默示选法在实践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在于,默示选法作为明示选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是当事人潜在的真实选法意思的实现途径。为防止扭曲或忽视当事人真实选法之表意,如果立法及实践对默示选法采认可态度,那么,在确定合同准据法的过程中,默示选法将发挥独特功用。
尽管默示选法在实践中还面临一系列问题,但相对于灵活性更强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而言,由于默示选法所禀赋的意思自治原则之价值,强调对当事人潜在法律选择意愿的尊重,这就决定了默示选法在实现当事人对合同法律适用结果的预期方面,与国际合同法律适用所应恪守的法律适用结果的确定性、可预见性以及公平性之基本政策是完全吻合的。ML
参考文献:
[1]Brooke Adelf Marshall.Reconsidering the Proper Law of the Contract[J].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102, (13): 12-14.
[2]游启忠. 论国际私法上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于我国最高法院判决运用之研析[J].中正大学法学期刊,2001,(5):270-272.
[3]李浩培.李浩培文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03.
[4]Peter Nygh. Autonomy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06.
[5]Aubrey L. Diamond. Harmonization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Relating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J].Recueil des Cours,1986,(199): 258-259.
[6] P. B. Carter. The Proper Law of the Contract[J].International Law Quarterly,1950,(3): 255,259.
[7]M. Giuliano and P. Lagarde. Report on the Rome Convention[R].Official Journal C282,1980:17.
[8] Peter North.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Problems in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M].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3: 106.
[9]威廉·泰特雷. 国际冲突法:普通法、大陆法及海事法[M].刘兴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51.
[10]Friedrich K. Juenger. The 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Some Highlights and Comparisons[J].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1994,(42): 381,388.
[11]Mary Keyes. Jurisdiction under the Hague Choice of Courts Convention: Its Likely Impact on Australian Practice[J].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2009,(5): 181,202.
[12]Dicey,Morris and Collins. Conflict of Laws[M].14th ed. London: Sweet and Maxwell,2006: 1574.
[13]陈隆修. 中国思想下的全球化选法规则[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176.
[14] Campbell McLachlan. Splitting the Proper Law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J].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1990,(61): 314-315.
[15]Aubrey L. Diamond. Conflict of Laws in the EEC[J].Current Legal Problems,1979,(32):160.
[16]Giuditta Cordero Moss. Tacit Choice of Law,Partial Choice and Closest Connection: The Case of Common Law Contract Models Governed by a Civilian Law[M].Copenhagen: Gyldendal,2007: 376.
[17]P. North,J. Fawcett.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M].13th ed. London: Butterworths,1999: 563.
[18] Peter Kaye. The New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ntract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mplementation of the EECs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Conven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under the Contracts (Applicable Law) Act 1990[M].Aldershot: Dartmouth,1993: 150.endprint
[19]Adrian Briggs. The Conflict of Laws[M].2n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166.
[20]Jan L. Neels,Eesa A. Fredericks. Tacit Choice of Law in the Hague Principles on 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J].De Jure Law Journal,2011,(44): 106.
[21]Ole Lando. The Conflict of Laws of Contracts: General Principles[J].Recueil des Cours,1985,(189): 308.
[22]T. C. Hartley. Pleading and Proof of Foreign Law: The Major European Systems Compared[J].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1996,(45): 291.
[23]M.JnterJareborg.Foreign Law in National Court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Recueil des Cours,2003,(304): 346-347.
[24]刘仁山.“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适用中的适用限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64-65.
[25]保罗·拉加德,亨利·巴蒂福尔.国际私法总论[M].陈洪武,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305.
[26]宋晓. 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14.
[27]刘仁山. 国际私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224.
[28]保罗·拉加德,亨利·巴蒂福尔. 国际私法各论[M].曾陈明汝,译. 台北:正中书局,1997:302.
[29]Gilles Cunibert.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for Contracts: The Most Attractive Contract Laws[EB/OL].(2014-02-10)[2014-05-06].http://ssrn.com/abstract=2393672.
[HT]
Research on Implied 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Contracts
LIU Renshan, HUANG Zhihui
(Law Schoo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China)
Abstract:
As for the Problems of the law applicable to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contracts, respecting the parties intention of implied choice of law has been broadly accepted on the levels of domest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treaty law. There are also many academic arguments concerning implied choice of law. The parties implied choice of law shall be the ascertainment of the parties actually existing intention rather than presumed intention or hypothetical intention. Furthermore, the parties implied choice of law should be treated as a special form of express choice of law substantially. In practice, the indicators used to ascertain the parties implied choice of law include the selection of arbitration (court) clause, the choice of law clause in relevant transaction, the contract referred to a national law or incorporated the above law into the contract as well as the contracts with standard form. In determining the parties implied choice of law, the above indicators must be considered as a whole with the terms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of the contract. Correlative practices on the levels of international treaty law and domestic law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exists no formed consistency on the problem of the testing requirement of implied choice of law. On the precondition of the recognition of implied choice of law, we should impose strict standard on its proof on the one hand, and further to clarify the difficult questions which should be notic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mplied choice of law on the other hand.
Key Words: party autonomy; implied choice of law; application of law
本文责任编辑:邵 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