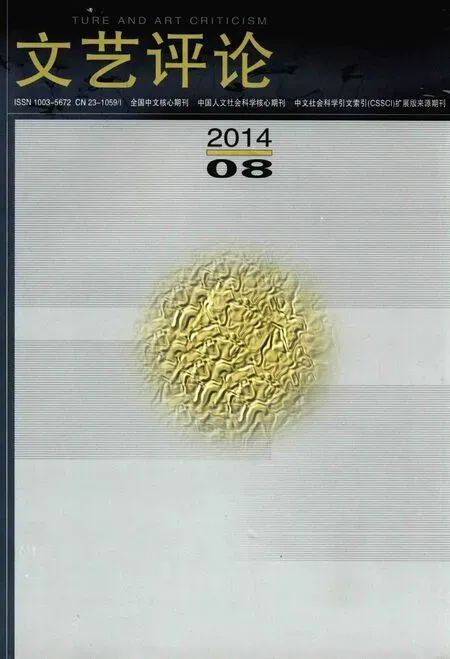徐渭“艺苑失位”原因探析——兼谈明中期文学生态
毕天华
清初学者黄宗羲有《青藤歌》云:“忆昔元美主文盟,一捧珠盘同受记。七子五子广且续,不放他人一头地。踽踽穷巷一老生,崛强不肯从世议。破帽青衫拜孝陵,科名艺苑皆失位。”①他认为徐渭艺苑失位的原因在于没有得到复古派的肯定。观察明代中期文坛,复古派声势最盛,其代表人物李攀龙、王世贞相继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黄宗羲所说的原因是成立的。笔者以为,徐渭之“艺苑失位”,与当时作为文坛主流的七子派的排挤有很大关系。而其排挤徐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徐渭的布衣身份使其难以得到七子派的认同接纳
徐渭科举失利,一生未入仕,布衣终老。复古派对待布衣的态度由谢榛可见一斑。万历四年(1576),徐渭写下了《廿八日雪》,揭露了后七子内部的矛盾,徐渭颇为布衣诗人谢榛抱不平:
“昨见帙中大可诧,古人绝交宁不罢。谢榛既与为友朋,何事诗中显相骂?乃知朱毂华裾子,鱼肉布衣无顾忌。即令此辈忤谢榛,谢榛敢骂此辈未?回思世事发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②此诗叙述的是复古派与谢榛“削名相骂”一事。李攀龙嘉靖二十三年(1544)中进士,历顺天乡试同考官、刑部广东司主事、刑部员外郎、刑部山西司郎中。王世贞生于以衣冠诗书著称的太仓王氏家族,其祖父王倬终南京兵部右侍郎,其父王忬终兵部尚书。王世贞登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屡迁员外郎、郎中,累官刑部尚书。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同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均授为刑部主事,后宗臣改吏部考功司主事。他们都是新科进士、郎署要员。而谢榛出身寒微,自幼“眇一目”的生理缺陷使他无缘科举。谢榛以写诗为生,走上了干谒寄食之路,终以诗歌称雄于世。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攀龙、王世贞、梁有誉、徐中行、宗臣等人与布衣谢榛赋诗酬唱,相与结社。当时,李、王初出茅庐,而谢榛已是声闻遐迩的大诗人。由于谢榛在诗论上有独到见解,李攀龙、王世贞等“心师其言大力延誉”③,“茂秦实以布衣执牛耳”④。然而,不久即意见相左,李攀龙贻诗《戏为绝谢茂秦》宣布与谢榛绝交,“元美诸人咸右于鳞,交口排谢榛。削其名于七子、五子之列”⑤。甚至谢榛“眇一目”的生理缺陷,也作为李攀龙等人侮辱和嘲讽的理由:“岂其使一眇君子肆于二三兄弟之上,以从其淫而散离昵好,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⑥王世贞也在《李于鳞》中指责谢榛:“老谢此来何名?狼独失策。六十老翁,何不速死?辱我五子哉。且不轻用常人态责于鳞,彼不记游燕集中力,真负心汉!遇虬髯生,当更剜去左目耳!”⑦
王世贞所用“何不速死”、“剜去左目”等语之恶毒,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而非正常的文学纷争。对一位年长的穷老布衣不遗余力地攻讦谩骂,颇有仗势欺人之嫌。从他对谢榛恨之入骨、视若仇敌的姿态可见,王世贞是后七子中除李攀龙之外对异己势力最有力的批判者。
无独有偶,对待其他布衣诗人,七子派也是大力排挤。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沈记室明臣》中说王世贞排挤布衣诗人王稚登、王叔承、沈明臣,“夷三君于四十子,而登胡元瑞于末五子,虽未能一切抹杀,其用意轩轾犹前志也。徐文长独深愤之。自引傲僻,穷老以死,终不入其牢笼。于论谢榛诗见志焉。”⑧徐渭对于七子派这种排挤布衣文人的行为十分愤恨,“自引傲僻”,终身不入复古派。
再考察徐渭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谓融洽。
李攀龙在嘉靖三十五年辞官,回到故里山东历城,在鲍山前建了一座“白雪楼”,取宋玉《对楚王问》中“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之意,以寓自身清高,不同俗流。然而白雪楼门虽设却常关,将许多慕名而来的人拒之门外。这既是李攀龙性情简傲,也是存在圈子意识,与非我派别的人不相与谋。徐渭作《拟寄白雪楼》讽刺李攀龙,诗云:“闻道楼成贺雀飞,题颜却是怨金徽。齐风大国谁其解,楚雪高张听者稀。岛蜃翻来窥百尺,啼蛟只自堕双玑。古来一曲令人老,此曲多从弃妾非。”⑨诗中对李攀龙名为清高实则排外的作为充满讽刺。李攀龙于隆庆四年(1570)去世,尔后主盟文坛者为王世贞。对于当时的文坛盟主,徐渭依然表现出放肆嘲讽的态度,在《九马圉人图二圉醉频堕》中称王元美为“太仓老王”,最后两句“此时倘堕无扶持,马且失矣太仆(指王世贞)笞”尤为明显。
明代文人结党是一大特色,政治上的党派表达共同利益诉求,而文学上的社团追求共同文学主张。虽然旨趣不同,但共同构成明代士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参与者多有重叠,就难免有所关联。利用文化联络而培养政治感情,达成政治互信,又成为官场通例。文艺行为沾染上政治色彩,而政治相争的意气风习同样渗透于文艺行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了造成了对文坛盟主的影响。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谈到:“王元美继二李之后,狎主词盟,引同调、抑异己。……海内词人有不入其门墙,不奉其壇墠者,其能自立者亦鲜矣。”⑩可见,王世贞在成为文坛盟主后并没有打破圈子意识,依然是对同党派亲信大加扶植,对不同意见者大肆讨伐,加深了复古派的门户之见。
徐渭抵死不入七子派,除了对复古派“削名相骂”谢榛一事表现出对布衣文人的轻视态度,引起徐渭的愤慨不满外,还与徐渭自身文学观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志不同、道不合有关。
二、徐渭与王世贞等人的艺术趣味相异
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以复古为己任,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基本承接了前七子的复古主张,但更加注重法度格调的强化和具体化。王世贞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所谓“语法而文,声法而诗”(《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八《张肖甫集序》),但他们过多重视古人诗文法度格调,这都有些束缚他们的创作手脚,影响他们情感自由充分地表达。
徐渭“传姚江(王阳明)纵恣之派”⑪,形成了“疏纵不为儒缚、眼空千古,独立一时”的思想作风。与之相关的是他的文学思想。徐渭作诗强调“必出于己之所得”,反对复古派的剿袭模拟。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师心横纵,任其野性,崇尚俚俗。徐渭在《书田生诗文后》中评其诗文说:“田生之文,稍融会六经,及先秦诸子诸史,尤契者蒙叟、贾长沙也。姑为近格,乃兼昌黎、大苏,亦用其髓,弃其皮耳。师心横从,不傍门户,故了无痕凿可指。”⑫这些充分展示了徐渭在阳明心学等影响下的草野文人心态和艺术追求的精神。他在文学创作上独立于七子派复古思潮之外,直抒胸臆,自成一家。
王世贞和徐渭论诗都重视自我情感的表达,王世贞也提出“有真我而后有真诗”,然而王世贞拘泥于古人的文法窠臼,过于强调法度格调,造成王诗多数作品生涩古板。反观徐渭,他主张创新,反对因袭,对复古文风发起了拾击:“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⑬将亦步亦趋地拟古视为鸟学人言,对复古文风表现出极大不满。王世贞、徐渭都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但王世贞明确表达了对王阳明的不满。“长沙、新建,据高收广,挟声起听,号为霸儒。逮迩晋江、昆陵欻起创立,耳观之辈,蝇袭若狂。”(《弇州四部稿》卷十三《赠俞山人允文》)长沙,李东阳;新建,王阳明。这里王世贞称他们为“霸儒”,对他们造成舆论声势之大表示不满。
由此可见,文学结社带有政治色彩,而毫无政治地位可言的诸如徐渭等布衣文人,则被剥夺了发言权,不为主流文学所接受,使得他们只能偏安一隅。而文坛主流声音是以前后七子为首的复古派,在七子派的打压下,其他文学声音相对弱小,乃至无疾而终,这就造成明中期文坛闭塞狭窄的文学环境,不能包容多种文化因素的存在、发展,部分文化现象失语,无法形成较大的全国影响力。这其实也是明中叶诗文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