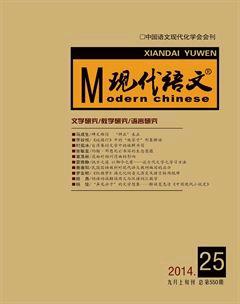由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谈刘亮程散文中的“真”
摘 要:刘亮程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荒凉而真实的边地乡土世界中构建起一个独特的审美想象空间。他借助村庄里生存形态各式各样的生命体为自然人性唱响的赞歌传达出他对人性之真的推崇。同时,作为一个两栖人对边地农耕文明的留恋与向往表达了他对精神家园的迫切回归。
关键词:《一个人的村庄》 真 边地乡土 人性 农耕文明
谈到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的时候,“真”、“善”、“美”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善”是文学传达出的人文关怀,“美”是优秀文学作品外在形式的表现,而“真”是一种内在的审美尺度。散文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并且作为一种自由进退于文学和历史、哲学、伦理学、民俗学等非文学体裁之间的文学体裁,“真”也是散文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标准。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是在1999年出版发行并在文坛上引起轰动的,所以他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而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评论界的非同凡响,就在于它的不娇柔造作,在于它有一种强烈的真实之美。那么这种真实美来自何处?
在喻大翔所著的《现代中文散文十五讲》中认为“散文的真”可以分为五个层层深入、共融共铸的层次:对象的真,主体的真,时代的真,文化的真,人性的真。“我们追求的真,就是在一篇满意的散文里,通过对象真的载体,经过主体真的化解与选择,穿越时代与文化,而达到人性的共真。然后,拨开共性,向下层层反观,我们又可把握到人性、文化、时代、主体与对象独特的具体性及其在特定环境中的演化。”[1]消解了各个层次间严格的界限后,喻大翔这种哲学层面的审视与划分在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里则融为三种真实美。
一、边地乡土的真实美
好比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山东高密县和贾平凹的商州,一个地域会因为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而呈现出它的独特魅力,而作家也成为这片土地的代言者。刘亮程也是通过《一个人的村庄》而成为边地乡村的代言者。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展现了边地乡土世界的真实美。边地的乡土世界是《一个人的村庄》描绘的对象,也是它依托的真实空间。这个世界为刘亮程的写作提供了客观的对象,自然也为它真实美的呈现提供了材料上的真实性。
但是刘亮程的村庄——黄沙梁,在现实中从何处来,归依何种文化背景呢?“新疆,特别是坐落在天山以北广大的山前平原中的村庄,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人文景观。目前这片已经连为一体的耕地和房屋,在百年前还只是马帮驼队的驿站和游民们的乐园,最早在这里点燃生活的是沿着丝绸之路北道去的中原商人,这些疲惫不堪的跋涉者日出而行,日落后就在荒原中的羊圈、卵石小屋和芦苇棚中栖身,渐渐地,由职业的习惯应运而生的小滩小铺出现后,一些规模不大的村庄也就在西部背景上定格了。”[2]边地乡土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景观上默默生长:干旱缺水,气侯环境恶劣,交通十分不便。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割据式的居住,使得新疆与外界的联系异常困难,各绿洲之间的来往也不是那么密切。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似乎与世隔绝。生态环境的偏僻荒芜赋予边区文化封闭而自足的文化基因,人烟稀少的现状使它更加注重人与动物、人与植物、人与土地的关系。
所以,依托对象的真实性,在散文集里,他真实书写了边地这一特有的自然风貌:当然不是熙熙攘攘的集市,你来我往的邻里之间,而是无限的荒野和沙漠,倔犟而又卖力的老牛,卧在墙根的猪,年复一年遍地荒芜的野草,东荡西荡的大风,起伏向远的沙梁,踽踽前行的黄土路,路上的几串脚印,天边的几朵流云。然而,这种真实的边疆风土,在刘亮程的散文里却是充满着诗意情怀与文化自信的。所以在他的审美想象里,你会看到“一株草的死亡或许引起遍地草木的哀悼和哭泣”[3],“路比什么都永恒,它平躺在大地上,折不断、刮不走,再重的的东西它都能禁住”[4],“在狼天性的孤独中我看到它选择唯一食物的孤独”[5],“一朵云下的黄沙梁,也是时间的浮云一朵。吹散它的风藏在岁月里。”[6]“晨光很有劲。这面墙迟早会被早晨的阳光推倒。”[7]这样的审美想象,村庄里微小的生命并不是比人卑微的个体存在,而是同人一样或集体向上生长,或孤独地指引人生。他对细微生命的描绘与关照赋予他的散文一种虚化的真实美,而读者也在他构建的审美想象空间里体悟出庄子的齐物观。由此,荒凉而真实的边地乡土世界在他的散文里成为一个美的审美想象空间。
二、自然人性的真实美
人性的真就是人的真。“对于爱情的追慕与哀怨,对于自由的渴求与压制,对于生的烦恼与赞美等,这些尽管在不同的文化圈、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主体身上有着不同的内涵,不同的准则,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表现形式与途径。也有着不同的影响与力量,但基本的欲求与表达是不会消逝的。”[8]为自然人性唱响的赞歌便表现为刘亮程对人性之真的推崇。这种“真”有对自由的渴求,有对压制自由的悔恨,有对生的迷茫也有对死亡的向往,但是他却忽略“我”的主体性,而借助村庄里生存形态各式各样的生命体,甚至没有生命的个体也被他赋予了生命意识。
因此,在探寻人与边地事物的关系上,他把眼光放在人与一头驴,一条狗,一只牛,还有一片草,几棵树,一阵风,甚至一个坑,一坨牛粪的关联上。于是,“秋天,粮食不会按姓名走到谁家里。粮食是一群盲者,顺着劳动之路,回到劳动者心里。”[9]只有劳动才有收获,这样简单质朴的道理指引人要脚踏实地地行走。“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很少人一辈子种好它。”[10]荒地再荒凉也不如心地的冷漠更让人心寒。“这块石头已作为父亲生命中最坚硬的一块骨头提前埋进了土地中。”[11]父亲命运的遭际深刻着如地界石一般坚硬不屈的人格尊严。“你无意便将一棵草籽从秋带到春。”“春天空空来临。你走过不再泛绿的潮湿大地,你觉得身上痒痒,禁不住抖抖身子——无论你是一条狗、一只羊、一匹马、一只鸡、一个人、一只老鼠,你都成为大地春天唯一的救星。”[12]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就是这么奇妙,尽管略带诗意色彩,然而村庄里的人就是这样和村庄里的各种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endprint
的确“这个地图上确定存在的黄沙梁却在他的笔下不断地被虚化,他的文字让这里的一切变的更像一个寓言。在这里,你看不到村庄里的任何具体的人事纷扰,是非争吵,张家的媳妇儿、李家的婆婆,似乎这些从来不曾存在,只有这里的牲畜、花草、风月才是真实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他写生命的生生不息,写生命在一种静止状态下是怎样消耗的,他写岁月的变换改变了多少东西,又改变不了多少东西。这些都是属于刘亮程的描写对象,但刘亮程的生存体验是不可置换的,这才是一个人的村庄。他以本真的状态呈现出它自身的、内在的精神气质,以最原始、最简单、最真实的方式撞击我们的心灵,引出我们最丰富的感慨和联想。”[13]这就是刘亮程,对边地自然风物的呈现,表达出对自然人性深沉的关怀。
三、边地农耕文明的真实赞歌
文化的真指的是散文的历史性、民族性、地域性与世界性之种种,是以不同心理基础为核心的广义文化传统。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里》寄予自己对边地农耕文明乡土文化基因的深沉留恋与向往。“生活在西部的游牧民族,在外部因素的驱使下,追赶着水草丰富的生活环境,他们生命里所具有的流动性的因子,是独特的生活方式所赋予的:‘动态的生命形式赋予他们特殊的生存方式,使他们努力在每片生活过的土地上留下自己的生命痕迹,这也就形成了具有独特色彩的西部乡土文化。面对西部的荒凉和未开垦过的土地,拿起锄头,扛起铁锨,也是西部人生活的一种必然选择——‘刀耕火种的文明在西部同样留下了它的传统印迹。”[14]由此可见,西部边地的农耕文明是西部游牧文明的变异,虽然是和土地而非水草息息相关,但是西部的农耕文明有着西部游牧文化的深刻烙印,并有着独特的乡土情结。这种独特性在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里昭然可见。如有评论者说“农耕文明则多会形成一种乡土情结,如农耕文明的表现者刘亮程的散文,就充分展现了作为一个西部作家,对故土深刻而执著的爱恋。在刘亮程的笔下,农耕文明业并非对种田垦荒的生活景象的描写,而是通过一个村庄的人物与生活细节,把这种文明的制造者农民,形象地展现在读者眼前。”[15]当然,与周涛、柯红等西部散文家擅于表现游牧文化强健奔放的原始生命力不同,也与张承志选择沉于民间底层、放浪西北大地,与民众为伍挖掘真实的民族文化记忆不同,刘亮程更愿意以他的村庄——黄沙梁为中心,抒发细腻的乡土情怀。当然,刘亮程的乡土情怀也同西部文化的其他言说者一样,表达着与现代工业文明相抗衡的强烈隐喻意味。只不过,刘亮程作为一名边地“土著”建设兵团的后代,一者,他是借助西部的文化精神来改造主流中心文化,而非以西部精神资源表现主流中心文化的精华。二者,他对农耕文明的向往和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温和抵抗表达了他深切的乡土情怀,以此守护着人类的精神家园。
在他的《一个人的村庄》里,刘亮程的乡土情怀寄托在一头驴、一只牛的身上。比如,在《通驴性的人》里,他把西部“自然生命精神的优越自信物化到驴身上,他们的驴不承认世界,它只相信驴圈,‘谁都不敢独自直面世界,但驴敢,驴的呜叫是对世界的强烈警告[16]”[17]。因此激发的情怀是如此昂扬:一旦鞭子握在别人手里,我会首先想到驴,宁肯爬着往前走绝不跪着求生存,把低贱卑微的一生活得一样潇洒、风流且亢奋,而且并不因此压低嗓门,低声下气。用激扬的呜叫压过沸沸人声;必要时,更要学一点拉着不走打着后退的倔犟劲。驴也好,人也好,永远都需要一种无畏的反抗精神[18]。他所表现的是即使是西部的生物,也是天地造化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个体。这不正是一种独特文化视角下的崇拜?不正与中心主流文化下驴的丑陋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正是有着对西部农耕文明的真挚情怀,刘亮程才能借助于西部特有生物的特有品格建造他文化人格的自然原乡,以抵抗中心主流文化的强势侵袭。
刘亮程的乡土情结还表现在对农耕文明的守护和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抵制上。实际上,数千年农耕文明是刘亮程散文书写的精神资源,而他的《一个人的村庄》则是对边地乡土文化的深情回馈。于此,他才对黄沙梁发出“我将不再走远,静坐在墙根,晒着太阳,在一根歪木棍旁把你给我的一天过完——这样平平常常的一天在多年前,好像永远过不完、熬不到边。”“我有点可惜自己,不愿像那根木头一样朽在这个院子里。我离开了家。”“故乡是一个人的羞涩处,也是一个人最大的隐秘。我把故乡隐藏在身后,单枪匹马去闯荡生活。我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走动、居住和生活,那不是我的,我不会留下脚印。”[19]虽然刘亮程是他村庄的代言人,是边缘写作的力挺者。但是,刘亮程终究是一个现代工业文明中的城市人,他借助于《一个人的村庄》所表达的更是一种两栖人的文化乡愁。“早在十八世纪,当文明进步露出它辉煌的曙光时,启蒙先躯卢梭就警告说:文明与科技同样也会毁掉人类精神的宝藏,它提出著名的‘回到自然的口号。现在,人们完全处在都市硕大无朋的水泥空间,处在电子计算机亿次/秒的速率中,无不感到一种愈来愈重的精神压迫和畸化。被土地和大自然悬离的空茫、焦虑、莫名躁动、无力感、漂泊、无家可归的困惑,引诱人们想往一种坚硬、踏实、永久的精神居所。乡村中的麦地,村庄里的护河、大堆大堆的秸秆、磨光的锄把、镰刀、向日葵、瓷碗乃至麦粒,亦便成了小小的精神寓托之所,因为它们着实代表着土地,代表土地一种澎湃的生命和强旺的生机。土地——生命,村庄——生命,不约而同勾起他们对一种叫做‘家园的总体精神形态的想往与追寻。”[20]二十多年的乡村生活镌刻着刘亮程的童年时光、初恋的心事和青春的追忆。居住于城市之后,这些青春期的精神资源无时无刻不召唤者他回归灵魂最初的栖居地。地理意义上的家乡,社会学意义上的籍贯,文化意义上的故乡因此成为他寻找精神家园的出口。当代作家苏童的小说《逃》中“我”的叔叔陈三麦,在满载荣誉回到家乡后的再一次逃亡使人迷茫。为什么还逃呢?没有日常的理由,那是精神世界需要的精神归宿。《米》中的五龙带着城市的罪恶,坐上回往枫杨树乡村的火车,也是源于对地理意义的故乡的留恋和精神上的故乡的向往。所以,刘亮程所呈现出的这个村庄不仅仅是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而是一类人共同的精神家园,是灵魂的栖息地。如他所说:“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个人精神世界,要靠自己一土一木去构筑。我们的‘圣经只能是自己居住其上的村庄大地,读懂它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把整个一生安置其中,开始是生存居所,最后是灵魂圣地。对村庄的写作其实是对自我灵魂的永久构筑。因着一颗心灵的力量,一座沉寂于黑暗时间的村庄被唤醒、照亮。”[21]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刘亮程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抵抗是温和的、不激烈的,他在对黄沙梁的朝拜中隐藏着对现代生活人心荒芜的批判。
四、结语
从古至今,由外国到中国,写村庄的名家作品举不胜举,从书写苦难、贫穷,抒发国仇家思到诗话乡村、寄托处世理想,村庄附带着艺术家们或沉重或无为的思考被代言,同时也为艺术家们的立言贡献自我。然而,刘亮程笔下的一个人的村庄——黄沙梁,却能够深深打动读者和吸引读者,不是因为它指引人们关注苦难与蒙昧,也不是因为它带着绿水青山的诗情画意。而只是因为,这片土地是他灵魂的皈依地,是他创作的全部动力与根基。如果一定要为《一个人的村庄》寻找它富于真实美的理由:在荒凉而真实的边地乡土世界中构建起一个独特的审美想象空间;借助村庄里生存形态各式各样的生命体为自然人性唱响的赞歌传达出他对人性之真的推崇;同时,作为一个两栖人对边地农耕文明的留恋与向往表达了他对精神家园的迫切回归,一定是必须审视的三个缘由。
注释:
[1][2]喻大翔:《现代中文散文十五讲》,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第40页。
[8]张功臣:《边地快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4][5][6][7][9][10][11][12][16][18][19][21]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3]吕新峰:《一个人的村庄 一类人的家园——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散文创作探析》,新西部,2009年,第16期。
[14][15]傅文靖:《西部文化的宏阔观照与诗意的生命关怀》,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
[17]范培松:《西部散文:世纪末最后一个散文流派》,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
[20]陈仲义:《乡土诗学新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秋之卷(总第25期)。
(杜真真 广西南宁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 53000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