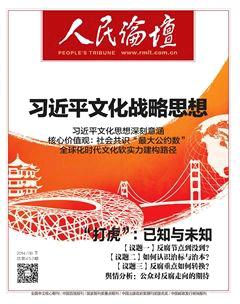第一祈祷词(外八首)
世界上有无数的祷词,都不如
我四岁女儿的祷词,
那么无私,善良,
她跪下,对那在烟雾缭绕中
微闭着双眼的观世音说:
菩萨,祝你身体健康。
等候
我使劲拔草,山突然变
矮了。我捧起黄土,
它被洞穴吸走,
就像风吹走炉中的香灰。
我顺着泥泞的脚印走去,
雨已经下了很久。
天空中,
几只眼睛找不到脸。
途中,在简陋的雨棚下
有许多人在避雨,
我挤到他们中间,
而他们仿佛在等我。
我一定还活着,否则不会痛苦地
感觉到:我已死去很久。
暗礁
眼泪在天上流着。
这里很快就会
变成海。
当一艘船驶来,
一根被埋葬的骨头
会蓦然挺立
警告它——不,也许,
它仍将选择
成为一块暗礁。
树木都是女巫
树木都是女巫
吐着咒语——
绿色的咒语
飞出了鸟儿。
她的舌头不是蛇信子
便是蚯蚓。
树木都是女巫,
她拔剑割破舌尖
然后把血喷向河流。
蚂蚁
诗人必须对着过去的天空说话,
每个字的缝隙里都塞满了风。
而在他的脚下,尘土正聚集成未来,
就像不知从何处而来的一群蚂蚁。
裂缝
我来了,我跟随
一个裂缝而来。很久以前,
黑夜就预言了这个裂缝。
那里塞满了秘密集会,
蚂蚁的集会,麻雀的集会,
各种声音的集会。
我需要耳朵使用指南,不用你教我
怎么使用眼睛。我需要听见
大地的商店播放的音乐,
而不是黑暗的橱窗。
从这个裂缝诞生的,还有我的心,
一个隐秘的地球仪——
不,我不是一台精密仪器,
尽管我的梦如此精妙
就像天花板挂着的熄灭的水晶灯。
夜饮
灯光从一个政党的房间走出,
留下一堆破衣服,
我们刚刚喝下第三十杯酒,
在那个暧昧肮脏的小酒馆旁,
黑暗从我们的尿道射出,
在阴沟中急速翻动,
天空即将爆发流血的革命,
狗叫声形成一只漏斗,
钟表匠在街头恢复时间,
鞋匠在街头恢复速度,
人匠在窗内恢复人而放飞灵魂,
你在瞳孔深处点燃一枝烟……
读史
这片古战场长出了一群蒲公英。
某个夜晚,风开始像清凉的流水,
一粒蒲公英纵身跳进水中
向我隐秘地躺卧的地方漂来。
我感到泥土的颤栗,长满哭声的
堤岸正在晃动,也听到了
神秘的笑声。我抚摸四壁,
打开墓穴的天窗——窗棂是折断的箭杆,
翎毛已被鸟带走。而你径直漂进
这个摇曳着青草的酒杯里。
它曾经和你一起飞向天空,
却被一只流血的手丢弃在这里。
我合上书本,邀请你饮酒。
于是我们一起坐在杯中,
在我们的唇边,依然有血的滋味,
有萤火虫在黑暗中采集的星光。
多少年前,你和我初次相遇也是如此,
也是一个白骨敲击歌声的夜晚,
雪白的浪花吻着坚硬的石头——
一个是侠妓,一个是义鬼。
深夜的车祸
一场车祸在夜里发生,
但很快,一切已恢复宁静,只有
黑色树叶像尖叫的余音。
你朝街道推开窗户,
玻璃有条裂缝。飘动的白云
仿佛一块纱布。
黎明正一点点降临。突然
一个鬼魂爬起身走了,
弥漫的黑暗回到他身上,
真正的血从天上流下。
你关上窗户,穿上衣服,
推开门,消失在一个
充满逃逸肇事者的人间。
唐不遇,现居广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