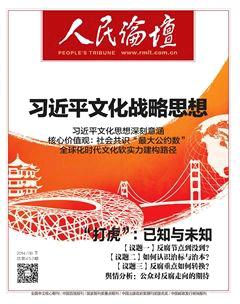词语中的生活
散步
某天傍晚,我出街散步,锻炼身体。
我是真正需要散步的人。因为写作需要长久静处,长久伏案,散步就是必需的运动。清晨和傍晚,到河堤之上,在园林之间,活动身体,吐故纳新。
我觉得散步是对静止和停滞状态的修正。
早年在矿井之下的硐室我也会散步。硐室就是石头砌的,穹形的居所。
在矿井之下有不少这样的地方。通常矿井之下的医疗急救站是穹形的,它建在井下的大巷之间,在巷道的墙壁上开凿出一个穹型的用石头垒砌的居所,也有门窗,居所里也有桌椅,还有一壁橱,那是放医药用品的地方。这硐室坐一穿白大褂的人,就是医疗急救站了。还有火药库也是这种类型的硐室,在大巷之间,在巷道的墙壁上开凿这么个穹型的石头垒砌的硐室。硐室放着成箱的炸药和雷管,这是危险物品,每个纸箱上印着交叉的枯骨和骷髅头,用以警示,这就是火药库。还有一类硐室——就是我所在的放置变压器以及电动开关和高压电缆的硐室,相对来说这类硐室更重要,因为它负责整个矿井的系统供电,使巷道有充足的风量保证人的正常呼吸,保证矿井里的各个电器正常运行。
我们都是机要重地。急救室、火药库和变电所都不能在工作时间离开人。
只要缺岗,遇到出事故麻烦就大了。那种麻烦想也能想得出来。
在黑暗的矿井里,我们不能离开硐室,身体又不能长久处于禁止和停滞状态。虽然硐室放置着铁床但是不能长时间睡觉,不能长时间写作,也不能长时间阅读。因为时间长了身体内的细胞就会反抗,它们更自由也更适宜在变化中运行。
我说的我们,就是指我和急救站的年轻医生B、看火药库的老库工E。我们都是这样的情况。在工作时间,他们不能脱岗就会到我的硐室来。因为我的硐室有高压电流的辐射,硐室里很温暖,尤其在寒冷阴湿的冬季,这种温暖是我们需要的。只要是在我的硐室,时间长了我们都需要散步。在散步之前,我们都手握书本阅读,独特的矿井生活让我们成为热爱阅读的人。我们的区别只是读物的差异。
他们带到矿井里的书多是武侠或者言情类。我带的书多是严肃的人文书籍,包括海明威、福克纳、卡夫卡写的书。
但是我们的阅读姿势是相同的,坐在黑暗的硐室里,捧着书籍借助矿灯的光映照阅读。
在矿灯的映照之下,阅读的时间长了眼睛生疼,身心困倦,散步就是我们调节自己身心状态的有效方式。可以想象我们散步的状态,三个人在狭窄逼仄的硐室里交错着来回走动,彼此相视微笑。那些血液和细胞体,它们喜欢我们的身体是活跃的,充满生命能量的。我想这是散步的原始形态。这样的散步方式我早年在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的回忆录《绞刑架下的报告》中读到过,后来也在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自传《与自己对话》中读过。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也描述过。只是他们散步的现场是在监牢里。
散步成为奥义繁复的词语是在后来才有的情况,人们把上街请愿戏谑为散步。
联想到当年我散步的情况,我以为无论是在监牢,还是在矿井,或者在大街,散步的功能应该是相似的。那就是人的身体里的血液和细胞体不喜欢僵冷、停滞、委顿的生命状态。当血液冷却的时候,生命也可能是僵冷的。
“为生命提供能量”,我想这是人们愿意散步的理由。
迁徙
早年我不愿意固守家乡,想到外面的世界闯荡。
但是我有一份工作,那是与姐姐竞争之后,获得顶替退休父亲的名额赢取的工作机会。
在矿井里做矿工,这是我又恐惧又向往的工作。恐惧是因为矿井里的黑暗和艰险,向往是因为这是我能够养活自己的一份工作,我能每月按时领取薪水,这份薪水除了交给母亲存着,还可以有零花钱给自己买书,买衣物,或者进城里去逛逛。
然而我很快就厌倦了这份工作,幻想到外面的世界开创新生活。
父亲强烈反对。他认为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也就是不能丢失这个工人的身份。
“谋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有这个身份你还能被人当人看,没这个身份你连个人都不算。”父亲教训我。
父亲作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的老兵,当然是有阅历的人。他对我的教训也是来自于他大半生的人世经验。没有身份的人就是盲流,而盲流是一种罪。
这是我在早年就知道的。
多年后我访问作家杨显惠,这个西北风沙吹出粗粝面孔的白发老人写出《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三部曲。我有三次在不同的现场看到老人忆及所访问的大饥荒幸存者,都像儿童一样失声恸哭。听他讲过很多残酷骇人的故事,比如因饥饿无法爬到炕上死在地上的孩子,因饥饿无法移动死在炕上的老人,眼看老人肉身腐烂的妇人。
类似的故事是1960年代中国乡村大饥荒史实中的沧海一粟。
让我惊骇的还有那些盲流。“在当时人是不容许流动的,盲流者会被视为坏分子拘捕。很多村子设置关卡,拦截和追捕试图逃离村子去外地逃荒的人。”杨显惠说。
饿死者就有被困在饥荒之地不能自由流动的灾民。
人是被规定在某个区域的,不能任意调动,不能自由迁徙。
人自愿或者被迫失去这种规定,成为没有约束和限制的自然状态被称为盲流。
在中国社会语境,有的描述人的状态的词语带有侮辱性。
盲流即是之一。它是贱民的一种。小时候看到有民兵背着步枪押着某个神情慌张的人敲着铜锣游街,游街是常见的街头一景,被游街的有地富反坏右,有牛鬼蛇神一贯道,还有一种就是被称为盲流的人。在社会中生存的人要有固定身份,这是我早年就明白的。这个身份由社会赋予,有身份就被尊重,没有身份就被歧视,或者被社会敌视。这个身份的凭证,一是所属社区的户籍,一是工作单位。户籍有户籍资料,单位有档案说明,那些深藏在文件库里的档案写有个人政治鉴定和社会评价。我们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这些鉴定对我们人生做出的隐秘政治判别,然而有一些人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借此鉴定对人进行优劣判断。荣耀的纪录会跟随一生,耻辱的纪录,甚至罪恶纪录也会跟随一生。endprint
人就是这样被规定着,无疑也被限制和禁锢着。
1994年的秋天,我就是不愿意固守在家乡。我的出走意志让父亲焦虑和愤怒。
父亲对我有很多不满,比如那时嫌弃我头发长,嫌弃我穿奇装异服。
但是我觉得不能听他的话。我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心愿安排自己的生活。
不服从是我有意对自己的训练,包括不服从父亲。
我知道父亲在的时候,我是很难让自己有逾越常规的举动。他会严加管制,不容许我做他不愿意我做的事情,比如辞职,在他看来这是触犯天条的事情。
然而最后我还是辞职了,在父亲去世之后。父亲的辞世当然令我悲伤,但是我也真实感到自己的解放。
我想,在父亲之后,这个世界再没有人能管制我。
能约束我的就是生而为人的天良,我愿意服从的唯有良知。
告解
2006年6月。我去波兰访问。
第一站是去格但斯克采访波兰前总统瓦文萨,他也是团结工会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退出政坛后隐居在故乡格但斯克小城,这也是他当年的出发地。
在见瓦文萨之前我去了位于格但斯克的一家著名的天主教大教堂。
据说那是欧洲最大也是保护最完好的一座教堂。
进去之后,在管风琴奏响的音乐声中,我看到教堂开阔宏大金碧辉煌的内景。
我也看到那些安坐木桌前低垂眼帘在静默中祈祷的男人和妇女。
他们默默地向着内心的神明告解内心的疑难。
这样的情景令我感动,也让我伤怀。他们让我想到另一种人群。
那是求告无门的一些人,他们没有信仰,内心疑难无从告解,生活中的困苦也无从申诉。
有一天清晨。我从家乡返京,在火车站候车室候车。
候车室蜂拥着稠密旅人。我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头看到我以前在矿工会的领导L。十多年没见,他额上的头发更稀疏,腰背也更佝偻。“你到火车站做什么?是要远行么?”我问他。“甭提了,在这里给人家搞截访呢,一大早就得蹲守在车站。”L说。
听到截访这个词,我心动了一下,就问他怎么截访?
原来工会已经不做工会的事情了,人员都被派出来搞截访,就是在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驻防蹲守,严格管制人们到外面上访。矿上有很多常年外出上访的人,到太原,到北京。L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准备外出上访的人拦下,阻止他们外出。
“这是政治任务,不能有半点马虎。”L说。
混杂在拥挤的旅行人群里,L的脸上满是无奈。他告诉我他们是值班制,矿上在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包下酒店和旅馆的房间,机关的人全部安排到这里做截访。轮值的时候就住在酒店或旅馆,一天二十四小时,每趟车发车前他们都要到候车室,在人群里排查那些准备外出上访的人。哪些人是访民,矿上都会建立档案,每个访民都由专人负责看管,谁的责任区出现外出上访的人,谁就被惩罚。看着L眼神涣散、神情困倦的样子,我还真有点同情他。
在以前我也听到过截访这个词,就是没觉得跟自己有关,好像都是遥远的别处的事情。
比如我到报社上班的时候,每次在选题会上就听到有同事报题,说是京郊某处一宾馆就是截访点,有上访者被拦截到那里秘密收容。有时还爆出女访民被强奸的事情,跑社会领域的记者们对这些事情起劲地争论,愤怒之情难以言表,隔几天就会看到这些争议性的事件被报纸报出来。我也在某地参加会议时看到地方官交流截访的经验,比如他们会派警察或保安开车拉着那些死硬的截访者到荒无人迹的地方,把他们扔到野外,让他们没吃没喝自己回家。这么来回折腾几次,上访的意志就垮掉了。听到这些地方官员的截访经验,心里实在是有些惊骇。
关于截访,我听到的最触动我内心的事情还是在家乡。
有领导要来矿上访问,矿上提前就要做好各种迎接的准备。
环境要治理好,彻底消灭脏乱差。人也要管控好,防止那些上访的人借机上访。
还有就是取缔有碍市容的一切事物。街上有几个傻子,平时他们多半会在街上晃,
L奉命带着保安队收容这些傻子。他们开着车在街上走,看见一个就逮到车上来。L逮到三个傻子,他们开着车出矿区,在荒郊的乡野上行驶,到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们就把那几个傻子放下车去,开车回矿。
L觉得自己是做了一件丧良心的事情,想起来就不安。
也不知道那些傻子后来怎么样了,他们有没有吃的?在荒郊野外能不能找回家?这些事情很长时间都在折磨L,他每天都会在街上留心那些傻子的行迹,然而终难看见,看不见的时候就成了他心里的病。
“妈的,老子的良心是让狗吃了。”
有段时间L逢人就说。
逆袭
飞机在高空之上飞行。机翼之下是海岛的全景。
海洋、风浪、摇曳的椰树,在飞机向高空升起时拉远,最后抽象成剪影。
从舷窗之外看到烈日映照的高空,这是纬度不同的高空,阳光灿烂,碧空晴朗。
我想和别的纬度不同的是它的热力。这热力的普照使海南岛成为炎热之岛。
但是这天空之下的城市和乡村的实况,你不降落其上是无以体察的。
那时我想起离开海岛时的情景。
顺势生长的椰树伸展出锯齿形叶片接收着阳光照耀。
它的上部是光区,下部是暗影。椰树的枝干在作环状摇摆,那是从海上袭来的风。天空并不晴朗,有颜色发暗的云浮在天空,看不到太阳并不是因为它不在,而是我们视野的角度所限。这是机场候机厅的茶餐厅,日式风格,悬吊的方形的顶灯映出昏黄的光。我要了一杯芒果汁、一碗千叶屋的日式面,我准备在这里吃饭,同时等待航班起飞的时间。餐座的客人很少,也许是午后的缘故。送我到机场的司机说,三月本来是旅行的淡季。也好。我愿意在人少的季节出行。海口的机场跟我所见的别的城市的机场不同,除了候机楼帐篷般的造型,还有它内部的气息。那是晒干的鱼类散发出的气息,它们被风干晾在每一个商店。
广播里不断播放着航班延误的讯息,候机厅的电子显示屏滚动着延误航班的班次和时间。等候在大厅里的旅客多是焦躁不安的神情,他们散乱地坐在候机的座椅上,有的乘客因为不满跟机场工作人员争吵,在哪里都能看到这种纷乱、躁动和嘈杂。
离开酒店去机场时,我坐在出租车里观察这座城市,这是我的方式。每次在我离开或到达一座城市时就坐一辆出租车环城而行。观察城市的景观,道路、桥梁、滩涂、建筑,我不想走进任何一条街道,只想这样远远地观看,把一座城市的样貌尽收眼底。
前往机场时,出租司机选择的是城际道路,狭窄、车辆繁多,声音嘈杂。我问为什么不选择机场专线或者高速公路?他说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又让农民给封了。
司机说通往机场的道路经常被组织起来的农民设阻,他们封路的时候就很麻烦。
封路大多是因为政府征地引起的纠纷,因为邻近机场,周边生活的农民私有土地经常会被政府征用,转手高价卖给开发商。经手的官员无例外地贪污,这样的事情常常成为农民抗议的缘由。现在的农民见过世面,有组织能力,团结起来维权。
“这样的事情多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政府会如何处置?”我问司机。
“很多。只要发生了就有警察来疏导,有官员来解决。这也是农民们经常上街阻路的缘由,用流行词说,这也是一种逆袭。是无权者和权力者的博弈。”司机说。
夏榆,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散文集《黑暗的声音》、长篇小说《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