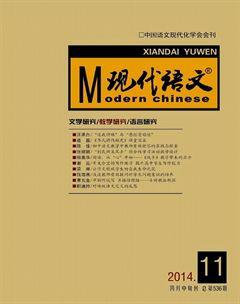语文教学中的三大错位及思考
当前语文教学出现诸多亮点,呈现出许多令人鼓舞的新景象。但与此同时,笔者从自己的教学实践、聆听观摩示范课、公开课中,也深感语文教学在发生令人欣喜鼓舞的变化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错位与误区,值得关注与深思。
错位一:“机械化”训练与语文素养养成的错位
在理性主义知识观的影响下,精确、客观成为语文知识的本性,语文教学内容便有“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八字宪法的框架限定,教学方法便是庖丁解牛式的分析和技巧的授受训练,语文教学就是保证语文知识的传递,语文学习则要求牢固掌握或熟练运用这些精确、客观的语文知识。当前,这种丧失语文学科的人文精神和感情灵性的语文课堂已有了明显改观。但为了确保知识的掌握,获取“高分”,反复机械训练在语文教学中仍较为普遍地存在。
语文素养本来就是一种修养,对于它的内涵,可从三个维度来认识。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维度来说,是指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习惯,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从知识与技能的维度,是指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丰富学生语言的积累,发展思维,培养语感,培养学生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从过程与方法的维度,是指学生语文学习的策略,学生语文学习过程的体验和反思。[1]语文学习是一个感性与理性结合的过程,这种感性,非养不可得。语文素养的核心在于语文情趣。学生如果没有语文情趣,素养这种潜移默化、动态的、须经由感悟——积累——运用过程的素质,很难养成的。
然而,我们语文教学依然围着考试指挥棒转,考什么教什么,不考不教,现在语文考试更是几乎不考平时教的内容。为了学生考试过关,语文教师不得不通过大量的练习来实现所谓知识迁移与知识点落实以及应试能力的培养。这种机械训练不要说使学生的语文情趣几乎丧失殆尽,就是教师也变得近乎麻木、疲于应付,完全体会不到语文教师应有的人格魅力与乐趣。于是,有人试图这样调和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三年两年搞素质,一年搞应试;一学期三个月搞素质,一个月搞应试。”
事实也表明,通过这样反复机械的训练,学生能在语文考试中取得相对较好的成绩,也有别于没有经训练的情况。要让这种丧失语文情趣的“机械化”训练远离、让语文素养的培养不成为一句空话,首要的是评价制度、评价方法要改变。一句话,如果经过机械训练的学生在语文考试中不能取得较为理想的成绩,教师意识到这种训练已失去作用,谁还会去做“无用功”呢?同时,我们语文教师必须孜孜以求学生语文情趣的养成。
当然,我们强调摈弃“机械化”、“技术主义”的训练,并不意味着我们语文教学就不需要训练。不能将“训练”和“练习”简单等同起来,训练决不是简单的练习,它强调的是为达到一定目标而进行的言语实践。《语文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这样要求:“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给学生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
错位二:文本多元解读与过度解读
我们时下的语文课堂似乎又陷入不同于过去的另一个极端:学生以“我以为”的线路与文本对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什么都是对的。比如,有说《红楼梦》作者缺乏优生优育、宣扬近亲结婚的,有说鲁智深是知法犯法(明知打死人是要偿命的)的凶手的等等。
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教材和教师参考用书在文本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的、强大的解释体系。它教条、僵化、贫乏、单一、概念化,它把学生与文本的联系隔开了,它甚至取代文本,使教师在解读中失于牵强和盲从。我们阅读教学所采纳的一直是“大纲主导的‘鉴赏者和教材设定的‘作业者束缚下的在教学中实际形成的语文教师备课样式的‘阅读取向”。[2]学生在学习中采用的是“为了去‘讲课文的那种阅读姿态、阅读方式,学生一直被培养的是围绕着‘思考和练习的‘分析课文的能力”。[3]这样的阅读取向显然是不恰当的,它使“培养学生探究性、创造性阅读能力,提倡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的目标无从谈起,也必然扼杀学生的创造力,泯灭学生对生活、对生命独特的感受力。事实上,文本的意义不是先于读者而客观地存在于文本之中的。没有读者,也就没有被读的文本,当然也就不存在文本的意义;所谓“意义”就是读者在与文本交谈中的收获。学生与课文的关系在本质上跟读者与作品的关系毫无二致,即学生与课文之间的交谈、对话。因此,我们的阅读教学取向应从“鉴赏者”、“作业者”转变为“解读者”。倡导“解读者”的阅读取向正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及命题。
“解读者”取向所提倡的多元思维对于解构“作者中心说”和意义专制具有合理性,但又缺乏一元思维所具有的确定性、明确性和总体性。当一切价值的相对化变得绝对化时,其实正是价值的消解。符号美学认为:作为艺术符号的能指本身便是一种符号性存在物,也就是说,在它自身中包含着某种意义的意向境域所有的规定性,能指本身的这种意向境域内在地制约着意义的可能性境域。因而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不再可能是任意的结合。[4]由此可见,对文本意义的解读并不是无限的。在语文教学之中,对文本意义(所指)的解读必须以文本(能指)为依据。当前的语文教学仍需大力提倡多元解读的阅读取向,但同时,为防止对语文文本盲目、随意、过度的解读,我们必须至少考虑三方面的制约因素——文本整体性、文本历史语境和文本意义层次性。
错位三:“对话”式教学与教师“讲解”的尴尬
新课标强调“阅读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倡导对话式教学。然而,时下借“对话”教学之名,把语文课上成自由“交谈”课,似乎已渐成时尚。学生以“我以为”的线路与文本进行“对话”;“阅读对话”成了学生的“独白篡位”,“教学对话”成了学生的“你的理解”“你的看法”“你的理由”“你的生活体验”;教师处于不敢“讲解”、不敢“分析”,更不敢“练习”的尴尬境地。教师不是“师”的角色,更像是伙伴,教师似乎期待着学生在围绕课文所涉及“话题”的交谈中能自发地生成阅读能力。endprint
教学必须预期一定的学习结果的出现。教师的指导作用一旦缺失、引退,就很难保证课堂教学能达到预期目标。“教育作为一种以培养人为目的的活动,就是教育者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和促进受教育者的身心按照一定的方向去发展。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这种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指导和管理。”[5]
课堂不能失去其“知识建构”的原本之义。语文课堂教学不同于自然状态下的阅读,不能直接等同于学生的感知、理解,必须含有高于自然状态下阅读的“成分”。离开了教师的指导,语文课堂教学也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我们似乎有一种惯性意识,认为讲解就是灌输,讲解等于压抑学生学习和思维的主动性、发展性。教师对“讲解”这一教学行为存在或隐或显的规避心理,尤其在提倡“对话”教学的今天,更不敢讲解、分析。讲解作为一种教学行为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它是“作为‘中介语言提高学生认知水平的重要技术手段,它在解构知识内容,建立知识与新知识的课题联系、点化认知误区、分析教学材料原理(而非事实)等方面,不可或缺地成为学生认知的依据和范例。”[6]“学生的学习和思维主动性、发展性必须建立在充分认知的依据之上,假如讲解阙如,教学中知识的综合贯通(认知水平之一)即成一大问题……”[7]由此可见,今天的语文教学仍需要讲解、分析,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讲解”、如何“分析”。我们当然不能对课文做“庖丁解牛”式的分析讲解,在对话式的教学中,语文教学中教师的讲解、分析应该采取“体验性描述”的价值取向,“把自己的体验说出来,一定不会有错”(李海林)。我们语文教师应运用自己的“体验性描述”引导学生深深地进入作品的迷人世界,调动起学生的感受、体验、直觉、妙悟、移情等心理机制,让学生为作品的情景所吸引,为人物所感动,更多地深刻体验、品味文本“不在场”的“味”。
注释:
[1]郑国民.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3]王荣生.语文科课程理论基础[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4]董志强.消解与重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35.
[5]郑金洲.教育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4.
[6][7]区培民.语文教师课堂行为系统论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陈德耀 浙江省苍南县金乡高级中学 32580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