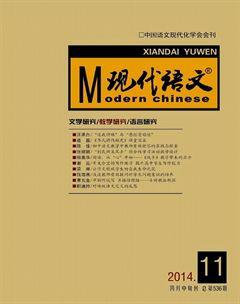“还我诗魂”与“感性受动性”
“还我诗魂!”是当前一部分中学生对诗歌教学中存在的唯理性解读现象的变相质疑[1]。“自我”“也是受动的”。“受动性”是费尔巴哈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中提出的哲学概念,它标志着对滥觞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西方近代古典唯理性哲学的“去弊”,标志着西方现代感性哲学的发轫。
一、何谓“诗魂”
“一堂堂课下来,老师可以把作者的写作目的、诗歌的主要内容、深层意思、写作技巧等等说得清清楚楚,但是诗歌给我的最初感动却荡然无存!诗歌那丰富美丽的语言变得只剩下几句大白话而已。诗歌带给我的丰富的感受只剩下‘表达了作者……的感情之类的字眼。诗,还是诗,只是被抽走了灵魂。我想哭,我想大喊‘还我诗魂!”
由这位中学生的“最初的感动”、“丰富美丽的语言”、“丰富的感受”等词汇可知,其所谓“被抽走”的“诗魂”,主要是指内蕴于诗词中的“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古人之神气”(刘大櫆《论文偶记》)——诗人与读者间情感共鸣,与读者“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却“于我心有戚戚焉”(梁启超《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的“借古人之歌哭笑骂”而得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的情感宣泄的诗词的音韵美。
二、“诗魂”“别宥”
庄子认为“人有所宥”(《庄子·天下》),人皆有认知上的障碍与局限性。而法国近代艺术哲学大师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更明确有言:后中世纪人,文明过度,“观念过强”,日常的精神生活都成了“纯粹的推理”[2],而理性如果只是单纯的知性,就会变成“无根基”的东西[3]。
在目前的中学诗词教学中,部分教师比较注重通过对诗词意象、意境的分析,通过各种概念对作品进行理性的解读,从而遮蔽了诗词的本体。
《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毛诗正义》注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4]。”事实上,中国古代诗论者,如刘勰等“认为‘情和‘志这两个概念不是彼此排斥,而是相互渗透的”[5],不仅经常以“情”、“志”对举,互文足义,而且每每把近代所谓属于感性范畴的概念与属于理性范畴的概念关联起来思、用。
所谓诗之本体,历代典籍也皆有所论及:“哀乐之情感,歌詠之声发”;(《汉书·艺文志》)“诗者,持人情性”;(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毛诗正义》注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藏在内心的思想感情就是志,而表现为语言就是诗”[6]都认为诗作为一种文体,发生于诗人表达情感的心理需求,从而都突出了诗词抒情的文体特征。
相对于叙事性文体,诗是一种抒情性文体,就大体论,散文的功用偏于叙事说理,诗的功用偏于抒情遣兴,“事理可以专从文字的意义上领会,情趣必从文字的声音上体验”[7]。美国文艺理论家苏珊·朗格认为抒情话语是一种表现性话语,具有象征性地表现情感的功能,通过“类似音乐的声音组织”和富有意蕴的画面来体现难以言传的“主观感受过程”[8]。也就是说,字音不仅可以组成优美的声调,而且还可以象征性地传达感受、表意抒情。布雷蒙(Abbe Bremond)的“纯诗”说更是声称诗是直接打动情感的,“不应假道于理智”,应该像音乐一样,全“以声音感人,意义是无关紧要的成分”[9]。
可见,所谓“被抽走”的“诗魂”,应主要是指诗词中的音韵美。
三、“受动”“去蔽”
那么,所谓的“诗魂”又是如何“被抽走”的呢?
“人的感性受动性”一直被部分“文明过度”的语文教师的唯理性意识“遮蔽”着[10],这是其主要原因。
人的“受动性”,一般被理解为人的受限制性和受制约性。但马克思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指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就是指“它是受动的”,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性,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11]。
事实上,今人被称为“文明过度”,就是相对于古人之于“感性受动性”的深刻体悟而言的。就诗论而言:《礼记·乐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12],强调的是“感”物而“动”,终“形”于“声”。那么,“感于物而动”之“感”与“动”,又当作何解释呢?“感,动也。”[13]《说文解字·心部》:“感,动人心。”[14],可知,“人心之动”就是“感”。“感”之“动”与人心密切相关,可以说,“感”而“动”就是费尔巴哈所谓的“感性受动”。
钟嵘《诗品序》进而明确强调“感于物而动”的结果是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白居易的《与元九书》[15]更是尤为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感于物而动”的传统诗学理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16]。
具体到诗词鉴赏而言,古人之于“感物而动”的途径,多体现于对古诗文的“吟”“诵”中。严羽《沧浪诗话》:“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由孟浩然之诗,感知到“金石宫商之声”,具体而明确;袁枚《随园诗话》强调:诗之“音律风趣,能动人心目”,体悟到诗歌藉音律而可收动人心目之效。刘开《读诗说中》称读诗之法须从容讽诵以习其辞,优游浸润以绎其旨,涵泳默会以得其归,往复低徊以尽其致,抑扬曲折以寻其节,温厚深婉以合诗人之性情,和平庄敬以味先王之德意。不惟熟之于古,而必通之于今,“不惟得之于心,而必验之于身”,从陶情、味趣、悟旨等诸方面阐释了“感物而动”之效用[17]。
清代“桐城派”诸人更是把“感物而动”在诗词鉴赏中的作用夸向了极致,认为鉴赏古人作品,欲求作品之妙,须当反复吟诵,然后始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阐明通过音节而体味古人作品之神气,进而获得与作品的共鸣。姚鼐则宣称鉴赏古人作品,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18]。
四、“意声相和”
古代学者之于藉由“感”之“讽”、“诵”而体悟诗词情志之论述,具体体现于古文之“声”、“意”关系的阐释中。endprint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云:“意声之相和……恒也。”[19]揭示了中国文论“以声传情”、“寓情于声”及“以声求气”中“意”与“声”,“情”与“声”,“声”与“气”的内在联系。
刘勰《文心雕龙·声律》:“声含宫商,肇自血气。”总括了人声来自性情,是为本;音律抒写声情,是为用的关系。而于声音诸要素与性情各要素之相互关系,论述尤为详尽。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篇中指出:“凡声有飞沉”,“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飚不还”[20],平仄相间,以求得声调的抑扬顿挫是近体诗平仄的基本要求。明代谢榛认为诗法妙在平仄四声而有清浊抑扬之分,“试以‘东‘董‘栋‘笃四声调之,‘东字平平直起,气舒且长,其声扬也;‘董字上转,气咽促然易尽,其声抑也;‘栋字去而悠远,气振欲高,其声扬也;‘笃字下入而疾,气收渐然,其声抑也。夫四声抑扬,不失疾徐之节,惟歌诗者能之;而未知所以妙也。非悟何以造其极,非喻无以得其状”[21]。
这是论述四声之于“气”感的关系,而对诗之于韵律,清代诗人沈德潜作喻为诗中韵脚,如“大厦之有柱石”[22]。
五、回归“受动”
周振甫在《诗词例话》中这样分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音节:平仄韵交替,“音节和谐”,构成了“流美婉转”之美感的风格[23]。
近代龙榆生评述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平仄韵脚“‘拗怒多于‘和谐”,发音“硬碰硬的地方特别多,迫使它的声音向上激射”,恰好和本曲的“高亢声情紧密结合,”最适宜于表达激越豪壮一类的情感[24]。论述了声音的抑扬顿挫与情感的喜怒哀乐及其起伏波动的相关关性。
基于现代人“观念过强”、遮于“纯粹的推理”之弊,而呼唤“诗魂”的中学生们又生疏于平仄、黏对、旋律等理性概念,且历代学者又尤为强调借助“吟”“诵”之“感”以“求”取古诗词之“气”,那么,回归“感性受动”,当不失为追寻诗词“音韵美”之一途。
例如: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第一、二两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25]
其散文翻译:
“你没见那黄河之水从天上奔腾而来,波涛翻滚直奔东海,再也没有回来。你没见那年迈的父母,对着明镜感叹自己的白发,年轻时候的满头青丝如今已是雪白一片。”
散文韵译:
“看啊!黄河之水汹涌澎湃从天上倾斜下来,一去不回头直奔向烟波浩渺的东海;看啊!头上的青丝转眼间成了雪一样的白发,高唐上对着镜子只能是概叹、悲哀!
读者只需跟着诵读时的直感,用“/”划分一下这三类句子的意群停顿,就会发现,只有李白的原诗句是三意群停顿的句子,可以淋漓尽致地抒发诗人或激越或缠绵之情感,却又极少受累于发音之碍障;而其散文常态译句、散文韵态译句,因须补足必要的副词、介词,多为超过三意群停顿的长句子,诵读起来,总感觉拖沓啰嗦,与原诗句相较,虽堪称达意,却难言尽情。
再如:
《苏幕遮》(燎沉香) 周邦彦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苏幕遮》(碧云天) 范仲淹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苏幕遮·碧云天》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主持防御西夏军事时,在边关防务前线,有感于秋寒肃飒之际,将士们思亲念乡之情,而借景抒怀之绝唱。
试诵读苏词词尾的“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与范词词尾的“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相忆否”与“休独倚”中,因“忆”为去声,音调下沉,反衬尾字上声“否”,读来意味深长;“独”字阳平调,反衬尾字上声“倚”字,读来气力疲乏。“梦入芙蓉浦”中“芙蓉浦”两阳平调紧跟一上声“浦”,读来舒徐悠远;而“相思泪”中两平声调接一去声“泪”字,读来低沉凝重。
周邦彦是客居京华、羁旅官场,有感于故土风情,自可挂印飘逸而去,“忆”字去声后跟上声“否”字,堪拟词人归隐之超然;戍边将士,身系家国安危,“独”字反衬“倚”字,诵声疲乏,“相思”两平调紧接一“泪”字,凝重低沉深合将士卫国任重、有家难归之无奈与凄重。
再读: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与宋徽宗赵佶《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虞美人 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25]。
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宋徽宗赵佶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徽宗赵佶因荒淫误国,于公元1127年与其子钦宗赵恒被金兵掳往北方五国城,囚禁致死。徽宗于北行途中,忽见杏花烂漫,百感交集,遂作此词。
《虞美人》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句,皆为三意群停顿句,读来语调绵长悠回,恰可模拟词人情思之悠绵;《燕山亭·北行见杏花》的“裁剪冰绡,轻叠数重”句为两意群停顿句,而两意群停顿句多被用于抒写激越、昂扬之情绪,此两意群停顿句与词人思念故国之凄凉情绪,难觉吻合。
《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与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同为亡国之君抒写故国之思,一词妇孺皆知,一词少见提及,大概“诗味”有别,当是缘由之一吧。endprint
综上所述,中学生所呼唤的原初的“诗魂”,应主要指被部分诗词教学者的唯理性解读所遮蔽的诗词之音韵美,费尔巴哈的“感性受动性”当不失为“解蔽”诗魂之可行性途径之一。
注释:
[1]邓彤.诗歌教学:从技术走向艺术[J].教学大参考,2006,(1):18.
[2]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上海:三联书店,1959.
[3](法)丹纳.何洁,曾令先,李群译.艺术哲学[M].重庆出版社,2006.
[4]本文作者注:康德的知性即近人所谓的理性.
[5]雅斯贝尔斯:理性与生存,转引自德国哲学论丛1996—199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望仙馆石印.毛诗注疏[A]、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光绪丁亥年.
[7]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72.
[9]朱光潜.诗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胡塞尔著.邓晓芒,张廷国译.经验与判断[M].上海:三联书店,1999.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9.
[12]郭绍虞.礼记·乐记.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3]李鼎祚.周易集解卷第十四[M].北京:中国书店,1984.
[1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6]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7]刘开.读诗说中刘孟涂集卷一[M].中国古典美学资料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
[18]姚鼐.与陈硕士书.选自姚惜抱轩先生尺版卷六,转见吴聪.姚鼐考证鉴定之思想与形成[A].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成立暨第二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C].2005.
[19]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l976.
[20]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1]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四溟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2]沈德潜.原诗·说诗晬语(卷下五十五)[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23]周振甫.诗词例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
[24]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2.
[25]人民教育出版社等编著.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选修)[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
(汪承台 安徽省金寨县南溪中学 23736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