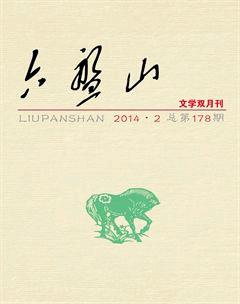鱼庄
刘健彷

吃过午饭后,你看到的就是太阳怎么也不愿露脸了,只是把一些细弱的光线撒到地面上,维持着天黑之前的一段时光。远处的乡间小道上有人唱着小曲,优美的旋律轻轻地撞在房子的窗玻璃上,也撞在高大福老汉的胸腔上。高大福老汉每次出门,都要穿一套侄女梅花给他准备的鲜红色的美人鱼服装。这怪异的衣服他是不想穿的,但不穿不行,他得听梅花的话。
“人老了就不能有自己的主意喽!”高大福老汉每次穿上美人鱼服装都要这样感叹,他感到自个已到了必须按小辈人的意思办事的年纪,他心里时不时地就会升起一丝悲凉。
美人鱼服装显得很轻薄,耍赖似地上了高大福老汉的身,把他的脸映成了一团黑红色。皮衣的后背印着美人鱼的图案,皮裤上印着几只小金鱼的图案。高大福老汉有一头扎眼的白发,配上这套花里胡哨的衣服,整个人看上去怪诞而滑稽。他苦着脸,扭着身子,羞于见人的样子。他在心里说:“天呐,别人看我肯定是个丑八怪!”过后他又对自己嘀咕:“老高头,你不是老没出息,你是舍下这张老脸帮梅花呢。”高大福老汉每次穿美人鱼服装时都会说这样的话,他是自己安慰自己。
梅花在城里开服装店挣了钱,回村后在村子东头离黄河边不远的地方,置换了十亩水田挖成了鱼池开始养鱼。几年工夫,她在鱼池的周围种了几排枣树,这些枣树都是以前没见过的新品种。树上的红枣各种各样的,有的像娃娃,有的像灯笼,有的像茶壶,有的像小鸟。她还在离鱼池不远的地方盖了一排房子,里面装修成城里宾馆的样子,摆上了麻将桌,吸引城里人到乡下玩。虽然乡下盖起的房子像宾馆,院子里却种上了菜,种上了葡萄树,搭起了葡萄架,还在葡萄架下摆上茶桌茶椅,供人们休闲聊天。村里人议论梅花在城里混了几年,自个土不土洋不洋的,回来又把村庄也弄成了土洋结合。没想到梅花竟从村里人的闲话里得到了启发,她又养了几群鸡,几只被她叫做“航母鸡”的母鸡领着几群小鸡在枣树下觅食的样子,让村里人像是又回到了六七十年代。庄户人大都喜欢凑热闹,他们听说梅花是想把城里人忽悠到乡下玩钓鱼的把戏,他们都觉得这把戏挺有意思,就纷纷去给梅花帮忙。村里人帮梅花,梅花是付工钱的。谁知就这样帮来帮去的,梅花就弄起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鱼庄。
鱼庄的四周都是庄稼地,不远处的渠坝上和黄河岸上都长着碗口粗的白杨树。有风吹过时,树叶在阳光中轻轻颤抖,清淡的粮食的芳香飘在空气里,如丝如缕,挥之不去,迷惘的蜜蜂旋转飞舞,嗡嗡地闹成一片,像风琴奏出的乐曲。青蛙最喜欢表现自己的歌喉,藏在水草下面一个劲地乱叫。在田地和树木之间,不时地有庄户人进进出出,来来回回地走动着。有的戴着草帽,有的头上顶着色彩艳丽的头巾,有的肩上扛着锄头,有的手里拿着铁锹。他们忙忙碌碌地追着季节播种,欢欢喜喜地头顶太阳收获粮食。有时他们会对着地里的庄稼说悄悄话,有时他们会对着天上的云彩唱小曲。空中的鸟儿受到感染,对着大地尽情地鸣叫,似乎和庄户人比赛谁更快乐。
以前的高大福老汉是孤独的,他独自住在空荡荡的三间屋子里,村里人都各忙各的,没有人上门找他闲聊。从七十岁后,他自己也不愿出去串门,怕村里人嫌弃他。生命的钟摆在他眼前沉重地移动,他想有个孙子,他想成为一个每天晚上给孙子讲故事的祖父。可是儿子高鹏却说他媳妇不想生孩子。那时他想对着电话冲高鹏喊:“天呐!我犯了什么天条,她竟不给我们老高家传后?”可是这话却塞在他喉哤里,他怎么也喊不出来。他真是想破了天也想不明白,这世上竟还有女人不愿生孩子?从那以后,高大福老汉每天晚上就对着房梁发呆,痛苦盘踞在他的胸上,压在他的心上,碾挤着他的皮肉。
梅花在村里修建鱼庄的时候,高大福老汉没去凑热闹。后来梅花亲自上门要接他去鱼庄工作,他推辞说自己是土埋脖子的人了,怕是去了要给她添麻烦。他嘴上虽这样说心里却着实兴奋了几天,还暗骂自己没出息骨头轻,有点好事就睡不着觉。可是到了鱼庄后,他才知道自己不是以人的身份而工作,而是要穿着美人鱼的服装以鱼的身份而工作,这让他的心顿时凉了下来。不过他转念一想,如果没了这身鱼皮,鱼庄的工作那能轮上他这个棺材瓤子?高大福老汉左想右想的,就把自己当成了一条老美人鱼。
入秋后,到鱼庄钓鱼的客人越来越少,虽然梅花没少花钱,在她所能想的地方都散发了宣传单,在本地的电视台和报社,还有城市人群密集地方的电子彩屏上都做了广告。现在鱼庄的生意不景气,天气也总是阴着脸像是有心事。有一个多星期了,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来这里打一夜的麻将,吃一顿美味的“鱼香宴”,就连连打着呵欠走了。“鱼香宴”是以鱼为原料做成的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这也是鱼庄的招牌菜。鱼庄的招牌菜做得很讲究,会做这菜的厨师小明说话也很讲究,他总说他是白领,他和高大福老汉是不一样的。每次高大福老汉看着客人们吃鱼,就想和他们说说话,听听他们对鱼香宴的评价,但他们吃完就忙着打麻将,没心思搭理他。这些稀稀拉拉来鱼庄的人,还是梅花求她那些在城里做生意的朋友介绍来的客人。
梅花打电话求人的样子,总是会让高大福老汉的心狠狠地疼一下。然后他会轻轻地叹着气,想到自己的一辈子……
高大福老汉小时候家里非常穷,母亲恨不得把锅挂在墙壁上。那时他跪着求母亲,让他上了三年学。二十几岁的时候,他苦苦地求村里的老王叔把闺女嫁给他,他给老王叔家白干了两年农活,老王叔的闺女就成了他老婆。接下来老婆不生孩子,他便在每年寺庙过会时提着供品去求送子娘娘,求了十几年,人到中年时老婆才为他生下了儿子高鹏。再后来高鹏到北京上大学,他到处求人借钱,艰难地供高鹏读完大学。还有就是老伴死了,他又求村里人把老伴埋到了自家的祖坟里。到了他这把年纪,他以为他再也没啥事求别人了,可是仔细想想,高鹏大学毕业留在了北京,这远天远地的,他病了怎么办?他死了怎么办?这些事是他不敢想的。有时候他看着自己渐已不多的日子,就想求高鹏回老家来。可是高鹏每次打电话时都求他,求他千万注意身体,好好活着等他成功。高鹏说的成功他不懂,他只知道高鹏是怕他病了添麻烦呢。这世上的事说不成,他不想让高鹏留在北京,可是高鹏被工作牵扯在北京了。也许在这世上除了愿望外,另外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在心愿的力量打瞌睡时乘虚而入,做了他和高鹏的主。
高鹏每次打来电话,高大福老汉都有一种伤心伤肺的感觉。他知道高鹏在北京生活也难,他就告诉高鹏他好着呢,村里人都在照顾他。他求了一辈子人,儿子求他,他却是这样经不起。
鱼庄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冷清,高大福老汉的心里也一天天犯起愁来。他总是抬头去看天,盼着天上的太阳露露脸,他以为天气好了鱼庄的生意就会好。可是老天爷就是不给他面子,连续几天都阴着脸。
刚刚来了几位客人,他们对钓鱼没什么兴趣,一头扎进客房打起了麻将。厨师小明给客人做好了鱼,他看高大福老汉愁苦的样子,就问他:高老头啊高老头,你干啥成天拧着眉头过日子?高大福老汉看了小明一眼,想责怪他没大没小又说不出口,就端着小明油炸的脆黄小鲫鱼给打麻将的客人送了去。
高大福老汉送完油炸小鱼,又给客人送了些水果和茶水,就从客房里走了出来。他站在客房外面,听着客人咀嚼小鲫鱼的声音,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他在心里说:小明啊小明,鱼庄的生意冷冷清清,我咋能不愁呢?我要愁的事太多太多,你是不懂的。
高大福老汉在心里这么说着,远远地看着一群鸡在枣树下觅食,另一群鸡在鱼池边闲闲地散步。他心底竟升起一丝羡慕,不过这也就那么一眨眼的念想罢了,他的思绪又飘到了别处。梅花已有五天没来鱼庄了,不知在城里忙什么。听说梅花的服装店一直亏钱,她在城里筹钱想保住她的服装店呢。昨天,有个在鱼庄工作的小姑娘耐不住寂寞辞工走了,这事梅花还不知道呢。高大福老汉心烦得不行,他不时地抬头去看天。
老天爷还是阴着脸,比了先前,云稍稍地淡了一些,薄了一些,缓缓地透出零散的亮光,可是却无法变成大片的亮光,让真正的阳光洒遍大地。
这样的天气,似乎让高大福老汉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在客房外站了许久,等听不到客人咀嚼东西的声音时,他才又进客房收回了鱼盘和水果盘。他做这些事时一直是不慌不忙的,他喜欢干这些杂事,也喜欢干杂事时的不紧不慢的节奏,他还喜欢宽阔的空间和整个鱼庄的气味。放下鱼盘和水果盘,他又走到鱼池边去喂鱼,沉在水底下的那些鱼儿嗅到了鱼食的味道,哗地一下跃到水面抢鱼食,有的跳出水面很高,又砰地落在了水里。他天女散花般地把定量的鱼食撒到水里,费了他不少的力气。他叹息自己身上的力气越来越少了,没准再过些时日,他就连这些鱼都喂不动了。叹息声似乎又消耗掉了他身上的一些力气,他觉得自己没力气再去另外几个鱼池喂鱼了,他就想坐在鱼池边休息一会儿。
鱼池没有钓鱼的人,显得太安静了,刚好适合高大福老汉想心事。
夏天的时候,来鱼庄钓鱼的客人特别多,鱼庄的收入也好。梅花在城里成立了一个钓鱼俱乐部,会员一拔一拔地来鱼庄休闲打牌,学着钓鱼,有的客人每个星期都来一趟,把钓到的鱼买了带回到城里去。那时梅花高兴得对他说,等鱼庄挣了钱她就带他上北京去找高鹏哥。村里人都知道,高鹏结婚时打电话请他去北京,他却把家里仅有的一万元钱寄给高鹏,说是给儿媳妇的红包,硬是坚持没去北京。他没有钱,自觉没脸见亲家。听说北京的房价几百万,高鹏结婚连婚房也置办不起,他这个做爹的没法在婚礼上露脸。后来村里人说高鹏做了上门婿,以后他这个当爹的再去北京恐怕就更难了。那时他为了这张老脸没去北京,自从梅花说了要带他上北京的话后,他心里就有了盼头。
整个夏天,他都穿着那身怪诞的美人鱼服装在鱼庄穿梭往来为客人服务,有时送烟点烟,有时端茶倒水,有时侍候客人擦汗。有时客人嘀嘀咕咕表示不满,他就陪着笑脸。他的兴奋过于裸露,幸福的光晕在一张布满沟沟坎坎的脸上扩散着,长时间地滋润着他将要枯萎的心田。有时客人还他跟开玩笑,说他的脸上贴了两个红太阳。
高鹏在北京工作很忙,经常加班,不敢请假回老家。五年前高鹏回村里看过他一次,听说就因为那次回老家,高鹏没在公司当上主管,惹得儿媳妇差点离婚。为这事,高大福老汉总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儿子。有时候,他就想高鹏在北京的家是什么样子,还有他没见过面的儿媳妇和亲家都是咋样的人。这样想时他去北京的心情就更急切了。盼星星盼月亮,他盼着鱼庄能挣到钱。等啊等,盼啊盼,他美滋滋地等着要去北京的那一天,他会拿梅花发给他的工资买些枸杞和发菜送给没见过面的亲家,也许这些土特产亲家见了会觉得稀罕。他还想请梅花帮他给儿媳妇买个贵重的礼物,好给他挽回点做公爹的脸面。
往常高大福老汉要喂几个鱼池的鱼,等他全部喂完鱼,也得两个多小时。偶尔要是天气出现异常,刮了大风,或者下了暴雨,刮坏了一些路标和鱼池边的警示牌,扯坏了放置鱼具的塑料棚,高大福老汉还得花些时间维修。在这方面他是行家,哪里需要修补,或者是怎样修补,他心里是有数的。前些日子刮风,塑料棚顶从中间扯坏了,至今没法修补起来。他只能用一些纤维袋子暂时遮住了那些鱼具,不让鱼具因风吹日晒而受损。他等着梅花从城里运回新的塑料布,但梅花总是被服装店的事绊在城里回不来。
想起夏天的那些事,还有鱼庄热闹的情景,高大福老汉的心情有了些变化,他觉得鱼庄的生意过些日子会好起来的。鱼庄这么好的地方,城里人没什么理由不来呀。也许最近城里人忙,等过些时日,他们又会想起鱼庄来,又会一拔一拔地跑来钓鱼。这样想着,高大福老汉身上又渐渐地生出了一些力气,于是他把自己的心事收起来,挣扎着站起身,去把另外几个鱼池的鱼也喂了。喂完了鱼,他又看到了那些裸露在外的鱼具,说什么也得先把这些鱼具保护起来。他想起小明经常在网上买东西,他就鼓起勇气去找小明,想让小明从网上买一些塑料布回来搭棚。
鱼庄有客人时,小明就做“鱼香宴”,没客人时小明就在电脑上打游戏挣金币。高大福老汉看小明打游戏,就站在小明身后嘀嘀咕咕抱怨鱼具这样露天放着,以后就用不成了。小明却说这是老板的事,他一个打工的管那么多闲事干嘛。高大福老汉说,你怎么能这样呢?鱼庄破败了,你咋办呢?小明哼了一声说,我有什么不好办的?跳槽到别的地方去干,在哪里不能挣钱啊。小明黑黑的头发抖动着,露骨地张扬着他意气奋发的样子。在这丛黑头发面前,高大福老汉感到想要维持自己的地位竟是那样艰难,他心中暗骂着小明的无情无义,脸上却无奈地陪着僵僵的笑意。
就在这时,梅花打来了电话,说明天她要带一个大老板回来实地察看鱼庄,她已打算把鱼庄卖掉,用卖鱼庄的钱救她城里的服装店。梅花还叮嘱高大福老汉把鱼庄收拾整齐,说什么也要卖个好价钱。梅花又说了许多,高大福老汉的脑子一直嗡嗡地响,等他放下电话时,他的头脑已经空虚了。梅花的声音没有了,他战战兢兢想把那失踪的声音追回来问个明白,可是脑子里只存放着梅花要卖掉鱼庄的消息。这消息一下就击倒了他,想起自己到鱼庄工作的日子,每天穿了怪诞的衣服忙来忙去,别人不干的活他抢着干,他爱鱼庄就像爱自己的一部分肉体一样。只是他的内心,常常有一种力不从心的隐痛,他对谁也不说,自己也不敢承认,竭力不去想。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梅花要卖掉鱼庄,他整个人就像挂在空中的一堆没有生命的肉,这肉要往下掉,非掉不可。这肉掉下来的同时,还要把周围的一切都拉下来似的。
高大福老汉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小明的屋子,他心里的苦水多得倒不完,也不知往哪里倒。他得先去把鱼池周围的杂草拔了,还得去把枣树下的那块地整干净了,还得把那几群鸡喂一喂。总之,这是他在鱼庄的最后一天了,他要把该干的活都干了,到了明天,这鱼庄就是别人的了,他就是想干别人也不要他了。高大福老汉边想边走到了枣树下,他抓了两把玉米喂鸡时,突然发现鸡群里那只最漂亮“航母鸡”不见了。那只“航母鸡”的毛是紫红色的,锦锻一样光滑。它是鸡群中最艳丽的一个,总是像个贵妇一样仰着头招人眼球。现在它竟不见了,它在梅花将要卖掉鱼庄的紧要关头不见了踪影,这让他明天怎么给梅花交差呢?他的心顿时慌了,他担心这只丢失的鸡去了近旁的庄稼地里觅食,找不到回来的路。或者它被附近庄稼地里干活的人捉走,已煮进锅里成了下酒菜。
一只丢失的“航母鸡”,居然让高大福老汉牵肠挂肚起来,他要找到它的愿望也变得异常地强烈。
他觉得没有了这只最漂亮的“航母鸡”,鱼庄就会缺少些什么。他不管鱼庄明天是谁的,他都一定要把这只丢失的鸡找回来。于是,他穿着那套美人鱼的服装,像鱼一样游进了密密麻麻的庄稼地里。他挥动着手臂拨开拂在他脸上的玉米叶子,嘴里“啁——啁——啁”地叫着鸡,他指着玉米地里的青豆秧子命令它们把他的“航母鸡”交出来,他找了一只在田间飞舞的蝴蝶想叫它变成“航母鸡”。在找“航母鸡”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怨梅花了。鱼庄是人家梅花的,人家想卖就卖,难道你想让她守着鱼庄喝西北风?高大福老汉在庄稼地里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了再爬起来,他一门心思就是想找到那只“航母鸡”。可是找啊找啊,他找到天黑都没有找到。
周围的一切都暗了下来,他在暗夜中摸索着前行,到后来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甚至把自己也忘了。这种情形是出其不意的,他忽然觉得一片虚空……好像什么想法都没有了。等到他清醒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他茫然若失,发现自己还在庄稼地里,在黑的玉米林子里。天上的星星向他眨眼时,他也久久地看着夜空,就刚才找鸡的几个时辰,仿佛自己过了整整一生。
后来,他在庄稼地里脱掉了身上那套怪诞的美人鱼服装,平平展展地躺在了金黄色的粮食上。没有了鱼庄,他不知道自己该上哪儿去,当然是回村里的那三间旧屋里等死。等死?这是一件多么糟心的事啊,他不愿想这件事,但不由自主地要想,而一想到这事他就心灰意冷,浑身变得没一丁点力气。死的事把他的身体毒害了,他的神经受到了种种折磨,一忽儿胸口受到了压迫,一忽儿又是一阵疼痛,一忽儿又喘不过气来。梅花要卖鱼庄的事似乎和死一样可怕,使他受着临终的痛苦。他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他也相信人死了会上天堂会下地狱之说,但他不喜欢上天堂也不喜欢下地狱,他很害怕自己在睡梦中就突然死去…..天哪!天哪!他再也见不到儿子了,他还有未了的心愿,他怎么可以死去呢?这样胡思乱想着,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从七十岁开始,高大福老汉就怕睡觉。无数漫长的夜里,他总是睡不安稳。这个夜晚也一样,他睡在庄稼地里先是断断续续做了一串怪梦,浑浊的空气使他呼吸阻塞。他的头和胸腔都热烘烘的,白天的事在睡梦中格外夸大了,化为种种幻觉。在神经极度紧张之下,黑夜挤压着他刺激着他,让他的痛苦似乎无穷无尽。
天亮的时候,梦中的他坐在鱼池边钓鱼,像那些客人一样,把鱼饵一本正经地丢在鱼池里,等着鱼儿来咬。他不时地拉起鱼杆,觉得鱼杆有些沉重,像是钓到了什么宝物……他喘着气拉鱼杆,鱼杆竟从中间折断了,把他像鱼儿一样甩进了鱼池…..
鱼庄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它不分昼夜,不论晴雨,就那么存在着。哪怕创建它的人不要它了,要把它卖给别人,它也还是存在着。高大福老汉在梦中又想起了那只丢失“航母鸡”,他想自己一定要把它找回来交给鱼庄的新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