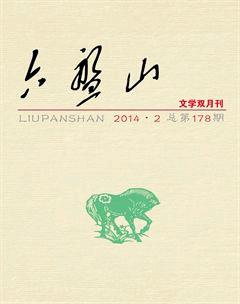女诗人的榆树
许艺
她静默着,看窗外挺立在盛夏阳光中的那棵榆树。
一只黑猫在浓荫下蜷成一团,用慵懒的午睡打发漫长的时光。很难确证那究竟是一棵树在高处分成了等粗的两枝,还是原本就是两棵树。一堵旧围墙刁蛮地遮住了地面以上的一部分树干,围墙这边的人几乎永远不可能知道这树的真相。她静默着,看它龟裂无情的树皮,看那些像疯妇人一样颤抖着伸展开来的枝桠。
在眼疾葬送掉她的前程之前,她是位享有盛誉的诗人。
那时候她还很年轻,甚至可以说还完全是个女孩儿,台下的人高举着皮面笔记本或者印有她诗歌的稿纸——也有的年轻姑娘挥动着头巾,希望她能为他们留下签名。诗会的组织者很快地引领她离开现场,这常常使她对身后热情的呼喊感到羞愧。当然她也经历过真正的羞辱,她的诗歌才华引起了一些官员的注意,当她没有勇气一一咽下官员们杯中火烈的白酒,他们就会很生气,用她并不能完全听懂的话刻薄地辱骂她,因为她的行为让他们丢尽了面子。她像每一个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女孩子常做的那样哭起来,官员们看着她那一串串滚落的泪珠面面相觑。
当然这些都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想起来模糊得厉害,像是小时候听过的一个虚构的故事。有时候她会真诚地怀疑,这一切终究是不是真的,它们是不是只在她的想象中发生过。
现在,每天晚上十一点半她开始跑步。
一开始这样做是听说睡前跑步有助于治疗失眠症。有时开灯跑,那样她跑过的道路是一卷扁平的,硬而脆的白色卷纸。不开灯的时候分两种情形,有月光的和没月光的。有月光的时候她跑在一枚鸡蛋里,那鸡蛋被掏走了蛋黄,透明的蛋清刚刚凝固,散发着青白的光泽,她就在那样的鸡蛋清上跑。没有月光的时候道路最广阔,没有墙壁没有栅栏,没有小草投在地面上的细碎重叠的阴影,那是一条大家都不陌生但谁也没有真的注意过的路,诗人试图寻求恰当的比喻,告诉人们那究竟是一条怎样的路,但她至今没有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喻体。
就这样,诗人以跑步来迎接每一天的开始。在深蓝色夜空笼罩下沉睡的大地上,在她所居住的这座沉入睡眠的小城,在沉睡的街道、水泥建筑、杂货棚和老榆树之外,诗人在摆放了床、书桌和洗脸盆的十平米地下室里跑步,她的双脚在床与书桌之间一尺宽的空地上奔跑,脚印和脚印不断重合,在她的脚下厚厚地堆积起来,诗人渐渐升高,在白色卷纸、鸡蛋清或者那条最熟悉的路上跑步。四下里寂静无声,诗人脚下是地下室结实的水泥板,再往下是纵横交错、锈迹斑斑的旧式下水管道系统,而头顶是长年空置的一楼的一间房子,那里面寂寞的木质家具偶尔因为干燥发出一两次响声,像人类过于衰老的骨骼常常经历的那样。
这样的跑步很容易让人麻木,一旦开始就会忘记主动停下来。或许正是这样才让人感到疲惫,进而驱走了失眠。有几次这样的跑步让诗人迷失了方向和时间,她遇见过一次小学同学,另有一次她遇见了初恋的爱人,他还像当年那么瘦。因为瘦,远远看起来他的两个肩膀像佩戴了肩章一样高高地耸起,可这样成熟严肃的肩膀实在和他本人不相配,那时候他正绞缠住双手嗫嚅着不敢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诗人在麻木中感到心脏一阵钝痛,闭上眼跨大了步子越过他。
诗人究竟是怎样染上了眼疾很难说得清,北方的风沙,小城的煤渣,长期熬夜,营养不良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可并不是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长期熬夜的营养不良者都害这种眼病,医生的解释是:“个体差异”。这是一个太富玄妙色彩的解释,她不能满意。她久久地坐在诊疗室的长椅上不肯离开,恳求医生再给她做一次全身检查。医生解释说完全没有必要,但她还是不走,看着医生一个个诊断病人,开出药方。诗人觉得医院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何况长椅上还有暖融融的阳光。
在追问眼疾的根源这个问题上,她丝毫不具有诗人的浪漫和感性,她坚持寻找一个硬邦邦的根源。她找到了,是毛巾,她的常年生着霉斑的毛巾。
这地下室原本会比其他的地下室干爽一些,因为它有一部分高出了地面,在接近屋顶处开了一扇窗户。虽然只是窄窄的一扇,但与普通的地下室相比,已足以让人感到振奋。比对一下这栋建筑的破旧程度和窗外榆树树干的粗细,就可以知道这座钢筋水泥建筑竣工的时候,那榆树还没有栽下。而现在,榆树以水分和时间为筹码,轻易地击败了这钢筋水泥建筑和它铝合金的窗户,把她规划好的振奋变成了淤泥一般的沮丧。设若原本就没有窗户,那么淤泥是一滩,而在振奋之后降临的沮丧,让淤泥变成了两滩。两滩淤泥压得诗人喘不过气来,她常常像此刻这样静默着,透过窗玻璃和榆树密匝匝的叶子,寻找天空和偶然穿透了榆树叶子的阳光。
榆树有手腕粗细的一枝不知何故被劈开了,像脱臼的胳膊一样吊在主干上,真是大快人心!而养分通过那没有劈断的半个枝条继续运输,那脱了臼的手臂竟还活着,恬不知耻却葱笼地活着。“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顽强的敌人”,诗人一边得出这个结论,一边在想象中挥舞两柄利剑,追逐着太阳的角度砍削它的枝叶。她想象着它们像干枯的毛发一样颓然飘落,金黄的阳光锐利地射进窗户,落在她的床上,书桌上,落在她的洗脸盆和毛巾上,落在她夜间跑步的空地上。潮气如鬼魅的飞蛾一般忽闪一下翅膀就不见了,她的床铺散发出童年时代干燥麦草的香气,而毛巾——毛巾干爽鲜亮,墨黑或灰绿的霉斑像梦魇一样退去,诗人自己眼眸清亮,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一部新的史诗。阳光照着稿纸,看得清纸页上最细微的绒毛,以及笔尖投下的淡淡的影子。
“啊,阳光,啊,阳光”,诗人望着榆树,粉红色的眼角蓄满浑浊的泪水,她朗读巴尔蒙特的诗歌:“为了看见太阳,我来到这世上……”
这一切都不是虚妄的想象,因为冬天的时候她实实在在地经历过那样的幸福。
绝大多数树种都是薄情寡义的恋人,不管躁动的春天和殷实的夏天说过多少动人的情话,一旦肃杀的秋风刮过几场,它们一定会有预谋地慢慢蒸腾掉叶子里的水分,徒留给叶子一个挺括的表象。它们一边敷衍着叶子傻气的热情一边为最后的背叛谋得策划的时间。当白杨树陆陆续续丢尽了叶子,榆树还极力拉长着承诺的限度。寒风再来的时候它一夜之间卸光了所有的叶子,缩紧肩膀露出薄情的真面来,它眉眼紧闭任由寒风像暴怒的情人一样抽打它的枝条。
这样的日子,对于诗人来说无异于一个节日。
那真的像一个节日,她炖了一锅骨头汤来庆祝这个节日。十平米的屋子里弥漫着肉汤的香气,揭开锅盖,浓白的肉汤里翻滚着娇媚的枸杞、黝黑的木耳和憨厚的冬瓜。当她盛出一碗放到桌上的时候,阳光正好透进来。榆树颓败的枝条只能给床单上投下淡淡的影子,像可爱的水印,整间屋子暖洋洋亮堂堂的,连墙壁上没有涂抹开的涂料粒都看得见自己笨拙的影子。那时候诗人满心欢喜,她重新拿出稿纸来,在每天阳光能照到书桌的短暂的半个小时内,试着写下一部史诗的开头。阳光豁达地漫过她的脸,她假装低头对着稿纸沉思,却调皮地望着自己鼻尖金黄的绒毛嘻笑。
当冬天的干雪渐渐夹带起暧昧的水分越来越快地融化,诗人重新回到窗前,忧心忡忡地望着她的敌人。它的枝条暂时还紧缩着,但她知道它已经挺过了隆冬的严寒,从昏迷中醒来。“你在假寐,我很清楚”,诗人理智地对榆树说。一只黑猫在矮墙上从容地走过,经过那枝最矮的枝条时,它竖起尾巴来勾了一下干树枝,两小块纠缠的湿雪就掉落下来。黑猫看都不回头看,迈着优雅的步子往矮墙的另一边走去。
没有阴云的时候阳光照样每天光顾诗人的小屋,可她看得出来,阳光已经不再散发金灿灿的光芒,它面色惨白,像个没精打采的病人。诗人不知道这样的时候她是该抓紧时间再写几行有光亮的句子,还是该静静注视着它移动的脚步,她不知道究竟怎样才算是更有效地珍惜它。像送别一个即日就要出门远行的亲人一样,诗人日日盼着天晴,盼着与阳光多一次叙谈,她希望这样的分别慢一些,再慢一些,她希望这是一场拖泥带水的分别。
诗人依然每天晚上跑步。她感到很苦恼,不仅仅因为春天要来了,还因为她无法解释自己自相矛盾的行为:她不想冬去春来,却每晚跑着去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
“你很急切吗?”
“并不——完全不,我希望慢一些。”
“那么你还是要奔跑?”
“我不知道……”
诗人在内心常常与自己进行这样无声的争论,这样的时候她越跑越快,一只脚印还没有完全落下另一只又很快地覆上来,脚印虚蓬蓬地摞起来,踩上去软塌塌的,像堆积起来的腐叶。一不小心脚就会陷住,再拔出来时鞋面粘着几片碎叶子。这时候是跑在葳蕤的丛林里,藤条和撑破地面的树根硌得脚生疼,乔木灌木和野草纠缠在一起,看不到光线,连空气都是稀薄的。
春天来的时候总是比冬天快,她像个急性子的女人推推搡搡地挤走了温顺的冬天。诗人的眼角已经开始发痒了,她知道更大的溃烂即将到来。黑猫整夜整夜地呜咽,像狂风的琴弓在电线的弦上来回地拉,尾音总落在凄厉的高音部上。这演奏招来了另外的一些琴手,它们此呼彼应,唱和不休,复调部分的曲谱里掩藏的全部是关于春天的流言。诗人奔跑在深冬的暗夜里,白天撒下的纸钱在夜风里无助地翻滚,每只猫眼都是一柱强光,光柱迅疾地交错,追击着诗人的脚步。它们是真的焦躁,真的渴望春天早一点到来。狡黠的猫们毫不怀疑,当小城的一切都堕入睡眠的时候,只有跟随诗人的脚步才能最早踩上新的一天的时间。这时候的路是一条越狱之路,诗人一路被绿色的光柱射击,她成为一个逃犯。
诗人愁容满面,她又去找医生。坐在柱灯下,医生又打开一只钢笔一样的小灯,诗人的上下眼皮被轮番地翻过来,溃烂的粉红色眼睑上布满蛙卵一样的小泡,穹窿部堆积着一团脓点。医生略皱一皱眉头,给她开了四种眼药水。诗人忍无可忍,她焦躁无助得像个孩子:
“大夫,您不能再这样年复一年地对我采取保守治疗了,再这样下去我的两只眼睛非瞎掉不可。”
她的眼眶里立刻蓄满泪水,她自己说出的“瞎掉”这个词让她感到无比悲伤,“我再一次请求您,请给我做一次全身检查吧!真的,否则您永远不知道我为什么总是被眼疾困扰,霉菌已经长进我的肺里肝里肠胃里了,我的前程就这样被葬送了您知道吗?”医生以职业化的亲切劝慰她,安排她在长椅上坐下,还递给她一杯热水。诗人还沉浸在“瞎掉”带给她的伤害里,她握着一次性纸杯,看水汽像细沙一样升腾起来,在阳光里散开,无影无踪。
四种眼药水编了号,每隔半小时换一种。诗人仰面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看见自己蛙卵一样溃烂的眼睑,睁开眼睛看见窗外被雪水泡得肿胀的敌人的枝条。她绝望地往自己的眼睛里滴药水,像腌制泡菜一样把眼珠腌进药水里。她知道这些药水什么用也不管,满溢出来的泪水和药水混在一起,滴落在毛巾上,留下一个又一个墨黑或灰绿的霉斑。
连诗人奔跑的路都长了霉斑,鞋底的霉斑和路上的霉斑碰在一起,像麦芽糖一样粘住彼此难以挣断,留下一个又一个发霉的脚印。诗人在深夜掩住口鼻竭力奔跑。她自暴自弃地在暗夜里吼叫:“来吧来吧来吧,春天,你索性就呼啸着降临吧!”和猫们彻夜的演奏放在一起,它们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乐团,可以演奏最复杂的协奏曲,而她是一个蹩脚的领唱,嗓子里是一只破了滚珠的轴承在仓皇运转。
榆钱就长了出来。远远望去像一簇一簇嫩绿的桃花。
诗人这时候完全病倒了。她的两只眼睛肿得像荔枝,上下眼睑像两片砂纸,睁开磨自己,闭上磨眼珠,粘稠的眼泪渗出来,将糜烂传染给眼角,眼睫毛一根一根地倒在脓液里。霉斑在枕头下整块整块地蔓延。
诗人无法跑步了,床与桌子之间一尺宽的空地上,脚印互相推搡着前行,底下的翻上来,上面的被踩下去,像魔术师玩着一大摞扑克牌,一遍又一遍耐心地洗牌。霉菌在脚印上大有作为,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着新的一天的来临。
一株榆树每年要经历两个秋天。当白杨树长出了婴儿巴掌大小的新叶,榆树满枝挂着的榆钱就变薄,变黄,风一吹,它们像眼泪一样飘落。诗人打开窗户,看它们一瓣两瓣地飘进窗户,落在她的枕边。诗人从结着脓痂的眼睛看出去,猛然发现那惨白的榆钱和她深夜跑步时在路上翻滚的纸钱何其相似!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榆钱落尽的时候白杨树已经唱起新一年的情歌了,它晃动树身,任意两片相遇的叶子都可以呱嗒呱嗒地拍出掌声。诗人在清晨的歌声和掌声里醒来,她看到窗外的榆树光秃秃地支棱着细枝,像灰凄凄的旧稿纸上凌乱的折痕。阳光重新透进窗户来,照在她的病眼上。
“诈降”,诗人对榆树说。
从榆钱落尽到新叶长出,还有至少两个礼拜的时间。这期间诗人的病情明显缓解,她又可以下地了。在阳光照进屋子的这一段宝贵的时间里,她仔细地清扫屋子,灰尘从笤帚上升起来,在阳光中欢快地翔舞。床和桌子之间一尺宽的空地上,脚印湿霉成残片,诗人把它们一下一下扫进簸箕里去。
深夜里,诗人熄了灯站在空地上。下过一场春雨的天空在此刻现出暧昧的玫瑰色,榆树枝嵌在天空,像玫瑰色金丝绒上烫印的图案,那是一堆散落的花枝,只是遗失了花朵。她久久地站在空地上,像长跑冠军伏在起跑线上等待着发令枪啪地一声响,她将像子弹一样被射出去,奔跑,奔跑,昂首并竭力向前拱出胸膛,去挂终点处新的一天的彩条。哦,不,不,她不能再奔跑了,她的眼角刚刚结痂,这样会让干硬的眼眶迸裂,血水横流。
整整一夜,空地上只留下了两只脚印。孤零零的。
次日清晨,诗人早早醒来。梳洗完毕,她坐在阳光最先降临的床脚,眼睛望向窗外。
细细的榆树枝鼓胀得像少女的乳房,她看得出它们的不安和期待。榆钱褪落的地方将长出新叶来,一簇一簇的新叶,它们在几天里就可以迅速地长大。它们兴奋地缀满枝条,在轻风里摇晃。
“我要出去一趟,总有个地方能治好我的眼病。”
诗人想着远方,想着她回来的时候眼角干爽,眼眸清亮。“等我回来,大概已经是夏天了。”
榆树摇晃着,先长出来的三五片新叶挑在最高处阳光充裕的地方。少不更事的新叶不知是否懂得,它们是为战争而生的,战斗是它们的宿命,这将贯穿它们的一生,不管将遭遇强将还是弱兵。在这漫长的战役里,它们会学习射击和躲避,学会用脏话辱骂敌人和战友,它们会被阳光催迫得强壮,放任肤色从晶莹透亮的翡翠色变成浓重的墨绿。
“你们喜欢夏天,我知道。夏天是你们的荣耀。——像我喜欢冬天一样。”
黑猫引来了另一只黄猫。它们在树下的矮墙顶蹲伏下来,你一声我一声地拉动琴弓却久久不肯靠近。它们在试探,在考验。或者其中一只已经厌倦了,想要离开,却苦于找不到一个体面的借口。恋爱变成了对峙。没有谁愿意第一个撤退,战争一旦开始,无一例外地都会坠入这个毫无理性的怪圈。
“为了看见阳光,我来到这世上……”诗人一遍遍念着诗句,像念着一句柔若无骨的咒语。她就这样坐在床脚,像一位苍老的先知,守望着即将射进地下室窗户的第一束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