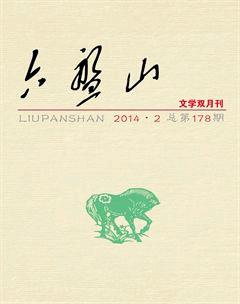钥匙
吟泠
阿维在市体育馆对面的玫瑰花园住了十三年,最近才搬到离单位近一些的亲水苑。房子虽然是二手的,但装修和户型都不错,阿维一眼就看上了。是老同学汤红珍给牵的线——原主人是市交通局的领导,工作调动了,房子当然不能带走喽。一百五十平米,精装修,外带一个地下室,总价五十六万还包过户,第一次见面就谈妥了。事后,阿维私下里又打探了二手房交易价格,暗自算了一番账,心里的欢喜,就像女孩害羞时泛起的红晕,很久都不曾消退掉。
现在,阿维住在亲水苑3幢308室,已逾数月。金三银四,阳光充足,视野开阔,令人舒爽,阿维的心里也充满了阳光。先前玫瑰花园那套90多平米的房子,则以9000元的价格租给了兰州来的两个工程师。这么合适的房租,和这么合适的房客,不是很容易就能碰到的。因此阿维觉得本命年自己诸事顺利,吉祥如意。两年前,像阿维这样带家具的三室两厅,顶多能租4000块,这两年,因为从河南来的传销人员激增,房租也就日渐水涨船高,炙手可热。汤红珍总说阿维财运好,想啥来啥,事实似乎确也如此。
像阿维这般年纪的女人,上班都是做做样子,没有人会把腰酸背疼腿抽筋的她当成单位里的顶梁柱。可以按时来,也可以迟来,但不可以不来,是常见的那种老油子。班还是要上的,阿维想。再过三两年,年龄一到,想上班都没处可上了,就彻底放了羊,大半辈子在单位里修炼来的种种“功夫”呢,端端是白费了。一想起自己的年龄,一想起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阿维就如遗失了珠宝,有空空如也的失败感。这种不甚美妙的感觉,跟失眠、健忘、多汗和月经紊乱一样,已经伴随更年期的阿维很久、很久了。
那天是个礼拜天,下着小雨,阿维正在浴室中精心保养那张比同龄人显得年轻许多的脸,电话忽然响了。是房客打来的。阿维拿着话筒,听着。听到最后,阿维挂掉电话,坐在沙发上,张着嘴发起呆来。脸上的海藻面膜还黑乎乎地顺着颧骨往下慢慢滑动着,像一窝蚯蚓在那里蠕动。
原来昨天晚上,租住在玫瑰花园的两位房客喝酒回来,上错了楼层,拿着阿维留给他们的钥匙,居然将四楼张校长家的屋门打开了。当时张校长老两口正在客厅看电视,看见两位不速之客忽然醉醺醺地闯了进来,还以为进来了两个歹徒,张校长的老伴心脏病差点就给吓犯了。
就在阿维坐在沙发上发呆的时候,手机又响了。是张校长打来的。张校长也是刚刚从任职上退下来不久,还处在心理调试期,因此说话的口气就不大好。张校长用上级告诫下级的口气对阿维说,他老伴已经卧病在床,都是昨晚让那两个贼给吓的。张校长还说,他已经让开锁公司换了防盗锁,是最贵的那种。末了,张校长还说,我们做了十三年楼上楼下的邻居,幸好还没发现丢过什么贵重的东西……不忙的话,请你还是抽空过来一趟吧,看在多年老邻居的份上,我就不给派出所打电话了。阿维只有嗯嗯喔喔的份儿。一开始,她以为那两位房客在胡说八道,还半信半疑着。张校长电话打来后,阿维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张校长的老伴有心脏病,以前阿维住在玫瑰花园时,她就被送到急救中心急救过两次,有一次还是阿维帮忙打的120……张校长的老伴是个药罐子,每当看到那个佝偻着背的半老太太,阿维仿佛就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张校长的意思,阿维已经听出来了。第一,张夫人受了惊,闹出病了。第二,他为此付出了金钱。第三,他已经给了阿维一个面子,那意思很明显,让阿维看着办。阿维是个聪明的女人,当然能听出张校长电话中的意思来。她一边清洗脸上的面膜,一边想着当时的情景,别说是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这事即便让自己遭遇上,阿维想,她也会吓个半死的,而且还是深更半夜。因此,阿维觉得非常有必要到张校长府上拜访一下,买上些慰问品,表个态度,给张夫人压压惊,以表歉意。尽管这事本身跟阿维没什么直接关系,但她毕竟是房东,房客把这事如实告知了,她也就没法装聋作哑。
当然,应阿维的要求,两位工程师也及时更换了门锁和钥匙。玫瑰花园附近就有一个老陈开锁店,十三年来,阿维无数次从那间很不起眼的小店前经过,鄙夷着那店铺生意的冷清寥落。看来,阿维也许想错了,老陈的开锁生意,大约还是不错的呢。
初秋的黄昏雨,已经很有些凉了,细细的雨丝飘落在红色的雨伞上,发出轻轻的滴答声。本命年,阿维从里到外都是红色当家,图的就是诸事顺利,心想事成。因此,从背后看去,穿着玫红色风衣的阿维,颇有一番成熟女人的香艳之感。阿维的业余时间和金钱,几乎全都花在保养脸面和身段上了,但这依然掩饰不住藏在她脸上的秘密。对女人而言,这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
现在,走在去玫瑰花园张校长家的路上,阿维脑子里全是关于钥匙的事。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看来,这句老话不大靠得住。若在十三年前,遇上这样的事情,阿维会用减法处理,很快就能将这件小事从自己的脑海中删除。但现在,阿维由不得自己了,她总是在盘算这件事,就像陷在泥沼中的动物一样。从昨晚到这个落着雨的黄昏,她觉得自己的脑袋,似乎都要变成钥匙的形状了。最让阿维恐慌的是,她在家,或者不在家的时候,亲水苑陌生的邻居,也许也会上错楼层,用自己的钥匙,一不小心打开她的门锁——这样一想,阿维心中的不安与恐慌,自然就多出来一层。出于戒备心理,在跟房客和张校长通过电话后,阿维也在第一时间更换了亲水苑的门锁,换了最贵的一套防盗锁。这样,她心里才踏实起来。换锁的时候,她跟干活的师傅聊天,才知道做这一行的,原来是很能赚钱的。按照阿维的逻辑,开锁店的生意,本不该很好的。比如阿维,年轻时也有点随随便便马大哈的样子,但这么多年来,居然还不曾丢过钥匙。因之,她对开锁店是很陌生的,若不是遭遇这事,她真的不曾有机会光顾这种鸡毛小店。得知这样的鸡毛小店生意居然都很火时,不知怎么,阿维心里隐隐约约觉得有些不爽。
于是,阿维就给汤红珍打了电话。电话那端,汤红珍笑得跟野鸭子一样。很多年前,汤红珍的笑声可没这样难听。看来,女人老起来时,连声音也会变老,变难听的。所谓银铃般的笑声,合该只配得上妙龄女子。汤红珍笑过之后,没有直接回答阿维,却反问她:难道一个男人只能跟自己的老婆睡觉吗?难道一个女人只跟能自己的老公睡觉吗?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得了吧!然后,汤红珍说还要看股市行情,没工夫理她,就挂断了电话,还不忘顺便嘲笑阿维神经过敏。
难怪汤红珍会这么说。据阿维所知,这位老同学的老公,和老汤本人,似乎都被另一把“钥匙”打开过。老汤虽然没有明说,但酒后断断续续的言词中,已经数次漏了底,有发泄对老公的不满,也有炫耀自己,双方打了一个平手的意思,阿维能听出来。
阿维觉得,自己确实有些小题大做,神经过敏了。她试图把汤红珍和她的话撂在一边,抓紧时间安抚张校长夫妇,然后就忘掉这个意外事件。但她发现自己并不能支配自己。在偌大的客厅里,她像一只漂亮的金属球,在钥匙这两个字眼上滚来滚去,直到自己的脑袋都被研磨成钥匙的形状。
只有阿维明白,自己之所以变成了一个加法行事的人,都是年龄惹的祸。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使她这个老油子在单位很不受待见,她的意见和建议,不过让别的同事觉出她的老态罢了。阿维很能感觉到这一点。她觉得自己像一个过了气的二流演员,越来越被生活这个大导演忽略和冷淡了。跟48岁一起来临的,居然还有很多琐碎的附属之物,这是阿维之前不曾预料到的。不是亲历,她感受不到这些菌类般细小的微生物对自己一点一滴的,也是致命的侵蚀。
比如,在究竟给张校长买什么礼物上,阿维就陷入了僵局。一开始,阿维将礼物的标准定在一百元之内,到了礼品店,才发现这个思路有问题了。看上去体面些的礼盒,每一盒都在二百元左右,便宜些的,自己都看不上,贵的呢,又心有不舍。何况,自己素来跟张校长没什么交情,仅仅知道他是校长。至于究竟是哪所学校的校长,阿维还真说不上来。至于那个面色阴郁的校长夫人,阿维就更不熟悉了。都是钥匙惹的祸。阿维想,若没有这个小插曲,她才懒得跟这对曾经的清高且倨傲的邻居打交道呢。阿维的电话,大概也是张校长从房客那里索要来的,阿维记不起她曾给楼下的邻居留过电话。
阿维想,她的房客本不是小偷,事情只不过是一场误会,何至于如此兴师动众,斤斤计较?因此,阿维要无端为张校长破费银子,这使阿维不爽。但,只能硬着头皮应付一下,阿维也是有教养的人。现在看来,一百元无法打发曾经的芳邻,还得多破费一点。踌躇片刻,阿维买了两盒礼物。一盒黄金搭档,一盒特仑苏奶,也就二百元的样子,可以啦。很久没人可以探看,也不被他人所探看,阿维不知道现在的人情物什一路上涨。张校长换的那把门锁,大约就这个价钱,能让他得到一些心理安慰,也就行了。出了礼品店,阿维自己都觉得她过于纠结了。
两只手要拎东西,红雨伞只好收起来了。幸好雨也停了。没有了伞的遮挡,视野宽了许多。阿维用眼睛的余光发现有路人不经意地在打量她,心里就有一点微微的摇曳感,好像在靛蓝的暮色里,她变成了诗意而忧伤的、曾经的蒲苇。一时间,她有点迷离和恍惚。也许是这样一个久违了的靛蓝色的黄昏打动了她。实话说,很久以来,她很少被什么东西所打动过。而这会儿,她像是中了时间那镀了金的子弹,受了一点轻伤。走在秋雨后的台湾路上,阿维的眼睛里有点潮,因为陌路人在暮色里对她那不经意的一瞥。
从亲水苑到玫瑰花园,大约有四站路,没有直达的公交车。但阿维还是选择了徒步,也算低碳吧。阿维深深呼吸了一口气,打起精神加快了脚步。
这时,她看见了他的背影。准确地说,是特别像他的一个背影,在她前面数米远的地方,以跟她相似的速度匆匆走着。阿维一直跟着他走,因为这张背影所要去的地方,似乎跟阿维一样,也是玫瑰花园。因此,这一男一女,相距不远,走过台湾路,拐到大庙街上。据说很久以前,这里曾有一座庙,很有些灵气,因之香火就很旺。后来不知怎地,就一天天地败落了,无人问津,若干年前,以危房为名,最终被拆掉了。据说,就连大庙街这个名字,也将要被地名办改掉,新的街名,还在相关部门的酝酿与征集中,大约也是很时髦浪漫的一个名字吧——这些,阿维只是听说,她早就不再关心这些与己无关的咸淡事情,从十年前开始,她就开始割裂自己与生活的种种联络,一点一滴地,循序渐进地,当然更是刻意的——她尽一切努力,使自己居于忘川之上,好去做一个善忘之人。
时光的子弹呼啸着飞来飞去,其实阿维早已经遍体鳞伤。
那个蒙面的枪手,就是阿维的丈夫。那个绰号“一枝花”的男人,在十年前的某个傍晚,很不体面地死在了石榴的床上,是突发性的猝死。石榴是天方小城里小有名气的女人,开着一间杂牌子内衣店,据说她的一半收入,都直接来自于男人的荷包。因此,“一枝花”的死,就有做鬼也风流的意思了。这件事情,在不足三万人的天方小城里,很是热闹了一阵子。彼时,阿维真的被逼到了悬崖边上,有粉身碎骨之感。在此之前,石榴接客还属好事者影影绰绰,隐晦不明的闲言碎语,“一枝花”的猝死,呼啦一下,就把那道肮脏的遮羞布给扯下来了。
最让人气愤不过的是,石榴并非是貌美的女人,且身材短小,出身市井。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女人,都能在“一枝花”那样有身份的男人身上揩油,混吃混喝,漂亮些的女人,只要自己愿意,就更容易得手了。
彼时,阿维觉得自己就要死掉了,然而,她还是奇妙地存活了下来,似乎自己不过是被一条恶狗狠狠地扑咬了一口,她只需要打狂犬疫苗,还不曾因之致命。
更让人气不过的是,据说枪手猝死之后,石榴的生意并没有受到多少负面影响,反倒是阿维自己,在天方小城没有立锥之地了。阿维能做的,就只有逃离,像离弦之箭那样,飞快地逃离。
这件事情跟汶川地震发生在同一年,但阿维真地无暇顾及到令世人瞩目的、那个伤痕累累的地方。躲在另一座陌生城市的一个角落中,独自举杯,泪流满面。但在红与绿水吧偶遇汤红珍的时候,她又露出一派欢颜,那欢颜跟不少名烟名酒一样,是掺了很多假的,老辣的汤红珍一眼就能看出端倪。汤红珍很同情阿维的先生英年早逝,她知道他们是很恩爱的一对。当然啦,在阿维口中,“一枝花”的死因,直接变成了一场惨烈的车祸。这是阿维对汤红珍撒的最大的一个谎言。阿维以为,离开了谎言,生活反而会露出更大的马脚。
就这样,阿维只身来到了青山市,跟随她一起来的,还有她那颗被自己屏蔽、冷藏起来了的心。汤红珍在这里很有人脉,地盘也大,跟安置那些老实巴交地拆迁户一样,很容易就安置了有着一技之长的阿维。因此,阿维笑称老汤是“留得青山在”。阿维说这样的玩笑话时,眼里是半潮的。彼时彼刻,在阿维眼里,老汤就是千手观音,及时出手,从绝境中搭救了她一把。这份情谊,阿维不能忘。阿维对老汤守口如瓶的,是老汤的老公在某些时候对自己的种种暧昧与暗示。因为那个老男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单身已久的阿维,一定不会拒绝他的暧昧与暗示,除非她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一想起这个,阿维就有一些难言的伤感。她替老汤难过,也替自己难过。难过老汤的佯装糊涂,和自己真的已经不是一个完完整整的或者是正常的女人。
这使阿维更相信,一个女人在有了难处时,其实应该找同性,而不是异性来求助。想想看,假如当初阿维在红与绿水吧遇到的不是汤红珍而是牛万里,结果又会怎样?牛万里同样在青山市供职,也是阿维的老同学,且很仗义,但,因了枪手留下的那枪伤,阿维很难再相信任何男人,任何男人在阿维眼里,都有“一枝花”那道貌岸然的下流影子。事实证明,阿维是对的。就在阿维在青山市安顿下来不久,牛万里就出了事。牛万里酒后失德,居然放胆跑到小情人家里睡觉,偏巧遇到小情人的老公突然回家,情急之下,平日里以智叟自诩的牛万里,居然慌不择路,义无反顾地从四楼跳了下来,腰腿都摔成了好几截。接到居民报警,110介入之后,“牛处长坠楼事件”就很难再遮掩下去了。更叫人大跌眼镜的是,牛万里的那个小情人,是新当选的全市精神文明标兵,先进事迹刚刚上了《青山日报》的头版头条。
这就是阿维越来越冷笑、戒备那些高大者与光荣者的理由。“一枝花”当初就是那样一个高大者与光荣者,奖章得了一大堆,阿维当成宝贝珍藏着,直到他衣衫不整地死在石榴的床上。从“一枝花”身上,阿维明白了一个男人其实有多么分裂,生活其实又有多么荒唐。阿维常想,假如“一枝花”没有死,被救了过来,他们还会一起生活吗?虎口脱险的“一枝花”会不会像别的天方小城里那些拈花惹草的风流人物,不以之为耻,反以之为荣呢?这样的人,在天方小城大有人在。阿维一直觉得,天方小城的风气,是倾斜而异样的,是低到尘埃里的,是失了底线与准则的,也是以丑为美的。阿维困惑的是,这种倾斜与异样究竟始于何时。很多人跟阿维一样,对此已经没有了记忆。
在青山市,由内而外,阿维渐渐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新的生活中,不包含男人这个字眼,也不包括爱情这个字眼。阿维想试一试,没有男人与爱情,她还能不能诗意地生活。或者,陷入了唯美与完美主义的阿维,更愿意虚构一个王者,来供自己倾慕与膜拜。老汤嗤笑阿维的衰老与残缺,阿维也并不在意。经过一劫,阿维超脱了许多,站在了高处,眼光自然就远了。也就是说,阿维更喜欢从背后,而不是前面来看一个男人。她喜欢背影的神秘感与距离感,也需要这种梦幻式的精神浸润与滋养。
此刻,在初秋的黄昏雨中,阿维前面就有这样一张似曾相识的背影,不甚高大,但修直挺拔,一步一个脚印,踏实稳健,有着军人的硬朗气质与风格,像“一枝花”一样,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这就是曾经的“一枝花”的背影,阿维曾经在这张脊背上幸福地靠着,躺着,用她细腻敏感的肌肤,一寸一寸, 一点一滴地感受着雄性的力量与美,啊,那是多么短暂的力与美!虽然与这张背影已经时隔多年,但,在这个薄雨的秋日的黄昏,只是在一瞬间,阿维就失掉了自己。昔日重来,她有十多年前那种被流弹击中的感觉,眩晕而疼痛,疼痛而眩晕。
一时间,阿维一反常态,眼眸一片蒙胧,一点不像阿维一贯的做派。阿维一贯的做派是什么?麻木、冷漠、倨傲,是钢丝绳拧成的几何图案,透着不可调和的僵直。但这时,只有阿维自己明白,她内心中所有的图案,其实都是由棉花拼成的,轻轻吹一口气,便漫涣开来,改变了原来的形状,或者,已经变得没有了形状。
因为她并没有,也并不能彻底忘记过去,除非她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白痴。也只有阿维自己,能明白自己究竟有多么分裂,不是简简单单地一分为二,而是无极限地分裂开来,那一地的破碎,难以计数,也难以捡拾,在这个黄昏闪着岁月的银光。跟在这偶然而神秘的背影之后,阿维竭尽全力控制着自己。雨是停了,她的眼泪却无声地狂流起来,她极想放声大哭,像荒原上一只失去了伴侣很久很久的母狼。她一直心存幻想,假如“一枝花”当年没有死在石榴的床上,侥幸活了下来,他对阿维说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而阿维又要不要听呢?……死亡真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开始与结束!
一声尖利的急刹车,惊醒了阿维的迷梦。在大庙巷的尾巴那里,在一个略显狭窄的路口,一辆红色现代差点就撞进路边的一间小店面——那正是让阿维耿耿于怀,心有不爽的开锁店。不知司机开了小差,看了短信,还是喝了小酒。事不关己,阿维很快就从红色现代收回了目光,带着敌意瞥了开锁店一眼。再看前面时,被跟踪者、“一枝花”、棒球帽等等已经不见了。暮色已然浓了许多,阿维看不清别人,别人也看不清阿维,特别是她脸上的泪水。阿维清楚的是,那个影子像灰色的幽灵一样,在红色的急刹车声里消失不见了。
眼前是一个陌生而陈旧的小区,有一种没落的贵族气息。楼上已经有几束灯光亮起来,刻画出窗的轮廓。那是按时回家,没有加班,也没有应酬的人。更多的楼窗是黑的,看来是不按时回家,经常加班,和有应酬的人多一些。这剪影般的画面,让阿维再度有了蒲苇似的飘摇之感。 她坚信,刚才走在她前面的那个“一枝花”式的背影,笃定是进了这个小区,她有一点点恨意涌了上来,莫名其妙的一点点恨意。
她执拗而急切地想要见到他,想要把这埋藏起来的恨发泄出来。此时此刻,阿维早已经忘了张校长和那个遭了惊吓的病秧子。她只想迅速地打开自己,给自己找一条笔直的通道,只因为她已经将自己禁闭得太久太久,已经成了一头困兽。
困兽犹斗。
楼梯里是旧旧的那种灰,影影绰绰。黄金搭档和特仑苏奶已经被阿维彻底忽略了,她两手空空。她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个台阶,靠着灵感和神的旨意,在一扇酱紫色的防盗门前停了下来。她以前的家就有这样一扇酱色色的防盗门,居中的门板上,也贴着一张吉祥如意的大红剪纸,显得温馨、和谐而喜庆。阿维伸出手,一把就撕掉了那张圆形的红色剪纸,因为撕得不甚彻底,就显得很难看了。一时间,阿维觉得自己也变得像那团废纸,很是难看了,这是她一直不肯承认的现实。一时间,阿维觉得一枝花、石榴、老汤、老汤的老公、牛万里甚至还有那个素昧平生的精神文明标兵……纷纷将自己包围起来,且做出瞄准射击的样子来。
阿维莫名地咕哝着叫了一声。她抖抖索索地掏出包里的钥匙,抖抖索索地将钥匙插进防盗门的钥匙孔里,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大脑以及肢体。
防盗门打开了,当然不是阿维打开的,而是这屋子的主人从里面打开的。阿维可没她的两个房客那么幸运,这屋子的主人拨迅速打了110,她径直被派出所的人带走了——这幢居民楼最近连连失窃,人们恨死了那胆大妄为的蟊贼。不过,谁也没想到,原来这蟊贼居然是个举止优雅、风度翩翩的女人。想不到啊!阿维被穿着警服的公安干警带走的时候,那些像暮色一样深深的陌生的眼神中,就隐藏着这样的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