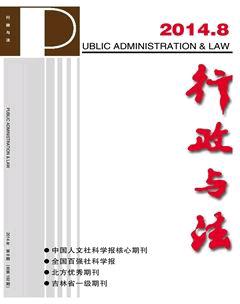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摘 要:本文从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国家”面向,追问了企业在进入某国市场时该国法律对企业国际化选择可能具有的作用;从合约的角度分析了如何运用交易成本及准备成本对企业国际化的约束、上头成本对企业国际化的保护及其限度问题。
关 键 词:企业国际化;准备成本;上头成本;合约
中图分类号:D9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4)08-0126-04
收稿日期:2014-05-09
作者简介:齐伟 (1983—),男,辽宁海城人,沈阳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民商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沈阳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软科学研究专项)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F13-315-5-41。
“企业国际化”是企业成长和规模扩大的一种表现,也是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经营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我们首先需要注意区分界定这种现象的两个角度。从企业的角度,企业国际化可以看作是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由国内市场延伸到国际市场,由国内企业发展为国际化企业的过程;[1]从国家的角度,企业的国际化包括两个方面,即本国企业越出本国市场以及外国企业走进本国市场,也就是企业的“引进来”与“走出去”。[2]本文从企业国际化的“国家”角度和面向,追问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该国法律对企业国际化选择的作用。
一、企业的合约理论
交易成本的思想虽然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但学者一般都认为,交易成本到了科斯(1937年“企业的性质”以及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手中,才首次得到开拓性的分析。[3]对于“企业”的定义,科斯在文章的开始强调要遵循罗宾逊夫人的告诫,即不仅要易于处理(用马歇尔发展起来的两种经济分析工具——边际和替代),同时也必须是现实的,要与现实中的“企业”相同。在传统企业理论中,企业仅仅是作为一种生产函数,而不是一种组织,即是从技术角度,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企业在技术、市场和经济条件约束下做出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计划,同时工人的工资按照边际生产力决定。但是这种理论只有在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清晰、竞争完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才能够达到。现实情况是企业作为一种资源的配置方式和协调生产的方法,“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化指导着生产,通过在市场上的一系列互换交易来协调。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取代交易的复杂市场结构的是企业家的协调,企业家指导着生产。很显然,存在着许多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然而,考虑到这种事实,即如果生产可以通过价格变化来控制,生产就可以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得以开展,我们要问:为什么会有组织?”[4]科斯认为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建立企业是有益的,最主要的原因似乎是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使用价格机制来‘组织生产最显明的成本是发现有关的价格是什么。”[5]
制度运行成本的差异导致了企业代替市场,而市场交易涉及产品,企业内的交易涉及生产要素。假定私人拥有生产性投入,那么,每一生产性投入所有者都有三种选择:⑴自己生产和销售产品;⑵把投入全部卖掉,⑶把投入的使用权委托给代理人,获取一定的收入。[6]当作出第三种选择时,就出现了企业。在私有产权的条件下,当生产性投入所有者签订上述的合约加入企业时,他预期相对于其他的选择而言收入会增加。
以合约安排看企业,企业不是代替了市场,而是一种合约代替了另一种合约,重要的是要分析合约不同选择的交易成本影响。科斯并非没有从合约的角度看企业,只不过科斯的合约是另一种含义上的合约:“企业的存在并不会使合约被取消,但大大减少了。某生产要素(或它的所有者)不必与在企业内同他合作生产的其他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的合约。当然,如果这种合作是价格机制起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那么这些合约就是必要的。在这个阶段,重要的要注意合约的特性,也就是说企业中被雇用的生产要素是怎样进入的。生产要素凭借合约,为了获得某特定的酬金(无论是固定的还是浮动的),同意在特定的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示。合约的本质是它规定了企业家权力的限度。在这些限度内,他才能够指挥其它的生产要素。”[7]科斯眼中的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力,这些合约关系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但这并非企业合约关系的全部,企业还与非劳动力生产要素、供应商、股东、债权人以及其他企业签订合约。与本文相关的是,以狭义界定的合约分析企业的规模以及企业边界是否合适?更进而能否分析和解释“企业国际化”?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界定“合约”本身的含义。
二、理论架构的提出
从合约的角度界定企业,是现代企业理论对传统企业理论的重要批评和发展,但对于合约本身,并没有得到学者应有的理论反思。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词的问题,如果说是交易成本打开了企业的“暗箱”,那么,对“合约”的追问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看清“暗箱”的组成和结构。
科斯指出企业本身是一种合约,只不过科斯笔下的合约是以雇主和雇员关系为原型,也部分因为这种局限性,张五常向科斯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一个苹果园主和一个养蜂人签订为果树授粉的合约,那么会产生一个企业还是二个企业?”[8]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因为订立的合约可能是一份工资合约(此时为一个企业),也可以是租赁蜂箱的合约(此时为两个),也可以是这些合约和其他一些安排的选择,合约关系具有复杂和多样性。因此,张五常认为企业的规模具有模糊性,确定企业的边界毫无益处。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合约本身进行重构,即合约是一个界定关系的范畴,这种关系大至可达整个社会,小至只是两个人之间,合约的这种性质我们叫做合约的差序性。科斯认为:“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取代交易的复杂市场结构的是企业家的协调,企业家指导着生产。”[9]企业家在企业中运用手中的权力来调配生产要素,而为了做到这一点,生产要素就得置于等级分明、规章制度健全的管理机构之内。企业的边界就由这种管理机构来识别,企业家和企业内部人员的合约关系也在这一点上区别于企业家在企业之外与其他合约人的关系。后来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指出:“企业经理的自主权和自由决定权以及低层次管理人员相对较小的自主权已是企业的主要特征。”[10]同时,科斯的“企业家”也是决定企业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解释了企业规模扩大或者缩小的限度。在企业对外经营方面,“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本身。所谓的经营就是利用价格机制,在市场上签订新的合约,由于企业本身运行也是有成本的,那么当一种成本的节约与另一种成本的上升在边际上相等时,合约的替代就会停止,企业的规模也就得以确定,即“企业倾向于扩张到在企业内组织一项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同样一项交易通过公开市场交易的成本或者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的成本。”[11]endprint
企业的本质是一种合约,这里的合约是广义且具有差序性的合约。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空间扩大、交易本身的差异性以及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组织成本和经营的亏损也会增加,这些都影响了合约替代的程度,即合约向外发展的限度。也就是说,决定合约关系(替代)距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不仅决定了合约关系的选择和类型,而一个更为重要的层面是交易成本对合约关系本身的达成以及拓展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合约的这种替代和延伸在某交易成本下一旦完成,合约的边际即从经济的角度界定了企业的范围,而在合约的边际之内,分析合约的种类和性质就是简单的工作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有了一个分析企业国际化与法律关系的理论框架,即交易成本约束下的合约替代理论。企业的国际化从合约的角度看是合约的替代和延伸,但法律却把它看作是一种交易成本。故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法律约束着企业国际化的程度。[12]
三、理论架构的具体应用
(一)准备成本约束着企业国际化
企业国际化并不仅仅是企业规模在地理空间上的延伸,“国际”尤其提醒我们注意到不同于其他企业规模扩大的层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家无论是对本国企业的“走出去”还是外国企业的“引进来”绝对不能听之任之,特别是对于后者,为了国家安全、保护国内企业、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又或者任何其他的考虑(即便有些目的是不“合理”,甚至仅仅表达该国的文化、传统甚至偏见),或鼓励,或设置障碍,这种态度可以体现在该国的法律文件中,也可以表现为政策或者一些默认的惯例中。在这里,我们把企业在市场范围的地理性演进方面由于越过国界所额外支付的成本以及面对来自国家层面的阻力和障碍都称之为准备成本。顾名思义,准备成本是企业为进入某国市场做出的准备性工作所不得不支付的成本,它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规定的成本。法律成本是某国法律对外国企业进入本国所明文规定的一些实质性条件和要求,例如资金比例、市场范围、进入区域、经营年限等,这是因为国家的社会性质、发展水平以及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外国企业在本国产业和行业的进入以及进入程度。由于这些成本在某国的法律中已明文规定,所以此类成本的识别比较容易。
由于国家层面介入,还有一类准备成本是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所不得不支付的,即风险成本。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的经营,影响着企业国际化的选择与程度。各种(政治)风险要成为准备成本,必须是可以预测且可以采取应对措施(例如风险评估、通过各种承保机构签订保险合约以及进行风险管理等);如果不能预测,又或者可以预测但不能采取相关应对措施(例如某些不在保险机构承保范围内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国际化经营过程中本身所固有的商业风险以及新出现的风险,[13]应该以信息成本处理,不会影响合约的替代和延伸,即企业国际化本身。这一点不能混淆,因为以不同的成本处理,法律对企业国际化作用是不同的。
对准备成本的存在,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无论是从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的角度,还是从权利、合约自由出发,都认为这些成本都应该越小越好乃至最好完全不存在。这些观点虽不无可取之处,但笔者关心是在一个更宽广的视域下,不同准备成本的含义是什么。上文分析的一个隐含的视角是局限在某特定国家,但从多国视角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企业的国际化是有不同国家选择的。原则上,市场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取舍的均衡点,扣除企业的不同偏好、管理上不同的制度以及各类成本,其预期的回报率应该一样。
准备成本的存在,是国家选择的结果。然而,国家一旦做出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被选择了,被企业选择,更被国际市场选择,而且这些准备成本并不是像国家所想象的那样有效,也并不是刚性存在的。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准备成本的不同,必定影响着企业家的选择,企业国际化的选择必定是准备成本低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预期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继续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回过头重新审视各种固化的准备成本。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缩小,这种准备成本也趋于减少或者趋于相同。相同与不存在,从经济角度看是一样的,指的是企业国际化的选择没有准备成本上的考虑。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全球化不仅作为背景,而且也是正在进行的过程,是企业国际化的结果。
(二)上头成本保护着企业国际化
准备成本支付与否,对企业国际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区分。实际上,准备成本不仅约束着企业国际化,更在一度程度上保护着企业的国际化,只不过这种保护是另一种成本形态的保护,而且重要的是要区分准备成本的支付与否。概括而言,已经支付了的准备成本对企业国际化的保护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比较容易理解,另一个由于涉及到另一种成本形态则显得比较晦涩和隐蔽。首先,一个意图参与竞争、进入该国市场的企业,要想入局的话,也必须做出相同或类似的准备成本投资,不能支付的话当然就不能进入该国市场,所以国家在这方面是维护着已经入局的企业利益。其次,已经入局的企业,这种准备成本的支付就转变为另一种成本形态,即作为租值存在的上头成本,这种成本由市场界定,由市场摊分,由市场维护,当然一定程度上也由企业自己维护。
上头成本,就是指只要企业继续经营,不生产也要支付的费用。例如签了土地使用权合约(使用金要付),买了厂房、购置了工具(利息要算),签了保险合约(保险金要支付)。与上头成本相对的概念是直接成本,它是指那些不生产就不需要支付的费用,例如餐馆营业时的食品原材料费用就是直接成本。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直接成本是成本,但上头成本不一定是成本。什么是成本,“成本是无可避免的最高代价。”[14]成本起于有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成本。企业进入某国市场之前,为进行诸多准备性活动,例如获取资格审批文件、土地使用权证书、特许经营权以及签订的各种保险合约所支付的费用,一旦支付,就成为历史,不再是成本。这或许是因为上述大多数准备活动所取得的各类资格、证书、合约等大多为不可转让的,没有选择;又或者即便是可以转让的,这转让之价可高可低,若价格的变化并不影响企业的决策和继续经营,这类成本也不是成本。endprint
从没有选择而不变的角度,上头成本不是成本;从有选择而可变的角度,放弃了的收入是上头成本的成本;而从有选择而不变的角度看,上头成本也不是成本。变与不变,这里指的是企业继续经营与否,而上头成本不是成本,要以租值的角度判断。“上头成本是租值。不是先有上头成本而后摊分,而是倒转过来,从每种产品可以赚到的直接成本以上的盈余加起来而求得的。作了投资,开了档,每种产品之价是指定了产量后,经营者可收尽收,但要受到市场竞争的局限约束,而这约束决定直接成本以上的盈余。”[15]作为租值存在的上头成本,由市场界定,由市场摊分,也由市场维护。
企业国际化可不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它们要的是在国际化了之后,能够在东道国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和争取更多的企业利润。实施国际化的企业以及国家的选择之间的某种耦合关系不是偶然的,这不仅是因为只有那些财力雄厚,或规模巨大或组织合理,或管理科学,或技术先进,或其他显著优势的企业愿意且能够支付大量的准备成本,更重要的是因为也只有这些性质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和获得营业利润。决定企业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生产成本的大小,相比较而言,能够国际化的企业的生产的直接成本偏低应该是没有多大的争议的,同时作为租值存在的上头成本,由市场界定、摊分和维护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由自己保护着。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上头成本保护企业国际化的程度问题。既然上头成本是准备成本是另一种形态,所以上面关于准备成本限度的分析也当然适用于这里,不过还需要添加的是市场竞争的程度以及企业自身竞争力的大小也决定了上头成本保护的限度。
【参考文献】
[1]刘松柏.论企业国际化和国际化企业[J].理论学刊,2003,(03):61-64.
[2]张五常.论新制度经济学[A].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C].易宪容,张卫东译.商务印书馆,2000.438-441.
[3]Yoram Barzel and Levis A.Kochin.Ronald Coase on the Nature of Social Cost as a Key to the Problem of the Firm[J].Scand.J.of Economics,1992,(94):19-31.
[4][5][7][9][11]Ronald H.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1937,(04):388-395.
[6][8]Steven N.S.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26).
[10]保罗·米尔格罗姆,约翰·罗伯茨.谈判成本、影响成本和经济活动的组织[A].(美)詹姆斯·E.阿尔特,肯尼思·A.谢泼斯.实证政治经济学[C].王永钦,薛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86.
[12]杨忠,张骁.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09,(02):32-42.
[13]杨震宁,刘雯雯,王以华.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边缘化风险与规避[J].中国软科学,2008,(10):86-97.
[14][15]张五常.收入与成本[M].中信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徐 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