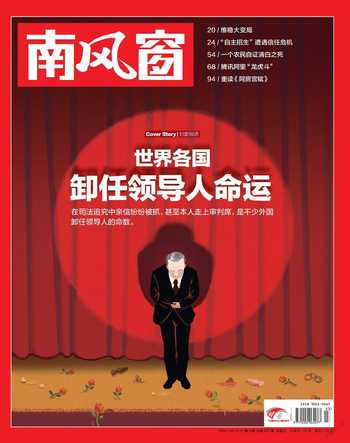我们为什么需要“团体”?
甄静慧
21世纪的都市人群像是一只只背着厚厚外壳的蜗牛踟蹰前行—这里指的不是“房贷”、“名利”之类老生常谈的压力和欲望,而是那厚厚的社会面具,有时它已经厚到变成一个“壳”,甚至是维京诺曼式的盔甲。
记者曾采访一位女企业家,她的事业、婚姻在社会意义上都很成功,她自己也为此而自豪。没想到采访后她突然问我,“能找个时间出来喝喝茶吗?聊点女人的话题。”那刻她的眼神无比落寞。原来在她内心深处,最引以为荣的成功同时也是个沉重的包袱:公司里,她需要在下属面前保持威仪;与同行及客户一起,充满各种利益算计;最无奈的是,即使面对关系最亲密的丈夫依然无法完全敞开心扉,需要太多技巧和智谋来避免女强人式的婚姻失败。
当一个人保持着优雅的姿态在现代社会孤军奋战,每日觥筹交错,心灵却越来越孤寂,到最后竟要找个准陌生人才能吐露内心苦闷—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在人群中发生,然而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存在主义心理大师欧文·亚隆认为,我们生而为人必须面对四大终极困境:死亡、自由、孤独和无意义—人们被孤单地抛进存在,没有一个注定的生命结构和命运,且终将独自面对死亡。
埃里希·弗洛姆则说,孤立是焦虑的第一来源。
由此,每个人都需要与他人建立连接、实现自我价值以及寻找归属感。它虽然不能彻底解决存在孤独,至少可以提供慰藉,大大缓解这种令人绝望的焦虑。
然而在现今社会,人们甚至很难做到与他人建立真诚的关系。
这句话似乎有点怪异。毕竟,人是社会性动物,只要生活在社会中,就会与他人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可是,只有那些具备真诚、理解、无条件(至少是低功利性)关注和支持等要素的关系,才能使人从中得到滋养和成长。这无关阶层,也无法用金钱赎买。富豪、政客、平头百姓莫不如是。
而当我们抛开存在性的哲学问题,只看普遍的人际孤独,就不难理解它其实是由致使亲密性崩解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所致。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末下午,简单而整洁的环境,十多个来自社会不同领域、本来是陌生人的成年男女围坐一起度过3小时。对苏丹来说,这是一次非凡的体验。过往近30年的人生,包括此前好几次这样的聚会中,她都表现得像个爱照顾人、没有脾气的傻大姐。然而这次,当大家又像以往那样理所当然地拜托她到隔壁去拿些靠垫进来时,她感到突如其来的愤怒。
“我抱着一大堆垫子,路都快看不到了,耳朵里听见他们在说笑、闲谈、吃水果,一股火蹿上脑门,仿佛有个声音在叫,‘为什么又是我!’”紧接着,她做出了从未有过的失礼行为—把垫子往地上乱扔,冲着所有人大喊大叫。眼泪流出来那一刻她才知道,这些年自己一直在职场和亲密关系中委曲求全,多么委屈。
苏丹是一家大型外企的白领,半年前她参加了一个心理成长小组,这是其中一次小组活动的场景。正是从这次起,她开始接触到更为真实的自我,并学会在人际互动中体察自己真实的情绪与需求。而与此同时,她亦开始审视自己在过往人际关系中的功利和麻木,“为何我总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满足社会和他人欲求的工具?”
事实上,几乎所有小组成员都有类似的感受:我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普遍不重视人的存在价值—只根据社会地位、利用价值等功利的属性来对人进行评价,人和人之间缺乏纯粹和真诚的关系。
这样的人际互动非但不能给人滋养,反而让人想要努力逃离。越来越多人爱上泡吧和独自旅行,并由此衍生出一个流行的都市游戏:“只爱陌生人”。
著名心理学家朱建军认为,当今中国社会这种普遍性人际孤独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近数十年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剧烈转变。
对于传统社会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宗族关系是人生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的父系氏族时期,是以某一男性为中心、由其直系男性后裔及其家庭依照一定伦理规则而组成的血缘群体。
“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因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凑玄孙,一家有吉。自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合聚之道,故谓之族。”(《白虎通》)
可见,传统宗族天然具有聚合共同体以及互相亲爱的要素,其与儒家思想结合,形成了维系社会结构的纽带。
而除了与族群的天然联结之外,诸如传统灯会与寺庙活动这样的民俗活动也拓展了人们社交和精神活动的范围。
族群联结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权力对农村地区的渗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先是集体主义下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以及人民公社制度渐渐取代了宗族维系的功能;其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城镇化的加快,人民公社制度伴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又迅速解体。曾经某种程度上承担族群联结意义的城市大国企的衰落,也将更多城市人群抛入更原子化的存在状态。
与此同时,西方价值观和后现代思潮猛烈冲击着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在社会文化上,体现为物质至上主义,个人价值与财富及社会地位前所未有地紧密捆绑在一起;生活方式上,则从族群聚居向散居演变—代际分隔的城市家庭被一个个互不往来的楼房单元彻底分隔。
吊诡的是,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并不是变得更少,而是随着社会功能的分化、信息技术的发达而变得越来越多,甚至错综复杂。只是,当人心变得疏离、精神让位于物质,日益复杂的功利性社会关系不但无法使人们之间的联结加深,反而让其社会面具变得越来越厚,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2013年9月6日,资深心理学工作者韦志中从广州飞往秦皇岛,对从全国各地聚集于此的心丝带“心灵驿站”志愿者进行为期7天的体验式团体培训。2008年,他撰写出版《本会团体心理咨询实践》一书,提出在中国大陆围绕本土文化的心理团体概念,其后成立心丝带志愿者协会,目的是在社区和普罗大众之中推广一种支持性团体文化。

心理团体并不是什么新鲜概念,这种形式最早出现于1900年的美国,其时受工业革命影响,大量移民涌入底特律、波士顿等大城市,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心理学家帕森斯首创团体心理辅导形式,帮助人们认识自我、适应社会,广受社会欢迎。此后,美国团体心理的发展分别在二战期间,以及社会问题纷繁复杂的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两次重要高潮。
而在中国,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心理学家就开始在高校开展心理成长小组,经过20多年的发展,各种形式的心理团体技术已日趋成熟。然而,直至近几年,非治疗性的心理团体参与者都是以心理学爱好者为主,相对小众。
不过,韦志中认为,这一现状将会在近几年实现重大突破,这也是他成立和推动心丝带的原因。
理由很简单。如果我们需要用所有精力来关注下个月的饭钱,就不会注意自己的寂寞。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如今越来越多人已经从对物质的全然关注中渐渐抽离出来,这时他们开始关照内心,往往会大吃一惊。
就像记者在采访中遇到的女孩雪莹,眼下她在人际交往中需要学习的课题是表达情绪,包括学会哭泣。因为从小父母教育她在外人面前要“喜怒不形于色”,所以长久以来,她对着每个人礼貌地微笑,心里却筑起防范的篱笆。直到有天发现所有人都成为了“外人”,自己则欲哭无泪,她才知道她“病”了。
但是,不可逆的城镇化和社会价值演化,导致中国社会不可能回到以往的宗族生活方式,需要一些新的形式去满足人们对关系的需求。
这时,“寻找真诚关系”的游戏开始暗流汹涌。
记者有一个好朋友,在她读初中的时候,父母就因为感情失和而分开,她的整个童年都是在复杂的家庭纷争中度过。中学阶段她一度非常痛苦,精神几近崩溃,家族、学校和社区都无法给她足够支持。于是她参加了一个团体,每周一次的小组活动给了她极大的心理支持。“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敞开心扉,只要你愿意说,大家就会耐心听,并且持续关注。”她坚信是这些温暖的力量陪伴她度过了最艰难的心理成长期。
这种叙述方式或许会让人产生错觉,似乎真诚的人际支持关系只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事实却恰恰相反。
前年记者曾好奇地问了十几位华南企业家:为什么参加狮子会?
那是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国际慈善组织,由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会员组成:企业家,CEO,专业人士之类(否则你可能交不起会费,或者因为赧于出席隔三岔五举办的慈善筹款晚宴而被边缘化)。
然而以上并不是狮子会最大的特色—“参与式慈善”才是。中产们在这里不能只付出金钱,还得经常以普通志愿者身份参与所资助的公益活动。由于会员身份地位相当,又没有生意往来,组织内往往能体现出一种难得的平等性。记者常常在他们的活动场所见到平日在公司颐指气使的老板们穿着标准的黄色T恤努力搬抬桌椅布置会场。
“我第一次当志愿者时,他们让我给山区老年白内障患者滴眼药水,连续滴了10个小时,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眼睛。”一位企业家说。在那里没有什么“老板”,他们需要因此而面对比日常更多的人际冲突,经由物质和社会地位带来的关系优势荡然无存。听起来真是花钱买难受,但所有记者采访过的会员,百分百的都表示这正是狮子会最大的魅力所在—一开始可能很难受,但接下来,他们了解到他人眼里更真实的自己,并开始碰触内在的自我。由此他们不再那么孤独。
正是这样,人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基于宗教、兴趣、相似的角色等共同点,寻找日常社交以外真诚关系的可能性。这使得读书会、公益行动小组、单身女性俱乐部等等五花八门的小团体都进入了兴盛时期。
而面对这样普遍性的社会需求,心理学工作者们认为自己能够做得更多。
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罗杰斯就从专业的角度总结了团体运动兴起背后人们的本质需求。
“这是一种对真实而亲近关系的渴望。在这种关系中,任何感受与情绪都可以自由地表达出来,而不用担心与压抑;人们深层的经验—失望或决裂—可以分享出来而无需恐惧。也就是说,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可以冒险,可以不断地尝试,从而能被接受,如此一来,未来的成长才有可能。”由此,他带领美国社会掀起了一场旋风式的团体运动,并以实践证明带来了极为正面的社会效应。
而欧文·亚隆则更精准地概括了存在主义心理团体能给参与者带来的11个疗效因子,包括利他、团体凝聚力、提高社交技巧、宣泄、原生家庭的矫正性重视、重塑希望等。
“当然,中国的心理学团体与西方的人本主义团体有所不同,后者带有基督教新教色彩,而我们则更多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朱建军说。
不同取向的团体如治疗性小组、成长性小组等,其侧重点当然也会有所不同。对心丝带的“心灵驿站”,韦志中的定位是:由专业心理学工作者在社区组织的公益支持性团体,不带有治疗及深度成长目标,而提供最普适的自我探索及社会支持功能。
他希望这样可以覆盖更多更广泛的社会人群。“最好是能像罗杰斯的会心团体一样,形成一股风潮。”
(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