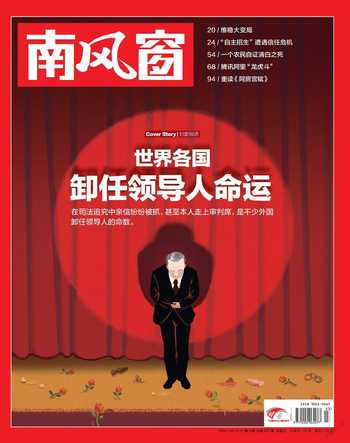要共识,不要合流
李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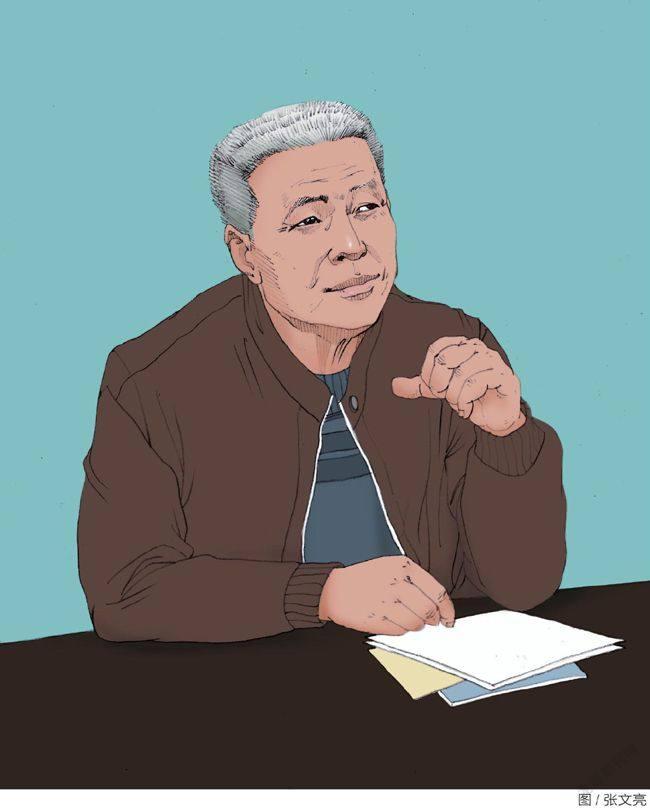
作家曹征路的作品勇于反映严肃的社会现实问题,被认为是文学界“底层叙事”的一位代表人物。近日,本刊记者就当代社会的一些思想热点问题,与其进行了深入交流。
《南风窗》:你曾说过,写作是为了表达对时代的困惑,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好。推而广之的话,也可以说在公共空间里发生的讨论是知识分子群体对时代困惑的表达。我有一个直观的感觉,观察最近几年知识分子讨论的议题,仿佛大家的困惑变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GDP总量成为世界老二之后乐观情绪的上升。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同感。
曹征路:老的话题在淡化,新的话题也在不断涌现。国家在经济层面是比过去强了,但在社会层面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知识分子群体的分裂也会越来越鲜明。
改革的推动力并不是GDP的增长,而是财政的增长。我在基层党政机关工作过,我知道在当初改革之所以有吸引力,一个很大的动因就是财政困难,各级政府都面临没钱花的状态。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腐败,干部还都想做事,但就是没钱,所以才愿意先搞好经济,其他问题等把钱挣了把亏空补上再说。把生活搞好其他问题都好解决,是那个时代各级干部的共识。
经过了政治风波,经济发展似乎就承担了提供政权合法性的作用,但发展方式上过多地选择了向国际资本倾斜让步。结果下层老百姓还是没有钱,为什么经济转型这么困难,为什么内需拉动不起来?就是因为老百姓没钱。中国农村人口占了大多数,农民没有钱,盖多少高楼都没用。政府财政虽然是增长了,可是压力还是很大。为什么要紧盯着GDP的增速呢?表面的理由是保就业,可是真实就业率从来就没有公布过,说明政府主要目标还是保财政增长,只有财政稳了,才能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不出问题。
至于拿GDP来衡量中国是不是世界老二,这个我不太同意,国家是否强大不是靠统计指标支撑的。GDP不过是一种统计方法,按这个方法计算,中国从明代到晚清一直是世界第一,甲午战争前GDP是日本的几倍,那时中国强大吗?
《南风窗》:前些年很热的议题比如“三农”问题、国企职工下岗问题、从更早的关于人文精神丧失演化来的社会道德滑坡问题等等,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淡化了。事实上,中国的问题并不少,老的没有完全解决,新的还在产生,问题的存在和问题意识的淡化形成了对比。
曹征路:问题没有解决,只是危机往后推迟了,过去的热点被新的热点取代了,话题也就跟着转移了。这主要是由于新闻媒体的引导。
比如中国周边形势的问题近年凸显出来了,这个问题在过去一度是不存在的,大家觉得我们就是要向西方学习,就是要走向海洋,就是要向美国靠拢。但这样的声音现在弱了,连有些右翼人士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对中国是不安好心的。但这又被另外一个幻象代替了,就是我们已经很厉害了,已经可以亮肌肉了。但这显然也有问题的,中国的军力与日本相比到底怎么样,是没有经过检验的。
《南风窗》:知识分子整体上危机意识越来越薄弱,在2005年前后还有过一次关于改革的讨论。现在呢,讨论雾霾之类的话题仿佛是在谈论一个幸福的烦恼,毕竟这是发展带来的后果嘛。
曹征路:没错。我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整体上还没有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范畴,基本上还是旧式文人,所谓旧式文人就是“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要把自己的那套东西卖给某个主子。我也讽刺过左右之争,在我看来争论的背后都是精英主义在起作用,都以为他的焦虑和建言会被采纳,但当家的人根本就没放在心上,争的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除了少数人还在打口水仗之外,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南风窗》:过去挑起争论的、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一般被归纳为左翼的,近年来倒是左翼比较积极地在归纳中国模式什么的,好像左翼比右翼还乐观。
曹征路:左翼的问题也正是刚刚说到的精英主义,或者说潜在的精英意识吧,一方面要为人民说话,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高于人民;一方面要批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右翼的攻击。由于这原因,左翼显出了很矛盾的状态,在争论的过程中也就慢慢地接受了主流的某些东西,比如你说的中国模式等等,我以为都是被设计出来的。
《南风窗》:这也契合了当下的一个时髦,寻求共识。
曹征路:社会需要共识,但共识需要建立在面对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的基础上,需要在承认矛盾解决矛盾的动态过程中去创造,这样的共识才有意义,否则就成了为找共识而找话题。
最近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香港的知识分子写的,把秦晖、郭于华、邓晓芒等人称为左翼,言外之意是把以往被定位为左翼的知识分子划定为“极左”,从主流话语里把他们剔除出去了。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策略,如同以往把思想论争称为“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一样,似乎左派是反对自由的。这样一来,共识就成了右翼和其外围之间的共识。
总之思想界面临着非常复杂的状态,一方面是多数人麻痹了,觉得没有意思,中国就这样了。另一方面呢,交锋的焦点在转移,不断有新的话题被制造出来,话题泡沫化了。
《南风窗》:中国很大,问题很多,人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问题总是有限的,如果知识分子不能通过严肃的讨论把所有值得严肃面对的问题反映在公共空间里,那么对大众来讲问题就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直面问题的所谓“合流”是很危险的。
曹征路:是的,其危险性在于用话语掩盖了中国的真实处境。另外我们还应当看到,老百姓的小市民意识空前高涨,消费主义盛行,这使我们越来越麻痹。这种现象很像南宋时期,无论读书人还是老百姓,都觉得小日子还可以,还过得去。有忧患意识的人被边缘化,现在居然有人还这样想问题?大家都觉得很可笑。
《南风窗》:小市民意识高涨是因为经济发展了,从这里倒可以引出另外一个视角。思想界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潮是很厉害的,很重要的一个根源就是改革开放后开眼一看,原来中国这么穷,于是在很多人的眼里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这么多年下来,无论付出的代价如何,中国毕竟有很多人生活富裕了,很多人出去旅游,年轻人出去留学,亲眼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感觉也就那么回事。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社会心态上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中国人看世界和看自己的感觉跟过去开始有不同了。这反过来也会作用于知识分子的心态,甚至国家的政策取向。你怎么看待这个趋势呢?
曹征路:30年不打仗,遍地都是黄金,这是老话了,口袋有点钱不奇怪。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从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热衷于置业,喜欢积累,这使得中国人比起其他民族来对物质生活更加向往。而且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嫌贫爱富的,说中国人不懂得消费,那是瞎胡扯。但是这样一种文化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当口袋里有了一点积累之后就会产生幻觉,我们还不错,不比别人差。中国人不同于日本民族,也不同于美国人,他们有危机意识,总有一群人不断在制造对立面,渲染外部威胁,由此在内部产生凝聚力。但小富即安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由巨大的分配不公带来的对秩序的质疑和更深层次的虚无主义。
《南风窗》:你的文学写作一向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把握的都是时代的主题。就个人层面来讲,你对时代的感受或者说困惑,近些年来有什么样的演变?
曹征路:我是越来越悲观的,感觉写小说很没有力量,所以才会跟一帮年轻人去拍纪录片。其实不光文学在边缘化,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也在边缘化。就拿我们学校的同事来说,前些年讨论起问题来也是剑拔弩张的,现在我退休了,当然争论的机会也少了,可是我们一起吃饭,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房子、车子、女人这些东西。
《南风窗》:这就涉及知识分子的责任了,知识分子应当把社会问题转换成公共议题来讨论,引起重视,进而解决。如果知识分子放弃了这个责任,就出现了打开电视天下太平一团和气,直到有一天麻烦到来。
曹征路:现在的情况就像是,一群喝醉酒的人还在接着喝,大家都说自己没醉。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其实是自觉的,拿大学老师来说,大家都不觉得自己是学校的主人,学校怎么样跟我没关系,我就是给校长打工的,至于学校怎么发展根本不关心。倒退到2000年以前还不是这样,那时大家都还是很有责任感的。
《南风窗》:这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状态差别非常的大了。
曹征路:精神格调要低得多了。
《南风窗》:那时候知识分子有那时候的问题,比如虚无主义倾向很严重,可是在虚无主义外面也包裹着一层理想的色彩。
曹征路:是的,尽管方向不一定对,但那种想要参与社会改造的精神是可贵的,有它积极的一面,但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了。会不会有转机?我自己的看法是,历史的钟摆没有摆到尽头,恐怕不经过一次大的冲击还清醒不过来。
《南风窗》:其实,当年驱动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造的动力很大一部分说到底也是来自私欲,整个80年代知识分子焦虑的是待遇低,“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随着这些年来与资本和权力的结合,知识分子的这部分要求可以说已经得到了满足。那么,知识分子责任感的驱动力是不是就没有了呢,还是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生发出更高层次的责任感?
曹征路:知识分子都觉得就自己应该比工农高一等,就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补偿,当他和工人农民一样的时候,他就觉得受了侮辱。这也是整个精英集团的问题。毛泽东晚年读《枯树赋》读得泪流满面,他担心的问题的确是有道理的。我在深圳接待过一个工人出身的干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单位工作,后来他提拔起来了,最高做到了省级干部。他说,你们知识分子要求的东西不都得到满足了吗,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我说知识分子要的不是这些,是民主、是平等,他就觉得很可笑,觉得我虚伪。他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采矿工出身,他也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