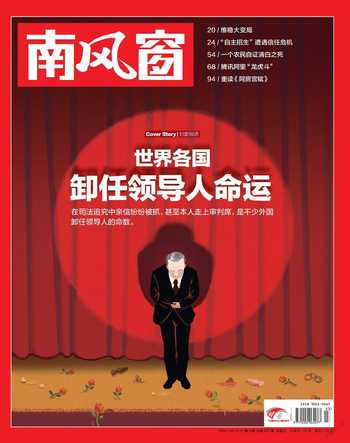应该相信世界正在变好
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
看看报纸或者看看新闻,你会觉得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坏。镜头里,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死亡、毁坏、绝望,越多这样的消息,媒体就越兴奋。一本丹麦新闻学教科书说:“好故事通常都是坏消息。”
偶尔(只是偶尔)我们也可以从新闻中看到一些正能量的关于“越变越好”的故事。这时媒体就会收获一种带着内疚的快慰。因此,我们通常会觉得世界比实际上更糟—尽管我们感觉自己的生活正在改善。
举个例子。1978年以来,美国消费者每年都会填写一份问卷调查,看看他们当前的财务状况比一年前更糟还是更好。在过去25年中,平均有38%的人说情况更好了,有32%的人说情况更糟了。但是,在被问及美国经济总体状况时,平均有47%的人说情况更糟了,只有38%的人说情况更好了。更多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在改善,而别人的生活在恶化,也许这就是新闻记者长久以来偏好坏消息的结果。
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美国。自1977年以来,盖洛普公司每年都会向世界各地的人发出问卷,看看人们是否认为明年会比过去的一年生活得更好。对于2014年,近50%的受访者说生活会变得更好,只有20%的人认为会变坏。但是,再被问及世界经济,观点几乎是五五开,32%的人认为会变好,30%的人认为会变坏。
因此,有必要回过头查看并确认许多指标,不少指标都表明:全球状况正在改善。世界银行的新数据表明,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在过去30年中下降了一大半,从1981年占总人口的42%下降到2010年的17%。尽管12亿发展中世界的人们每天的生活费仍不到1.25美元—这毫无疑问是必须得到解决的问题—但极端贫困率从未如此之低。经济学家估算,在接近200年前的1820年,超过80%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类似地,想想教育方面令人欣喜的改善吧。如今,20%的世界人口仍是文盲,但比起1900年的70%(估计水平)已是天壤之别。在繁荣的西方,20世纪初就实现了识字率的快速上升。在发展中国家,类似的大规模改善出现在1970~2000年(且仍在继续),其中中国的成就最为显著。
穷人接受教育的成本是巨大的。比如,1950年,巴基斯坦和韩国的教育和收入水平基本相当。如今,韩国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年,而巴基斯坦不到6年。在此期间,韩国人均收入提高了23倍,而巴基斯坦只提高了3倍。
经济学家在与哥本哈根共识(Copenhagen Consensus)的合作下试图评估因文盲人口带来的成本。据我们测算,如果1900年便已消灭了文盲,世界应该比实际情况多拥有2400亿美元(经通胀调整)的财富,相当于当时全球GDP的12%。因此,可以说1900年全球文盲问题让全世界付出了12%的GDP的代价。如今,全球文盲造成的成本下降到GDP的7%。到2050年,文盲率将下降到12%左右,其成本将减少到只有GDP的3.8%。
类似地,战争也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和人力成本。不过,尽管如今我们可以比以前更快、更生动地看到关于战争的画面,但我们仍然未能正确认识到冲突是何等无处不在。在20世纪,冲突夺走了1.4亿人的生命,其中两次世界大战就杀掉了7800万~9000万人。
有一个不太被公众了解的好消息(之所以不太被了解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们是好消息),那就是无论未来军事开支会提高、不变或降低,20世纪的高军事成本已经几乎成为了一种“永久的和平红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成本相当于全球GDP的20%,二战则还要高出一倍。
在考察冲突的成本时,哥本哈根共识经济学家估算的是全球军事开支的实际成本。如果我们还纳入战争中的生命损失,那么估计值还会提高50%左右。
根据这些估计数字,20世纪军事成本每年大约平均相当于GDP的5%。但是,自朝鲜战争的顶峰(7%)以来,全球军事成本一直在稳步下降,1980年大约为3.5%,现在为1.7%左右。即便是悲观的情形也表明,到2050年这一成本只会上升到1.8%;而在乐观情形中,军事成本将进一步下降到GDP的1.6%。
世界仍然充满各种问题,新闻媒体每天都在披露。我们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消除贫困、消灭文盲和推进和平上。但我们也需要记住,总体而言世界比我们认为的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