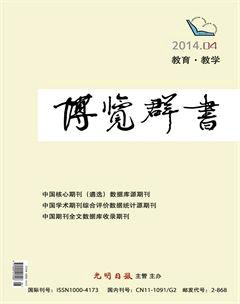金庸小说的佛学观
张晓娟
摘 要:《天龙八部》写作时借用佛典概念探讨生的哲学,抒发人生之感。读者难免误以为本书尽为佛家之言。但是这种解读似乎与金庸的用意相悖,毕竟结局只是众生归于平淡,并非“落了偏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对于金庸乃至读者而言,佛家之言赐人慧眼,却太过消极,人欲易于张扬,却是人性本然。故而找到佛性与人性的平衡点,不仅是生而为人的责任,也是获得生的大智慧的最终。
关键词:佛家;人性;空;存
佛家言世,万事空空,美女身藏脓血枯骨,功名利禄终归尘土,修佛求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故所谓抛下花花世界,求得一日发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成就彼岸金身如来,方是为人之本业。然则,喜怒哀乐出于胸次是人之本性,佛家形而上的追求与人形而下的审美习惯存在本质上的相悖,但是,偏又是人性的不可控使两者的得以互为衬托。呈现在《天龙八部》里,便是一个无所谓善恶,只是一时为贪嗔痴蒙蔽了心性的侠客世界,彼处人人皆苦,但是一旦得救赎,纵使丁春秋也可以在少林觅一修心养性之所。
虽《法华经·譬喻品》警世人,人有八苦,所谓“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胜阴”,沉沦其中仍不在少数。面对沉沦,苛责甚至绞杀根本不是解决之道,常怀悲悯情怀解众生大苦才是佛家之法。《天龙八部》书名取自佛经,金庸在《天龙八部·序》释名道,“天龙八部”均非人,是以天、龙为首的凶残神道怪物,如来讲经,他们便常常在旁听取。那么,书名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善恶并非绝对。但若如此便解释了金庸这部小说的全部内涵,那么这至多算是一部佛典演绎,不会给人长歌当哭的悲壮感。作者在佛家悲悯与人性本然之间找到的平衡点,无论善恶超度文中芸芸众生,是小说内涵得以扩大的所在。
一、王图霸业血海深仇尽归尘土
所谓“五胜阴苦”,又作“五阴胜苦”,色、受、想、行、识为五阴,亦是是人之常情,但过胜则为苦。《天龙八部》除却少林扫地僧,人人均受此苦,但又各有偏重。白世镜、段正淳以及他的情妇们主在色苦,沉溺于身体色相的淫惑之中,钟灵、玄苦、玄慈因心性敏感主受苦,丁春秋、游坦之、李秋水、天山童姥痴癫于目的而主想苦,萧远山、萧峰、慕容世家主在行苦。万事有缘均是把个别目标放得太大,失掉人生的平衡,承受不能承受之重,是为识苦。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少林扫地僧是一个对比的存在,若非慕容博、萧远山欲在藏经阁做生死决斗,他势必生不为人知,死不为人挂。这般默默无闻的人,却身怀超越萧峰的武艺、超越玄慈的佛法觉悟,本身便是对武林众生的一种讽刺。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人本能会争取各种社会符号,所谓“北乔峰、南慕容”,所谓“少林方丈”。符号会贴上去自会被剥落,当剥落了一切符号后还能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价值吗?乔峰的出场,英雄男儿,功名遍身。杏子林丐帮叛变首先剥去他帮主功名,由大宋英雄沦落为契丹北狄。而后遇见阿朱,却又因对仇恨耿耿于怀一掌丧了她的性命,儿女情长之乐剥离。与生父重逢,但在少林老僧的化解之下父离子去,天伦之乐难继。最后的雁门关外一场,与义兄耶律洪基生死相隔。至萧峰死时,除却段誉虚竹,能为他的存在带来意义的都已经离他而去。他追求的英雄大义是在民族冲突的立场上的,他追求的伸张正义是在善恶明辨的基础上的,他想要的儿女情长是在没有仇恨纠葛的立场上的,他所追求的敬师尊亲是文化赋予他的价值准则。但是一旦这些大背景大时代超越了他的意料,试问天下之大,他何以容身?
慕容一家面临的困境与萧峰的困境同出一辙,以伟大的社会符号求证自身存在的意义,谓之恢复家业。然而,历史的动作第一个人发出是为创举,第二个人再为是为闹剧,后代一种存在于前人的理想之中是无法做到超越的。且时空易转,再创当年辉煌自是痴人说梦。玄慈亦是,僧人四大皆空,再剥去他天下道德典范的社会符号之外,他的空虚感比之萧峰有过之而无不及。三个以天下为大背景的英雄沦落为天下的牺牲品,是社会的悲剧亦是人性的悲剧。意图在既空且大的符号后面找到个体存在的意义是为贪,因空大的功利对个人的意义太短暂,只有不断去寻求方能充实自己,但是这样一直着眼于更高更远的目的,却往往会忽视作为人生而来的七情六欲观念的认同。
二、输赢成败又争由侠算
闯荡江湖,是把社会符号层层贴在身上,修行佛法,则是把社会符号层层剥离,最终余下本真自我,本真自我的含义何在?佛家看世界总离不开“空”“苦”两个字。符号易易主,人也不过百年之期而已,如果一切真是空空如也,那么从生到死一气呵成便可,何苦用皮囊来徒增罪孽。如此简单悲观的否定所有存在,剥离一切给人造成巨大的空虚感。从这般意义层面上讲,佛家空言未免太过悲观。但是人若在追寻价值时,不知满足,甚至有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那也是磨灭了人的感性所在,沦为实现目的的工具,这便是过度张扬了人欲。佛家与人欲的过度张扬走的是人的两个极端,人性成长,终究是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找一条如何不偏废人性,同时又不至于落入人性过度张扬的窠臼的道路。
虚竹是萧峰意外得的义弟,却也不失为金庸为萧峰设计的另一种人生观的对照。自陈家洛到袁承志到郭靖的萧峰前半期的辉煌时光,一代大侠总是为国为民,但是百姓最渴求的是世道清和。大侠为人崇拜的救人水火的形象,乃是以牺牲千万百姓的理想为手段而实现的。进一步说,以英雄救世掩盖百姓取得幸福的更多可能性,那么,侠的存在本就是神话。大侠为国为民的同时,却也牺牲了最基本的人伦之乐,放弃了人的情感性本质。大侠追求一个空泛的社会化符号,百姓放弃自己作为个体的人存在于社会的价值,成为推崇侠的整体之一,个体与群体的差别太大预示的是社会结构的失衡。可是这种牺牲值得吗?自小拼搏赢得一身真功夫的萧峰死去,生不好武被强行灌输武艺的虚竹、段誉却在无意间以一身武艺叱咤武林。这算是继扫地僧之后对武林的第二个讽刺:边缘化的人,却成了武林的核心。
从萧峰到段誉虚竹,佛家的“剥离”思想是撕裂英雄温情脉脉面纱的关键。所谓大侠,是一堆社会符号的堆叠,剥去萧峰“丐帮帮主”“大宋英雄”“南院大王”种种称号之后,萧峰甚至找不到一个能为他为自己而为的存在。但是剥掉虚竹“逍遥派掌门”“灵鹫宫主人”的称号,剥掉段誉“大理世子”的称号之外,两个人还有私心杂念。这些为完美英雄所鄙弃的自私之处却恰巧证明了两个人人性的一面。所谓大侠,或许凡人都不如。endprint
三、向来痴 何必醒
《金刚经》言“须知美女,身藏脓血,百年之后,化为白骨”,所谓“狐媚偏能惑主”,所谓“红颜祸水”,在传统观念里,女人从来是亡国灭种之关键。如果承传统观念而来,那么王语嫣的设定本该如此,尽管无意,但大燕复兴,是必为慕容复皇后。然而因慕容家的理想成空而遭弃,因缘巧合,段誉的痴恋修得善果。另一方面,西夏公主德貌双馨,却不惜大成本寻找当日冰窖中之人。这些女性重情重义之处,与男子比肩也不减色。
虚竹段誉与萧峰性格的反差显而易见。萧峰是大豪杰,处理大事干净利索而又面面俱到。他的两个义弟与他相比则显得婆婆妈妈,段誉出口首先必是儒佛大德,能力不足却又喜欢事事往身上揽。虚竹面对大事时总是犹豫不决,存一好心做事却总使自己身陷两难之境。但是无论是手足情深还是儿女情长两人却都表现异常坚持。诚如传统的解读,段誉向来是堕入“痴苦”之内,在求而未得之前对王语嫣痴痴相向。然而同样是痴,鸠摩智与段誉业果却千差万别。鸠摩智痴武,为武学不择手段,不是自己该有的都据为己有。段誉痴人,但直至王语嫣答应之前对她不逾矩,却是用诚心尊重她,最终赢得美人归。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求之物必难得。为目的不择手段失去底线,那么触怒的又何止佛祖,鸠摩智堕入的又岂止痴苦,还有求不得诸般苦集于一身。其二,段誉求王语嫣,是渴望一种人性的关怀。但是鸠摩智求武,是寻一种虚无的满足感,所谓贪得无厌。看似无心为之,实则从心性开始,业果造就种下。
与段誉一般,虚竹可以挨饿不破荤戒,但是一旦美女入怀终究还是难以把持。而结局自是意料之内,段誉与王语嫣斜阳午后携手同归,西夏公主与梦中郎终得相见,两个痴人皆大欢喜。
求功名并不意味着抛弃人之常乐,人之常乐往往伴随的是感性情感的波动,这些情感是为人性本色。金庸在书中把功名、国民大业、嫉妒、贪恋等等化为云烟之后,武林重归平静,但是存余了可以与英雄气概比肩的儿女浓情。为追寻一些空大的大义,英雄萧峰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大,而萧峰最终的泯灭本也就说明,能为自己存在的意义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证明的重要性。借段誉与虚竹,金庸把这个证明写为: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天龙八部》金庸借由佛法慈悲化解诸般苦楚,却也并非教人从此堕入空门。其一,人生本来便是感性动物,磨灭七情六欲势必带来异化的人,那么人沦为目的的工具也是意料之内的结果。其二,说万物皆空也并非磨灭人本性追求实现更高自我的本能,只是追求时切切不可忘了人性之本,而为人保留人性所在,便是最基本的人伦之乐,血性男儿,不出于此。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