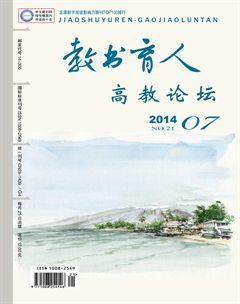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张宝石
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俗是道德发挥其社会功能的主要路径。道德是对人们的行为(无论是个体行为还是集体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从人类社会关系和人类活动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历史起源和发生过程,认为“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精神,是特殊的意识信念、行为准则、评价选择、应当理想等的价值体系,是调节社会关系、发展个人品质、提高精神境界诸活动的动力”。[1]而教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带有非常明显的阶级属性和时代内涵,它把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主要内容,从而有目的有计划对个人的身心和个性施以塑造性影响。
事实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德育的称谓、内容和要求都是不同。有的把德育称为公民教育,有的称为道德教育,也有的称为政治教育,这些称谓反映出了在德育内容和要求上的不同侧重点而已,但有把德育内涵简单化之倾向。从这些名称可以看出,无论哪种称谓都反映出德育所具有的一个重要本质,即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蔡元培德育思想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生成的,历史性和现实性贯穿德育思想始终。
一历史背景
1救亡与启蒙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惨痛历史,千年的“天朝”帝国,仿佛一夜间灰飞烟灭,屈辱的伤痛刺痛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而随之而来的前所未有的震荡,拉开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序幕。正如马克思所言:“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2]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签订了各种五花八门的屈辱性条款和条约,而腐朽的清政府并没有认真去分析这种屈辱“巨变”的原因,反而变得更加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中国完全坠入令人痛心的深渊。当时的有识之士并没有坐以待毙,就此沉沦,他们怀着拯救华夏的使命感和危机感,发出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叹息。然而,不在沉默中爆发,就要在沉默中灭亡,有识之士的叹息不会成为千年一叹,这种叹息预示着他们将痛定思痛,誓将这屈辱的枷锁用思想的启蒙和暴力的革命将其砸碎,恢复华夏民族固有的自由与尊严。
民族危机的加深促使有识之士力求变革,因此,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有识之士的思维逐渐发生变化,他们将改造国民性,重塑国民人格作为思想启蒙的出发点和立脚点,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思想以启发民智。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毅然举起思想启蒙的大旗,“由对社会客体的思考转向了对社会主体的探讨,由对西方列强的不可逾越的‘夷夏之大防,到承认在‘蛮貊和‘夷狄面前的战败事实,从而逐步转向了对国民素质的探究和对国民性改造的思考。”[3]严复是中国最早阐述思想启蒙问题的,1895年3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从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三方面进行国民性的改造,他说:“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妨;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4]严复在改良主义范畴内,表达了使中国走向富强的根本立场。这种改良主义的道路亦为当时许多启蒙者所奉行,比如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维新运动,这场维新运动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为爱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革命理想开辟道路。但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不但不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也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最终宣告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和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蔡元培在维新运动失败后,“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并且认为维新运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5]这是蔡元培教育救国思想的最初萌芽,也是他委身教育,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
2教育与救国
蔡元培一生服膺于文化教育事业,立志通过教育实现国家的富强,他虽然一生笃信革命民主主义,并追随孙中山左右,然其革命思想始终没有与教育救国相脱离,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他看到培养革新人才之重要,随着对社会现实认识的深入,认为“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小部分,然后能集成良好的大团体。所以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6]他在1919年回顾近代中国自强的历程时指出:“我国输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知教育之必要。”并且明确提出:“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这就真切的阐述了蔡元培“教育救国”的思想。由此可见,启民智、新民德、倡教育,并把教育作为救国的主要手段,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在总结屈辱历史经验中提出的一个主张。经历史的检验表明,单纯依靠教育手段去达到救国的目的是不现实的,如果把教育救国的主张同民主革命相结合,培育革新人才,这种主张不但具有进步意义,而且也符合历史潮流,从此层面来说,蔡元培所倡导的教育救国理念,就属于这样一种进步主张和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行动。
蔡元培之所以提倡教育救国,是因为他意识到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和作用,他说:“盖尝思人类事业,最普遍最悠久者,莫过于教育。”[7]“人类所最需要者,即在克尽其种种责任之能力无可疑。由是教育家之任务,即在为受教育者,养成此种能力,使能尽完全责任,亦无可疑也。”[8]蔡元培所说的“尽完全责任”亦即为国家、为社会的无私奉献精神,利用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回报社会、服务社会。此外,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使蔡元培对近代中国历史有了更清醒地认识,他认为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必须依靠国民教育,没有教育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境界的提升,民主共和的事业不可能完成。蔡元培对维新变法运动的态度就已经清楚地说明,他说:“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可见,蔡元培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腐败局面,单靠几个人和孱弱的君主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少数的事业,重要的是要从教育入手,培养革新人才。正因如此,蔡元培弃官从教,为教育事业奔走于中国之内。蔡元培诀别仕途之后,先后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等教育团体,这些教育团体目的就是救国救民,培养学生“暴动的种子”,“暗杀的种子”,所以他要求:“革命精神之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endprint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提出,教育要“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1917年,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中指出,“当满清政府未推倒时,自以革命为精神。然于普通之课程,仍力求完备。此犹家人一面为病者求医,一面于日常家事,仍不能不顾也。至民国成立,改革之目的已达,如病已愈,不再有死亡之忧。则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完全人格,男女一也。”
总之,蔡元培以教育救国为根基,以兴邦育人为良策,虽曾有“教育万能”之错误认识,然其始终坚持从教育着手,去改造社会,深信只有“养成健全人格,提倡共和精神”,才能“救我们贫弱的国家”。在教育实践过程中,蔡元培勇于改革,开拓创新,他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并同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先后废除“忠君”和“尊孔”等条文,提倡德、智、体、美和世界观教育,“五育”并举,培育了无数的爱国青年。可以说,以爱国为核心,以启民智、新民德、救中国为己任的德育思想和育人精神贯穿了蔡元培教育实践的始终。
二传统文化的滋养
蔡元培是受传统文化浸染的饱学硕儒,虽然他大胆改革,锐意创新,积极引进吸收国外学术思想和德育理念,但是他的血脉里一直跳动着华夏民族的文化因子。蔡元培对传统德育思想的继承与弘扬最鲜明之处,就是对传统德育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蔡元培开篇就谈到写此书的意义,他说:“人之生也,不能无所为,而为其所当为者,是谓道德。道德者,非可以猝然而袭取也,必也有理想,有方法。修身一科,即所以示其方法者也。”[9]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实现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没有“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根本就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因此,深受儒学影响的蔡元培非常重视修身之道,他认为“夫事必有序,道德之条目,其为吾人所当为者同,而所以行之之方法,则不能无先后。其所谓先务者,修己之道是已”,“夫道德之方面,虽各各不同,而行之则在己。知之而不行,犹不知也;知其当行矣,而未有所以行此之素养,犹不能行也。怀邪心者,无以行正义;贪私利者,无以图公益。未有自欺而能忠于人,自侮而能敬于人者。故道德之教,虽统各方面以为言,而其本则在乎修己。”[10]“修己”是道德之教的前提,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德育的核心。
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是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而人作为道德存在物,要想发挥和实现道德功能,必须拥有合理的途径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蔡元培也深知此律,尤其是在内心信念方面,他把中庸之道提高到内心信念的层面进行论述,并且认为是“伦理界不祧之宗”。他说:“理论实践,无在而不用折衷主义:推本性道,以励志士,先制恒产,乃教凡民,此折衷于动机论与功利论之间者也。……人民之道德,禀承于政府,而政府之变置,则又标准于民心,此折衷于政府人民之间者也。……然周之季世,吾族承唐虞以来二千年之进化,而凝结以为社会心理者,实以此种观念为大多数。此其学说所以虽小挫于秦,而自汉以后,卒为吾族伦理界不祧之宗,以至于今日也。”[11]即使在民主共和时代,蔡元培也认为中庸之道具有普遍适用性,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他曾用中庸之道评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为“三民主义虽多有新义,为往昔儒者所未见到,但也是以中庸之道为标准。例如持国家主义的往往反对大同;持世界主义的,又往往蔑视国界,这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族主义,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12]他之所以重视中庸之道,主要原因在于他视中庸之道为中国的民族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的根源。“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文化交融理念就是中庸之道的理论运用。
道德是蔡元培思想的根本目的和终极关怀,同其他近代知识分子一样,道德在蔡元培那里不仅仅是行为规范,他更将道德视为人格完善和人性升华的路径和标识。但是蔡元培不像严复等近代知识分子,只强调公德而忽视私德,认为只有公德才能有助于国家的富强。在中国,传统道德大多属于公德的范畴,因此,传统道德被认作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而成为众矢之的。其实“道德之为道德,就在于它有一种‘绝对命令式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根源于人的良知或实践理性。”[13]蔡元培认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仅与公德有关系,更与私德关系重大,因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个人素质的高低决定社会道德状况的好坏。因此,蔡元培认为私德与公德同样重要,二者不可偏废。他说:“今人恒言,西方尚公德,而东方尚私德;又以为能尽公德,私德之出入不足措意,是误会也。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14]因此,要完善人格,必须通过教育,而“德育实为人格之本”。但是,蔡元培所提倡的道德并非纯粹的传统道德,他清楚地知道传统道德缺点和不足之处:“我国伦理之说,萌芽于契之五教。自周以来,儒者尤尽力发挥之。顾大率详于个人与个人交涉之私德,而国家伦理阙焉。法家之言,则又偏重国家主义,而蔑视个人权利。”[15]虽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是在对待西方文化时,他主张要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形成民族特色,而不能“为其同化”。
三西学的熏陶与借鉴
蔡元培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愤然离京南下,放弃仕途,献身教育事业。先后创办了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组织中国教育会,创立光复会,主持同盟会上海分会,在国内参与反清的各种革命活动,可以说,蔡元培的名字与当时的民主启蒙运动是紧密相连的。但是蔡元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也表现了他的弱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轻视群众,过分看重了个人的作用,将自己和所谓‘群氓对立起来,不愿意在群众中作艰苦的工作,对革命怀有急躁冒进情绪,因此,很容易在革命方法上接受民粹派的影响,企图用个人恐怖去代替群众的革命的发动。”[16]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革命队伍出现分裂,蔡元培感到“所图皆不成,意疲倦”,于1908年迁居德国莱比锡。endprint
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共学习三年,先后研习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等课程,正是在德国的这段时间,蔡元培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并翻译了《伦理学原理》一书,他以康德哲学作为自己哲学的框架,吸收了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伯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但是他反对尼采的强权主义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也不赞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由于蔡元培博采众长,涉猎广泛,在此,笔者简要阐述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思想对蔡元培的影响。
兼容并包的文化交融思想是蔡元培社会进步理论的基础,也是其德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梁启超、严复为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启发,认为社会以残酷的生存竞争为特征时,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进入了蔡元培的视界,后者否认进化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战争来实现的逻辑前提,宣称:和谐与合作,才是人类自然生活的本质特征。蔡元培坚守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互助合作不仅发生在特定的团体之间,也发生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的进步不是通过单一的自然选择的淘汰方式完成,而是通过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交流过程实现的,在这个文化交流过程中,也有淘汰现象发生,淘汰的是陈旧的观念和准则,究其原因是:“只有那些将自己与外界团体的所有接触顽固地隔绝开来的社会才会真正地被淘汰。”蔡元培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一篇文章中,用互助论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战胜同盟国,并称为“是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他说“从达尔文等发明生物进化论后,就演出两种主义:一是说生物的进化,全侍互竟,弱的竟不过,就被淘汰了,凡是存的,都是强的。所以世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一是说生物的进化,全侍互助,无论怎么强,要是孤立了,没有不失败的。……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约国,互相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约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17]可见,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正是蔡元培德育思想的源头之一。蔡元培多次留学国外,他比同时代的学者对西学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后人评价他“一方面接受了固有的文化遗产,一方面又吸收19世纪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互助论的新思想,加以发扬光大,这样才成了中国近代思想界的火炬。”[18]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5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
[3]陈剑旄.蔡元培伦理思想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4:21.
[4]严复.严复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
[5]周天度.蔡元培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
[6]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
[7]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414.
[8]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63.
[9]张汝伦.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138.
[10]张汝伦.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138.
[1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51.
[12]桂勤.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18.
[13]张汝伦.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15
[14]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4.
[15]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68.
[16]周天度.蔡元培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8.
[17]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16.
[18]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10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