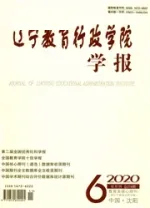明代的地震灾害与国家应对举措
郑民德,吴志远
1.聊城大学,山东 聊城252059;
2.郑州大学,河南 郑州450000
明代地震灾害在全国都有分布,但陕西、甘肃、四川、山西、宁夏诸省为重灾区,无论是发生的频率,还是地震的烈度,都远远高于其他省份。地震灾害在明代之所以主要发生于西部与西南部,是因为那时这些区域正处于华北地震区与青藏高原地震区的活跃时期,加上此时对地震没有科学的认识与了解,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给国家与社会稳定都带来了巨大危害。地震灾害发生后,如何组织灾民自救,防范瘟疫、流民、治安败坏等次发性灾害的出现,成了地方与中央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通常情况下,除根据地震的破坏程度豁免税粮、拨粮银赈济、安抚民众外,最高统治者与当地官员还会祭祀天地、省身自悟、大赦刑狱等,希望通过自己虔诚的祈祷来获得神灵的救赎与怜悯,这种现象的出现既体现出中国古代社会对地震知识缺乏最起码的了解,也反映了在小农经济状况下,国家与政府无法以足够的物质力量去应对灾害,保障所有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近年来中国的西部与西南部地区连续发生了数次规模较大的地震,与明代地震灾害的分布呈现出类似的特征,因此加强对明代震灾的研究,对现代社会的防灾赈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明清地震灾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关于明代地震灾害研究的前期成果参见:邓瑞生:《关于公元1515年永胜地震的震级问题》,载于《地震研究》1980 年第2 期;江在雄:《明清时期西昌三次地震救助措施及社会影响》,载于《四川地震》2005 年第2 期;张钰:《明代甘肃地震分布特征及影响》,载于《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1 期;任晓兰:《论明代地震灾异与地方治理——以嘉靖乙卯陕西大地震为例》,载于《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3 期。但这些研究多关注于个案或某地区、某省份,而对地震的整体与宏观研究不多,也没有系统、全面、综合分析地震中国家、地方政府、基层民众的应对态度,因此有进一步深化与扩展的必要。
一、关于明代地震灾害景象与危害的史料记载
明代的地方志与文人笔记保留了大量关于地震灾害发生时的景象描述,这些史料虽然在语言方面不免有夸张与渲染的成分,却是反映当时地震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对地震中房屋、城池、人群、气象、天地、河流的描述,不但体现了地震的破坏力与危害性,而且也凸显了地震目睹者的心理变化与直观感受,真实地再现了瞬间巨变中人类的错愕与恐慌。
(一)关于地震景象的描述
明初洪武、永乐、宣德年间虽有地震发生,但因震级不高,危害性不大,所以在史料中的记载都较为简洁。宣德后,随着数次大规模震灾的发生,关于地震的记录也逐渐成了地方志、文集、笔记,甚至正史、实录、政书、名臣奏议等重点关注的对象,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史料。成化元年(1465 年)湖北襄阳发生地震,“屋宇摇动,轰轰有声”,[1]三年(1467 年)三月“辽东、宣府地震有声,四川尤甚,至一百七十五震”,[2]十三年(1477 年)夏四月“陕西、甘肃天鼓鸣,地震有声,生白毛,地裂水突出高四五尺,有青红黄黑四色沙。宁夏地震有声如雷,城垣崩坏者八十三处,甘州、巩昌、榆林、凉州及山东沂州、郯城、滕、费、峄等县地同日俱震”,[3]十六年(1480 年)九月“四川威州地震有声”,[4]成化年间关于地震的记载,对房屋、地动声音、频率、水涌、沙石都做了仔细的描述,而这一时期的地震也主要发生于四川、甘肃、陕西、宁夏、辽东、湖北、山东等地,在中国的西部、西南部、东北部、东部都有分布,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弘治在位18 年,在明代诸帝中在位时间并不算太长,但是全国各地发生地震的次数却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弘治元年(1488 年)八月,四川德阳、石泉二县,汉、茂二州同时地震,“仆黄头等六寨碉房三十七户,人口有压死者”,[5]茂州即今四川省北川、汶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辖地,在明代就是地震频发的地区。同年十二月,“四川建昌越嶲、宁番等卫并成都等府,潼川、遂宁等州同时地震并雷电、雨雹、阴霾,自辛卯至是日乃止”,[5]因地震而引起的环境与天象的变化,往往使各种自然灾害重叠与并发,从而造成次发性灾难的产生。弘治二年(1489 年)二月,“四川威州地震有声如雷”,[5]同年十一月“四川威、茂二州同日地震有声”。[5]弘治三年(1490 年)正月,“四川汶川县地震有声如雷”,[5]同月“四川茂州地震有声如雷”,[9]其后一直到弘治末年,四川的汶川、威州、茂州等地区的地壳始终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几乎每年都发生一次或者数次地震,特点是频率虽高,地震烈度却不大,所以造成的损失有限。弘治年间除四川各州县地震剧烈外,陕西省也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地震,十四年(1501 年)正月,“关中地震,朝邑为甚,坏城郭官民庐舍,高原井竭,卑湿地裂,奄忽水深尺许……至十一月犹震不已”,[6]而据当时的陕西监察御史燕忠奏称“西安并长安等县申称,弘治十四年正月初一日申时分忽然地震有声,从东北起响向西南而去,动摇军民房屋,本月酉时分复响有声如前,至次日寅时又响如前”,[7]这次陕西地震不但延续时间长达一年,而且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属该时期规模较大,级别较高,损失较为严重的地震。
正德与嘉靖年间,地震的频率与烈度均达到明代的高峰期,这是因为嘉靖帝在位长达45 年,地震累积次数较多,另外,由于此时正是中国各地震带最为活跃的时期,加上洪旱蝗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震灾的危害性。正德元年(1506 年)十月,四川威州、茂州、汶川地震。正德五年(1510 年)七月,“四川威、茂地震有声如雷,漳川、乐至州县皆震”,[1]其后这一地区屡震不止。嘉靖三年(1524 年)八月天津发生地震,“自东北方起,西南方去,地震声响如雷,将官舍,人民居住房屋震动,人皆惊恐”。[8]嘉靖三十四年(1556 年)陕西发生大震,“地震山移数里,平地坼裂,水溢出。西安、凤翔、庆阳诸府州县城皆陷没……山西平阳、河南河洛诸郡县皆连及之”。[9]关于该次地震,时人归有光曾有记述“丙辰岁予在南宫,见关陕之士问前岁地震,云往往数百里崩陷,华山亦忽低小,秦雍之间碑石多摧碎,圆如鹅卵”,[10]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陕西,却波及到山西、河南二省,甚至达到了山移、水泄、碑碎的程度,可见烈度之大。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蒲州、潮州各地震,东阳县出血”,[4]三十九年(1560 年)湖北竹溪县“地震出血”,[4]地震出血是由于地裂而导致的地下矿物质混合水流而引起的,属古人直观而非科学性的见解。
明后期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四朝的地震主要集中于万历与天启年间。隆庆二年(1568 年)四月,顺天府丞何起鸣自四川回京,途径陕西西安府兴平县,“忽遇地震,从省城东南起往西北去讫,有声如雷,平地起仆不常,远望城内乡村灰尘障天,臣不胜惊骇,疾奔城内,遍阅垣庐十室九欹,及至咸阳、泾阳一处较甚,一处至高陵则举城无完室,举室无完人,悲号之声彻于四境……经月而震,震而有声如雷者”。[11]万历二年(1574 年)“福建汀州府长汀县二更地震,三更崩裂成坑,陷没民房四十余间”,[12]十三年(1585 年)二月“淮安、扬州、庐州及应天、上元、江宁、江浦、六合俱地震,江涛沸腾”,[12]同年七月西安府及高陵县地震,“势如风,声若雷”。[12]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正月“四川地震三日”,[12]三十二年(1604 年)闰九月,“陕西巩昌府澧县地震声如雷,一日十余次,城墙房屋大半倾倒,又白阳、吴泉交界去处地裂三丈,溢出黑水,湍激丈余”,[12]地震中出现的声音与地质的变化,与震级、烈度是分不开的,而古人对这些景象的描述,虽然反应的是一种惊异与恐惧的心理,也不能从科学的角度进行解释与阐述,但却保存了最原始的记录,这对于后人分析当时的地震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天启元年(1621 年)二月,“四川广元县地震”,[13]同年闰二月“四川平武县地震”。[13]天启六年(1626 年)六月山西大同府地震,“从西北起,东南而去,其声如雷,摇塌城楼城墙二十八处。浑源州从西起,城撼山摇,声如巨雷,将城垣大墙并四面宫墙震倒甚多,王家庄堡天飞云气一块,明如星色,从乾地起声如巨雷之状,连震二十余,顷至辰时仍不时摇动,本堡男妇群集,涕泣之声遍野,摇倒内外女墙二十余丈”。[14]
从上面资料可以看出,明代时期的地震四川发生次数最多,陕西、山西地震烈度最大,虽然东部与南部、东北部也有地震的分布,但在发生频率与破坏性上均不及西南与西北地区。另外,史料中最常见的记载是关于地震中声音、气象、水流、山脉、城市、房屋的,这些现实中的物象不但直接反映了地震的强度,而且也体现了时人的心态变化。
(二)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明代地震的频发,一方面引起了人的恐慌与社会秩序的紊乱,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与经济财产的损失。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水平落后,国家与社会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进行地震监测与灾害预防,基层民众也因对地震存在困惑与不解,恐惧心理大于防范心理这,这也加剧了震灾的破坏力与危害性。
明代地震危害最大的时期集中于嘉靖与万历两朝,正统、正德、天启、崇祯年间也较为严重。正统五年(1440 年)冬十月,陕西庄浪等县地震“十日乃止,坏城堡,官民庐舍,压死男女二百余,骡马牛羊八百有奇。事闻,上敕三司修葺,赈恤之,并敕总兵官严督边备”。[15]景泰六年(1456 年)六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杨贡奏“五月初六日苏州地震,并常、镇、松江四府瘟疫,死者七万七千余人”,[15]地震不但造成人员伤亡,使日常生产工具与畜力损失,对农业的正常运作造成破坏,而且往往与瘟疫、饥荒、水旱等自然灾害相伴而生,这使得灾区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成化十四年(1478 年)秋七月四川监井卫地震,“廨宇倾覆,人畜多死”,[3]十七年(1481 年)二月“南京地震,江北四府、河南、山东、云南皆震,鹤庆、满川、通安州震一百余次,居屋倒压,男妇死无数”。[16]弘治十四年(1501 年)辛酉元旦,“陕西三府地震声如巨雷,倒廨舍五千余,死男妇百七十,韩城尤甚,安昌八里遍地窍水,有震裂一二丈或四五丈如河者,蒲州地震二十九次”,[16]该次地震使陕西朝邑县“军民房屋震摇倒塌共五千四百八十五间,压死大小男女一百七十名口,压伤九十四名口,压死头畜三百九十一头只”。[17]明代地震损失的统计内容包括人口、牲畜、房屋、城墙等,先由里甲报送州县,再由州县上报省布政司,最后禀明国家户部,经朝廷商讨后根据震区的损失程度进行赈济。
正德与嘉靖年间,随着地震活跃期的到来,这一阶段发生了数次巨震,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正德二年(1507 年)夏四月,“云南木密关地震如雷,凡五次,坏城垣屋舍,伤十有二人”,[18]七年(1512年)八月己巳日云南腾冲地震,“次日复大震,自丑至申,城楼及官民廨宇多仆者,死伤不可胜计,既而地裂涌水,田禾尽没”,[18]十年(1515 年)云南又遇强震“日二三十次,逾月不止,地裂水涌,死者数千人”,[16]正德年间地震多发于云南与四川,伤亡人数从十数人到数千人不等,这种差别既与地震的烈度有关,也与地震发生的时间、建筑物的质量、地质环境等密不可分,其结果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嘉靖十五年(1536 年)二月二十八日,四川建昌、宁番二卫,“地震如雷,吼者数阵,司及二卫公署内外民居城垣一时皆塌,压死都指挥一人,指挥二人,千夫长四人,百夫长一人,所镇抚一人,吏三人,士夫一人,太学生一人,土官土妇各一人,军民夷獠不计,水涌地裂陷下三四尺,卫城内外若浮块而已,震至次月初六犹不休,陷河之说殆是实然”。[19]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陕西、山西、河南同时地震,“或地裂泉涌,或城郭房屋陷入地,或平地突成山阜,压毙官民八十三万有奇”,[20]三省同时地震,并且造成83 万人员的死亡,甚至平地成山,房屋陷地,可见此次地震规模非常之大,在中国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隆庆六年(1572 年)十二月,“陕西巩昌府地震,岷州尤甚,声响如雷,城墙、楼台、官民房屋十倒九塌,死人畜不计其数,居民陈学房前摇出红水一穴”。[12]万历五年(1577 年)二月,“云南腾越州地震二十余次,次日复震,山崩水涌,倒坏庙庑官舍监仓一千三百余间,民房十分之七,压死者百七十余人”。[12]万历十八年(1590 年)陕西与甘肃等处地震,“坏城郭庐舍,压死人畜无算”,[12]三十三年(1605 年)广西陆川县地震“声若崩山,震塌房屋,压死居民男妇无算”,[12]三十七年(1609 年)甘肃地震“红崖、清水等堡军民压死者八百四十余人,边墩摇损凡八百七十里,东关地裂,南山一带崩,讨来等河绝流数日”。[12]地震不但使民众伤亡,房屋倒塌,而且引起了震区周边环境的变化,使其他自然灾害爆发的可能性提高。天启二年(1622 年)九月,陕西固原、隆德等县地震,“城垣震塌七千九百余丈,房屋震塌一万一千八百余间,牲畜塌死一万六千余只,男妇塌死一万二千名口”,[13]一次地震就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可见其破坏性十分惊人。
明代地震给基层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旱、涝、瘟疫、蝗等自然灾害不同,地震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往往在一瞬间产生严重的破坏力,使人产生恍如隔世的错觉,因此百姓心理上的创伤更加难以愈合。另外,地震破坏范围广泛,对民众的衣食住行诸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灾后重建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百姓的生存压力与负担。
(三)地震导致社会秩序紊乱
地震从表面看只是一种地壳运动,属自然现象,但是造成的社会冲击力却十分深远。地震发生后,房屋倒塌、粮食匮乏、百姓流离,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中谋取生存,灾民往往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获得食物与财物,同时部分劫匪与盗贼也利用地震后地方政府忙于赈灾而无暇旁顾之时从事抢劫与偷盗等犯罪活动,从而使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与政府能够采取有效的赈济手段满足灾民的口食之需,并且分步骤、有效率、积极而主动地加快灾区重建的步伐,使灾民尽早过上安定的生活,那么因震灾而引起的动荡将很快终止,反之则将引起社会秩序的失衡与治安状况的恶化。
嘉靖年间,直隶安州发生地震,结果引起了大变,“州人乘乱抢杀,目无官法,上司闻风畏避,莫知所出,杨少保南涧公(字守礼)家食已二十余年矣,先期出示晓以朝廷法律,越二日乱如故,公乃升牛皮帐,用家丁率地方知事者击斩首乱之人,悬其头于四城门,乱遂定”,[21]地震后的抢劫与变乱属民众的恐慌心理所造成的,不具备组织性与长期的规划性,只属暂时的动荡,所以致仕官员杨守礼采取国家律法与武力压制相结合的手段,很快就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同时期人侯汝谅任陕西按察司副使时,“地震异常,人多压死,劫夺蜂起,公循行禁缉,地方赖以无虞”,[22]另一人赵祖元任职山西按察司主事,“丙辰地震,河东蒲州境覆压过半,盗乘之猬起,抄劫昼行,公设方略解散其党,而悉籍其金钱之无主者数十万贮之”。[22]万历中,“蓟镇沿边诸郡地震累日,劫略之寇千百成群,出入城市,索民财物,吏不能禁”,[23]万历末年蓟辽等边镇连年战乱,百姓十不存一,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地震又使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因此治安状况恶化实质为社会与自然因素双重影响的结果。
明代基层社会在无天灾人祸时始终维持着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但是一旦旱涝、地震、蝗害、兵燹打破这种平衡,那么基层社会就会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进而诱发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使国家对地方的管理日益艰难。另外,地震所造成的危害大小也绝非仅与烈度、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相关联,更与国家赈灾力度、救济效率、安抚措施等多种政治性举措密不可分,实际上是对国家应对能力与经济实力的一种考查与检验。
二、地震所产生的政治性后果与各阶层的反应
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在明代社会却上升到了政治高度,甚至与党派斗争、皇权巩固、神灵祭祀联系起来,这其中既有忠臣认为地震是朝政日非导致天怨人怒的事例,也有君主利用地震彰显皇恩,通过罪己诏、赈灾、豁免税粮、大赦天下等措施来巩固皇权的举动,更有膜拜神灵、祭祀天地、祈求上苍等带有浓厚色彩的迷信活动。这所有的一切从表面看都是因地震而引起的,实质上却是一种权力上的博弈与现实政治冲突的反应。
(一)朝廷官员震后的态度
明代朝臣在地震发生后,除了积极组织灾区民众自救与申请朝廷的赈济粮食及款项外,还利用地震针砭时政、痛斥奸邪、激浊扬清,希望借此引起统治者对朝政与吏治的重视。建文元年(1399 年)南京地震,诏求直言,御史大夫尹昌隆上言,“奸臣专政,阴盛阳微,谪见于天,是以地震”,[24]尹昌隆以地震来贬斥时政,并且认为明军与燕军之间的战乱是导致地震的重要原因,希望朝廷能够息战火、祛奸臣、安百姓,采取果断的措施使天下平静。天顺年间,大臣李贤上疏称“往岁以来山崩河改,地动殿灾,蝗旱相仍,天象交变,谴告之意可谓至矣,当时若能废黜奸邪,任用忠良,克己自新以答天谴,未必不转祸为福也,惟其修省未至,是以不免于难”。[16]将国家政治与天象灾变结合起来,是明代大臣劝诫最高统治者的一种方式,即利用上天至高无上的神权来限制君权,从而达到使朝政焕然一新的目的,所以与其说明臣敬畏天地,不如说其本质是以天地之名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
成化三年(1467 年)四川前后地震375 次,十三道御史奏称“风霾地震灾异屡见,请侧身休省,日御讲筳,节无益之事,惜无名之赏”,[16]希望通过地震的发生来劝谏皇帝勤理朝政,节约资财,刷新政局。成化十七年(1481 年)南京、山东、河南同日地震,礼部奏言“考之传记,地震千里有大灾,又云春动者岁凶,二月动者水灾,今所动不止千里,又况凤阳、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庙社稷所在,关系尤重,乞行各处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变异;储广蓄,省费用,以备岁凶;浚河渠,筑河堤,以防水患,毋徒事虚文”,[25]数省同日地震,其规模非常之大,因此礼部建议处理民间冤案,发展农业生产与水利来消除灾害,用实际的行动来求得上天的怜悯与宽恕。弘治十四年(1501 年)正月陕西西安、延安、庆阳、潼关诸处地震,倒塌房屋,损伤人命,兵部尚书马升上疏言:“地乃静物,止而不动,动则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于中国之兆,历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涌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异,古今所未多见者也”。[26]古人对地震缺乏科学的认识,所以认为大地是静止不动的,如动必然关系到国家的气脉与政局,这就需要用行仁政、修省克责、广言路、重台谏、节府库来让民众休养生息,稳定社会。
正德十五年(1520 年)三月云南府、大理府、鹤庆府诸州县地震,有大臣奏“天下近年地震之变,云南独多,云南地方地震之变,银场尤甚,实由银矿采挖深酷,有伤地脉”。[27]地震的频发确实与矿产开采导致的地面塌陷有很大的关系,明代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是历史的进步。但地震又不完全是采矿造成的,更多为深层地壳运动的结果。同时期的大学士刘健曾上书称:“近者地动天鸣,五星凌犯星斗,昼见白虹贯日,群灾叠异并在一时,京城道路白日杀人,西北诸边胡虏猖獗,损兵折将,前后相仍,战则无兵,守则无食,民生穷苦,府库空虚,风俗倾颓,纪纲废弛,赏罚不当,名器冗滥”。[28]将各种政局败坏的现象与地震联系起来,实为以天道来劝诫君道,天灾更是人祸的体现,帝王必须有所反省。嘉靖二年(1523 年)正月应天、凤阳、山东、河南、陕西地震,给事中黄臣奏称“太监萧敬久窃重秉复,开传乞之门,地震之变斯人致之,宜加窜斥”。[4]同年南京地震,礼部侍郎刘瑞上言:“地震不于他处而独于南京,不于他日而于立春元旦,凡有耳目莫不骇愕,盖南都天下之本,而军民又南都之本也,本安则天下安矣”,[29]因此请求朝廷发帑藏赈灾,并派专人督察灾情与赈济事宜,防止贪官蠹吏侵盗累民,祭祀天地以顺民心,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批准。
万历元年(1572 年)四川与湖北连续地震,礼部上言曰:“地道承天以静为主,一有震动是为失常,今楚蜀之间相继地震,绵亘千里,厥变匪轻,皇上敬天勤民,感格有素,唯是大小臣工奉职无状所致,请行内外各衙门痛自省愆,勉图修职,毋图粉饰虚文。尤望皇上仰体天心,益修圣政,缉学问于无间……节用爱人,亲贤纳谏”,[12]这对大臣与皇帝两方面都提出了要求。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五月北京地震,“自西北乾方徐往东南,连震二次。各衙门大小官员痛加修省,各青衣角带朝参办事三日,尤望皇上勤批答,接阁部,纳直言,录废弃,恤四方水旱之灾,严九边戎兵之诘,以图消弭之实”。[12]京城地震引起了当政者的重视,不但大臣们修省自悟,甚至连疏于朝政的万历帝也以天心示警而自勉,这自然与北京作为“首善之区”的政治地位是分不开的。
明代大臣往往将地震与国家政局结合起来,越是在朝政腐败、权奸当道、皇帝昏庸的时期,这种联系就越加紧密。这不但反应了明人对地震的畏惧与困惑,也是朝臣彰显个人政治观点,以天道来抑制君道的一种方式,体现出了臣子利用天威与君权博弈及妥协的过程。另外从整体来看,大臣们的这种“以震灾挟君主”的举措在多数情况下是行之有效的,君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与统治,往往会对灾区采取一些赈济措施,并且检视自己的缺点与失误,听取更多正直之臣的建议,使某些弊端得到祛除与缓解。
(二)最高统治者对地震的反应
封建时代,皇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享有“家天下”的权威,有关皇帝的诏令、谕旨、敕命都拥有至高无上的强制性,尽管在某些时期这一权威会受到某些势力的干预与挑战,但是最终依然会回归正统。地震,作为封建时代重大的自然灾害,其巨大的破坏性自然会引起皇权的重视,除豁免税粮、拨粮赈灾、安抚百姓外,祭祀山岳与神灵、斋戒、修身省悟等精神方面的自我安慰也是皇帝舒缓地震灾害压力的几种方式。
永乐元年(1403 年)北京、山西、宁夏诸地皆地震,太宗询问侍臣地震频发原因,对曰:“地震应兵戈土木之事”,上回复“比年兵旅饥馑,民困甚矣。朕方日夜图苏息之,岂肯适一己之情,兴土木之工,重困民力,如楼居可以避暑,则午门、端门皆可居也,何必重建高台广榭,今后宫卑隘不足容尚不敢增修,虑劳民力,土木之事,在今不为。若云兵戈,但当敕边将严守备,戒不虞而已”。[30]经历过“靖难之役”后复发生大规模的地震,令永乐皇帝异常忧虑,所以他实行节资财、纾民力、严边备的措施就是为了尽快使国家休养生息,让民众过上平稳的生活。成化四年(1468 年)八月京师地震,“下修省诏”,[31]十二年(1476 年)发生大旱与地震“遣右副都御史赵文博祭祷中岳”。[32]地震后下罪己诏与祭祀山岳之神,精神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与其期望这些祀典真正发挥作用,不如说统治者只是得到了心灵上的慰藉而已。
正德四年(1509 年)北京发生地震,武宗谕令“朕心惊惕,尔文武百官同加修省,致斋三日,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33]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二月陕西、山西、河南地震,“敕户部左侍郎邹守愚往祭其山川社稷,城隍及所在帝王陵寝,领白金四万从便宜赈之”。[28]隆庆二年(1568 年)六月,“以陕西地震,命巡抚都御史张祉告祭西岳华山,西镇吴山之神”。[34]万历三年(1575 年)京师地震,“诏百官修省三日”。[12]崇祯时南京地震,思宗皇帝谕曰:“留都根本重地,灾异示警,朕深惕然……大小臣工宜图修省,各御史计议抚恤民隐,务修实事,毋循虚文,以称朕克谨至意,两京该部知道”。[14]明代皇帝对山川、神灵、宗庙、社稷的膜拜与祭祀,既是封建时代的一种仪式与信仰,也是地震灾害发生后,无力抵御自然重创的一种消极反应,因为朝廷既无法准确地预测地震,更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赈济灾区,只好在精神方面去寻求虚无的安慰了。
三、国家的震灾救济
封建社会标榜“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明王朝也不例外。地震发生后,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与保障民生,明政府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去赈济灾区,防止民众流亡,极力巩固自身的统治,其通常的措施为豁免赋税、拨款赈灾、施粥放粮等。这些措施有时单一使用,有时联合使用,其施用方式要与震灾的规模、分布区域、影响力大小相互联系。即便朝廷努力赈灾,但因灾民救济刻不容援,而赈灾物资由于交通不发达经常延迟,加之灾民数量极多,相关的救济不能满足灾民需求,所以往往造成大量民众的死亡与流浪,进而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与治安状况的恶化。
明代地震赈济分为国家与地方两方面,其中国家方面即动用国库帑金、京通仓粮、盐税、地丁银等援助百姓,而地方官府除利用常平仓、预备仓、社仓的平粜进行赈济外,还动员地方绅士、名流、大商人捐助粮食与银两,利用社会的力量来救济灾民。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陕西、山西、河南三省同时发生大地震,倒塌屋舍无数,压毙人口达80 多万,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地震灾难。震灾发生后,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赈济灾荒,三十五年(1556 年)先是“以地震免山西蒲、解、临晋、安邑、夏、芮城、猗氏、平陆、荣河九州县去年秋粮,而于平阳、潞安及汾、绛二州无灾之处加征补之”。[35]免除灾区秋粮对于缓解灾伤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将赋税压力增加到其他州县,又加重了这些地区民众的负担,可见明政府对赋税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百姓的安危。同年因三省灾民人数众多,仅豁免税粮难以满足赈灾之需,又“以地震发银四万两赈山西平阳府、陕西延安府诸属县,并豁免税粮有差”,[35]并拨帑银45000 两赈延绥、宁夏、甘肃等受到地震波及的灾区,以稳定当地民众的生活。明政府的这些救济举措对于灾区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相对于数十万乃至百万的受灾群众而言,这些救助又无异于杯水车薪。明政府既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保障所有灾民的生活,所以震后大规模灾民的死亡与流浪在封建社会也就不足为奇了。
嘉靖四十年(1561 年)宁夏地震伤人,“发太仓白金八千赈恤之”。[28]隆庆二年(1568 年)礼科都给事何起凤奏陕西西安府地震伤人,请求朝廷赈济,“上曰地震重大,所在被灾人民朕深悯念。赈济一事户部议处以闻,于是户部奏以本省织造羡余银八千八百三十两并预备仓粮相兼赈济”,[36]并命地方抚按等官委任贤能官员负责赈济事务,以使灾民均沾恩惠。崇祯元年(1628 年)大同巡抚张宗衡奏称:“大同兵革之后更逢凶年,陡于八月十九日霜降,九月初十日地震,自九月来斗米值钱四百文,持钱入市都无粜者,闻山西镇城积谷颇多,不拘何仓求发十万石给大同,准照时估抵该省民运额数,又临德二仓请发十五万石,每石作价六钱,将京运照价扣库”。[37]大同作为九边军事重镇,其地位异常重要,于是明政府多方筹措,发粮数十万石赈大同震灾。崇祯四年(1631 年)甘肃临洮、巩昌两府地震,“坏庐舍,损民畜,是天之不吊此一方之民也,而鹑衣草食,情景萧条,将糊口之不赡,而欲无逋赋,能乎”,经朝廷商讨决定,“查临洮府属该新派银二千一百九十五两零,巩昌府属该新派银七千一百一十七两零,即如按臣所言四年免派一年,其原派九厘及各项现征银粮姑与缓之”,[37]这里所免除的属于“三饷加派”银两,而国家正赋是不能豁免的,所以对于遭受兵乱与灾荒之苦的甘肃人民来说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也不可能减轻民众的苦难与流亡。除政府的赈济外,地方社会的宗族、社团、会社同样在灾荒期间起了一定的作用,“不同的宗族组织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墓祭、修族谱、建祠堂等方式敬宗收族,强化各自边界”,[38]在震灾时期起着赈济同族与乡里的作用,而以会馆、结社形式出现的规模相对较小,但联系性较强的组织亦起着同样的功能。
明政府的震灾救济既是国家的一项政治举措,其目的在于救济灾民、稳定地方社会、巩固统治,同时也发挥了重要的经济作用。因为国家拨放的粮银不但可以平衡市场粮价,保障市场供给,而且对于缓解灾民的恐慌心理,维持其最基本的生活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过分渲染与夸大政府赈灾的功能,因为明代地震灾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地震分布范围广,危害性大,损失人口数量多。明代地震范围几乎涉及全国,尤其是四川、陕西、甘肃、山西为重灾区,每逢大震,往往造成数十万民众死亡,数百万灾民流浪,而国家的赈济粮银数目难以与灾情的实际情况相符,不能保障多数灾民的生活。其次,明代的几次大震几乎都发生于嘉靖年间,而嘉靖时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也极为频繁,多重灾难的重叠不但增强了震灾的危害性,而且也加剧了政府的救援难度,国家分身乏术,财政吃紧,无法应对如此众多的灾荒。最后,地震救援决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灾害的应对,更多的是与国家政治局面、经济实力、应对政策等密切相关,在社会安定、国库充裕、吏治清廉的情况下,震灾的救济不但及时有效,而且瘟疫、饥荒等次发生灾荒发生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反之则可能导致灾民流亡与社会秩序紊乱,甚至引发农民起义与暴动。
四、小结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但是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传承方面与汉唐宋差别不大,在自然灾害的救济上依然属传统国家、地方政府、民众自救三方面的结合。与其他朝代相比,明代地震的发生频率较高、分布范围较广、危害性较大,这既与明代中国大陆地壳运动处于活跃期有关,也与这一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有着很大的关系。大量人口聚集而居虽然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但是在地震来临时也增加了伤亡的数量与救援的难度。另外,四川、陕西、甘肃、宁夏是明代地震的重灾区,这些省份不但地震发生的频率很高,而且经常发生大震与巨震,这与近几年中国西部与西南地区几次大震具有相同的特征与性质,均处于龙门地震断裂带与汾渭地震带的活跃时期,从全球地壳分布上看则处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的活跃期。不过与现代社会相比,明代科技与交通均不发达,加之百姓对地震普遍存在敬畏心理,所以在救援效率、运输速度、灾后重建方面均难以与现代社会相比,但是,明代保存的一些地震资料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地震为现代社会服务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M].卷22、卷27,明崇祯九年(1636)刻本.
[2] 万斯同.明史[M].卷234,清钞本.
[3] 明宪宗实录[Z].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165、卷180,成化十三年夏四月戊戌朔、成化十四年秋七月丙子条.
[4] 雷礼.皇明大政纪[M].卷16、卷24、卷24、卷21,明万历刻本.
[5] 明孝宗实录[Z].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17、卷21、卷23、卷32、卷34、卷34,弘治元年八月壬寅条、弘治元年十二月甲午条、弘治二年二月壬寅条、弘治二年十一月癸酉条、弘治三年正月辛酉条、弘治三年正月戊子条.
[6] 郭实.续朝邑县志[M].卷8,万历十二年(1584)刊本.
[7] 黄训.名臣经济录[M].卷7,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刘麟.清惠集[M].卷3,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范守已.皇明肃皇外史[M].卷36,清宣统津寄庐钞本.
[10] 归有光.震川集[M].卷5,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11] 孙旬.皇明疏钞[Z].卷23,明万历自刻本.
[12] 明神宗实录[Z].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22、卷158、卷163、卷306、卷401、卷8、卷59、卷224、卷409、卷459、卷24、卷285、卷53,万历二年二月庚申条、万历十三年二月丁未条、万历十三年七月丙戌条、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壬辰朔、万历三十二年闰九月庚辰条、隆庆六年十二月已未条、万历五年二月已卯条、万历十八年六月丙子条、万历三十三年五月辛丑条、万历三十七年六月辛酉条、万历元年十二月辛未条、万历二十三年五月庚子条、万历三年十月丁卯条.
[13] 明熹宗实录[Z].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6、卷7、卷26,天启元年二月庚申条、天启二年闰二月丙戌条、天启二年九月甲寅条.
[14] 金日升.颂天胪笔[M].卷21、卷2,明崇祯二年(1629)刻本.
[15] 明英宗实录[Z].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72、卷254,正统五年冬十月庚辰条、景泰六年六月戊寅条.
[16] 查继佐.罪惟录[M].卷3、卷3、卷3、卷9,部丛刊三编景手稿本.
[17] 马文升.端肃奏议[M].卷9,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明武宗实录[Z].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12、卷91,正德二年夏四月甲寅条、正德七年八月已巳条.
[19] 曹学佺.蜀中广记[M].卷34,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沈国元.皇明从信录[M].卷32,明末刻本.
[21] 冯梦龙.智囊补[M].卷11,明积秀堂刻本.
[22] 焦竑.国朝献征录[M].卷63、卷97,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徐象橒曼山馆刻本.
[23] 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M].卷244,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充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24] 陈鹤.明纪[M].卷7,清同治十年(1871)江苏书局刻本.
[25] 黄光升.昭代典则[M].卷20,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周日校万卷楼刻本.
[26] 唐鹤征.皇明辅世编[M].卷3,明崇祯十五年(1642)陈睿谟刻本.
[27] 何孟春.何文简疏议[M].卷6,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 何乔远.名山藏[M].卷70、卷26、卷27,明崇祯刻本.
[29] 张卤.皇明嘉隆疏钞[M].卷6,明万历刻本.
[30] 明太宗实录[Z].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25,永乐元年十一月辛未条.
[31] 邓元锡.皇明书[M].卷7,明万历刻本.
[32] 傅梅.嵩书[M].卷4,明万历刻本.
[33] 费宏.费文宪公摘稿[M].卷6,明嘉靖刻本.
[34] 明穆宗实录[Z].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21,隆庆二年六月已丑条.
[35] 明世宗实录[Z].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435、卷432,嘉靖三十五年五月丙寅条、嘉靖三十五年二月甲午条.
[36] 王圻. 续文献通考[Z]. 卷41,明万历三十年(1602)松江府刻本.
[37] 毕自严.度支奏议[M].新饷司卷21、山西司卷1,明崇祯刻本.
[38] 吴欣.村落与宗族: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宗族社会研究[J].文史哲,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