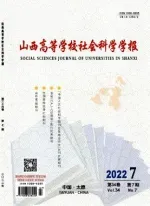论张爱玲《半生缘》的多重悲剧意蕴
胡伟栋
(太原理工大学 政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半生缘》是现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以其长篇小说《十八春》为基础改写的。作品在向人们讲述爱情婚姻悲剧的同时,还深刻地揭示了旧时代女性的悲剧以及人性的悲剧。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而毁灭的价值越大,带给读者的痛感则越强,越能达到悲剧效果。《半生缘》就是以其深刻的多重悲剧意蕴,打动了世人的心,让无数人柔肠百转,哀戚不已。
一、爱情婚姻的悲剧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中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2]93-94《半生缘》就是如此,整篇故事没有太多曲折起伏的情节,只写了几对平凡小儿女的爱情婚姻悲剧。与她的其他作品诸如《心经》里的父女之恋,《封锁》里虚拟的爱情,《倾城之恋》里白流苏、范柳原相互利用的爱情相比,《半生缘》少见地描写了一种至真至纯的爱情,把俗世普通人的爱恨悲喜阐释得淋漓尽致。
故事发生在20 世纪30 年代的旧上海。
平民家庭出身的顾曼桢,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职业新女性。她与来上海求学、工作的南京富家子弟沈世钧在同一个工厂上班。二人因志趣相投、性情相近;又因家庭都有着难言之隐,使得二人惺惺相惜,两情相悦。本应是长相厮守的有情人,却因为各自家庭成员的自私和阻挠,再加上双方的误会,终究是缘尽半生。14 年后重逢只能感叹一句“我们回不去了”[3]341,然后各自转身,行走在不同的人生路上,生离等同于死别。
翠芝和叔惠虽然没有曼桢与世钧那样轰轰烈烈的爱情,但也是相互倾慕,最有知己之感。翠芝与世钧从小一起长大,但是他们并没有产生爱情,只是家长们的一厢情愿。她遇到开朗热情、明快直率的叔惠后心生好感,但叔惠家世一般,翠芝母亲从旁阻拦,叔惠也在爱情面前望而却步,只落得一个远走异国,一个嫁与他人。多年后两人再见面,虽情丝难解,但已经于事无补,翠芝只能在潸然泪雨中感受到一丝凄凉的慰藉。
世钧与翠芝最终结婚,二人育有一双儿女,这个家庭看似温馨、惹人羡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可以通过书中的几个细节还原真相。因为要见到多年未曾谋面的叔惠,翠芝几乎无法自持,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亢奋起来,亲自收拾家务,料理酒菜,但世钧却浑然不觉她的变化。翠芝发现世钧在读曼桢当年写的情书后,也不过随意打趣几句,随即置之脑后。其实这两个人从来都不曾真正在意过对方,他们十几年夫妻却同床异梦。这场婚姻悲剧,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是俗世很多人的婚姻模式。
曼璐与豫瑾两小无猜,但曼璐因父亲去世,为一家老小的生计被迫沦落风尘,以至于年纪一天天大了,只好嫁给了鄙俗低劣的暴发户祝鸿才。曼璐又因失去了生育能力,为了保全自己的婚姻,与祝鸿才一起合谋诱奸了善良纯真的妹妹曼桢。曼璐毁灭了妹妹的幸福,自己也没有得到爱,最终在病痛与悔恨中死去。她把幸福寄托在祝鸿才这样一个人品低劣的小人身上,无疑是饮鸩止渴。
曼桢与祝鸿才,这是最不应该在一起的两个人却走在了一起。错位的婚姻,更加深化了故事的悲剧色彩,让人哀叹命运的诡谲。曼桢抱着赴死的决心嫁给祝鸿才,其悲无需赘述;而祝鸿才为了得到曼桢费尽心机,得到后却觉得她像一碗素虾仁般索然无味。他根本不懂爱,却也在这场婚姻中遭受了巨大的苦闷与压抑。他恶劣的行径,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很多人的悲剧,其中也包括他自己,这一点或许他始终没有意识到。
《半生缘》用一种洗尽铅华、冷静苍凉的笔调将人世的爱情婚姻还原得如此透彻明白。这一群俗世的小儿女,相爱的不能相守,相守的却不相爱,最终都回不去了,这是一场情感与命运较量的悲剧,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二、女性命运的悲剧
《半生缘》展现爱情婚姻不幸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还深刻揭示了在以父权为中心的时代,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无力把握的现实。张爱玲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女性在旧时代生存的艰难。“女人所处的环境,所受压力,有旧家族内的冷漠眼光,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4]515
曼璐的悲剧,揭示了女性在男权制社会夹缝中生存的艰难。曼桢给世钧叙说家事的时候说过曼璐其实是很忠厚的。一个原本善良忠厚的人,本身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为了自保,扭曲了纯真的本性,成了男权社会的帮凶。她对祝鸿才所犯的罪行极力掩饰淡化。曼璐道:“二妹,这不是赌气的事……他对你倒是一片真心……只要你肯原谅他,他以后总要好好的补报你,反正他对你决不会变心的。”[3]211“二妹,你难道因为一个人酒后无德做错了事情,就恨他一辈子,你看在这孩子的份上,就原谅了他吧。”[3]250她的这些游说表面看合情合理,是为了平复曼桢的创伤,可实际上蕴含着男权制下女性深沉的悲哀,她已经被封建男权制同化,甘愿与之同流合污,这正是她的悲剧。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诸如曹七巧、曼璐、许小寒都是病态的女性形象,但是曼桢是作者不多见的一个以赞赏而同情的笔墨倾心塑造的正面形象。曼桢为了一家大小的生计,每天辛苦地兼职好几份工作,却坚毅乐观,富有兴致。她天真地以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会使得家庭经济状况改善,进而与世钧建立幸福的家庭;但她不清白的家世,像沉重的枷锁一样带在她身上。她终究逃不脱世钧父亲这样的封建卫道士的质疑与诋毁:“就算她现在是个女职员吧,从前也还不知干过什么——这种人家出身的人,除非长得真丑,长大了总是吃这碗饭的。”[3]178世钧父亲实乃伪君子,自己本身无视道德,出入风月场所,却要求女性绝对清白,沾染不得一丝不洁。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即使没有曼璐和祝鸿才的计谋,曼桢和世钧要结合也难上加难。这再次证明,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宗法社会里,女性不能主宰自身的命运,要获得幸福几无可能。而曼桢最终因为原始母爱的迸发,嫁给祝鸿才,更说明了当女性在被动扮演母亲这一角色时,面临两难的抉择,无论作何种选择,都是一种悲剧。张爱玲把这个无法回答的命题抛给读者,正体现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考。
翠芝这个任性骄纵的大小姐,在面对与叔惠的爱情时,屈从于封建家长的门第观念,毫无反抗之力,只能是泪痕狼藉地送走叔惠,这一细节的描写展现了封建家庭中女性的悲哀与困境。新婚之夜,她哭着问世钧:“……你说是不是来不及了?”[3]243恩格斯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5]从这个意义上说,翠芝因为封建的门第观念而不能自主爱情,造成无爱的婚姻,在体面却平庸的生活中打发着时光,如书中所说:“在一个少奶奶的生活里,比在水果里吃出一条肉虫来更惊险的事情是没有的了。”[3]314门第观念无疑是女性命运的悲剧原因之一。
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谈到张爱玲所塑造的这三个女性时说:“她写得出色的地方依然是那些被社会所践踏(顾曼璐),被命运所捉弄(顾曼桢),被家庭所陷没(石翠芝)的女性。”[6]这样的概括,颇为恰当。
《半生缘》女性的命运悲剧还体现在封建礼教下旧式家庭中的女性身上。比如,世钧家庭中的女性。他的母亲和他父亲的姨太太,为了争夺丈夫之爱,多年来苦苦斗气。世钧的母亲得不到丈夫的爱,但却心甘情愿地为丈夫打理皮货店,只希望丈夫在年下回来祭祖,维持一家的体面;甚至为了把丈夫留在身边,苦苦相逼儿子辞职回家,明知道丈夫回来也不意味着破镜重圆,但这对于她来说也是一种满足。而姨太太极尽温柔之能事,用尽手段,但丈夫最终觉得小公馆无人可靠,弃她而去。一个女人把一生押在一个男人身上,却终究敌不过封建的嫡庶观念,无疑是可悲可怜的。还有世钧的大嫂,寡居的生活凄凉无比,只好做出些三姑六婆的事情,在家庭里搬弄是非来排解寂寞。
三、人性的悲剧
张爱玲很欣赏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剖析。她在台湾作家水晶对她的访谈中提到鲁迅,认为鲁迅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等到鲁迅一死这种暴露突告中断,很是可惜。这种看法有些偏颇,但也说明中国大多数作家缺乏直面人性深处的勇气。现代文学研究者王富仁谈到张爱玲时说:“她是女性小说中的鲁迅。”[7]的确如此,张爱玲最敢于也善于“深入人性的深处,挑开那层核壳,露出人的脆弱黯淡”[4]514。
曼桢与世钧的爱情悲剧,除了外力的破坏之外,也与世钧的性格弱点有关。曼桢被囚禁后,曼璐仅是靠一些很不高明的伎俩就骗过了世钧,使得他轻信曼桢辜负了自己。源自患难相依与志趣相投的爱情本应是弥足珍贵,但他却不相信曼桢对爱情忠贞不渝。一对相爱很深的恋人,突然间有一个离奇失踪,另一方却轻信别人说的曼桢回老家与豫瑾结婚的话,就草草放弃了这段情缘。正如曼桢说他:“有时候不能不拿点勇气出来。”[3]185但他连找到曼桢老家弄清事情真相的勇气都没有,他的不敢直面困境的懦弱、优柔寡断,还有对婚姻的草率,都使人语噎。
曼桢的不幸也与她性格的自暴自弃有很大关系。被姐姐幽禁期间,她苦苦想要挣脱,后来在医院产子时,靠着金芳夫妇的帮助逃走,但最终又选择嫁给祝鸿才,让人觉得痛心而不可思议。因为她毕竟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个新女性,完全有能力、有意志走出这段不幸,决然转身,去追求新的生活。但她这一选择并不明智,说到底,其中所蕴含的母爱牺牲精神让人感觉到一种壮士赴死的悲壮,但母爱绝不是应该对命运妥协的借口。
翠芝与叔惠在爱情面前也暴露了性格的弱点,都缺乏追求幸福与把握命运的勇气。翠芝一味地向封建家庭妥协,对婚姻的盲目、不清醒,叔惠的自卑感等都影响了他们的爱情与命运。
《半生缘》对人性的揭露还体现在人间亲情的沦落。除姐妹情谊的丧失之外,还描写了母爱的缺失。母爱是人间最圣洁、崇高、无私的爱,但是张爱玲却使母亲走下神坛,她笔下的顾太太母爱的丧失,使人痛彻心扉。曼桢被囚禁后,她在已经察觉曼桢处于危险境地的情况下犹疑怯懦,拿到曼璐给的一大笔钱后放弃了对曼桢的施救。贪婪和私欲打败了神圣的母爱,母爱到最后抵不过一叠八成新的温软的票子。
还有诸如祝鸿才的残忍可恶,曼璐心理的变态扭曲,世钧父亲的虚伪冷漠、母亲的偏狭保守,都使得我们看到了人性的阴暗丑恶。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2]3。这些恐怖的虱子,就好比阴暗丑恶的人性,聚合成一种巨大的力量,推动着悲剧的发生。
悲剧美是一种感伤的美。《半生缘》包蕴的由社会时代、人生命运、人性阴暗丑恶等造成的多重悲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警醒我们认真审视爱情婚姻,更多地关照人生,对命运进行思索、质疑和探寻。这也正是作品得以永恒的魅力所在。
[1]鲁 迅.坟[M]//鲁迅自编文集. 北京:北京未名社初版,1927:203.
[2]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张爱玲全集06.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3]张爱玲.半生缘[M]//张爱玲全集04.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4]钱理群.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78 -79.
[6]杨 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62.
[7]王富仁.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J]. 鲁迅研究月刊,199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