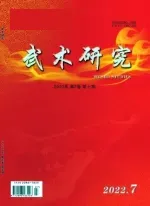民族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关系的研究——以武术为例
赵鑫 李斌
(成都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民族体育是“中华民族在日常社会生活实践中经验的沉淀和整个民族智慧与创造力的积累。”[1]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起源、繁荣与发展一脉相承的,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武术作为中国民族体育中发展势头较好的一项运动,现已走向全球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越来越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作为民族体育的代表,其起源、传承和发展每个历史阶段都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和内涵。如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地域性、多样性、民族性、传承性的特性,以及“儒家思想”、“天人合一”、“阴阳学说”的传统文化内涵,这些特性和内涵在武术里都可以寻找到。可以说,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载体。由此说明了武术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传承等一切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且不可分割的。
1 国内学者对民族体育、传统文化概念的阐释
1.1 对民族体育概念的阐释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民族体育概念还没有确切的界定,可谓是众说纷纭。其中,涂传飞认为:“民族体育是为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所有民众所共同拥有和享用并对其产生民族认同意识的一种特殊的传统体育文化。”[2]从密林认为:“民族体育应该理解为世界各民族的体育,包括中华民族体育和外来体育,中华民族体育又包括我国现有56个民族的体育和已经消亡民族的体育。”[3]等。从众多学者们给出的定义中,笔者根据自己的视角,对民族体育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民族体育是属于某个或某些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传统文化成果,其伴随着这些民族传统文化共同发展着,是这些民族内部的精神文明寄托,也是这些民族精神文化的有形载体,在一个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1.2 对传统文化概念的阐释
想要理解“传统文化”这个概念,首先,要了解“文化”一词的含义,对此,国内学者们各抒己见。如陈振勇在《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研究热点问题分析与展望》一文中提到:“文化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意义系统(罗红光,2013)。”[4]陈华文在《文化学概论新编》(第二版)一书中提到:“所谓文化,就是人类在存在过程中为了维护人类有序的生存和持续的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有形无形的成果。”[5]。其次,还要区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对此有过系统的解释。如,陈振勇在《中国武术传统在现代发展的文化思考》一文中就提到:“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母体。传统文化是文化传统不断增长的谱系”[6]等观点。
而对于“传统文化”概念的解释,目前,国内学者解释,陈华文在《文化学概论新编》(第二版)一书中提到:“传统文化是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的,指过去的一切文化现象。”[7]张岱年在《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一书中提到:“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8]等等。而笔者对于传统文化概念的理解是在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内部所形成的,且不断传承下来流传至今的民族文化,在其民族或国家内部具有高度的群体认同意识。
2 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对武术的影响
中国武术首先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基础的,同时也是中国武术保持其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关键所在。而组成传统文化的特性有很多,其中,包括文化的地域性、多样性、民族性和传承性四个方面。
2.1 中国传统文化地域性和多样性对武术的影响——门派、拳种众多
在中国有句俗语:“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而中国就是一个地缘广阔,地理环境错综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中,会造就不同的人文性格,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而多种文化汇聚在一起,经过融合、吸收和创新,文化的发展就夹杂着多样性的色彩。这就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地域性。而武术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熏陶下特有的产物,因此,武术的传统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如在传统武术门派分类中,就有按地理位置进行分类的方法。譬如武当派、峨眉派、少林派等。武术的地域性划分必然导致武术文化的多样性,地域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
在中国地理位置、气候环境不同的地区,都有着不同的民族体育项目。武术作为民族体育项目中的一项,也必然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性。中国有句俗语:“南人善舟,北人善骑”,同样,在武术当中,也有:“南拳北腿”一说,其风格迥异,特点鲜明。这些正是由于地理环境位置的不同所形成的。“南拳北腿”说法的形成,是由于南方大部分地区处于亚热带地区,居住南方的人,身材普遍比较矮小,用腿与人对抗不占优势,所以,南方人善于用拳与人对抗;而北方人则相反,身材普遍魁梧,善于用腿法与人对抗。其中,南拳的代表有咏春拳、洪拳、蔡李佛拳等。北腿的代表主要是戳脚。这充分说明了,武术作为民族体育项目,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多样性。
2.2 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性对武术的影响——中国的名片
武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环境下特有的产物,武术的民族性表现为中国文化对它的深刻影响上。武术运用《周易》等思想来阐释内外合一的技法原理,积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文化积淀,不仅影响着武术理念的发展,还涉及到武术的运动特征和功能的发展,成为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9]
邱丕相曾在《“温总理,你会武术吗?”引发的思考》一文中,这样写道:“2004年3月14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收到一封来自美国堪萨斯州托尼科市30多名中学生写给他的信,在信中美国中学生向他提了54个问题,其中,“温总理,你会不会武术?”[10]虽然,这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有时误读也不完全是坏事,这件事情恰好能说明武术正显示出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国际名片,已经起到了很好的效应。武术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特有的产物,已彰出显著的民族特性。
2.3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性对武术的影响——传承机制多样性
民族体育有着悠久的文化发展历史,其精髓就在于其鲜明的民族文化的传承性。有人说:“打开民族体育的名册,就如同打开了一部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11]当然,中国民族文化是需要保护,但是更需要传承。所谓文化传承性,是指一个国家从时间纵向上来讲,文化的一种继承与传递。而在武术中,“师徒传承制度”是最能表现出武术文化的传承性,师徒传承是指:“师与徒双方聚合在一起,按照一定的规范要求和权利义务,以传习武术技艺为纽带而组成的一种社会活动方式。”[12]虽然如今这种民间拜师学艺的师徒制已有所改变,但是,其实质性的内涵依然没有蜕变。
如今,武术有了更多的传承方式,如在全国各地出现的武术培训班,以及在全国各大体育院校设置了武术专业,并且制定相关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案。特别是高等体育院校则是标准化的传承教育模式。这些措施都对武术本身和所蕴含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措施。武术从起源、发展到演变的整个过程都深深被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着,无不体现出武术的文化传承性。
3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对武术的影响
民族体育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深受各个领域文化的影响,这些具有民族优秀品质的内在文化素养,都集中反映在濡家思想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天人合一思想、阴阳学说等在诠释其内在的独特的文化价值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民族体育。而武术就是其中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典型代表。
3.1 “儒家思想”对武术的影响——倡导尚武崇德的优良传统
众所周知,在中国,儒家思想已经延续两千多年,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作为民族体育文化中的武术,更是融合进儒家思想当中;武术中强调“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并在训练中提出了习武与修身养性的统一,且要求习武者要尊师重道,这些都体现了儒家的思想。
武术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道德体系—“武德”。诸如:“‘缺德者不或与之学,丧理者不或教之武。’‘拳以德立,德为艺先。’‘以德为先,技道两进。’”[13]又如武术中,“讲究正宗嫡传和遵循一定的道德价值规范,以健康长寿为目的,强调精神情感,讲究养神、养性、养德。”[14]等说法,虽然说法不尽相同,但在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有多少门派和拳种的存在,所有门派都潜移默化受到儒学的影响,都把“武德”作为习练武术的先决条件。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对武术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3.2 “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对武术的影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法则
“天人合一”思想是道家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协调的辩证统一性,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武术中,古人强调“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要求内外合一、身心兼修的习练原则。特别是在武术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如太极拳,要求“以意行气,以气催力”、“动静结合、刚柔相济”;形意拳讲究“内三合,外三合”。在习练传统武术时,古人是非常讲究借助自然环境对机体的影响来提高锻炼效果,如按不同季节、时辰练习不同的功法,都是天人合一、主观顺应客观在练功方法上的体现。此外,在武术套路中,还有许多象形拳,就是模仿一些动物的外形、体态、攻防等动作进行创编的拳种,譬如,猴拳、鹤拳、螳螂拳等。在习武过程中形成的“形神兼备观念的形成,促进了习武活动中内外兼修的出现。内外,就像形和神一样,要相互依存,传统武术在具体实践中提出了‘由身至心,由外至内’的训练观。”[15]纵观以上叙述,无不深刻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3.3 “阴阳学说”对武术的影响——造就武术特有的练习技法
“阴阳学说”自古以来就是被武术家们当做拳理的哲学依据。这在太极拳中表现最为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慢”和“静”相当于“阴”,而“快”和“动”则相当于“阳”;而太极拳练习就讲究“动静结合、刚柔相济、快慢相间”等技法要求。如“快慢相间”的练习原理,关于“快”,是在练习动作时,遇到蓄劲发力处时,需要瞬间发力,发力过后,即刻转为慢;关于“慢”,记得陈振勇教授说过:“太极拳慢练的原因,在达到一定境界后,慢练是为了寻找身体在不同空间位置的感觉,练习身体控制肌肉的高度敏感性,也是为了寻找身体在不同空间位置的精确定位。”太极拳讲究柔和缓慢的练习方式,这与“快慢相间”的运动特征不谋而合,也正是贯彻阴阳之理的具体表现。
4 结语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特有产物——武术;其融合并吸收了儒家、道家、佛家的文化精髓,可以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这使得武术在体现其独特魅力的同时,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属性。武术作为民族体育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我们回顾武术近些年的发展历程,可谓是步履蹒跚;在一味迎合西方体育观念的基础上,有了现在的竞技武术套路,其已经忽视了武术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这不仅不能使武术更好地走上世界,反而造成了“西方不认可,中国人不接受”的尴尬局面。
在如今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不断博弈中,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在坚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再进行文化传统的改革与创新,始终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化之路。
[1]钱介庵.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关系[J].搏击·武术科学,2013(04):98-100.
[2]涂传飞.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概念再探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9(11):27-33.
[3]从密林.民间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概念辨正[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14(01):3-5.
[4]陈振勇. 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研究热点问题分析与展望[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01):20-24.
[5][7]陈华文.文化学概论新编(第二版)[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1-21,263-281.
[6]陈振勇.中国武术传统在现代发展的文化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04):17-21.
[8]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0.
[9]李成银,宋爱真,于红梅,等.武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J].山东休育学院学报,1996(02):67-71.
[10]邱丕相.“温总理,你会武术吗?”引发的思考[J].搏击·武术科学,2004(02):1-2.
[11]朱 凯.第九届民运会落幕——民族体育活力四射[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9-19(第001版).
[12]王岗,刘帅兵.中国武术师徒传承与学院教育的差异性比较[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04):55-61.
[13]黄莉.中华武术与儒家文化[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1(03):22-24.
[14]胡永南,姚军波.民族传统体育的人文内涵及其伦理教育功能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08):1023-1025.
[15]王海鸥,闫 民. 哲学视角下武术传统与现代传承的反思[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3(03):219-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