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玫瑰霜柏,及其他
李万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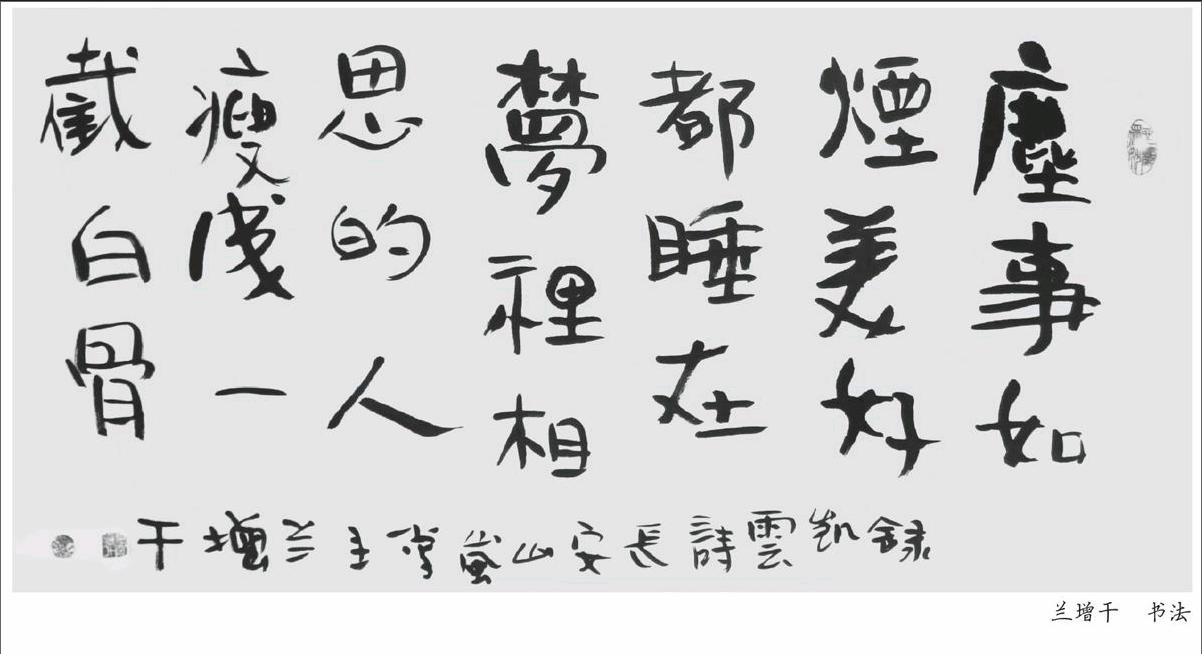
霜柏
如果花花草草的世界只有黑白二色,李渔也会拈它们来当棋子琢磨,但是李渔又将花草分成三六九等,后宫佳丽一般,还是让我不舒服。我在植物稀缺的高原见到一丛猪耳朵草都要发一阵呆,哪里还有挑三拣四的毛病。如果李渔写大漠写风雪写寒山瘦水也那般挑挑拣拣,我便相信他挑剔因为他是处女座,然而不是。李渔写松柏,又有点倚老卖老的可爱,说松柏与梅贵老而贱幼,而自己恰也到了与松柏同入画的年龄。
杜甫写《古柏行》便与李渔不同。李渔闲人说闲事,杜甫却是心有不平,说“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又说“苦心岂免容蝼蚁,香叶终经宿鸾凤”。我搁了书,看一眼屋外远山,茫无涯际的想:如果要我做一株柏树,我还是不要入画,也不要大才有大用,常年栖鸾凤,我只要在深山中寂静就行。
去年七月的小镇街头,有人运来三棵侧柏,揭去水泥地坪,掘三个大坑将树栽下去。侧柏树身高挺,看着也是长了几十年的老树,只是姿态恭顺,少些肆意,一看便是圃里的树木。柏树要长在深山岩间经些风雨挣扎才会有遒劲的苍老,所谓霜柏。以前我生活在山里,云杉黑青,黑桦木质纠结,红桦衣衫褴褛的事情常见到,柏树也见得多,知道柏树的叶子不会轻易变黄,也不会轻易凋落。柏树是最能保持青春的树木,也是最能体现老态的树木。那三棵移来的柏树被三脚架支撑着,树身吊着笨拙的输液袋。我自然不知道那输液袋中的液体是营养液是药还是植物调控液,因为第一次见到,便好奇。早出晚归的经过,扭着脖子看。有时看着那些输液袋就多情地想,这世上心思柔软的人还是居多。只是那柏树渐渐显出些萎黄来,这不同于苍老,我便知道它们要死了。但是树木死在街头多少是件不光彩的事,后来那三棵柏树就失去踪迹。
我见过死在山林中的柏树。那也只是采药人或者牧人到达的深山老林,青色岩石裸露嵯峨,悬崖深渊,云横在远处山腰,即便是七月,雪莲也只将革质的叶子探出冰缝,秃鹫常在半山坡滑翔,野猫壮如藏狐。那是通体枯黄的柏树,叶、枝干、球果,枝上的纵裂深如刀割。它将根探进岩缝间,身体贴着岩石向上傲立。它死去多少年无人知晓,但它的死去如同它依旧活着:枝叶密集,水分似乎依旧在枝叶间流淌,尽管身体焦枯。
柏树原是性子极高的树,受不得人的浊气。那时山下院子里一棵柏树长了几十年,我们从不曾将洗脸洗菜的水泼到树底下去,也不曾折取枝叶,尽管初一十五的早晨常常要熏香。在山里,熏香已经成为一种仪式,用柏枝燃烧出的烟来洁净自身,也用来洁净神灵。神灵似乎总是存在,那怕门前一个土坡,房后一处水洼,人们因此不会轻易在大地上挖掘。那一棵柏树里住着麻雀,叽叽喳喳的不知道有多少。青白的麻雀屎一层层盖在树下,有几次我拣公雀屎和蜂蜜擦脸,因为听说那样可以让肌肤变白,但公雀屎糊在脸上,黏糊糊的,不好受,因此脸就没能白起来。
柏枝煎水喝是要上瘾的。山居时隔壁的女子性格乖戾,守着大片山野还说要去云游,常年穿一件深蓝的褂子。我有时逢着她,总是不敢面对,觉得她身上那股冰冷的气息来自冥界。那时她似乎总在林中游荡,我曾多次见她站在柏树下摘球果吃,有时好奇,我们便也跑到远处摘球果尝。那些带有柏香的灰绿色小果子,只有豌豆大,然而里边的苦涩那么多。女子熏香熏上瘾,家里柏香缭绕不断,后来拿柏枝煎水喝,每天晨起第一件事便是将柏枝熬出水来喝,晚间睡前也要喝,家人试图阻止,又阻止不了。我离开山林后,听说女子的情形越加严重,开始拒绝食物,只喝柏枝水。再后来就失去消息。
失去消息是件简单的事情,犹如一片叶落,或是一季草黄。我们一路的时光,寂静亦或鼓噪,最终不过是个过程。这个过程漫长或者一瞬,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总要失去。
玫瑰花开
安徒生讲故事总是那么信马由缰:“我必须总是开花,总是开玫瑰花。花瓣落了,被风吹走!不过我却看见一位家庭主妇把一朵玫瑰花夹在赞美诗集里,我的另一朵玫瑰花被插在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的胸前,还有一朵被一个幸福地欢笑着的小孩子吻了一下。这些都叫我很高兴,这是真正的幸福。”王尔德不一样,王尔德的玫瑰只有在月色里用歌声才能使她诞生,只有用生命对她浸染,她的花心才能变红。王尔德的玫瑰带短刺,我有些怕。
高原上,小街人家的院子里种植的多是月季,刺玫也多。月季丛开,刺玫成树。树到底有气势,尤其一番风雨后,刺玫花飘坠,深红匝地。月季色彩多变,且艳丽,刺玫花暗旧,多少跟玫瑰相似。说玫瑰、月季、蔷薇是蔷薇科三杰,但高原人家的院子里就是不见玫瑰,也没有蔷薇,让人多少有点想不通。这是否与高原气候寒凉,氧气稀薄有关,去网上查,说蔷薇也耐寒,是大范围种植的花,既然可以大范围种植,此处独不见,于是更加想不通。相比花跟人不一样,人多浪迹,易于混同,花多少带了些喜鹊一样的墨守成规。你看喜鹊,它从来不换衣服,破屋子永远是枯枝搭几根羽毛。
但是花又跟鸟雀不一样。鸟雀是越来越少,花不断改良,研发,突变厉害,纯种的玫瑰大约也是越来越少。曾记得开在大山深处的玫瑰,那是弱小的一株。山里气温,总是十几度左右,便是夏季风沿着河谷拂来,草约的芬芳透着清冽。山体高大嵯峨,山顶积雪常年覆盖,这使得花开异常艰难,晚开不说,绽放的时日也被天气左右。譬如晨间一些虞美人和野罂粟刚刚撑破花萼,午间便是一场冰雹。冰雹砸折植物的茎干是常事,青稞因此倒伏不起也不足怪。一株玫瑰在院子里,奇怪的是它的四周再无其他植物。几近荒蛮的院子。玫瑰在一个早晨突然开放。要知道那个早晨阳光刚好洒到西墙上,黄土夯筑的院墙搭上刚好金黄的阳光,而玫瑰恰好将暗紫的小花瓣在阳光中展开来,仿佛娇小顽皮的发小。
我见得玫瑰开放,只那一次。也许后来也有纯种玫瑰偶尔开放在曾经的路旁,不过与年少时碰见玫瑰花开已不一样。少年见到的色彩,纯正单一,并且深植记忆之中。长大后总是从一种色彩中透视出另一种色彩。这其间的过程,看似波澜不惊,其实有一种艰难,也有摧毁。
山里的玫瑰凋零后,总有用处。我们将玫瑰花瓣晒干,和红糖,腌制。母亲有时用它做馅饼,有时蒸糖包。馅饼总是用油煎过,糖包可以捏出几种花型来。其实馅饼或者糖包也只是一年吃一次,毕竟玫瑰一年只开一次,每次开,也只是那么稀疏的几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