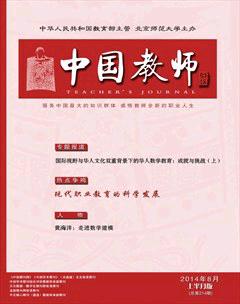作为“士”的中华教师:超越专业化
向蓓莉
彤对我说,“芒种之夜的古琴雅集源起是你”。其实只是我的一声探问,源起还在“湖上书院”,这个与中华文化源头携手、聚集了作为“士”的知识分子的教师发展之所。今年早春,我收到彤寄给我的“湖上书院”院刊,顷刻之间即爱不释手:“春”那一卷,兰交斋青瓦灰砖一袭剪影,似浓淡相宜的水墨画;“湖上书院”行楷题字典雅素朴,我在这个名字里流连忘返。湖上,历来是中华文人生命里的后花园,古今多少“士”,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亦是文人墨客游目骋怀之境,抒发个人的悠悠情思,抒发国家天下兴亡之叹。
无锡是既可享湖上之抽象情怀,又可享江南太湖蠡湖之波光。中华教育史里的书院,始自718年唐玄宗创设的丽正修书院,而其风格宗旨,可追溯至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间齐桓公创建的稷下学宫,其时其地都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源头。诸子百家汇聚于齐国临淄稷下,兼容并包,百家争鸣,不仅致力于教学与学术研究,且议论国事与“干政”,为君主问政提供治国安邦之策。更何况,无锡本就是有可传世的书院之地,“东林书院”与“湖上书院”相距仅16公里,那是北宋理学家杨时、明代思想家顾宪成先后聚众讲学之地。“东林书院”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丽泽堂,有士人议政的依庸堂,我们青少年时代就镌刻于心的那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为顾宪成所拟,镌刻于此。书院的英译名也匠心独具,不知谁最早将中华的“书院”英译为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经典学习学园),颇得西方文化之妙。Academy(学园)是与西方文化史一样漫长的学术机构。巧合的是,Academy诞生的其时其地,也是西方文化史的重要源头。公元前387年,爱琴海边的古希腊,柏拉图在雅典西北角的阿卡德摩(Academus)创立了学园,其创立时间不仅与稷下学宫相若,职能亦然,亦为授受知识、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咨询之所。
“湖上书院”其实是别称,大约相当于文人名字里的“字”,它的大名是“无锡市滨湖区教师发展中心”。奇特的是,似乎有了“湖上书院”这个跨越时空、与中华文化史源头续接的好名字,它的风格、涵义与职能立刻卓然独立,不仅着眼于教师的专业发展,更着眼于教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发展,乃至朝向作为“士”的知识分子的发展,这是院刊中教师们写就的随笔传达的讯息,我就是在这些描述中得知2013年3月30日书院首场古琴雅集的消息的。
那天,我手捧刚拿到的院刊,舍不得放下,就坐在车中一篇一篇地翻阅,遍览“春”卷后,才在余味悠长中启动车子。京城一路车水马龙,有诗词琴书萦绕于心,我百喧不侵。这“春”卷,起首居然是教师们描述与余光中先生夫妇在兰交斋品茗对谈的回忆,实在是太过“奢侈”,让我倾羡不已。《乡愁》那些诗词、散文当然是绕不过去的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片段,江苏省锡山高中的梁国祥老师则写到他那三个深刻乃至犀利的提问,其中一则是问余先生所写的《听听那冷雨》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有何关系。梁老师用“如此谨慎”评论余先生的答词,并推断“余先生跟他的老师梁实秋先生一样,是一个纯粹的文化学者,跟龙应台等公共知识分子不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自觉地跟政治保持着距离,所以他们的作品即使在表达家国情怀时,也是非常克制的,有时甚至会刻意模糊作品的时代背景”。因此,在余先生的《乡愁》中“读出那么多的政治内涵,真真是天大的误会”。梁老师感叹余先生的许多诗文美艳、深刻得让他说不出话来,同时亦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他与大师人格平等的精神、质疑的智勇,让我看到“士”“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的风度,这种平等论辩、探究学术的氛围,正闪烁着稷下学宫透过历史烟尘透射的光芒。“春”卷,古琴雅集是压轴之题。此外,文化的主题还有吟诵、摄影,教育领域有脑科学与学习理论、绘本与阅读、班集体建设,生活主题与女人节相关,谈“现代知识女性当下的生存境遇”,讲女性的内外兼修。
书院研习内容以“人”的丰富性涵括教师职业的专门化,回归到中西方对“人”的假设和期待。在这个强调专业化的时代,我们在专业化——包括教师专业化——的过程中,却往往悄然地成为专业的套中人、单面人,生命展开的空间逼仄到越来越狭小的范围,包括教师在内的任何一个职业,怎能完整地表达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全部呢?所幸人类文化漫漫长河中对一个完整的“人”的期待并非如是,我们还可以停下匆忙的脚步回观,如音乐的修养正等待一个中华式的文艺复兴。在中华,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皆有修为的人;古希腊的“七艺”理想,涵括的是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与音乐。我们当然要温故拓新,在回抱完整的“人”作为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在重新界定、修正和补充的基础上,重塑完整的“人”在当下的新阐释、新意义。“湖上书院”广博而深远的教师培训,超越了教师专业化,拓展到去实现一个个独特、完整的“人”的终生成长。“春”卷里,“半枝莲”在《又遇女人香》中讲述她和朋友互用“清平乐”与“江城子”词牌互酬唱和,我不仅看到了教师们的专业修养,也看到了生命对丰富绽放的渴望,看到了以文会友的情谊;我读到了“江南琴社”顾颖社长讲述的古琴与湖山之相通:古琴的“线状音迹”“很适于表现山林秀水之间幽深渺远的意境”;我的好友、时任育红小学校长的潘望洁在古琴曲里发现了一个“桃花源”,她期待着一个又一个的雅集,“做一个沉醉不归的幸福旅人”。一篇篇描述让我心驰神往。李祥霆先生一袭长衫即兴演奏的《唐人诗意》已伴我多年,只是我还未亲聆古琴,这种愿望,已蛰伏在内心多时了。
于是,来无锡行前,有了对“湖上书院”陈彤院长的这一声探问:能否拜访古琴社?这声探问,终由书院设计成面向公众开放的古琴雅集——“湖上论琴”。彤拟的词,如此静美——“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静夜点灯,湖上天籁。一声入耳,万事离心”。多谢顾社长、中国民族音乐博物馆潘一东馆长和诸位琴人成全,我们不仅可以听琴,还能在潘馆长与顾社长的讲解中认识琴的中华意味。
《阳关三叠》、《忆故人》、《良宵引》、《秋江夜泊》、《鸥鹭忘机》……弹奏的乐曲皆从容沉静,吟咏文人真趣、操守、友谊。琴音悠远,一唱三叹,将兰交斋的我们带至松林,琴音、清风、明月。诚如望洁所言,琴音里有桃花源,可以“悠然见南山”,第一次亲聆古琴,却仿若是重逢,唐诗、宋词、元曲的魂魄中一直有它,它的节奏、韵律,它的悠远,它余音袅袅里的幽思。古琴与古筝同为弹拨乐器,我刚开始学古筝,第一次课后,在家中练习《春江花月夜》这最简单的改编单音曲,即便在那样简单的曲调里,在跨越一个音区的低吟唱和中,那个从容悠远的中华也萦绕心间。曲罢而意犹未尽,我不由得幽幽念诵柳永的那阙《雨霖铃》,流连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的微醺,那一刻,乐音与诗词相遇相知,这就是音乐与诗词之间的通感吧。古琴的悠远从容,我在中国画欲说还休的留白中看到过,在京剧唱腔的“一唱三叹”里听到过,在“士”天人合一的“生而不有”中了悟过。登山之路不一,望巅之月相同,那是中华文化之“月”。
无论身在何处,中华文化所在之处,即是故乡。雅集讨论时分,潘院长一位挚友回顾自己1980年代留学美国期间,生活艰辛,原本偏好西洋古典音乐的他,竟蓦然发觉那些乐曲全都散发着冷色调,不忍猝听。所幸他还带着中华民乐磁带,一时之间,异国他乡地下室里琴筝笛箫的乐音听来全是暖色调,漂泊游子藉故乡之音取暖。我想,此间冷暖,哪里是乐曲自身的色调,实在是听者与音乐之间交汇的生命体验唤醒归属与否。不是唐诗、宋词、古琴里有一个故乡,它们就是故乡,我们在其间入世、出世,群居、独处,修齐治平、遗世独立,可以远隔重洋,可以物是人非,一句“床前明月光”,一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华人就置身故乡。
这个文化的故乡,道不远人,点点滴滴,浸润在日常生活里。2011年乍暖还寒的早春,彤带着望洁和我访“湖上书院”的前身,由“桐油大王”沈瑞洲先生于1937年创办的锡南中学,学校已于2003年与华庄中学合并为太湖高中。故址草衰楼危,我们在昔日学校教师宿舍昏暗的残垣断壁边找寻可下脚之地,边讨论它未来的模样,蓦的在二楼一间宿舍左侧墙壁上,发现半壁贴满了在毛边纸上写就的毛笔书法残篇(当然是繁体字),楷书“何處無明月清風”、隶书“會真趣,得天機”、行书“久經風雨心當泰,能讀詩書命亦佳”……那一刻,我们欣喜有如考古学家在故城废墟里意外发现熠熠发光的珠贝。
这次重返书院,彤和望洁告诉我,她们寻访到了珠贝的主人,太湖高中的生物教师徐广泊,业余时间写毛笔字是这位生物教师的爱好。毛笔是中华文化中最古老的文化器具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依稀留有它的笔迹,东周竹简、木简上的文字已广泛用它来书写,湖北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中便有春秋时期的毛笔。毛笔及其书写的汉字,就这样绵延两千余年,一代一代,活在华人的日常生活里。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果然不是遗迹,是拥有不同国籍、身处不同地域的华人共同的日常生活。
文化,包括古琴里的文化,亦在华人的日常语言中。潘馆长讲述孔子不仅善鼓琴,而且善作曲,创作了多首琴曲。有意思的是,但凡华人都免不了多少以万世师表的孔夫子自况,三十岁生日那天免不了要反思自己是否“立”,四十岁那天要自问是否已然“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既然孔子也是古琴演奏和作曲家,那么,华人也免不了以音乐家自况罢?
古琴甚至不是“士”的专利,它还属于山野村夫。我出生于子期的家乡,当年伯牙鼓琴,一曲志在《高山》,樵夫子期在乐音里看到“峨峨兮若泰山”;一曲志在《流水》,子期听到“洋洋兮若江河”。自此,《高山》与《流水》琴曲合一,“高山流水”也成为华人日常生活中的知音之喻。
在江南琴社古琴的悠韵里,我想,我们的文化没有断裂,它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活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阳春白雪里有它,下里巴人里也有它。书可以焚,儒可以坑,而文化已然融入华人的语言和生活,细流涓涓,代代相传。只要语言还在,文化就与我们须臾不离分;只要语言还在,文化的“离离原上草”定然“春风吹又生”,吹出文化的繁盛春天。
当然,书院能成为着眼于教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发展、作为“士”的知识分子的发展之所,不仅因为它有一个好名字,还因为在无锡有一拨为书院称其为“书院”的教育人的盛襄共举,方能吸引志趣相投的朋友们来此相会,如切如磋。书院就在这悠悠文化中,春风化雨似的管理着。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中解释,“管”似“笛”,以玉作音,神人唱和,凤凰来仪;“理”为“治玉”。清代段玉裁于《说文解字注》中解释: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段注将“理”与“情”并举——“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书院在管理中应探索平衡“情”之仁慈与“理”之正义的中庸之道,由“管”及“理”,在“情”、“理”并举之间,“璞玉”遂成“美玉”,人变成潜能可以得到充分实现的人,即“仁者人也”之人。
清代文人张潮尝于《幽梦影》道:“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独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以渊明为知己……一与之定,千秋不移。”“湖上书院”有这许多“士”为知己,可以不恨。
一与之定,千秋不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孙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