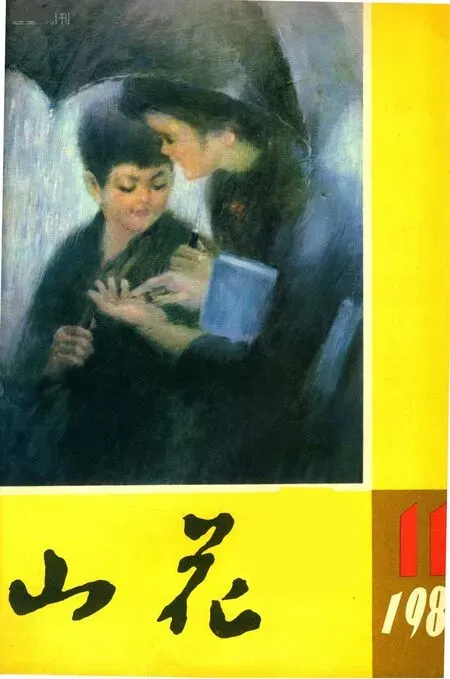消失在雨中
那件事发生时,徐州在加班,单位的工作像小山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按理说,这些并不是他的活儿,但领导安排下来了,他又不好推辞,更何况这都是部门的工作,人手少,他又年轻,不多做一点又怎么办呢?
每次妈妈打电话来,他都说在加班。加班,加班,怎么老是在加班呢?妈妈很不解。他又懒得解释,只好说,加班和在家里都是一样的,总是要对着电脑,也不干什么体力活。其实这怎么不算体力活儿?腰酸背痛、眼睛发暗、头脑发昏,腰上、肚子上的赘肉都渐渐地占领了青春年少的肌体,才三十岁爬几层楼梯都喘得不行,免疫力越来越低,而又懒于运动,下班回来,直想填饱肚子倒头就睡。坐办公室,说得好听,不过是花固定的钱买断了你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罢了,又没有奖金,又没有加班费,忙季一来,简直是随时待命,什么时候有活什么时候就得到办公室去干,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回家。
幸好妻子林萍也是理解的,她也经常加班,彼此也能体味其中的辛酸与不易,倒也不会说些什么。而且,他们目前也没有孩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责任要担负,也没有什么必须的精力要付出。
这个星期一直下着雨,清明快到了,雨绵绵不断地落,整个城市又潮湿又伤感。本来是不需要加班的,但上面临时来了文件,说上头的领导要来检查工作,随机抽中了徐州所在的单位,于是所有相关无关的人员都加起了班。
春天无处不在,这个城市多雨。但从周三开始,雨渐渐有加大的趋势,间或停一会儿,又开始下,并且比之前的大一点。雨在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式变大。到了周五,整个世界都好像浸泡在雨中了,之前被雨水洗过的鲜绿的树叶,如今是一片昏暗,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出太阳了,本来徐州打算周末若是晴天就和林萍一块到乡下去,油菜花此刻正是好时节。可是这雨,哎。
窗外马路上行人稀少,天早就黑了。徐州快下班的时候已经告诉林萍今晚要加班,不知多久才能回去,电话打去才知道,林萍也在加班。“我应该比你回去的早,我把手头上的这点儿活忙完,就可以了,这样也可以过个好周末。”林萍匆匆忙忙地说,“周末下雨,我要在家好好睡个懒觉。”
徐州不禁笑了:“好好睡个懒觉?算了吧,典型的周末睡不着上班睡不醒,还想睡懒觉?”
“哎哟,你怎么乌鸦嘴!现在下雨了啊,下雨天,睡觉天。肯定可以的!好啦好啦我不跟你说了,半个小时我差不多就搞好了。到家给你打电话!”
等徐州忙完手头的工作时,已经十一点过了,他伸个懒腰,万分庆幸地想明天我也可以睡个懒觉了。
一晚上很安静,他才意识到自己没有接到林萍的电话:也许是忘了吧。他拨过去,一个不带任何感情的普通话女声传过来: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信号又不好,联通总是这样。徐州收拾东西回家去。家离得不远,平时他都走路上下班,不过这几天加班晚,又下雨,他都搭同事的便车,顺路就把他丢在小区门口。
街上的水很多,在夜晚的灯光下,一路看过去,像一条波光粼粼的河。
“大街上都可以游泳了!”同事打趣说。
“可不,去年下大雨,天津人民可真逗!”
到了家,黑漆漆的,以往,林萍回来得早都会在客厅留一盏小灯给他,尽管他们租住的房子小得说客厅基本上没什么意义。他们买的房子还在建,明年才能交房。如今只好挤在狭小的出租房内。一室一厅,在离两人单位都不远的小区里,已经很难再租到价钱合适的好房子了。
尽管小了点儿,两个人把房子收拾得还算齐整。他爱看书,文史哲都涉猎,家里新的旧的大的小的书堆得到处都是,小客厅里放着他们从旧货市场买回的货架,货架靠着一面墙,上面摆满了书。只在靠窗户的地方搁了一张旧书桌,人在家的时候,旧书桌上的那盏台灯几乎不分昼夜地亮着——房子里太暗了。简陋的书架上、阳台上,到处都是林萍种的花花草草。什么肉质铁树、天竺葵、绿萝、铜钱草……杂七杂八的。一开始徐州嫌乱,又觉得碍事,每次找书都要一盆一盆地挪来挪去,很不方便,后来绿色渐浓,有花的也毫不吝啬地开放,徐州倒觉得当初对它们不满有些亏欠似的,看书累了,也给它们浇浇水。
一个小屋子,渐渐地有了家的样子。
林萍不在家。打手机又是不在服务区。按理说,她应该早就到了。
他打电话到办公室,也没人接。深更半夜,他有些担心又给林萍同办公室的小刘打电话,小刘用迷迷糊糊地声音告诉他:林萍不到七点就出门回家了!
他心里一激灵:这下糟糕!一切不好的想象都到了眼前。她出了什么事?被打劫?被车撞?他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大雨中掉进下水道的人,啊,多么可怕!他再也不敢想,但是他不得不想,坐在桌前,他内心竟笃定地认为她,掉进了下水道。她一个人在漆黑的管道里,水也许淹没了她,也许还没有,总之是“正在”,她一定很害怕……大雨的声音在窗外,他越来越害怕,一面胡思乱想,一面又安慰自己,不,不会的。这个喝绿茶都不会中“再来一瓶”的人,怎么会这么巧就掉进了下水道?世界上的事不会那么偶然的。而且而且,这下水道刚刚吞噬一个年轻的生命,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但是林萍,他的妻子,不见了。这是真事。
他报了警。警察让他在家等消息,又叫他再打电话问问朋友,是不是因为雨太大,到什么地方躲雨去了。他木讷地拨电话,礼貌地问人家有没有见过林萍。
夜里两点多了,他听见手机传来的一个个睡意朦胧的声音。有时,旁边传来另一个声音:这么晚了,谁呀真烦。
他停了手。四周安静,只剩下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不知道什么时候雨竟然舍得变小了。此刻的声音才像是春雨的声音:温柔而缠绵,似连绵不绝的爱意。窗台上一盆栀子花缀满了花苞,一个多星期前,这些花苞就长出来了,却一朵还没开,它们可真沉得住气。林萍说,你得给它们时间呀,这阴雨绵绵的,它们不愿意开,它们心情不好。雨一打,空气里潮湿,它们的花瓣发黄得快,就不美了!
他哈哈一笑。
此刻他站在窗前,灯光下一丛翠绿间闪着一点白,他凑过去,竟是一朵栀子花初初挣破了外面的骨朵,露出了花瓣的颜色,尽管很小,在这翠绿中却十分明显。也许明天就会开了,也许明天林萍也回来了。
他坐在桌子前,翻着手机,想着还能打电话给谁问一问林萍的下落。翻来翻去,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人。
尽管在这个城市里已经生活了五年,他们的社交关系却仍十分简单,她单位里的几个同事,大学的三两个同学,他的偶尔下午会聚集在某个书吧的书友,除此之外,其他就什么也没有了。对于这个城市而言,他们是陌生的,尽管已经准备安家落户,但他们仍是异乡人。
也许是没有自己的房子,林萍说,等有了孩子就好了,孩子会让咱们在这里扎下去。孩子会把这里当成故乡。
一说到这里,徐州就很失落,孩子将把自己的出生地当成故乡,可他们的故乡在哪里呢?那个叫布口的地方,就只能在需要填写籍贯的表格上出现了吗?小时候他填表,觉得籍贯一栏很是多余,对于一个高中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乌有市的人来说,对于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布口的乡村孩子来说,籍贯只是一个多余的词。如今他终于感受到它存在的意义。
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只几分钟,就觉得疲累,又坐到桌边坐下。她去哪儿了?也许不是什么大事,手机没电了,被偷了,也许掉在水里冲走了。但是她为什么不回家?他不是善于想象的人,他总是往不好的地方想。一边想,一边眼前似乎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她在雨中走着,哗啦一声,像那个新闻中报道的女孩一样掉进了下水道,或者连哗啦一声都没有,她连发出惊叫的时间都没有,就消失在水中了;她正在雨水中撑着伞,一边准备给自己打电话,后面的车飞驰而过,将她撞飞了;她往前走,不提防几个坏人一刀捅死了她,并抢走了她的东西……越想越觉得可怕,仿佛这样的事情交替在发生、不停在发生,而且都是他亲眼所见,渐渐地,他的眼前模糊了,泪水涌了出来。多么悲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多么悲惨。
过了好一会,他才在这种想象中止步。
坐在一盏台灯的光影里,他看见桌子上反扣着的一本书。他翻过来看,是《我的米海尔》。以色列小说。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他向来不喜欢林萍看的书,因为他看她看书的时候会傻乎乎地落泪,而因为看书而傻乎乎落泪,多么愚蠢。
他放下来,然而无事可做,又害怕胡思乱想,于是他重新拿起来,就从反扣着的那一页开始看。
“整整一个冬天,耶路撒冷的寒风都在吹动着松柏,而风离去时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你是个陌生人,米海尔。你夜里躺在我的身旁,可你却如此陌生。”
那一页这样写。他看见她在下面微微画了一道细线。
耶路撒冷的寒风。
他嘴里念出这几个字。仿佛有风吹过,屋里一阵凉意。他突然喜欢上了这个词“耶路撒冷”。世间怎么会有如此诗意的地名,怎么会有如此诗意的翻译?这几个字组合在一起有一种幽微难言的美。
他停下来,拿起手机,想看看有没有新的消息。
但是什么也没有。
这样的雨天里,除了等待,他没有了其他的事做。他翻架上的书,他翻她看过的,她留下笔迹和记号的。如果一本书被翻过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迹——连一道细线都没有,他就很失望地放下来。他似乎忘了从前自己从来不翻她的书。他不喜欢读小说。小说太假了,太晦涩了。但是他没有读过,他有时候会想自己对小说的这些印象从哪里来的,但是没有头绪。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他不看小说,尤其不喜欢她看的小说。但是这个长长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雨天里,她不见了的雨天里,他百无聊赖地看起了小说。
不得不承认,他从前的想法是错的,至少一大部分是错的。
“不要相信写小说的人,要相信故事。”他的脑海里冒出这样的一句不知是谁说的话。
可是,那些故事有什么意思?你想也想不到的事情每天都在身边活灵活现地上演,比小说丰富,比小说精彩、也比小说更荒唐。破不了的凶杀案、扯不清的偷情人,无法直视的车祸、不能理解的阴暗……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清晨起来,一个个“大道”、“小道”消息、娱乐八卦,就几乎都是一篇篇精彩纷呈、跌宕起伏又百转千回的小说。
真实的小说们已经比不上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固执地写?林萍们为什么还要固执地看?
徐州想不通。
然而这世上想不通的又何止这一件事。他有些黯然。
徐州一直觉得雨停了,林萍就会回来了,但是没有。这雨一直没有停。这些天,他坐在家里,雨像浓雾一样将他住的房子包裹,他位于包裹的正中心,一个字都没有说。
他在家里独坐。
他开始收拾房子。这阴雨天,花草们发着幽暗的绿,似乎有些忧伤。他努力回想她浇花的样子,却始终想不起来。
他又开始回想她的样子。他知道她是她。但是太可怕了!他竟然也想不起来。他不知道怎样描述她。他伸出两手在空气中比划,但是很失望,他没有比划出她的模样,甚至连轮廓都没有了。他的两只手无奈地打着手势,似乎在和对面的什么人说话:他正要告诉人家她的样子,却突然完全遗忘了她的模样。
他坐在房里,不敢想象要去翻电脑里的照片才能想起来她。但是,真的,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他实在想不起来她长什么样子,他的眼前晃动着一团烟雾一样的影子,她长长的头发散落在肩上。
他打开电脑。点开照片,可照片上的人那么陌生。陌生的人。全都是陌生的人。
这一定是梦。是梦境。他使劲叫自己睁开眼睛。眼睛是睁开的,天花板上斑驳的一块仍在头顶,栀子花有一盆骨朵儿,绽开的一朵仍在散发香气。
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徐州看着电脑中那张笑脸,十分陌生。只有那一肩长发似曾相识。他想象自己的手穿过那长长的头发,他想起一首歌,那歌词别别扭扭地说: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如此矫情却在此刻如此真实。
但是,她怎么成了陌生人?徐州觉得可怕。这些天,他嘴边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可怕。但是他一次也没让它蹦出来。仿佛他只要说出来了,就会真的发生很可怕的事情,所有他想象中可怕的事情都会变成无法更改的现实。
他开始寻找所有熟悉的线索。
房间是真实的,窗台是的,花草是的,台灯下的影子是的,桌上的书,衣柜里的衣服,到处都是真的。所有的一切都在。
唯独她不在。
雨一直不停,但徐州仿佛心无挂碍了,他笃定地认为,只要雨停了,一切都会回归正常。这雨下得如此不寻常,一定是个梦。
梦有什么好怕的呢。
他坐在书桌前,有一搭无一搭地翻着手边的书和笔记本。那些大大小小,装帧各异的笔记本被她随便地放在书桌上,或者抽屉里,他都拿出来胡乱地翻。有些很明显,是她摘抄书上小说里的话,有的标注了书名和页码,有的没有;有些是她自己随手写下的句子。她的字体不固定,有时候工工整整,有时候凌乱潦草,有时候小巧玲珑,有时候又大大方方,像男人的字。而用的笔,也是五颜六色的,整个本子就像是小孩子随便划拉的草稿纸。
翻着翻着,徐州突然发现自己并不了解她。这个和他一起生活了四五年的女人,他并不了解。他有点慌乱,但随即又镇定下来了。
怎么样才算是了解呢?你和一个人共同生活,你知道他/她的上下班时间,知道他/她今年多大,身高多少,你知道他/她一顿能吃多少……但是,这是日常生活啊,日常生活怎么描述呢?
“他不会知道我有几件衣服,他也不会知道我最近穿的鞋子是什么样的。但我知道他的。”林萍有一天的日记里写。
徐州有些羞恼,这是什么话?这也需要知道?即使不知道,在人群中,还不是一眼就认出了你!徐州真想拉她出来辩解一翻,但如果她真的要问,徐州也只会懒得理她。但是,这百无聊赖的雨夜,徐州仔细地想了想,也的确是的:我不知道她穿什么衣服,她的衣服都有什么样子,尽管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认出来,但如果要贴寻人启事,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写衣帽特征。是啊,他看过太多的寻人启事:走失时身穿蓝色毛衣,深色牛仔裤,脚穿白色运动鞋……甚至衣服的品牌、质地都说得十分清楚。
平心而论,他不能够。
想了解一个人是多么的困难,即使你处处留心,即使你从不健忘。徐州不知道谁跟他说过这样的话。
比如她喜欢的、讨厌的,想要的、不想要的。比如将来生活的样子、未来的孩子。他一直都没有和他谈论过这些,他觉得似乎没有什么必要。该来的总会到来,谈论有什么用呢?生活总会按部就班地到来,条件成熟时,自然会生孩子;生活好了,自然会有好房子。着什么急呢?
在林萍的笔记本里,有一天,她记录了如下的场景:
好没劲。本来想的对话应该如下:
老公,你的理想是什么?
啊,我的理想是……老婆你的理想呢?
然后我就可以向他表明我的理想了。可结果却是:
老公,你的理想是什么?(我那么严肃又一本正经,他倒好,爱理不理的,头也不抬,再叫一声,才说)
我没有理想。
干吗没有理想?快说一个!
挣钱呗!
好吧。
我的理想呢?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有一项也是挣钱。但是他又不问我。算了。我自己写写吧。
但是当天她并没有写。
什么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呢?他完全没有印象了。
如今,他坐在昏暗中,有足够的时间细细地想:她所说的理想是什么呢?
理想应该是不能实现的东西吧?不能实现的说了有什么意思呢?世俗的实际的生活已经叫他疲惫不堪,哪里有什么时间仔细地想那些并不能实现的东西,他只想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多挣些钱,买上房子,一家人热闹地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是不久将来的生活啊。如果将来的生活就叫理想,一步步总会实现的,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说多不如做多。
但是她的理想呢?她的理想是什么?当时在想什么,怎么不问一问?哪怕只是随口一句呢。
那么,等她回来,就问一问吧。
又一天,林萍写:今日天晴,无事。
有时,她淡淡地写“在爱情里没有受到过纵容的女人并不算真正被爱过。”却在句子的旁边打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五角星。红色的。
他内心一凛。
他有太多时间来想他们之间过去的生活。
从相恋到结婚,他自认对她不错,一心一意工作、挣钱,谋求更好的生活。逢年过节,给她的家人也打电话,该送礼时送礼,该请客时请客,并没有落下什么话柄。当然,也从来没有爱过别的女人。
但说到纵容,什么又是纵容呢?这些名词一个比一个让人费解,让他在这样的雨夜里茫茫然不知所措。
她在笔记本中还写:
“这世界上有谁以爱情的姿态爱过你?”
这一句,她没有标注,不知是引用还是有感而发。看看时间,是不久之前。
他想起有一次争吵。一点小小的事情,她气得哭起来,他觉得不可理喻。林萍在哽咽中说,不错,是你有理。我不对。
他默不作声。的确是她不对,这样的小事情有什么好吵的呢。幸好她还算明理,就此打住,很好。这件事后,两个人又重归于好。当然是重归于好,但是谁也没有向谁道歉,这有什么好道歉的?日子里谁不是磕磕绊绊过来的?第二天,还不是好好的。该上班上班,该买菜买菜,该吃饭吃饭,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徐州不觉有什么不对。别人的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再说,别人的生活怎么样,我们管得着吗?我们只负责管好自己的生活。
雨下了多长时间他不知道。好像就那么几个夜晚,又漫长得仿佛一个世纪。在这短暂里,他不断想同外界建立联系,他想找到她。而在这漫长里,他花了大多数时间来看她的笔记本和书。这个从来不愿意看小说的人,看了好几本小说,而且都是他不屑之中更不屑的爱情小说。那些小说里太多横刀夺爱的故事,但是,这世上,谁值得你为之横刀?
他摇摇头,叹息着合上一个又一个荡气回肠却漏洞百出的爱情故事。
他不想费力再去看那些。雨中的时间不如来想一想,她——他的妻子,究竟是怎么样的人。
她怕死。每次两人嬉闹,他作势要掐她的脖子,她就很紧张,大声尖叫,有时竟会掉下眼泪。
她不止一次向他说过类似的害怕。她要他捏捏后背,在他的手捏到后颈的时候,她会突然喊停:那里有个死穴!你别碰到了!
她告诉他,她躺在椅子上仰起脖子的时候,只要一闭眼睛,总觉得上面会掉下一把锋利的斧子,正好砍断自己的脖子。这样想的时候,就觉得脖子里凉飕飕的,吓得慌忙睁开眼睛立刻直起身子。
有一次地震,他出差了,她在家里吓得直哭。其实只是小小的晃了一两下,她说她的腿都软了。那天的日记,她记:不是害怕死,是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地死。没有同伴。
当然,世界灭亡她是不怕的。即使有人有船票,但那仍旧是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将一起死去。
她喜欢折腾一些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家里到处都是瓶瓶罐罐,里面装的啥,时间长了她自己都不记得。
她喜欢藏钱,在不穿的衣服口袋里装十块、二十块钱,等到再穿的时候拿出来会很惊喜。仿佛那钱是别人的似的。
她喜欢粘人,又啰嗦,一件事要反复地说几遍。
她不上进,工作不怎么认真,懒散拖拉。常常嚷着:啊,实在不想干了。我要辞职!但从来也没有付诸行动。
她还变过心,他们结婚后,她曾经喜欢过一个人。他知道。但只是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她和那个人连见都没有见过。
他们后来都没有再提起过。他甚至没有问过,她为什么喜欢那个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差错,使得她要去喜欢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有时也在猜测,究竟是为什么,是那个人更好?有钱?帅气?还是别的什么。但是他从来没有问过。
也许不问,就等于没有发生吧。
……
那些都是她。
有时候,他又有些恍惚,他觉得那并不是她。
但那是谁呢?
这绵绵阴雨里,房子里的花草竟渐渐地更茂盛起来。天竺葵开出了紫中带白的一簇大花;长寿花一簇一簇不停地开,新花与旧蕊交相辉映,给这黯淡的空气添了一点鲜亮;她一直抱怨不开花的韭叶兰这些天竟也抽出了花苞;绿萝的叶子油亮油亮的,硕大的叶片仿佛一块块墨绿的玉。
那盆栀子不知从什么时候由一朵变成了许多。
“我死后给我一个栀子花的花圈。”他耳边突然响起林萍有次开玩笑时说的话。
他看着那洁白的花,突然转身,打开门,径直走向雨水正在浇灌的大街。
作者简介:
西洲,1986年生于安徽,现居新疆。
那么,等她回来,就问一问吧。
又一天,林萍写:今日天晴,无事。
有时,她淡淡地写“在爱情里没有受到过纵容的女人并不算真正被爱过。”却在句子的旁边打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五角星。红色的。
他内心一凛。
他有太多时间来想他们之间过去的生活。
从相恋到结婚,他自认对她不错,一心一意工作、挣钱,谋求更好的生活。逢年过节,给她的家人也打电话,该送礼时送礼,该请客时请客,并没有落下什么话柄。当然,也从来没有爱过别的女人。
但说到纵容,什么又是纵容呢?这些名词一个比一个让人费解,让他在这样的雨夜里茫茫然不知所措。
她在笔记本中还写:
“这世界上有谁以爱情的姿态爱过你?”
这一句,她没有标注,不知是引用还是有感而发。看看时间,是不久之前。
他想起有一次争吵。一点小小的事情,她气得哭起来,他觉得不可理喻。林萍在哽咽中说,不错,是你有理。我不对。
他默不作声。的确是她不对,这样的小事情有什么好吵的呢。幸好她还算明理,就此打住,很好。这件事后,两个人又重归于好。当然是重归于好,但是谁也没有向谁道歉,这有什么好道歉的?日子里谁不是磕磕绊绊过来的?第二天,还不是好好的。该上班上班,该买菜买菜,该吃饭吃饭,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徐州不觉有什么不对。别人的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再说,别人的生活怎么样,我们管得着吗?我们只负责管好自己的生活。
雨下了多长时间他不知道。好像就那么几个夜晚,又漫长得仿佛一个世纪。在这短暂里,他不断想同外界建立联系,他想找到她。而在这漫长里,他花了大多数时间来看她的笔记本和书。这个从来不愿意看小说的人,看了好几本小说,而且都是他不屑之中更不屑的爱情小说。那些小说里太多横刀夺爱的故事,但是,这世上,谁值得你为之横刀?
他摇摇头,叹息着合上一个又一个荡气回肠却漏洞百出的爱情故事。
他不想费力再去看那些。雨中的时间不如来想一想,她——他的妻子,究竟是怎么样的人。
她怕死。每次两人嬉闹,他作势要掐她的脖子,她就很紧张,大声尖叫,有时竟会掉下眼泪。
她不止一次向他说过类似的害怕。她要他捏捏后背,在他的手捏到后颈的时候,她会突然喊停:那里有个死穴!你别碰到了!
她告诉他,她躺在椅子上仰起脖子的时候,只要一闭眼睛,总觉得上面会掉下一把锋利的斧子,正好砍断自己的脖子。这样想的时候,就觉得脖子里凉飕飕的,吓得慌忙睁开眼睛立刻直起身子。
有一次地震,他出差了,她在家里吓得直哭。其实只是小小的晃了一两下,她说她的腿都软了。那天的日记,她记:不是害怕死,是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地死。没有同伴。
当然,世界灭亡她是不怕的。即使有人有船票,但那仍旧是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将一起死去。
她喜欢折腾一些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家里到处都是瓶瓶罐罐,里面装的啥,时间长了她自己都不记得。
她喜欢藏钱,在不穿的衣服口袋里装十块、二十块钱,等到再穿的时候拿出来会很惊喜。仿佛那钱是别人的似的。
她喜欢粘人,又啰嗦,一件事要反复地说几遍。
她不上进,工作不怎么认真,懒散拖拉。常常嚷着:啊,实在不想干了。我要辞职!但从来也没有付诸行动。
她还变过心,他们结婚后,她曾经喜欢过一个人。他知道。但只是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她和那个人连见都没有见过。
他们后来都没有再提起过。他甚至没有问过,她为什么喜欢那个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差错,使得她要去喜欢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有时也在猜测,究竟是为什么,是那个人更好?有钱?帅气?还是别的什么。但是他从来没有问过。
也许不问,就等于没有发生吧。
……
那些都是她。
有时候,他又有些恍惚,他觉得那并不是她。
但那是谁呢?
这绵绵阴雨里,房子里的花草竟渐渐地更茂盛起来。天竺葵开出了紫中带白的一簇大花;长寿花一簇一簇不停地开,新花与旧蕊交相辉映,给这黯淡的空气添了一点鲜亮;她一直抱怨不开花的韭叶兰这些天竟也抽出了花苞;绿萝的叶子油亮油亮的,硕大的叶片仿佛一块块墨绿的玉。
那盆栀子不知从什么时候由一朵变成了许多。
“我死后给我一个栀子花的花圈。”他耳边突然响起林萍有次开玩笑时说的话。
他看着那洁白的花,突然转身,打开门,径直走向雨水正在浇灌的大街。
作者简介:
西洲,1986年生于安徽,现居新疆。
那么,等她回来,就问一问吧。
又一天,林萍写:今日天晴,无事。
有时,她淡淡地写“在爱情里没有受到过纵容的女人并不算真正被爱过。”却在句子的旁边打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五角星。红色的。
他内心一凛。
他有太多时间来想他们之间过去的生活。
从相恋到结婚,他自认对她不错,一心一意工作、挣钱,谋求更好的生活。逢年过节,给她的家人也打电话,该送礼时送礼,该请客时请客,并没有落下什么话柄。当然,也从来没有爱过别的女人。
但说到纵容,什么又是纵容呢?这些名词一个比一个让人费解,让他在这样的雨夜里茫茫然不知所措。
她在笔记本中还写:
“这世界上有谁以爱情的姿态爱过你?”
这一句,她没有标注,不知是引用还是有感而发。看看时间,是不久之前。
他想起有一次争吵。一点小小的事情,她气得哭起来,他觉得不可理喻。林萍在哽咽中说,不错,是你有理。我不对。
他默不作声。的确是她不对,这样的小事情有什么好吵的呢。幸好她还算明理,就此打住,很好。这件事后,两个人又重归于好。当然是重归于好,但是谁也没有向谁道歉,这有什么好道歉的?日子里谁不是磕磕绊绊过来的?第二天,还不是好好的。该上班上班,该买菜买菜,该吃饭吃饭,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徐州不觉有什么不对。别人的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再说,别人的生活怎么样,我们管得着吗?我们只负责管好自己的生活。
雨下了多长时间他不知道。好像就那么几个夜晚,又漫长得仿佛一个世纪。在这短暂里,他不断想同外界建立联系,他想找到她。而在这漫长里,他花了大多数时间来看她的笔记本和书。这个从来不愿意看小说的人,看了好几本小说,而且都是他不屑之中更不屑的爱情小说。那些小说里太多横刀夺爱的故事,但是,这世上,谁值得你为之横刀?
他摇摇头,叹息着合上一个又一个荡气回肠却漏洞百出的爱情故事。
他不想费力再去看那些。雨中的时间不如来想一想,她——他的妻子,究竟是怎么样的人。
她怕死。每次两人嬉闹,他作势要掐她的脖子,她就很紧张,大声尖叫,有时竟会掉下眼泪。
她不止一次向他说过类似的害怕。她要他捏捏后背,在他的手捏到后颈的时候,她会突然喊停:那里有个死穴!你别碰到了!
她告诉他,她躺在椅子上仰起脖子的时候,只要一闭眼睛,总觉得上面会掉下一把锋利的斧子,正好砍断自己的脖子。这样想的时候,就觉得脖子里凉飕飕的,吓得慌忙睁开眼睛立刻直起身子。
有一次地震,他出差了,她在家里吓得直哭。其实只是小小的晃了一两下,她说她的腿都软了。那天的日记,她记:不是害怕死,是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地死。没有同伴。
当然,世界灭亡她是不怕的。即使有人有船票,但那仍旧是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将一起死去。
她喜欢折腾一些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家里到处都是瓶瓶罐罐,里面装的啥,时间长了她自己都不记得。
她喜欢藏钱,在不穿的衣服口袋里装十块、二十块钱,等到再穿的时候拿出来会很惊喜。仿佛那钱是别人的似的。
她喜欢粘人,又啰嗦,一件事要反复地说几遍。
她不上进,工作不怎么认真,懒散拖拉。常常嚷着:啊,实在不想干了。我要辞职!但从来也没有付诸行动。
她还变过心,他们结婚后,她曾经喜欢过一个人。他知道。但只是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她和那个人连见都没有见过。
他们后来都没有再提起过。他甚至没有问过,她为什么喜欢那个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差错,使得她要去喜欢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有时也在猜测,究竟是为什么,是那个人更好?有钱?帅气?还是别的什么。但是他从来没有问过。
也许不问,就等于没有发生吧。
……
那些都是她。
有时候,他又有些恍惚,他觉得那并不是她。
但那是谁呢?
这绵绵阴雨里,房子里的花草竟渐渐地更茂盛起来。天竺葵开出了紫中带白的一簇大花;长寿花一簇一簇不停地开,新花与旧蕊交相辉映,给这黯淡的空气添了一点鲜亮;她一直抱怨不开花的韭叶兰这些天竟也抽出了花苞;绿萝的叶子油亮油亮的,硕大的叶片仿佛一块块墨绿的玉。
那盆栀子不知从什么时候由一朵变成了许多。
“我死后给我一个栀子花的花圈。”他耳边突然响起林萍有次开玩笑时说的话。
他看着那洁白的花,突然转身,打开门,径直走向雨水正在浇灌的大街。
作者简介:
西洲,1986年生于安徽,现居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