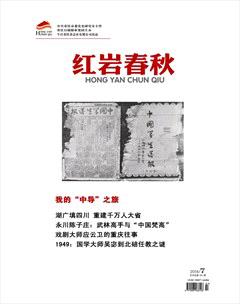永远的深情厚谊
袁明

袁超俊(1912-1999),原名严金操,贵州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贵州共产主义青年同盟领导人、贵州司机工会主席、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干事、上海工人救国会主席、上海全国救国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代表。1937年9月经周恩来交涉营救出狱,后一直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先后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湘乡八路军临时办事处负责人、衡阳等地办事处负责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党支部书记等职,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秘密交通。1943年7月随周恩来到达延安,在杨家岭周恩来处工作。1946年7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11月后,经周恩来安排赴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和到香港组建华润公司并开展贸易工作,先后任华润公司党支部书记、华润公司副经理、华润公司(含招商局、三联书店)党总支书记,同时承担电台机要工作直至解放。
问:您父亲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多年,感情很深,可否谈谈?
答:我父亲在周总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周恩来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人们常称“周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人们多称“周总理”。因此口述者多称“周总理”,有时也称“周副主席”——整理者注)身边工作有10多年,对周总理感情非常深。周总理在各种复杂、恶劣的社会环境下多次救过我父亲。
父亲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皖南事变前后,当时父亲在贵阳八路军交通站任站长,负责运送抗日物资及往来人员的接送。1940年前后,国际援华物资进入中国只有一条线(由于日军的侵占,东面、东南面及南面的交通运输线断绝——整理者注),那就是通过滇缅公路,然后经滇黔公路运到贵阳,再转运重庆,分发八路军、新四军,因此贵阳交通站就显得特别重要。皖南事变前,父亲在贵阳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但是总理已经感觉到了。有一天半夜,他打电话叫我父亲立刻返回重庆。父亲说,我把这边工作安排一下就立刻动身。但总理说:不行,你现在就得动身。周副主席下命令了,父亲就赶快找便车到了重庆。到重庆后,总理只让他住下待命,别的什么也不让做。父亲很着急,但到了第四天、第五天,就听说皖南事变爆发了。他这才知道,总理是为了他的安全。父亲想到贵阳站还有好几个同志,就报告说,我要回去,组织这些同志撤退。总理想了想说:不行,你不能走,你曾经被国民党抓过两次,在他们那里有案底,如果出事,你首当其冲,贵阳那边的同志我们再想办法,硬是把父亲留在了重庆。果然,没过多久,国民党就把贵阳交通站给查封了,6名留守交通站的同志都被关了起来。后来经过总理、叶帅(即叶剑英——整理者注)的交涉被放了出来。但如果我父亲被抓,不管谁去做工作都是出不来的。
类似的事不止一次。我父亲在沈钧儒先生的上海工人救国会任主席时,曾被捕,关押在国民党苏州反省院。1937年9月,经过周副主席的百般交涉,我父亲从苏州反省院释放了出来。1943年7月,周副主席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筹备工作,父亲随行,那时正值延安整风,因父亲两度在国民党监狱坐牢,一定会受影响,又是总理做了特殊安排,让我父亲住在他的窑洞院里,才没有受到影响。
还有一次就有点离奇了,周总理救了我父亲,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1942年,我父亲的工作一是负责南方局的秘密交通,还有一项是负责党的秘密财务。这天,我父亲要去给一个地下交通点送些美元,他精心做了准备:弄了个很漂亮的小手提箱,把美元全装进去,穿一身西装,自己开着车去。但到交通点后,准备上楼时楼上下来一个国民党军官,一把抓住他的领子:好你个小偷,我真是把你抓住了。我父亲一愣,心想是不是交通点出事了?一听说被当作小偷抓的,就放心了。但个人还是有风险,就和这个国民党军官周旋吧。那个交通点对面就是警察局,所以我父亲被抓到了警察局里。原来这栋楼前不久被小偷光顾过,他们把我父亲当小偷了。父亲争辩说,自己是做买卖的,不缺钱,还从口袋里掏出些美元来。但这些家伙不相信,特别是那个国民党军官。父亲见用这种办法脱不开身,手里又拿着大量的资金,还有任务,就另外使了个法。他说:我不跟你们说这么多了,咱们走,到徐恩曾府上就能说清楚了。徐恩曾是国民党特务头子,为什么要到他那儿去解决问题呢?因为我父亲对总理的行程安排非常清楚,那天晚上,总理正好要去拜访徐恩曾。从这里可以看到,即使是一个大特务头子,总理从统战的角度考虑,也要与之交往,结果这种交往救了我父亲。到了徐恩曾府上,我父亲说: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报告。父亲进去以后就跟周副主席的卫士龙飞虎说怎么怎么回事,龙飞虎就挎着个盒子枪出来了,说:你们搞什么?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们来的吗?那两个家伙一看这阵势,灰头土脸地走掉了。
我们家与周总理一家的交往和故事还有很多。我母亲钟可玉是印尼华侨,15岁离开父母回到祖国大陆。抗战爆发后,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报考了延安鲁艺。在鲁艺读书时得了疟疾,那时延安的医疗条件比较差,组织上决定让我母亲回印尼治疗,印尼治疟疾有很成熟的技术。中央社会部听说有人要去南洋就有一个想法,即发展南洋的共产党组织号召华侨支援中国的抗战,母亲的组织关系就转到了南方局(海外关系归南方局领导——整理者注)。这时候,叶帅去看我母亲,他当时是参谋长,又是我母亲的梅县老乡。他听说我母亲要回南洋治病,就说:现在是战争时期,你就这样走是走不掉的啊。这样,你就说是我的侄女,叫“阿叶”。沿途国民党关卡要查你的话,你就报我的名字,他们就会放你走。但是走到半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海上交通被封锁,没有船,印尼就去不了了。母亲因组织关系到了南方局,便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总理一看,这个新同志需要治病,就没有给我母亲分配工作。当时恰好夏衍同志在北碚租了一套房子,夏衍又不在重庆,房子空着,总理就说:这样,你到北碚去疗养一下,洗洗温泉,看看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好处没有。然后叫钱主任(即钱之光——整理者注)拨了笔资金做生活费,让我母亲去北碚疗养。说来也很神奇,母亲在北碚住了几个月居然好了。病好后回到办事处,就在电台工作。当时电台设在红岩村顶楼,铁皮屋顶,而且重庆的夏天很热,温度相当高。电台的人员有规定不能暴露,母亲负责的那台电台又是编外电台,所以没事不允许下楼,也不允许在院子里出现。我父亲懂无线电,电台方面有什么事都叫他去处理。就这样,因为工作的原因,父亲和母亲经常来往,慢慢两个人就好了。总理和邓妈妈对他们两个人非常关怀,1943年,父亲跟随总理去延安,出发前总理就跟我父亲讲:你看可玉的身体也不好,咱们都走了,就没人照顾她了。要不这样吧,安排一下,叫她到桂林去,那里有人可以照顾她。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又把我母亲调到延安,最后父母亲在延安结的婚。
那个时候结婚,组织上不安排房子,我父亲住在周总理窑洞对面的平房里,那个平房是个集体宿舍,所以父母亲是在周总理的窑洞外照的结婚照。照完相,晚上有一个舞会,在会上宣布一下袁超俊、钟可玉结婚了,大家祝贺一下,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都去了。散会以后就各回各的宿舍。后来我母亲怀孕了,回重庆后,有朋友送给周总理一瓶维生素,他自己舍不得吃,送给我母亲吃。就是这样,大事小事总理都非常关怀。我妈妈在生我和我双胞胎妹妹的时候遇到了风险。因为不懂,也没有医疗条件,不知道是双胞胎,母亲生下我以后,胎盘不下来,肚子还是疼,怎么办?突然想起来办事处还有一个医生,是一个荷兰归国华侨,好像姓毕。当时组织安排他返回荷兰去开展荷兰侨界的工作,但因为没有特定的社会关系一路安排照顾,总理就没让毕医生单独走,把他留在了重庆。这一留正遇上我母亲生产,我父亲就去找他。毕大夫不太会讲中文,他来后一检查,用结结巴巴的中文说:还有一个。但是怎么办呢?因为在办事处手术器械什么都没有,他就一拍脑袋说:我有办法。他事先煮了一罐咖啡,就把咖啡端来给我母亲喝,母亲就顺利地把我妹妹生下来了。假如总理不是为了毕大夫的安全留下他,我母亲和我妹妹的安全就不敢说了。所以总理又救了我们家一次。
问:周副主席对您父亲也十分信任吧?
答:是的。1938年八路军办事处从武汉撤退时不是直接撤到重庆,第一步是撤到长沙,然后一步一步撤,潇湘、衡阳,中间平江还停留过一下,然后到桂林、贵阳,最后才到重庆。因为我父亲开着一辆车,包括周副主席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李克农的父亲和岳父母、王明的家属等等,都是我父亲接送。到了贵阳后,考虑到当时有许多海外援华物资必须经贵阳才能进来,周副主席决定在贵阳成立一个交通站,我父亲任交通站站长。后来继续撤退的时候,由于沿途确实太颠簸,吃住都很困难,就决定家属不再撤,留在贵阳。
当时周副主席交给贵阳交通站的首要任务是运送物资,然后就是护送往来人员。新四军的人员、地下工作者要到重庆去只有走这一条路;再有,地方党组织当时破坏得很严重,一些地方的党组织恢复与南方局联系的任务也交给了交通站;再一个就是照顾这些家属。
我父亲是贵州人,一开始,他就利用我爷爷的关系开展工作。我爷爷和黄其深老先生的关系很好,贵阳有个很有名的学校,黄其深老先生是这个学校的董事。父亲通过黄老先生联系上这个学校的校长、进步教师商量,决定利用假期把校舍腾出来借给我们用。在这段时间里,八路军也积极筹措更安全更合适的办公地点,假期结束就搬过去。当时确定,城里设立办公地点,但为了保证安全,招待所、仓库、车库、家属的驻地都安排在乡下,在没有交涉好之前,这些家属在城里住着。周副主席的父亲就和我爷爷住在一起,两个老人也能说得来,经常在一起唠嗑,一起做饭。我爷爷是医生,周副主席的父亲也懂医,所以他们俩说得来,还交流交流医道。乡下的房子还没有物色好,日本人的飞机就来了。轰炸那天,我奶奶刚刚去世,父亲在上坟,一听飞机来了,就想:遭了!那几个老人还分散在各地住着呢,他们的安全怎么样了?所以他拼命地往城里跑,第一站就跑到我爷爷住的地方。房子还没倒,但房顶掀掉了,交通站的工作人员在帮助救护,爷爷没什么大碍,周副主席的父亲已经被接走了。父亲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稍稍放下,一屁股坐在地上。然后他又跑到邓颖超母亲安置的地方,也没出问题,再一家一家跑,幸好都没有出问题,只是我爷爷的房子被炸掉了。这样的惊险有好多次。不光是干部家属在贵阳交通站待过,我们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也经常过往,越南的胡志明也来过。
负责南方局的秘密交通是父亲的主要任务之一。秘密交通是当时特有的名词,特指人员疏散的时候按指定的路线和关系安全撤离的线路。当时主要有几条从北边出去的路线,只要能从北边离开重庆就可以到川陕边界。国共关系很紧张的时候,甚至有一个最坏的准备,那就是如果国民党彻底撕破脸,周副主席和叶帅就准备带着办事处的全体同志到川陕边界打游击。但具体走哪条路?谁接应?接应的人有没有正式的身份?这都要有安排。这个具体安排的执行人就是我父亲。于是,在往北边去的一路上,这里设一个石灰厂,那里设一个炼油厂,那里再设一个这个厂那个厂的,都是将来的交通线。我父亲的优势就是能开着车跑,有时候去一些隐蔽得很深的地下工作者那里取情报,都是我父亲去。这些秘密工作是周副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父亲的,除了父亲之外就没有人知道了。
父亲在南京办事处和武汉办事处时,职务是办事处的副官长。皖南事变以后,我们就再不使用国民党体制的称谓了。到重庆后,他负责的工作之一是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南方局的地下党的组织关系有很多也在我父亲手里。像广大华行就是为党筹集资金的机构,广大华行的同志就属于三线人员,平常不介入正常的工作,他们的任务就是赚钱。一旦一线、二线都被破坏了,三线就继续接着干,所以他们是不能暴露的。但是,南方局还得跟他们有来往,怎么联系呢?当时就做了这样的特殊安排:在三线的门对面再安排一个二线,二线都是一些摆摊设点的很随意的公开身份人员,他们可以随时接触生人。这样,既与三线人员保持着联系,又不会暴露他们的身份。如果三线的同志要去红岩村,就由我父亲开车去接送,他们藏在后座里,这样就不会被特务发现。
皖南事变以后,形势非常紧张,周副主席立刻召开会议,部署工作,加强警卫,加强纪律。周副主席亲自做安排,制定了一个秘密工作条例,这是由我父亲起草、周副主席审定的。比如,工作人员外出必须三人同行或者两人同行;联络用的信息,如果能背在脑子里绝对不留在纸上,在办事处保存不了的,就用电报发往延安,本地的文稿全部要销毁;实在必须留在手边的秘密信息,比如说联络人员、地下组织的联系方式,那就要用最小的字,写在最薄的纸上。当时,有一种香烟盒里有一层锡箔纸,里面是一层很薄的白色的纸,这些秘密信息就写在那种纸上,然后卷在一根火柴棍上。过去的火柴是不需要火柴盒就可以划着的,如果碰到紧急情况,抓住这个火柴棍,连同那个秘密信息,随便在哪里一擦就燃了,烧掉后立刻用一杯水把灰烬冲掉。因为烧过的纸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看到上面的字,用水把灰烬冲掉了就没办法看到了。周副主席当时就要求到这么细,每一项工作都有很详细的规定,以保证秘密工作的安全。
因为秘密工作的需要,我的小妹妹一出生就送了人。那是1947年4月我父亲根据周副主席的安排,到香港参与创办华润公司后的事情。当时在我家设立了一个电台,我和双胞胎的大妹妹还很小,小妹妹刚出生,家里还有译电员、报务员和他们的孩子。为了家里电台不暴露,就没有请保姆。但三个奶娃娃,加上报务员、译电员夫妇及孩子,我母亲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怎么办呢?最后,为了工作的需要,决定保电台、孩子送人。因为我和大妹妹是双胞胎,有一个说法是双胞胎不能拆开,所以没法送,就只有把小妹妹送人了。后来小妹妹长大了,爸爸想用一个很好的方式跟小妹妹说清楚,最后写了一个文稿,把过去的事都写了一下。我想,如果不是为了给小妹妹说清为什么把她送人的事,可能爸爸永远都不会讲秘密交通、秘密资金的事。我知道这些事,也是帮着整理爸爸的这些文稿才知道一些的。
问:您父亲多才多艺,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答:当年和我父亲一起从苏州反省院被周副主席解救出来的共200多人,都积极报名要到延安去。但是组织考虑这么多人,不十分了解,决定都送到新四军前线,在战争中经过考验再安排,唯独留下我父亲一人去延安,就因为他能写会画、会照相、会拉小提琴、会开汽车、会修表修收音机,是个多面手。去延安就要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办手续,当时是叶剑英、李克农在那里主持办手续工作。他们一看我父亲有这么多才干,就让他留在办事处工作。比如,要在哪个绸缎庄建一个电台,就叫我父亲去;比如,做假关防(当时地下工作人员从解放区到敌战区,必须通过国民党设置的关卡,需要政府的各种文书,即“关防”,还需盖上各个战区的印——整理者注)、制密写药水等;再比如,从各地来的地下交通人员,怎么搞秘写、怎么销毁、怎么在紧急情况下藏东西等地下工作的基本技能,都是我父亲手把手教的。
父亲的这些特长是在长年的地下工作中锻炼出来的。后来我们这些子女也受他的影响,家里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比如窗帘,都是自行车链条做的滑轮,比买的滑轮要好用。
问:您印象中父亲有什么特别的?
答:父亲嘴很严,口风很紧,为人很低调。我们和他生活了这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具体干什么工作。后来我到新疆去工作,中央电视台来找我,采访爸爸的事,但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帮父亲整理资料才知道一些。他们老战友聚会的时候会讲这些事,我们竖着耳朵听,很好奇,有时候他发现我们在听,就会把我们赶走。这是他们的职业习惯。
第二个就是不留文字,什么都不留。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写点关于父亲的东西,但就发现找不到什么可以写,能找到的唯一的文字,竟然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交代材料。因为我父亲跟江青是一个支部的,江青盯他盯得非常紧,所以我父亲写的材料是一份又一份。在上海地下党的那些我都知道,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没有材料。
在生活中,父亲就是一个平常人,不显山露水的。他和总理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但他从来不在外面说他和总理有什么样的交往。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口述人审核,题目为整理者所加。整理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主任。图片来源:资料图)
(责任编辑:杨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