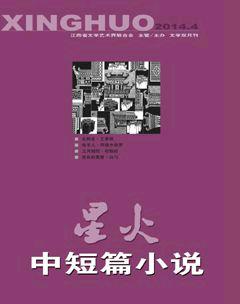抠号
高中毕业,我回队。队是生产队。回队头一天,队长安排我起大粪。大粪我熟悉,就是肚里存不住的货,自动泄出来,先泄自家厕所里,再由挑大粪的人来,一家一家的,给挑走,挑进公家大粪坑里,沤,沤上一两个月,起出来,才叫大粪。这样的大粪有劲儿,上到地里庄稼愿意长。所以,农民对大粪都有感情。可我不行,不但没感情,还鼻子斤斤着,尽量躲开它一点。队长眼睛毒,看我这个熊样,立刻发挥他权力优势,把我调离开,安排我去挑大粪。队长意思谁都心明镜:你小子不是想躲吗?给你来个前后夹击,看你怎么躲!何谓前后夹击?挑大粪的,一共两个桶,前边一个桶,后边一个桶,两个桶包围你,你往哪儿躲?
事情就是从挑大粪开始的。
我们生产队官方称谓:园艺队。而民间不这么叫,叫蔬菜队。说白了,就是一个种菜的生产队。另外,我们队也属于自然村,自然的,也有村名,叫温泉村。何以叫温泉村?以后我会解释这个的。
最初我对队长心存不满,可挑粪两天,发现其中蛮有乐趣。比如,两个大粪桶的吊环比较长,这样一来,担起粪了两个粪桶的底部几乎贴地。可是它却从来碰不着地!你说神奇不?再比如,一根大粪扁担,特别长,老长老长。之前我没明白它为什么老长老长的,这回轮到我亲身体验了,我滴妈呀,原来扁担长,一旦粪水洒了出来,不会溅到自己脚上啊!扁担长,等于安全半径也长呀。我们挑粪组一共十几个人,出去的时候,十几个人一起出去;回来的时候,十几个人一起回来。出去,就是去镇上挑粪。回来,就是从镇上挑粪回来。镇上和生产队之
间,隔着菜地。挑粪组来回去镇上的小路,必须经过菜地。小路两边种的是土豆,正值土豆花开,挑粪组从镇上回来途经那里,远看了,隔着大片土豆地,你看不见我们下面的粪桶,而十几条横在肩上的大长扁担,忽闪忽闪,就像我们有了很大的翅膀,在土豆地上低空掠飞。大粪组长,是个有点爱虚荣的家伙,发现远处有人向我们这里张望,他利用他的小权力,命令我们:换左肩!我们就刷的一下,把大粪扁担换到了左肩上。然后组长又命令:换右肩!我们就刷的一下,把大粪扁担换到了右肩上。那种一字排开的雁阵,那种极具表演秀的劳动,至今回想起来都让我很有艺术成就感啊。
可是有一天,我在镇上挑大粪,刚从一条胡同拐出来,迎面的,遇见高中女同学,韩玉霞。读高一时,我俩曾同桌。人家长得漂亮,心里想看她,可眼睛又不敢去看,就动了歪念,起早爬出被窝,去山上摘樱桃。摘了满满有一兜,趁着早雾掩护,提前钻进教室,将那一兜樱桃放入韩玉霞桌里。桌子是翻盖的,我想象着,韩玉霞翻开桌盖时,会是一种怎样的惊喜?可我又害怕别人发现是我偷送樱桃给她的,为避开嫌疑,我又在早雾的掩护下,赶紧离开学校。那天上学,我比平时晚去了几分钟。结果,嫌疑避开了,却没有看到韩玉霞翻开桌盖那一刻表情。我便偷偷注意她,一连几天,都没看出她有什么变化,好像她根本就没吃过樱桃似的,弄得我以后再也不敢造次了。
高三那年开运动会,我俩有过一次接触。长跑属于我们班的弱项。想不跑,可学校规定,哪一项都不准弃权。无奈的,老师找到了我,安排我跑五千。什么?让我跑五千?我直摇头,并说:老师我不行啊。老师说:那你说谁行啊?我知道谁都不行才安排你跑的。我还是一个劲儿摇头。老师说:要不,你指一个出来谁行,我就安排谁。我把我们班上挨个的想了,还真没谁行的。老师看我没吱声,就说:有什么难心的,不妨说出来?我说:鞋,我有。老师说:那好吧,短裤,我给你借。听老师说给我借短裤,我有点后悔,后悔说鞋也没有就好了。假如说鞋也没有,老师定会给我借的。可我爱面子,说自己连鞋都没有,多掉价啊。就这么滴,放学时,我偷拿老师一根粉笔,回家。刚进家门,立刻脱掉脚上鞋,把鞋放盆里,灌水,哗哗的,用鞋刷子奋力洗刷。洗刷完了,把鞋挂在菜园边的板障子上,空,等水空净,趁着两只鞋潮乎乎,赶紧拿出粉笔,往鞋上抹。抹得要均匀,否则你当时看不出来,等鞋干了,鞋成了花花搭搭的鞋,寒碜死了,还不如不抹。所以,我给鞋抹粉笔,算有经验的。抹完粉笔还不算完,晚饭后,趁着锅里有温度,在锅里横两条木棍,鞋搭在木棍上,盖上锅盖,就可以睡觉了。第二天早,揭开锅盖看,两只鞋就成了白鞋。这样烘干的鞋,贼白。刚穿脚上,我觉得扎眼,有点不好意思,好像走路都不会走了。于是我抓把灰,往上边轻轻撒了点灰。接下来走路,心里就舒服多了。那年头,能穿上白鞋,不一般人啊。但给白鞋撒了一点灰才可接受,由此得出一个真理:什么东西都不可追求完美,太完美了会远离大众,次完美,才更具普世价值。
跑五千是最后一个项目,属于压轴,最吸引眼球。可谁都明白,吸引眼球是一二名,哪怕第三也行,而我,心明镜,我是小鱼拴在大鱼串里,哪是长跑那块料啊。别说我心明镜,全校也都心明镜,长跑是我们班弱项,所以,发令枪响,别的班级锣鼓喧天摇旗呐喊组成最强啦啦队阵容,而我们班,哑巴悄声的,一片沉默。在弯道处,别的班级都有几名同学守候那儿,准备给自己班级运动员送水。何谓送水?其实很简单,手擎一只瓷缸,里面装着水,当然了,里面也泡着一只手绢,等运动员跑过来,掏出手绢,递给他,就叫送水了。那时没有矿泉水,用手绢送水,应该算当时最智慧的发明了。我心明
镜,弯道处没有我们班的人,可跑到那里,还是朝那里望了一眼。结果,白望了,确实没有我们班的人。细说也没什么,有人又能怎么样?有人也不能帮我跑,还不得我自己跑?所以对我来说,有人没人都一个样。然而跑了几圈,感觉不行了。最初感觉,口发干,接着嗓子发紧,上不来气。这都不算事,算事的,是别的班级啦啦队,一看我越来越落后,领头的那小子干脆冲我喊:喂!傻小子!掉过头来跑,你肯定第一呀!领头的也是领喊的,他这一领喊不要紧,我的妈呀,别的班级啦啦队也都加入进来跟着喊:傻小子!倒第一!傻小子!倒第一!就在这一片倒彩声里,忽然听见有谁喊我名字:方明贵!我循声望去,是韩玉霞,她挤在弯道区里,怕我看不见她,一只手在她头顶上方使劲摇,并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经过弯道区,我从她手里接过湿手绢,快速塞嘴里。可我抓她手绢时太用力,连她手也一起抓了,等我跑过去之后,听后边扑通一声,估计把她带倒了。我想回头看她一下,只听她喊:快跑呀你!于是我顾不得她,继续往前跑。不过,湿手绢塞嘴里之后,一股瓦凉沁入心肺,这才懂得,什么叫解渴啊。我跑完一圈再过来,她站那里好好的,跟没事似的,也就放心了。当我看她伸出一只手,是空的,心就明镜,她等着接手绢呢。我立刻从嘴里扯出手绢,塞给她。等我再跑一圈,回来,看见她从瓷缸里捞出手绢,趁着湿拉拉,虚握手里,平举着,等待我再拿。这回我加了小心,没有抓她手,抓了手绢,继续塞嘴里,继续跑。不用说,那次长跑成绩很糟糕。事后想想,也算对得起别的班级啦啦队了,终于没让他们白喊,我得了倒数第一。
运动会结束,人散尽,空旷操场上只剩我一个人,孤零零站那儿,发呆。回到教室,教室也空的,只好走出来,站着,继续发呆。暮色初降,想起我该回家,就抬脚走。走了不几步,影乎乎的,前边有个人,站在那儿,样子似乎是个女生,好像等人。等谁呢?我快走到跟前了,辨出她是韩玉霞。那时我真的太傻,居然傻乎乎问:你等谁?她嘴巴张了又张,想说什么,又憋住,却不得不说的,终于说出口:我等手绢。想起她手绢装在我裤兜里,就掏出来,给了她。她接过手绢,低着头,迅速跑进暮色,没影了。
我接着走,又看见一个人,影乎乎的,站在我前边路上,也好像等人。这时的暮色比原来的暮色变得深沉,所以我不好判断,这影乎乎的人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但可以肯定的,这人影是在等人。等谁呢?
当我走近了,昏暗中的人影向我发问:是方明贵吗?我答:是呀。我仔细辨认,才看出来,他是隔班的司富库,虽然不同班,也算同学吧。我问他:你等谁?他说:等你呀。我问:等我?等什么呀?他说:你说等什么?等短裤呀。这才恍然醒悟,原来老师借短裤,是跟他借的。我四周看了看,没人,可我依旧多余的,躲进树后面,把短裤脱了,还给他。
现在再说我挑大粪。迎面的,碰见韩玉霞,她先站下,与我打招呼。我肩上压着大粪扁担,虽然我也跟她打了招呼,大粪扁担却没有放下来。那么,我就肩着大粪扁担,跟韩玉霞说话。这是我俩头一回说话。大粪扁担长,这谁都明镜,可大粪扁担不仅仅长,它还沉啊。挑过大粪的人清楚,站立不动,那条扁担会更沉的。我也是傻,扁担放下来不就行了?可我偏偏没有放下来,傻乎乎肩着大粪扁担,跟韩玉霞说话!韩玉霞长得好看,在我们班里被公认为班花。不少男同学想跟她说话,都找不到机会,现在一下轮到我有机会了,我怎会放过?所以我固执地想,不放下扁担,就是不放下机会,我要抓住这机会,跟她说话。不过照实说,我心里也是很着急的。因为大粪组长在集合地点等着我,等我们汇齐了,好一起回队。韩玉霞并不知道我心里急,她只知道我的扁担来
回动,可能属于以逸待劳状态。扁担为什么来回动呢?原因简单,大粪扁担把我左肩压累了,就扭一下身,把大粪扁担平稳地换到右肩上。这有点像数学课上的几何题,拿圆规画弧,以我的肩膀为圆心,以扁担长度为半径,我换左肩了,画一次弧;我换右肩了,画一次弧。我画弧,不是我闲得抽风,恰恰相反,因我太累了,才隔一会了,换肩,画弧。再隔一会了,换肩,画弧。而画一次弧了,韩玉霞就得往后退两步,画完弧了,她再往前走两步,这样,她会与我保持最佳说话距离。我俩这个样子,引得路人好奇地朝这里张望。你想啊,一个男的肩着扁担,隔一会了,画弧,隔一会了,画弧,另一个女的,隔一会了,退两步,隔一会了,进两步。你见了这场面,你不觉得好奇?后来我眼睛余光注意到路人向这里张望,一下的,我掉进尴尬。那时我不够开放,在别人张望下与一个姑娘说话,就像有谁给我脸上浇了开水,那个烫呀,贼拉拉的难受。如果有面镜子,照一照,我脸肯定像一块红布!也恰在此时,等不耐烦的组长寻找到这里,突然喊:喂!大家都在等你,你小子却在这穷唠嗑,快跟我走吧!
组长这一声喊,等于给我解了围,我肩着大粪扁担,拔腿离此他往。
韩玉霞那天回来取衣物,只在家待一个晚上,次日返回青年点。也就是说,人家是下乡知青,而我,纯牌农民。现如今,人们对户口的概念已经淡了,可那个年代,户口决定脑袋,决定你的命,决定着你的身份和等级。城乡差别,简单的城乡两个字,两重天啊。所以,我把握这个尺度,控制自己别冒出傻念,一旦闹出贻笑大方来,多掉价?然而那天晚上,已经夜半了,我睡不着,顺着两只脚的意志,悄悄从家出来,往镇上走。不知不觉,走进了那条胡同,距离韩玉霞家十步之遥的地方,寻一块有阴影的街边,站下。尽管夜深了,街上已经没有人了,我却愿意站在阴影里,一边躲避着什么,一边悄悄向韩玉霞家窗口张望。她家窗口是黑的。镇上多数人家窗口也是黑的。我不知站了多长时间,不远处几个少数明亮窗口,次第灭了。已经下半夜,除了偶尔传来遥远火车的叫,再听不到别的声音了。在一片静里,我努力向她家窗口倾听,企图听到她的什么声音。白费,我体温渐渐给夜露打凉了,也没有听见有关她的哪怕一鳞半爪的声音。也曾试探往前走几步,可是看到她家窗前隔着一道墙,想想假如我翻墙了,会被人当成小偷,也就作罢了。有那么一刻,觉得我该离开,回家了,却不忍离开,心想再站一会儿,兴许会看到什么。就在这迟疑间,忽然的,她家窗口白了。窗口这一白,吓得我往后靠了靠,靠到街墙上,控制呼吸,不敢出一点大声。凭我的生活经验,窗口白了,接着房门会开的。我死死地盯紧她家房门,想看清出来的是谁。当然了,我暗盼着,出来的最好是韩玉霞。可是那扇门一直就那么静静地关着,没有开。而且不多时,灯灭了,那个窗口又黑了。
走出镇子,脚前小路渐渐变白。我以为小路变白是幻象,你想啊,刚刚看见韩玉霞那个窗口,白了,现在怎么会连我脚踩的小路也渐渐白了呢?难不成小路和窗口之间保持着联络功能,彼此互通有无,甚至可以山寨,才白的?我似乎被暗示着,就回了一下头,想回望一下韩玉霞那个窗口,是否又白了。白费,镇上所有窗口,拒绝山寨,都黑着。却在这一次的回望里,我眼睛给惊讶烫着了,眼前那些房屋和街道,也渐渐地变白。举目望天,半块月亮挂在那儿,我走它也走,我停它也停。它不像月亮,更像夜天上半开的一个白洞,洞里保有巨大库存,把源源不断的银辉从洞口撒下来。那么,房舍和街道,田地和树木,以及远山,近草,都染成了白。当我途经那片土豆地,发现最白的,是土豆花。没有风,也没有声音,我默看土豆花,它们星星点点遍布田间,一粒一粒
的都很耀眼。心里想着去数一数它们,明知数不清,却也愿意数一下。仿佛去数一数了,就等于亲自拜访它们了。无数土豆花寂寞开着自己的白,这似乎暗合了我当时心境,所以,数不清也愿意去数清的众多微凉,悄悄爬满我心房。
回到家里,我没敢点灯,但我觉出小腿发凉,探手摸一摸,知道那是经过土豆地时,给露水碰湿的。想看一下裤脚是否粘了草叶什么的,正在犹豫点灯好还是不点灯好的时候,忽然从窗口追进来月的银灰,把我家屋地照耀出一块白。
得空了,我总爱往司富库家跑。自从有了借短裤那件事,我俩变熟。之所以总爱往他家跑,原因简单,他家有一些书,属于禁书,吸引我去偷看。司富库更喜欢让我去,原因也简单,一来他可以当我面显摆,显摆他有禁书,二来他有个爱闹的小妹,他哄了,经常哄不好,有时遇上我,哄她,反而哄好。这无疑帮了他忙,何乐而不为?尤其演电影,遇上我没去他家,他反而会主动跑来,找我去他家。演电影的事,瞒不住人,他小妹一定闹着要去看的。所以,他找了我,是替他当帮手的。那时演电影都在野外演,也叫野场电影。按理我们应该正点到的,可同学小妹赖着不在地上走,非让人背,我俩只好当了背夫,轮流背那小丫头往电影场赶。尽管满头是汗,还是赶晚了,等我们到那里,开演了。那么,好的位置被别人占,次一点的,也没我们的份儿,自知之明,也算就近的,我们只能靠后边站着看。站着看,只解决了两个大人的看,还剩同学妹妹怎么办?于是我们的肩膀,成了同学妹妹座椅,她轮流骑在我们的脖子上,结果看电影成了她的次追求,她的主追求,就是享受骑我们的乐趣。同学小妹还有个乐趣,喜欢欺负外人。她本来应该平均骑我和她哥的,到后来,她干脆不骑他哥,专门骑我。你说,这不是欺外吗?我虽然心里有意见,却找不到发表意见的窗口啊。而多数情况下,她骑我脖子并不专为看电影,或者开头她看了,可看着看着,每次都看不到半途,她就睡着了。有一次,同学小妹睡着后,我忽然觉得后背发烫,心想坏了,她尿了。但没敢吱声。你想啊,小孩尿一个尿你就发表意见,那你还称职做一个合格大人吗?那次电影结束,往回走的路上,司富库说了两次:把小妹给我吧。我说:她睡得正香,最好别折腾她,一折腾,准醒,醒了闹你,你愿意?司富库想想也对,不再说什么。结果我走在那条夜路上,头顶搭压着同学小妹那颗头,因为她睡着,那一颗头很不稳当,忽而向左边歪一下,忽而向右边歪一下,累得我满脸流汗。可我的后背,却一片瓦凉啊,遭老罪了。
第二年,县里从各个公社抽调年轻人,集中出民工。听此消息,我高兴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等名单下来,那上面没有我名字。年轻人谁不爱出去闯荡啊。一下的,我情绪低落,总想随便找谁的茬,找到茬了,狠狠给谁一顿全世界重量级的胖揍,才解气。正好,司富库也落单,公布榜上没有他名字,我俩不谋而合,整天晚上聚一块堆。以前聚一块堆,还看看禁书什么的,现在可倒好,聚一块堆了,连话都懒得说,我俩像哑巴,干坐着。干坐一气之后,乘着夜色掩护,这儿游荡,那儿游荡,游荡一片西瓜地头了,我俩心照不宣,一个放哨,一个匍匐进去,然后摘西瓜,不管生的熟的,摘完了一个,放水里,摘完了一个,再放水里。水是流动的,西瓜漂浮上面,随着流动,流动到农民家中。套用时髦的话:西瓜不值几个钱,权当给农民发一次小小福利了。说到这,就必须把温泉村名字的由来交代清楚,否则你生疑:西瓜漂浮水面上,何以流动到农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