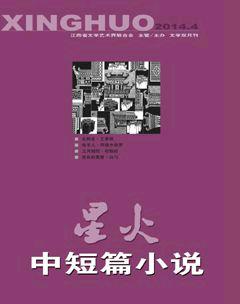牧羊人
阿微木依萝
春
早春,草尖悬挂着透亮的露水,朝阳还没有升起,风不大,山峰包围的村庄偶尔传来几声家畜的叫声。这些天然的动物声音,使这个村庄的早晨显得更加宁静。
山顶飘着薄雾,这是晴天的雾,它们和露水一样,太阳出来才会散去。人们在这时候不会早早起床,山沟里有冷风穿梭,恋床的人还能再睡一会懒觉。等到朝阳把露水从草尖上摘走,那些露水的香气和草的香气从半掩的木窗缝隙里飘进屋子,人们才陆续起床。
村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河谷村。村里住着六户人家,共有三十几号人。这些人即使聚在一起也不热闹,远不如一群麻雀热闹。为了增添热闹,他们喜欢高声说话,并且每家养狗,养鸡,养一切能发出声音的活物。当人们说话累了的时候,就让鸡和狗去说。
在这些高声说话的村民里,有一个人常年保持自己低声说话的习惯,他就是张果子。
张果子早晚间都在村前的小河边散步。河流什么时候涨水,什么时候水质最好,什么时候可以捞到肥鱼,什么时候水上漂来了牲畜的尸体,或者什么时候贪玩的孩子掉进了河里,只有他最清楚。
张果子是个羊倌。他放了五十年羊。从十岁开始放。现在他六十岁了。六十岁的张果子就像一只老羊。他身材干瘪,皮肤就像风干的羊皮皱巴巴粘在身上。他走路虽然不利索,骨子里却装着羊的野性和倔强。他每天赶着羊群上山,腰间别一把弯月形的镰刀。镰刀的岁数也不小了,刀把生锈,刀口钝拙,割草全靠人的力气。当然,年轻时候的镰刀是锋利的,就算是一棵树,只要进了镰刀的嘴,它也能两三下将它们咬断。
现在镰刀和张果子都上了年纪。翻山时遇到一些树枝挡路,张果子就抽出他的老刀,将树枝慢慢散散地砍断。他从来没有想过好好磨一下刀,似乎镰刀上了年纪不需要细磨,就像他现在不需要急躁了——走路是慢的,说话是慢的,就连生气也是慢的——人上了年纪就和钝刀的性情是一模一样。他虽然还有野性的倔强,但是野性的倔强不需要天天背一把亮闪闪的快刀上山。他的倔强只用来放羊,并且不能听取别人半点劝诫,一旦有人说他六十岁了应该休息,他就会向你吼道:“不放羊干什么?你说!”
“老放羊的!怪不得一辈子放羊!”人们很气愤。
张果子在春天起得早,比任何一个季节都早。他喜爱春天。春天的天气不冷不
热。当整个村子的人还在睡懒觉时,张果子已经起来了。他和鸡,狗,马,牛,羊,鸟,一起醒来。
春天放羊比任何一个季节都省力。而且小羊在这个时节出生最有口福。
这个季节的羊和张果子一样精神爽朗,它们在夏天是疯跑的,在春天却流连在草地里。张果子的羊大多是黑山羊,当然也有灰白色的山羊。它们的样貌没有绵羊温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它们的毛发和腿脚都不如绵羊好看。可是它们一旦站在绿茵茵的草地里,瞬间就有了一种本土羊族的帅气。它们身上没有鞭子抽打的痕迹。张果子从来不用鞭子。他放羊只用嘴,他和羊说话,这张嘴到了山坡就停不下来。他认为羊可以听懂人话。
这些羊不全是张果子一个人的。
张果子一年要帮许多人放羊。他自己的羊不超过五只。五只羊循环放了五十年,现在还是五只羊。当然他现在放的是最初那五只羊的后代。他也不能清楚地算出现在放的是第几代羊了。
雇他放羊的人们一年给他一百斤或二百斤粮食。这一切都是口头约定。他们凭良心办事。当他们需要张果子放羊时,就指着村子下方的河水说:天在上,河在下,千年不变的石头作证,你给我放羊,我给你粮食。
张果子很相信这些天地为证的誓言。五十年来,他凭着相信别人的良心而没有饿死。他没有土地。他的土地被泥石流毁了。他也没有妻子儿女和兄弟姐妹。他的父母躺在坟墓里快要二十年。他是个孤人。当然他曾经不是。可曾经太远,比上辈子离他还远。现在他脑子里存着的只有一个年轻女子的摸样。遗憾的是,这个人也死了。死了三十多年。她从高高的山崖摔下去——张果子现在看到的每一朵花仿佛都是她变来的。他喜欢春天,但是春天对他来说,实在太短暂了。
每个早晨张果子都有一个习惯,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数羊,先要确定他的羊是否都在,并且确定每一个都活着,他才能去忙别的事情。
羊圈里每年都会死几只羊,有时死在春天,有时死在冬天,反正每个季节都可能死羊,说不好什么原因。
如果死了别人的羊,张果子就要赔一只给人家,如果死的是自己的,那就把死羊弄干净煮吃。早先死了羊他会大哭一场,就像哭他死去的亲人一样动情。年年如此之后,他不哭了,觉得人生短暂,羊生也短暂。他说:“人和羊都是一个命。”
早些年他在羊圈上挂着一面镜子,是“避邪的”,现在那镜子也取下来了,挂在他的床头。
张果子的草房子搭在靠河的位置,为了不让羊扯着房子上的草,他把羊圈搭得与房子有些距离。他拴了一只凶猛的黄狗在羊圈门口当管家。
这个早晨又死了一只羊。张果子半靠在羊圈门上,垂着头望它。
“这么好的季节,你死得不是时候。”他说。
张果子拖着死羊去了河边。他将羊摔在河沙上,然后坐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大石头上抽烟。石头是从河里生根长出来的,涨水也动摇不了它。张果子一边抽烟,一边冷眼望着死羊。羊身上飞着苍蝇。
河边风大,比起草房子里冷一些。他的白头发被河风掀来盖在眼睛上。
“嗨!老果子,又死羊啦?”陈石头的声音从河岸传来,他赶着牛出去放。
“老石头!你看看我,正坐着你呢!”张果子指着屁股下面的大石头说。在这个村子里,他只和陈石头有话说,也只和他开玩笑。
“鸟话!”陈石头喝道。
张果子干笑两声,眼睛又转去望着河滩。这样一年死两三只,他的羊只够赔账。
虽然这些死羊最后都进了自己的肚子,张果子还是感到很失望。
“不要难过啦。正好可以打牙祭。多好的事情。卖给别人不如自己吃掉。放一辈子羊能舍得自己杀一只吃吗?还是死了好。死了就可以吃个干脆。东想西想划不来。你说是不?”陈石头将牛赶到河对岸,放在山边的青草地上。
张果子突然感到一阵揪心的痛苦,他想起死去的年轻女子来了。
那是个冬天无风的上午,穿着红花外套的女子站在村子的西口,她和她的家人刚刚搬进河谷村。他们在河边建了房子。按照村中的风俗,邻里之间要互相帮助。所以张果子被父母派去帮忙。张果子就这样认识了年轻文静的姑娘秀芝。并且在短短两个月后,也就是次年初春,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私下确定的。算是私定终身。这在村里是头一回。
秀芝读了几年书,比张果子强一些。她说话有趣,会讲一些牛郎织女的故事。不像张果子,总把牛郎织女与董永和七仙女混合在一起。从他嘴里出来的董永娶的妻子不是七仙女而是织女,七仙女总是莫名其妙嫁给了牛郎。
秀芝有着农村姑娘的脾性,吃苦耐劳,聪慧可人。村里人逐渐看出张果子和秀芝的感情后,都打趣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羊粪上。
陈实,也就是陈石头,他原名陈实,那时候还没有娶妻,他也喜欢秀芝。张果子突然发现陈实也喜欢秀芝,感到很生气,但是不能说出来。虽然他知道秀芝不会喜欢陈实。但万一秀芝的父母喜欢呢?如果她的父母极力撮合,难保秀芝不会妥协。因此,他在深情看着秀芝的同时,眼角的余光总是时刻注意着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陈实。那时他多么年轻,眼力多么好。
他们为了秀芝打过很多架,“陈石头”就是从那个时候叫出来的绰号。
“嗨,小果子,你怎么还不去放羊!”这是陈实遇着张果子时最爱说的话。言下之意是让他离秀芝姑娘远一点。
爱情使张果子的心情欢畅,使他年轻的双脚充满力量,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羊群赶到水草丰美的地带吃饱喝足,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将它们收圈。草草吃过晚饭后,在村子的灯光和天边的星辰逐渐亮起来时,他就穿上最干净的衣裳去见心爱的姑娘了。那段日子他的时间总感觉过得飞快。
秀芝姑娘梳着两条长辫子,用紫色碎花布条扎着,当她坐在河边洗衣服时,两条辫子的发梢就像蜻蜓一样点在水面。
张果子常常帮秀芝洗衣服,尤其在初春水冷时,更要提早嘱咐秀芝把脏衣服积攒起来,等他放完羊回来洗。
陈实是以公平竞争者的身份出现的。比起张果子来,他显得比较大度。当张果子用斜眉歪眼看他时,他用严肃的口气却不失温和的态度说:“你可以喜欢秀芝,我也可以。难道我不可以吗?她还不是你老婆。”
张果子经常被这个名叫陈实却一点也不诚实的家伙气得跳脚。他说不过陈实。如果陈实是一只羊,他决定饿死他。
秀芝后来也放羊,张果子因为熟门熟路,经常作为秀芝的向导领着她和她的羊在山林里乱转。而陈实也像一只本分的狗一样跟在他二人身后。张果子以嫌恶的口气叫他“滚蛋”,他摇摇头,表示自己也有权利守着秀芝。
张果子想到这里回过神来。
他的眼睛不由自主飘到一座树木葱茏的山上。那座山正是他们从前一起放羊的地方。山的底脚,那棵开着碎花的藤树下,陈实正在那棵树身上扯着藤子。藤子上的花和叶子都可以喂牛。他已经扯了很多下来,放在牛鼻子底下。
陈实又转身看看河边,正好看见张果子在石头上望着他。他们互相远远地笑一笑。
陈实朝张果子走来。
“还不准备剐么?”他问。
“杀。”
张果子从石头上跳下来。他把外套脱来挂在一根水麻树上。水麻树正发着新嫩的叶子,张果子转身之前扯了一把树叶攥在手里。
张果子用水麻叶认真仔细地把死羊擦了一遍,再将它拖到河边用清水冲洗。然后从腰间抽出那把钝镰刀。
“你不会只有这一把刀吧?太钝了。怎么剐!”陈实咬着嘴皮,两手用力扯住羊的后腿。虽然羊已经死去,根本不会挣扎,张果子和陈实还是不自主地用杀活羊的方式来解决这只死羊。他们让它完整地再死了一次。
张果子一边费力用镰刀割断羊的喉管,一边说:“让你死个明白。你是这样死的,不是那样死的。死了变成羊鬼去告诉你的羊伴,应该这样死,死在我的镰刀下才算是死。你们是我一手放大的,你们的命是我的。”张果子说到这里十分难过,用镰刀狠狠再割了一刀羊脖子,“你们没有一个是我的!害人的!”
“这话一年说几次,我都会背了。羊会懂吗?如果我是你就啥也不说了。没意思。”陈实搬起羊头放在石头上,双手掐住羊脖子往下挤血。羊血只是惨淡地滴了两滴,瘀血堵在血管里再也挤不出来。
“会懂!”
“会懂就不会再死了。”
“哎,死了也好。有时候我在想,可能她在那边也孤单单的,像只野鸟,要几只羊去放是应该的。她在这里只和我们熟悉,不捉我们的羊,难道还要去做贼吗?现在你改放牛了。她是不会放牛的。”张果子长声叹气。
“你又胡思乱想了。人死了还放什么羊。瞎扯。多少年的事情了——你要是放得下就放下吧。”陈实垂下头装作很认真地给羊清洗刀口。
“你放得下吗?”张果子问。
陈实停下手,呆滞的眼神望着河水。
“你当然可以放下了。你结婚了。儿子都娶了媳妇。我放不下。”张果子抓起羊脚,往羊蹄子上划一刀,再抓起另一只。
陈实望着张果子,没有说话。
“我是在说玩笑话。你有父母,你愿意不娶也不行。我不同……”张果子望了一眼山包上的两座坟。
“你这样剥下去,要剥到明年了吧!”陈实转开话题。
张果子嘿嘿笑道:“你不懂,钝刀正好剥羊皮。我这样用惯了。你真给我磨快了我还使不来哩。”
突然一只活羊窜到河边来了。是张果子的羊。它翻圈门跳了出来。这个时间张果子应该放它们在山上吃草。
“又是这只瘟神!稍慢一点就发疯。一顿不吃要饿死吗?”张果子放下镰刀,把另外半边羊皮留在那里。
“走吧!蠢货!”张果子一脚踢向羊屁股,他走向羊圈,把里面安分的羊一个一个领出来,带它们走过木桥去河岸吃草。春天放羊的好处在于不用去很远的地方找草原,就近的山草就可以喂足它们。
“我帮你剐吧?”陈实高声说,手已经利索地开始剐羊皮了。但是那把镰刀实在太钝,他握住刀把的手因为用力猛而不停发抖。
“晚上一起喝酒。”张果子在桥上回他。
月亮冷清地挂在天边,星星好像被山风吹缩到云层后面去了。张果子门前的石榴树发出新芽的气味,它们的叶子像花瓣一样只在夜晚展开。石榴树的左边,也就是张果子的羊圈背后,一片蓖麻树枝枝杈杈占据了一块空地,等到果子半熟的时候它们是紫红色的,叶子和果实都是紫红色,但是现在,它们像鬼影子,在月光不是很好的夜空下,张果子和陈实都不愿意多看它们一眼。
张果子和陈实在草房子门口喝酒。他
们烧了一堆火,边烤羊肉边闲谈。火焰的光照到张果子的菜园里,新撒的白菜已经冒出鲜亮的嫩叶来。
“晚上的空气好。”张果子忍不住感叹道。他扬起脸,深深吸了一口气。
晚上的空气确实好。植物的清香在这个时候都愿意跳出来,它们像顽皮的孩子一样四处乱窜。村庄沉寂,白天很愿意说话的人此刻一言不发。
“还是晚上空气好。”张果子又说。
陈实也吸溜了一下鼻子。不是吸新鲜空气。他不像张果子一样将他的老鼻子对准空气猛烈地吸,好像一个氧气不足快要死掉的人一样费力地吸着那些所谓的植物香气。他从来不这样去做一些滑稽的事情。
“你这样吸,羊粪的味道也很浓吧?”陈实说。
“羊粪也是草味道。吃草的动物粪便不那么臭。”
“也对。”陈实漫不经心道。他站起身走到张果子的草房下,拿下自己的外套披在身上。
“山沟里风大。”陈实抖了一下。
张果子很得意地看着陈实,在他眼里,陈实瘦巴巴的显得有些可怜。而他身体好。六十岁了,他的牙齿只掉了两颗,还是在里面,看不见。与他同龄的人简直吃不得硬一些的食物,而张果子还能啃骨头。所以当他看着那些没牙的老人时,总要咧开嘴笑,故意将他的牙齿露出来。
但是张果子怕下雨。他的身体只在雨天肯出毛病。
“我的身体一向这么好。我平常连感冒也少有。”张果子往火堆里送两根干柴。
“谁和你一样呢?老狗命。‘贱命硬梆梆。知道吧?一向有人这样说。”陈实端着酒碗往嘴里灌了一口。
“多喝点酒啦。堵住你的狗嘴就不冷了。”张果子装着很气愤的样子。
他们翻烤的羊肉已经飘着肉香了。
“这一点也闻不出是死羊的味道。谁能闻出来呢?是不是?”张果子满意地取下一块羊肉送进嘴里咀嚼。“你也来一块。”他说。
陈实取下一小块放进嘴里。他的牙齿不剩几颗了,吃得小心翼翼。
肉香从张果子门前一直飘到邻居那里了。不多一会子,月亮底下走来几个小影子。是四个孩子。他们低声嬉笑着,有些羞涩地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向前讨肉吃。
“回去问问你们的爹妈,我这是死羊肉,他们要是放心你们吃,就来。”张果子故意说得很大声,使他们的父母都能听见。
三个小孩风一样扫回去了。只有一个小孩站在月光下,动也不动。
过了两分钟左右,那三个孩子各自端了一只洋瓷碗奔来。
“我妈说可以吃。”
“我妈也说可以吃。”
“我妈也这样说!”
三个孩子抢着回答。他们吞着口水。为了不让张果子看见他们的馋样,每个都用脏兮兮的袖子捂住嘴巴。
陈实取下三块肉,一人一块递给他们。并且让孩子们先放下瓷碗,吃完再端几块回去。
没有跑回去端碗的孩子还站在远处,她好像不知怎么办才好,立在那里不敢动。
“你过来。”张果子喊她。
穿短红衣服的小姑娘向陈实和张果子走来,她的眼神空茫茫的。
陈实取下一块肉递给她。小女孩接过羊肉没有说话,闷声坐在火堆边,她吃得有些急。
“红花,你慢点吃。还多着,多着呢。”陈实这样对小姑娘说,他抬眼若有所思地望着张果子,想说点什么没有说。
山风吹得红花有些怕冷,她缩了缩身子像一只受冻的小鸡一样靠在陈实身边。陈
实想要脱下外套给她穿上,张果子摆了摆手,进去拿了一件自己的外套出来。
红花是个没有妈妈的孩子,她的妈妈死了,生下无数个女儿之后喝药死了。红花的爸爸想要生个儿子,但是红花的妈妈一直生到死也没有给他生下一个儿子。他们天天吵嘴,终于吵死了。
红花的新妈妈是个年轻的女人,不足三十岁,给红花的老爹终于生了一个病恹恹的儿子。红花的老爹每天抱着小儿子,就像老母鸡孵蛋一样时刻不离。红花的新妈妈十分凶悍,背地里不让红花吃饱饭。这些事情红花的老爹是不管的。他眼里只有他的小儿子。
红花只要吃上两碗饭,她的新妈妈就要瞪着一双傻气凶残的双眼望着她说,一个五岁不到的娃娃需要吃这么多吗?你是不是不知饱足?我真怀疑你的胃是不是坏掉了,不受控制了。
红花听到这些话会立刻放下碗,虽然她还不足五岁,但是已经表现得比十岁孩子还要懂事。她帮新妈妈劈柴,喂鸡,放羊,现在是春天,她还能学着大人的样子播菜种。她想尽量表现自己,让新妈妈给她多吃一碗饭。今晚要不是闻到肉香,她不会偷偷跑出来。
她是个乖巧得像个奴隶一样的孩子。
“哟,老果子大……哥,你们在烤羊肉吃呀?”是红花的后妈来了。她慢腾腾扭动着腰杆走来,手里拿着一件小衣裳,好像是刚巧经过这里一样。
“嗨,这娃娃,我到处找她呢。天气还这么冷,冻感冒可不好。”女人走到战战兢兢的女孩面前,慈爱地替她穿上一件外套。她把张果子披在红花身上的外套取下来放在一边。
“嚯,你对红花真好呢。”张果子说。他没有抬眼看她,也没有喊她坐下来吃肉。对于她那声讨好的“哥”也没有说一声感谢。但是他举起酒杯说:“要不要来一杯?”
女人自己坐下来了。她在烤架上取下一块羊肉放进嘴里,又接下张果子的酒喝了一口。
“有什么办法!我可是操碎了心。难道不是吗?小的还那么小,她呢,什么事情也还帮不上忙。我也不指望她帮忙。还不大的娃娃,又死了亲妈,我是要真真的对她好点才行。我刚来两年,已经给她做了五双鞋子。我自己生的还一双没做呢。就这样还讨来一些闲话。天地良心!”红花的后妈指着天说。
张果子和陈实都微微笑着点头,好像很同意她的说法。并且给她投去了同情的眼光。
“你果子爷爷的羊肉,可以多吃点。长胖些。”女人撕下一块羊肉放在红花手里。女孩接过肉,呆呆的。
“她穿鞋太费,我是机器也忙不赢啊。天地良心!”她指着女孩的光脚。
张果子和陈实又点一下头,继续喝酒。
女人已经吃下好几块羊肉了。她说话快,吃羊肉更快。不多一会子,酒足肉饱,她准备离去。
“这羊肉真是不错。老果子叔,你每年都吃两三只羊,真有口福。你的牙齿还这么好。我说的可是实话。天地良心。”她拍了拍腿后的灰土,站在原地准备走但是没有动身。
这回她喊他叔。
陈实憨憨地发出笑声。
张果子又往柴堆里添了一把干草,新放上架的羊肉烤出滋滋的响声。先前烤好的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你要是不嫌弃,就把那羊头拿去熬汤吧。也许可以烤来吃。”张果子对红花的新妈妈说。
女人一手提着羊头,一手牵着红花走了。她们的身影一高一矮地走在月色里。看上去,很像一对亲亲的母女。
“这个大嘴巴,你看她刚才那个样子,说得跟真的一样。你看……太他妈能吃了。”
陈实一脚踢开女人啃下的羊骨头。
张果子收起酒碗,他喝得差不多了。“你还来点儿吗?”他准备收拾见底的酒瓶时这样问陈实。
陈实摆摆手,他也喝够了。他二人并没有喝多少,如果红花的后妈不来,酒瓶里应该还能剩下半瓶。
星星已经布满夜空,月亮也白了起来。蓖麻树闪亮着叶子在风中摇晃,好像周身披满了珍珠。高山显得更高了,树影像黑色的棉被盖在山上,白天能一眼瞧见的花朵这时候什么也看不清。张果子依然吸了吸鼻子,好像要吸一口新鲜的花香含着去睡觉。
他们收拾了烤架。熄灭了火塘。
“明天早点起来。去高松树脚下放羊。那里水草好。今晚的肉真不错。”陈实说。
“可能南面的水草好一些。你明天再来吃。”张果子端了剩下的羊肉走进自己的房间。
月亮十分漂亮地挂在当空,但是没有人看它。几只夜鸟鸣叫,混着河水的声音飘荡在村庄。
夏
夏天到了,羊群在悬崖间跳来跳去。它们不仅显出焦躁的情绪,甚至还有些挑食的样子。
两只羊爬到悬崖下不来了。
放羊的张果子在这个时候伤透了脑筋。他像蜘蛛一样挂在悬崖的半腰上。
“你们有本事上去没本事下来,逞你妈的鬼能!”张果子气愤极了。
以前的夏天——多少年前记不清了,为了不让羊群跑到悬崖上,他会赶着它们去远一点的地方。比如东山脚下,那边水草不错,即使在夏天,水边也长满了枸皮叶,只要用镰刀砍下一枝就能刷下叶子喂饱它们。现在不行了,走到不算远的高松树也感到吃力。当然他不承认老,他固执地认为只是自己的腿脚出了点小问题。
“我的脚底生了个小疮,走不远。”他骗他的邻居。他也骗他自己。现在他走路总是一瘸一拐,好像脚底真的生了疮。
好心的邻居每天给他介绍偏方。有人甚至请他脱下鞋子让他们看看疮的样子,好给他寻一些更有效的草药。
现在,两只下不来的羊在崖壁上发出苦闷的叫唤。它们绝望的样子又让张果子生出一股同情。他抬起头看它们,它们也低头看他。阳光把张果子照得喉咙发干,两眼发晕,他的白胡子沾了一片晶亮的汗水,他想安慰那两只山羊,但一句话也说不出。
崖壁底下的羊也跟着叫唤起来,好像在商量什么办法。张果子拖着有些发颤的腿踅过悬崖,揽过山羊抱在怀里,再冒着摔死的风险从悬崖上倒退着下来。他的身子贴着崖壁,单手攀住石头。
张果子的羊摔伤了一只,腿脚流血。这一天下午,他抱着受伤的羊像抱着自己的亲人一样愁闷地回到住处。他细心给羊包扎伤口,再去弄了一些豆子喂它。
“啊,老果子,羊又受伤了么?”陈实摇摇晃晃走来,他走得就像一棵衰败的草。
“嗯。逞能的东西。活该。”张果子嘴里说着狠话,眼睛却充满关怀地望着受伤的羊。
“你的运气已经很不错了,你想一想,已经多少年没有死过羊啦?前年春天,是吧?我们还坐在门口烤羊肉。”陈实回味地用脚在地上划一下圈子,“就在这个位置,大概。”
张果子点了点头。他也觉得这一两年的运气很好。
夏天的河水小了一些,水质清亮,一眼能见到小鱼在河里游来游去。还有水鸟在河面翻飞。不大的孩子们在河里摸鱼,他们拿着自制的鱼竿和撮箕,笑声落在水里,喊声高过水响,裤脚湿了一片。张果子远远地看着他们嬉戏。当他见到这些孩子的时候才猛然觉得自己或许真是有些老了,他摸了
一下胡子,发现它们硬茬茬的有些扎手。
他刮掉胡子。
红花的后妈也到河边洗衣服去了,她路过张果子门前,听见陈实和张果子正在讨论死羊的事情。她十分激动地问:“老果子大哥,你的羊又死啦?”
这回她喊的是大哥。她一会子喊大哥,一会子喊大叔,搞得张果子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哥还是叔。
张果子气得脸有些发红,跳着脚说:“晦气!没死!”
红花的后妈缩了一下身子,张望的眼神从羊圈的方向抽回来。
“天地良心,前年春天的羊肉……”她叨念着,倒退了走开。
陈实咳了咳,转身去看望张果子受伤的羊。
张果子受伤的羊当天晚上就死了。它没有因为张果子赏赐的一碗豆子活下来。晚上风大,圈门上的薄膜被风吹得丝丝响。后半夜,张果子起夜,透着灰蒙蒙的月光看见羊僵硬地躺在地上。张果子这回流了两滴眼泪,但是很快他就收住了情绪,跑进草房子摸出镰刀放在窗口上。他想连夜剐了它。当他把那只羊从圈里拖出来后,已经累得直不起腰。他又把镰刀收回屋里。那只死羊也拖到屋里去了。他看着羊的尸体,整夜没有睡着。
天刚亮,张果子还没有起床,陈实已经来敲门了。他在门外着急喊道:“老果子!你那只受伤的羊不见啦!”
张果子有气无力打开门,现出死羊的尸体给陈实看。
“昨天还好好的不是?”陈实一阵惊讶。
“昨天是好好的。”张果子回答。
他们一起把羊拖去了河滩。这一天下着大雨,这是夏天第三场大雨,因为处于高山,夏天的雨一旦大起来就有了秋天的气味。张果子和陈实都穿上了外套。
这回杀羊没有用镰刀,也不是张果子杀,这回主刀的是陈实,他用自家的菜刀割断了羊脖子。
晚上天气又突然转好了,有星星和月亮。夜空经过一场大雨的洗刷,云彩十分亮白,在星辰的衬托下甚至闪出彩色的光。张果子和陈实把烤架放在沙滩上,他们没有将羊搬到门口去烤。火焰照亮的河水看上去是一种温和的美。
“今晚大概不会有人来了,河边风大,香味会被河水带走的。”陈实张望着说。
夜鸟停在河水中间的大石头上,它们对火光丝毫不感到害怕,在陈实和张果子干杯喝酒时,鸟的歌声在河岸响起。
“如果我们是打鸟的,它还唱么?”陈实兴致勃勃,同时又像个孩子一样捡起一块石子扔到对岸去。他的手太软了,石头还没有飞到对岸已经掉进河里。
“哎。”陈实冷叹了一声。他突然悲伤起来,想起自己的父亲。他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父亲连夜起来杀了一只羊庆贺他的出生。可是现在呢,他的父亲死了,他已经老得和父亲当年一模一样。他摸一摸被柴火烤烫的沙子,抓一把捂在手里。他的眼睛有些模糊了。当他抬起眼皮时,猛地看见张果子门前立着一个矮小的人影,他惊怕了一下,手中的沙子簌簌漏了出去。
“谁?”陈实慌张地问。眼睛眯成线盯着那个人影。那个影子轻微一晃,藏在张果子的柴堆后面去了。
“出来吧。红花。”张果子猜测到是谁了。
红花比前年高了一些,但还和以前一样瘦,所以她的影子就像一根短瘦的竹竿被月光扯得有些变形。但是张果子还是从柴堆后面滑出来的影子认出了她。
“你的眼神还是比我好。”陈实感叹。
张果子脸上颇有些喜色,仰头喝了一口酒,没有回陈实的话。
红花弱弱地从柴堆背后走出来,像一道黑色的月光缓缓来到河滩。她双手拉着一片衣角,不知所措的样子。
“爷……爷爷……”红花吃吃地说。
张果子用酒碗向下指一指,示意她坐下来。陈实很快撕下一块羊肉递给她。
红花的衣袖短短地罩在手弯上,衣服的下半截也盖不到肚脐,这是一件两三岁时候的衣裳,而红花已经六岁多一些。袖口已经破了,线脚像六月的枯草丝丝缕缕的飘着。
张果子垂眼望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她像一只孤鸟一样蹲在沙滩上,虽然是夏天,高山大雨后的空气依然清凉,她的小腿冷得有些发抖。
红花自主地向火堆靠近。张果子微微露出笑容,觉得这孩子还是很会照顾自己,在后妈的眼下,她已经学会了怎么生活。想想这些,张果子又痛惜她的亲生母亲死得未免早了些。
“红花今年长高了不少。”陈实摸一摸孩子的头,爱惜地,好像在自言自语。
张果子咂巴一下烟嘴,没有说话。
红花摊开两只手给陈实和张果子看,她默默地做出想要再吃的请求。两只手心里都有老茧和伤疤,手背上也有,皮肤不是六岁孩子应该有的细嫩,而是粗糙地起着褶子——那些伤疤像大风一样,把周围的皮肤吹皱了。
“红花,你想吃就说出来不要害怕。你也可以自己取来吃。没有人说你。嗯。”陈实低声说。
红花微微缩了一下手,更胆小了。
张果子往酒碗里倒了半碗酒。这是今年夏天他喝得最多的一次。
“你喝得差不多了吧?我喝得少。”陈实摇着碗。
“吆,你们在这儿呢!我说家里怎么没人,河边却燃着柴。”红花的后妈又来了。她还和以前一样鼻子灵光,闻到肉香就扑来了。
“这娃子到哪儿也不说一声,让我好找。”她噼噼啪啪折了一些什么草枝垫在沙滩上坐了下来。
红花微微地向后退了退。她的后妈不让她退到后面躲着。“你坐近一点。不要退到河里冲走了。我又不会吃人。这娃子——天地良心,我还要怎么好?”女人一脸委屈,抓小鸡一样抓着红花的手臂将她提回原来的位子。
“她还是个小娃子,你不能这么提她的手膀子,会脱的。”张果子说。陈实也点了一下头。
女人晃了两下脑袋,“嗯”了一声没有说出话来。她斜眼看了一下红花。
张果子和陈实一般不在红花的后妈面前多说话,比如让她对红花好一点,给孩子吃饱饭,买新鞋,或者添一件合身的衣裳等等,他们从来不敢说。他们怕一旦说出来,女人就要哭泣着跳起来喊“天地良心”。在整个村子,没有人不知道她的天地良心。
“我只是这样说说,你不要多意。人老了,话多。”
“嗨,不老。老果子大哥……”女人还想说点儿赞美的话,但是她抬眼看了看张果子灰白的头发和枯黄的皮肤,以及那双失神的眼睛,后面的话就这样被堵住了。
“都会老的。啊。”陈实模糊地说着,将一块羊肉颤抖地喂到嘴里。这几年,他的手总是不由自主抖得厉害,并且太阳越暖和,他越有困意。整个夏天,陈实有一半时间在打瞌睡。当院墙被太阳烤热的时候,陈实就像老狗一样偎到墙脚去了。
“老石头,你不要啃睡着了。”张果子提醒。
“啊?不会……”陈实摇着脑袋。
张果子感到一阵风从心里走了过去,把他烂在心里的往事都吹翻了。他望着眼前的陈实,怎么也不能将他联系到那个年轻小
伙的身上——为了心爱的人打架,膀子多么有力。
“你服不服!”——张果子还记得那天下午,他们像两只疯狗一样扭打在山坡上,陈实一只膀子压住他的脖子,使他不能动弹。他耻辱地发出像老公鸡一样的嘶叫:“服你我是你孙子!”
说起那场爱情,张果子和陈实都吃够了苦头。他们都喜欢秀芝。在那段日子,他们努力表现自己,对秀芝大献殷勤,她需要撑伞的时候,两把伞挤在了一起,她需要加件衣服时,两件外套又挤在一起,她需要有人送她回家,两个人就挤在一起了。最后为了在姑娘面前表现大度,他们整天咧着嘴和对方说笑,好像他们生下来就没有开怀笑过一样。为了不让对方有机会偷着和姑娘见面,他们二人形影不离,一起放羊,一起回家,连吃饭都端着碗到对方门前晃。
那是个极有闲心的时期。可是现在,张果子和陈实都老了,他们懒散地坐在沙滩上喝酒,听着夜鸟鸣叫,望着远去的流不尽的河水,看着风从对方的白发上走过去。
“你要是撑不住想睡觉,那就早点回去睡。”张果子说。
陈实又摇了一下脑袋,说他一点也不困,只是酒有些喝多,眼皮在打闪。
“我心里清醒得很哩。”陈实抬高了声调。
红花的后妈这时候也叨叨地说上了,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抱着酒瓶子喝了不少。
“去年我的儿子死了,你们是知道的。可是你们知道什么呢!你们只说我对她不好,天地良心,我要是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你们会觉得它红得和山茶花一样!”女人动情地抹了一把眼泪,看着山上黑漆漆的树影,“我为了红花可是操碎了心!难道不是吗?我嫁过来这些年,已经给她做了五双鞋子,我自己生的……现在已经死了,我可怜的儿子!他一双新鞋都还没有穿过。他的小身体用一块破布裹着就抱出去埋掉了。如果他生在好一点的人家,就算他还这么小,也该有一副棺木的吧。他还不会走路就死了。
“她呢,什么事情也还帮不上忙。我也不指望她帮上忙。还不大的娃娃,又死了亲妈。我时常做梦都告诉自己,要真真的对她好点才行。不好能行吗?可是这样还讨来一些闲话。我要是把心掏出来,你们敢说它黑吗?
“我死了儿子过后的几天,我想喝一口水,我说:‘红花,你去给我端一碗水来,我实在渴死了。她不动,她站在那里想了半天才去给我打了小半碗水。你们看,她也只把我当后妈看。但是我能和一个死了亲妈的娃娃计较吗?我没有!我那男人,她的亲爹,说这娃娃命带煞星,克死了她的亲弟弟……我的儿子。她爹吵着要将她送人,我没有同意。天地良心,我要是不把她当亲生的娃,我也会同意将她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