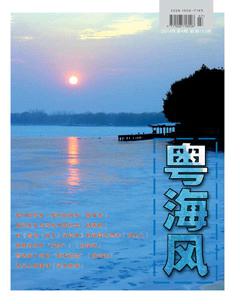就“史实辩正”再答吴永平先生
2007年年初,我从书稿《胡风、冯雪峰的友谊历程》中选择了几个章节组合成一篇文章《友谊的裂变和友谊的回归》(以下简称《友谊》),发表在《粤海风》2007年第3期。吴永平先生在《粤海风》第5期发表《胡风、冯雪峰交往史实辩正——关于叶德浴〈友谊的裂变和友谊的回归〉》一文,对我的文章提出批评,认为“叶文对胡风与冯雪峰交往历史的描述颇多失实之处”,“还对若干重大史实作了随心所欲的解读”。罪名不小。不久前,吴先生出版了一个集子,在刊物上登出广告,挑明,集子里收有《胡风、冯雪峰交往史实辩正——关于叶德浴〈友谊的裂变和友谊的回归〉》一文,再一次向我叫号。我觉得有必要对吴先生的《辩正》作些辩正,看看究竟是谁“对胡风与冯雪峰交往历史的描述颇多失实之处”,究竟是谁“还对若干重大史实作了随心所欲的解读”。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兴趣,也考虑到《粤海风》的篇幅,只谈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前,胡、冯两位是否可以称得上是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的战友。
吴先生认为不能。
论据一:抗战初,二人的友谊就出现问题。证明是1937年7月29日胡风致梅志的信里讥骂冯雪峰的话:“离开上海之前,冯政客和我谈话时,说我底地位太高了云云。这真是放他妈底屁,我只是凭我底劳力换得一点酬报,比较他们拿冤枉钱,吹牛拍马地造私人势力,不晓得到底是哪一面有罪。”8月23日信中又称冯雪峰为“三花”:“三花脸先生愈逼愈紧,想封锁我没有发表文章的地方……”“三花脸先生曾到黎处破坏过,但似乎效果很少。很明显,他是在趁火杀人打劫的。”我在写《友谊》一文时,《胡风家书》尚未出版,无从得知这些情况。但是,就凭1937年的两封信中不太友好的措辞用语,是不能贸然肯定胡风和冯雪峰已经不是亲密战友的。
从1950年开始,胡风和冯雪峰的关系不是由于胡风的缘故发生剧变,胡风称他为“三花”,是充满敌意的。1937年的情况不同。不妨逐一加以分析。先看第一封信。结合8月6日给梅志信,可以知道冯雪峰同他谈话时提到帮助鹿地亘翻译《大鲁迅全集》之事,冯雪峰说他有追逐名利之嫌,这使胡风感到十分恼火。他从1936年11月起一直到1937年8月,花去了这几个月五分之二的时间和精力,帮助鹿地亘翻译。鹿地不懂中文,由胡风逐句口头翻译成日语,鹿地记下来,回去整理一下,成了鹿地的翻译成果。而胡风得到的酬报,仅仅一百数十元。胡风是出于扩大鲁迅遗著影响的一片热诚,才接受了这个工作的。现在,冯雪峰却对他的工作动机作了这样严重的歪曲,他自然无法忍受。一股怨气无处宣泄,发作在给梅志的信中。把冯雪峰称之为“政客”,是因为他在7月初曾参加中共同南京政府谈判的代表团。“拿冤枉钱,吹牛拍马地造私人势力”,显然指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们。这个很偏激的情绪化评语,显然是冯雪峰同博古闹翻之后灌输给他的。现在用来讽刺冯雪峰,一时的气话,当不得真的。再看第二封信。信里谈到冯雪峰封锁胡风发表文章,指的是胡风写文章澄清一些有关茅盾的情况,冯雪峰怕得罪茅盾,不让他发表。胡风因而怒气冲天。这两段文字,都是写在给自己最亲密的爱人信上的,带有极大的即时即地的感情冲动性,没有经过理性的过滤,是非正常情况下的非正常的情绪爆发,不能与正常情况下的谈吐并论。事过境迁,感情平复下来,也就能正确对待了。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胡风听到冯雪峰从集中营出来,就立刻给他寄去《七月诗丛》和梅志的《小面人求仙记》;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在重庆重逢即接连两个夜晚作彻夜长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抗战胜利后胡风为冯雪峰代购机票,愿意同他同机回沪。总之,不从两封信的具体背景出发,是无法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理解的。人与人相处一生,即使是至亲好友,能毫无不快者极少,何况胡风秉性耿直,又是在家书中发发情绪,更是可以理解的了。《胡风家书》出版后,一些友人就担心有的读者可能由于不了解有关背景和胡风的性格,对家书误读,从吴文的情况看来,这倒不是杞忧。
论据二:冯雪峰在南方局为舒芜《论主观》召开的讨论会上说“用心是好的,但论点甚危险”。
吴先生的意思是,胡风对冯雪峰会上的发言不满,表明他们不是“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的战友。
需要看看胡风怎样向舒芜介绍那天座谈会的情况的:
当天下车后即参加一个几个人的谈话会的后半会。抬头的市侩(叶按:指茅盾)首先向《主观》开炮,说作者是卖野人头,抬脚的作家(叶按:指叶以群)接上,胡说几句,蔡某(叶按:指蔡仪)想接上,但语不成声而止。也有辩解的人(叶按:指冯雪峰),但也不过用心是好的,但论点甚危险之类。(《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卷第500页)
胡风参加的这个座谈会是中共南方局文委委员冯乃超主持的。他们名义上是批舒芜的《论主观》,实际上是批胡风。他们不把《论主观》的作者请来参加座谈会,却让胡风参加,就说明了一切。他们硬说《论主观》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就是胡风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详见《胡蜂评论集》《后记》《胡风全集》第3卷)在一片攻击声中只有冯雪峰一个人出来辩解,这就是了不起的“并肩作战患难与共”。胡风称冯雪峰为“辩解的人”,感佩之情溢于言表。吴先生隐去有关叙述,孤零零地挑出一句“但也不过用心是好的,但论点甚危险之类”做文章,做出一个他要做的论断来。实在无法佩服。
所谓“并肩作战患难与共”,指的是在对付外来的敌对势力时步调一致,并不意味着内部战友之间不允许存在某些意见分歧。内部战友间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是很正常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一点常识。
论据三:1945年胡风因在《希望》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而遭到“主流派”的围攻,冯雪峰并没有替胡风说话。
事情偏偏并非如此。前面提到冯雪峰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是替胡风说话的一个明证。再读读冯雪峰那时写的长篇论文《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便更可以明白了。当时,正是“主流派”加紧围攻胡风,胡风处境相当困难的时候,冯雪峰在长文中用了3000字旗帜鲜明地为胡风的文艺理论和路翎的作品辩护,这是直接同“主流派”唱反调的文章。冯雪峰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46年重庆出版的《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上,新中国成立后收在《雪峰文集》第2卷。1957年反右运动批斗冯雪峰时,“主流派”把它作为冯雪峰与胡风勾结的重要“罪证”提出的。吴先生应该看到,为什么视而不见?
论据四: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围攻胡风之时,“冯虽对胡风有所同情,但仍未能无所顾忌地支持他”。
冯雪峰看到《大众文艺丛刊》第2期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后,气愤地说:“难道又要重演创造社的旧伎?我们在内地的人怎么做事!”(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42页)冯雪峰这个表示,就是给胡风很大的支持。吴先生认为这只是“同情”,不是“无所顾忌地支持”,算不得“并肩作战患难与共”。认为必须“无所顾忌地支持”,才是“并肩作战患难与共”,这是犯了“左”倾幼稚病。当时,除路翎、方然分别在《泥土》和《蚂蚁小集》发表长篇反驳文章外,胡风的其他战友都没有“无所顾忌地支持”,难道他们都不是胡风“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的战友吗!
第二个问题:“撤稿风波”和“诗的案件”这两个公案究竟哪一个发生在前哪一个发生在后,究竟是谁犯了“前后倒置”的错误。
1951年批判《武训传》的运动中,张中晓在《文汇报》副刊《文学界》发表了《〈武训传〉·文艺·文艺批评》。箫岱写了《应该从实际出发看问题》予以批评。吴先生认为,张中晓曾写文反驳,稿子被《文学界》掌握最高审稿权的唐弢否掉。结论是,“撤稿风波”发生在“诗的案件”之后。批评“叶文没有细读及考辨已有的资料,竟将1951年7月发生的‘撤稿风波放在前,而将1950年6月‘诗的案件放在后,并说成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事实是,叶文称“撤稿风波”和“诗的案件”都发生在1950年,而且“撤稿风波”发生在“诗的案件”之前,正是细读已有史料的结果。根据的是唐弢1955年的一篇批判“反革命集团”头目胡风及其他“胡风分子”的文章,有关部分如下:
《起点》刊后,胡风分子通过文字所进行的罪恶活动,开始向《文学界》集中,罗洛、罗飞(即杭行)、冀汸等经常在那里传播反动思想。文协上海分会主席冯雪峰同志注意到这一点,召集常务理事会,决定由我参加审稿,理由是我既是常委之一,又在《文汇报》,便于就近掌握。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从17期起,凡是梅林看过的稿子,我再看一遍,又另外组织了一些文章。(字体加粗是引者所为。下同)反革命集团认为这是夺取“地盘”,对他们有意进行打击。在胡风的布置下,梅林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向雪峰提出抗议,一方面叙述自己怎样追随革命,一方面集中力量向我攻击,用他们惯常使用的下流口吻,骂我为“市侩”,故意把含有原则性的问题,拉扯成私人之间的意气。就这样耍手段,撒无赖,啃住不放,最后是要求恢复原有的“权力”。应该说,我们当时的决心不大,缺乏对原则的坚持精神,三期以后,就成立了一个编委会,仍旧让胡风分子梅林去担任执行编辑了。
接着,梅林发表了胡风分子冀汸的长诗《春天来了》,引起读者普遍的不满,纷纷来信,作为编委之一的胡风,以己度硬指这些都是别人化名的攻击。编委会开会,胡风拒不出席。当时决定根据读者意见,由雪峰同志综合成一篇批评,梅林把这篇文章给胡风看,胡风勃然大怒,用红铅笔在原稿上打了许多杠子,声言文章如果发表,便是对他有意的侮辱,使他下不了台。梅林根据胡风的意见在编委会坚持。(下略)(《我所接触的胡风及其骨干分子的反革命活动》,《文艺月报》1955年7月号)
这里有三点值得重视。
一、“从17期起,凡是梅林看过的稿子,我再看一遍,又另外组织了一些文章。”谈的正是“撤稿事件”。“再看一遍,又另外组织了一些文章”,不是表明梅林看过的稿子还得由太上主编唐弢再审查一遍,有的被撤下,这才需要“又另外组织了一些文章”吗!
二、第二自然段开头的“接着”一语,无比明确地表示了“诗的案件”发生在“撤稿事件”之后,而不是之前。这是只要阅读能力正常的人都不致误解的。
三、“应该说,我们当时的决心不大,缺乏对原则的坚持精神,三期以后,就成立了一个编委会,仍旧让胡风分子梅林去担任执行编辑了。”这是说,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主编梅林终于恢复了原有的终审权,唐弢只当了三期的太上主编,就被撵下太上主编的宝座,靠边站了。唐弢担任太上主编的时间是17期到19期,即1950年5月5日到5月19日。梅林恢复主编权力应该就在这年5月下旬。《武训传》的批判发生于1951年夏天。张中晓在《文汇报》副刊《文学界》发表《〈武训传〉·文艺·文艺批评》的时间是1951年6月4日,箫岱的批评文章发表于7月16日的《文学界》。张中晓如果写反驳文章当在1951年7月16日以后。这时唐弢早已靠边站,梅林早就恢复主编权力,根本不可能发生什么张中晓反驳箫岱的文章被唐弢“退稿”的怪事。——即使张中晓写过反驳箫岱的文章而且被退稿,那退稿的也只能是梅林,绝不会是早已被撵下台的唐弢。
唐弢是两次“事件”的当事人,他的话应该是可靠的。
(附带说,《文学界》那时是每周星期二出。第16期是4月21日出的,按理17期应该在4月28日出,但这一天却没出《文学界》,代之以《美术副刊》。这反映了编辑部内发生了“撤稿风波”。事情应当是这样的。在冯雪峰的授意下,唐弢以太上主编的身份,不顾梅林反对,要把已经上版的一篇文章撤下。梅林同冯雪峰、唐弢进行了激烈斗争,17期的出刊不得不延期了。在冯雪峰的高压下,梅林最后只好屈服。这才有了“从17期起,凡是梅林看过的稿子,我再看一遍,又另外组织了一些文章”这一荒谬绝伦的情况。)
吴先生在没有掌握有关史料的情况下,想当然地做了一通文章,生拉硬扯地“论证”出一个“撤稿风波”发生在1951年7月的“神话”来,最后说:“唐弢对该文的处理毋宁说是对张中晓的爱护。”——吴先生太会搞笑了。
总之,不争的事实是,“撤稿风波”发生在前,“诗的案件”发生在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犯了“前后倒置”的错误,“实在让人啼笑皆非”的,不是叶某,恰恰是过分自以为是的吴先生自己。
第三个问题:我是否“轻率地将冯著《回忆鲁迅》第三章定义为‘1952年的迷误,生造出一个胡冯交往过程中并未发生过的冲突”。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三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这里,我想先加一点解释。就是,对于当时的严重的宗派主义现象,我以为鲁迅先生是不能负什么责任的,因为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能证明他本人有什么宗派主义的思想和行动。但那一两年来和他接近的“左联”中的几个文艺工作者以及“左联”外的几个文学者却都有宗派主义的倾向,而且有的是严重的宗派主义者;于是,由于这部分人是和别部分人有对立的情势。则不但这一部分人要有意无意地把鲁迅先生看作自己这个宗派里面的人,并且别一部分人也就会有同样看法,所以,鲁迅先生也就要不知不觉地被牵引到当时的宗派主义的纠纷里面去了。(《新观察》1952年第4期)
我在《友谊》中指出,这是奇文中最出奇的一段,并作了这样的分析:
文章提到一两年来和鲁迅接近的几个文艺工作者是宗派主义者。一两年来和鲁迅接近的文艺工作者并不多。重要是这么几个:胡风、聂绀弩、萧军、黄源、黎烈文。他们的宗派主义表现在何处,只有在攻击他们的小报里可以见到,无如那都是造谣污蔑的谰言。
冯雪峰还煞有介事地指称,接近鲁迅的文艺工作者中有的还是严重的宗派主义者。不言而喻,这指的不是别人,而是胡风。
胡风看到冯雪峰的这篇文章,对冯雪峰看法自然不能不进一步恶化。吴先生说,“胡风并不反感冯著回顾‘两个口号论争时批评左翼文坛内部的宗派主义”。并由此得出我“生造出一个并未发生过的冲突”的论断。
我写《友谊》的时候,《胡风家书》还未出版,现在有了《胡风家书》,完全可以证明我的论述的绝对正确。请看1952年8月3日胡风给梅志的信:
前天晚上,三花约到他家去吃晚饭,客气得很,比上次口气软得多了。但又件件事推脱责任,推给宣传部,连报上那封读者信的内容也说记不得了。就是这么一个卑怯的东西!(中略)说到正在发表的“大文”,连忙说,那和你没有关系!就是这么一个卑怯的东西!(《胡风家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页)
这是胡风就两桩最严重的事向冯雪峰当面摊牌。第一件事,是1952年《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讯》和《文艺报》发表读者来信批评胡风的事。胡风认为这些信都是冯雪峰本人和王士菁写的。虽然路翎曾向他解释《内部通讯》出的时候冯雪峰还没有正式接事,但胡风就是不信,认定这事是冯雪峰所为,甚至写信向周恩来反映此事。这次胡风当面向冯雪峰提出责问,是下决心撕破脸皮的。冯雪峰说责任在宣传部,是实话,但胡风对冯雪峰已经完全不信任,因此认为是“推给宣传部”,并在给梅志的信里骂他“?卑怯的东西”。第二件事便是《回忆鲁迅》中对他污蔑的事。“正在发表的‘大文”,就是指正在《新观察》连载的《回忆鲁迅》。显然,胡风是毫不客气地问冯雪峰,在鲁迅周围的“严重的宗派主义”者是谁,所以冯雪峰“连忙说,那和你没有关系”。听了冯雪峰颇为尴尬的辩解之后,胡风作何应对,胡风在给梅志的信里没提,只发了一句“卑怯的东西”咒骂。凭这些情况,就足以表明吴先生加给我的“轻率地将冯著《回忆鲁迅》第三章定义为‘1952年的迷误,生造出一个胡、冯交往过程中并未发生过的冲突”的“罪状”,是怎样的可笑了。
第四个问题:胡风1952年5月4日给周恩来的信,是否控诉周扬的。
我在《友谊》中说:1952年4月初出版的《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讯》,发表了两封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胡风从友人那里看到,极为愤怒,于4月末草拟了两封信,一封致毛泽东,一封致周恩来,控诉《文艺报》主编冯雪峰。5月4日将给周恩来的信发出;给毛泽东的信不发。吴先生对此大加非难,认为这是“误读”“重大史实真相”:
周恩来于同年7月27日给胡风复信。信中写得非常清楚:“你致毛主席的信我已转去。”另外,胡风给两位领袖的信,控诉的不是冯雪峰,而是周扬。周扬于同年7月23日给周恩来去信,信中也写得很清楚:“翰笙同志把胡风写给您和主席的信,给我看了。信中提到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我感觉他似乎故意将我的话曲解(也许是因为他的神经质的敏感的缘故),把理论上的原则争论庸俗地理解为无原则的人事问题。”换言之,即使此时胡风对冯的态度发生了“恶化”,那也与“读者来信”无关。
这是说,周恩来7月27日给胡风的复信,是回答胡风5月4日的信的。“你致毛主席的信我已转去。”这是证明胡风写给毛泽东的信是发出的,是附在给周恩来的信里发出的。而且“胡风给两位领袖的信,控诉的不是冯雪峰,而是周扬”。
究竟是谁“误读”“重大史实真相”,只要看看周恩来7月27日给胡风的复信就可以了。全信如下:
胡风同志:
五月四日你给我的来信和附件均收阅。现知你已来京,但我正忙碌中,一时无法接谈。望你与周扬、丁玲等同志先行接洽,如能对你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并也可如你所说结束二十年来的“不安情况”。
舒芜的检讨文章,我特地读了一遍,望你能好好地读它几遍。你致毛主席的信我已转去。
致以
敬礼
周恩来
七月二十七日
(这个资料是晓风同志提供的)
胡风5月4日给周恩来的信,周恩来由于工作忙没有及时回信,7月27日在回复胡风到京后的信时,一并回答了胡风前一封的信。
这封信两段文章,需要分别作些诠释。
第一段,谈的是胡风5月4日在上海给周恩来的信。
“五月四日你给我的来信和附件均收阅。”表明胡风5月4日致周恩来的信并未附致毛泽东的信。“附件”,指的是《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讯》,决不是给毛泽东的信。周恩来决不会称毛泽东的信为“附件”的,这是常识。
胡风5月4日寄给一位领袖不是两位领袖的信,就是控诉冯雪峰的。梅志在《胡风传》中写得异常清楚:“ 他听从柏山的建议,写了信,并附了上述《文艺报通信员内部通讯》。他觉得应该相信党。”(《胡风传》第693页)信里附了《文艺报通信员内部通讯》,居然不是为了控诉冯雪峰,而是控诉周扬,太不可思议了。
周恩来对于胡风控诉冯雪峰显然是有看法的。所以劝告胡风:“如能对你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并也可如你所说结束二十年来的‘不安情况。”这是要胡风端正对《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讯》读者来信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他控诉冯雪峰的否定。
第二段,“你致毛主席的信我已转去。”指的是胡风7月19日到北京后写给毛泽东的信。
1952年,决策中枢决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清算,7月19日,他们把胡风从上海召到北京,要他准备检查。胡风想不通,写信给毛泽东,对周扬颇有微词,信是请周恩来转的。周恩来7月27日给胡风的信中,劝告他要认真思考舒芜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问题。这是进一步要求他端正态度,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的文艺思想,为参加专门为他召开的“讨论会”做好准备。这事实上是对胡风控诉周扬的否定。
这封控告周扬的信是请周恩来转的,因而胡风也给周恩来写了一封请托的信。这是应有的礼貌,但也含有向周恩来控诉周扬的意思。阳翰笙给周扬看的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两封信,就是这两封。
吴先生完全误读了周扬7月23日给周恩来的信,以为这两封信就是胡风5月4日在上海写给“两位领袖”的信。终于闹出个5月4日的信不是控诉冯雪峰而是控诉周扬的大笑话。
吴先生批评我“误读”“重大史实真相”。究竟是谁“误读”“重大史实真相”呢?
第五个问题:我在《友谊》中说“夏衍更作出令人震惊的把冯雪峰和胡风捆在一起打的‘爆炸性发言”,是否对“爆炸性发言”中心论题理解错误。
我写《友谊》,写的是冯、胡二人的交往史,理所当然地要抓住这条主线做文章,谈到夏衍的“爆炸性发言”,自然也要突出发言中把两个人捆在一起打的内容。在这样的要求下,在提到夏衍的“爆炸性发言”时,加以“把冯雪峰和胡风捆在一起打”的定语,根本扯不到什么“误读”“重大史实真相”上去。吴先生居然从我的这个定语里读出是对“爆炸性发言”的中心论题的概括,是主观武断。我在列举把胡、冯二人捆在一起打的事实后,这样说:“综观夏衍发言,中心意思就是一个,以《答徐懋庸》一文是冯雪峰‘用鲁迅名义写的为由头,否定这篇重要文章是鲁迅写的。”“夏衍他们把鲁迅的《答徐懋庸》这篇文章作为冯雪峰‘用鲁迅的名义‘写下的,从而扣上一系列帽子,什么‘与事实不符,什么‘缺席判决,放肆地把一桶桶污水泼到鲁迅身上。”这难道不是对“爆炸性发言”的“中心论题”的概括吗?“误读”云云,纯属无稽之谈,不值识者一笑。
第六个问题:冯雪峰的《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一文是否对周扬有利,甚至可以看到其中“友谊的信息”。
为了证明冯雪峰的这个材料对周扬有利甚至可以看到“友谊的信息”,吴先生举出了不少“证据”;然而所有的“证据”都是站不住脚的。只要用冯雪峰材料中的话一照,虚妄立显。限于篇幅,这里只摘录几个片段:
鲁迅认为周扬等人早已经要放弃革命文学的主张,急于要同敌人和形形式式的叛徒、叭儿狗们“联合”了。
他说:“‘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
他又说:“还提出‘汉奸文学,这是用来对付不同派的人的,如对付我。你等着看吧。”
周扬在攻击鲁迅的同时,也攻击我;从他知道我到了上海以及提出新口号的事同我有关的时候起,就散布关于我的谣言,例如说“假冒中央名义”“钦差大臣”“勾结胡风”“假冒鲁迅名义”等等。(《新文学史料》第2辑)
哪有半点“有利”的影子?哪有半点“友谊的信息”的影子!吴先生太热衷于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轰动效应了!
我觉得,吴先生看问题和一般人颇为不同,而且自信心也特强,强不知以为知,令人啼笑皆非。他送给我两顶大帽子,一曰“历史的描述颇多失实之处”,一曰“对若干重大史实作了随心所欲的解读”,可惜的是,帽子太大了,我无福享用,倒是戴到吴先生自己头上,不大不小,极为合适。
(作者单位:大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