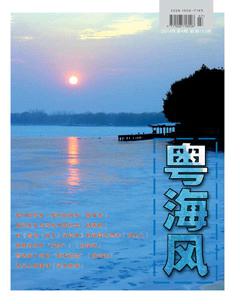鲁迅在广州的“别有追踪”
陈漱渝
1927年1月18日,鲁迅抱着梦幻来到了羊城,刚经历了一番海上风涛的他又经历了另一番陆上风涛,原来的梦幻又在梦境中被放逐了。
鲁迅跟他的爱人许广平是1926年9月2日在上海分手的:鲁迅乘“新宁”轮由上海赴厦门;许广平则于同日乘“广大”轮由上海回到她的故乡。当时广州政治风云诡谲多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内部实际上已经分为三派;一派是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具有双重党籍的人士;二是真心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三是反苏反共的右派分子。鲁迅是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者,也亲近共产党人,但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保持了政治上的独立性。许广平在女师大学生运动期间已成为国民党左派成员,履行了组织手续。她在1926年12月27日致鲁迅信中说:“我之非共,你所深知,即对于国民党,亦因在北京时共同抵抗过黑暗势力,感其志在革新,愿助一臂之力罢了……”(《两地书·一一五》)。然而许广平回到广州之后,就被推到了政治汹涛的风口浪尖。
1926年9月8日,许广平来到位于广州莲塘路的广东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报到,担任该校的训育主任兼舍监。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全广东的教育机构一律进行党化教育。广东第一女师训育主任的职责有十七项之多,其主要职能就是注重学生风纪,宣传党义,让学生“信仰国民党的党纲,作孙文主义的信徒,努力实行国民革命,以求中国之完全独立与自由。”(毅锋:《党化教育与革命》,载1926年5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许广平之所以能够担任这一职务,因为她有参加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经历,也因为当时广东教育厅厅长许崇清是她的堂兄。
许广平上任之后所做的一件快意之事,就是先后开除了两个右派学生的头目。但是校内八十多个右派学生迅速反扑,列队到省政府教育厅和财政厅闹事,要求撤换校长,并辱骂许广平是共产党的“走狗”。1926年年底,国民党内的很多左派领袖人物随政府迁到武汉,广东省的右翼势力更为嚣张,使许广平的工作极难开展,如同“湿手捏了干面粉”。继校长廖冰筠于1926年11月17日辞职之后,许广平也于12月16日辞职,拒绝接任女师校长之职,准备到中山大学担任鲁迅的助教。
大约在1926年3月至7月,郭沫若担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文科学长,曾提议聘请鲁迅担任教授。郭沫若参加北伐之后,中共广东区委为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又派恽代英、邓中夏等负责人跟担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的戴季陶进行谈判,条件之一就是要求聘请鲁迅来中山大学主持文学系。慑于当时中山大学左派力量的强大,学校当局不得不接受这一条件,发出了催促鲁迅来粤“指示一切”的电报。鲁迅在收到中山大学聘书两个月之后,毅然辞去厦门大学职务,奔赴当时被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非常注意做团结鲁迅的工作,专门委派了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磊等跟鲁迅联系,把《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党团刊物经常给鲁迅送去。陈延年指出:鲁迅是彻底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应该做好他的工作,团结他,跟右派斗争。他还特别嘱咐毕磊:“鲁迅是热爱青年的,你要活泼一点,要多陪鲁迅到各处看一看。”3月下旬,陈延年又亲自会见鲁迅,从此鲁迅跟我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然而,如果把鲁迅奔赴广州单纯理解为追随革命,那就会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1926年12月2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明确表白:“我并非追踪政府,却是别有追踪。”十分清楚,“别有追踪”就是追踪许广平的足迹。鲁迅在厦门任教期间,饱尝了恋人相处异地的相思之苦,许广平又不断写信鼓励他来广州,说广州情形虽云复杂,但民气发扬,思想言论较为自由,“现代评论派”在这里立不脚。这就更坚定了鲁迅离开厦门大学的想法,哪怕跟许广平同在一校任教也不回避。他在1927年1月2日致许广平信中再次表白:“我近来很沉静而大胆,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大约得力于有一个人的训示。”更何况中山大学副委员长朱家骅多次致信致电鲁迅,承诺月薪280元,还当设法增长,聘任无期限;除担任全校唯一的正教授外,还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以及担任由傅斯年等五人组成的中山大学“组织委员会”委员——这是鲁迅历年在高校的最高任职。
鲁迅到中山大学后,首先被安置在大钟楼西面的楼上——这是学校最中央最高的所在,据说非“主任”之类是不准住的。但是这里并非理想的工作和休息处所。夜间,常有头大如猫的老鼠纵横驰骋。清晨,又有工友们大声唱着他所不懂的歌。教务主任的工作是异常繁忙的,因为“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一类问题,以及为了考生是否应该录取所发生的无休止的辩论。更何况他还要亲自开设必修课和选修课,分别讲授文艺论、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这就常常使他“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把时间看得比性命还宝贵的鲁迅,不禁感到人是多么不情愿地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啊。但是,为了把中山大学办得像点样子,鲁迅并无怨尤。
这时,由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裂痕加深,握有中山大学领导权的国民党右派不容许鲁迅实行他进步的办学主张。他们特意任命后来成为国民党要员的傅斯年兼任文科主任,使他行政上位居鲁迅之下,但教学上又有权制约鲁迅,造成互相牵掣的局面。还有一些原来在舆论上攀附北洋军阀的“正人君子”,在北伐战争的高潮中纷纷南下,投机革命。他们的势力也蔓延到了中山大学。鲁迅预感到中山大学的情形难免要跟厦门大学差不多,甚至会比不上厦门大学。3月29日,鲁迅搬出中山大学大钟楼,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这里远望青山,前临小港,小港中是十几只疍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
不料,鲁迅刚到广州三个月,广州军事当局就奉蒋介石训令,在4月14日午夜密谋策划又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5日凌晨,佩戴白布蓝字臂章的军警向我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和农军发动突然袭击,大肆通缉、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山大学也遭到大搜捕,抓走了四十余人,其中包括常与鲁迅联系的毕磊、陈辅国。毕磊是14日晚来中大布置工作的,15日凌晨未及走避,不幸被捕。由于全市一日之中被捕多达两千四百余人,除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外,南关戏院、明星电影院等公共娱乐场所也成了临时关押所。一时间,腥风血雨,羊城在血泊中挣扎。
白色恐怖的魔影也笼罩到了鲁迅身边。15日凌晨,一位老工友气喘吁吁地跑到鲁迅家,惊慌失措地报告说:情况不好,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涉鲁迅的。他催促鲁迅赶快潜伏起来,免遭不测。但是,鲁迅并没有听从这位心地善良的老人的劝告。他不顾当晚彻夜未眠,冒雨赶赴中山大学,亲自召集并主持主任紧急会议,呼吁学校竭尽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一场看不见刀光剑影的战斗,就在这次会议上短兵相接地展开了。
鲁迅以教务主任身份坐在主席座位上,中大委员会副委员长朱家骅坐在鲁迅的正对面。鲁迅首先说:“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出面担保他们,教职员也应该主持正义,联名具保。我们还要知道为什么逮捕学生?他们究竟有什么罪,须知被抓的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批啊!”朱家骅闪着阴冷的目光,用威胁的口吻说:“关于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跟政府对立。”鲁迅反驳说:“学生被抓走了,是公开的事实。他们究竟违背了孙中山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哪一条?”朱家骅倚势压人,说:“中大是‘党校,党有党纪,在‘党校的教职员应当服从‘党,不能有二志。”鲁迅继续据理驳斥说:“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不惜发动全国各界罢工罢市营救。现在学生无辜被捕,我们怎能噤若寒蝉?”朱家骅自以为有理地说:“那时反对的是北洋军阀。”鲁迅以凌厉的气势迅速反击说:“现在根据三大政策的精神,就是要防止新的军阀统治。”会场气氛紧张到了无法转圜的地步,与会者大多保持缄默,会议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鲁迅归来,一语不发,不思饮食。次日,他仍然捐款慰问被捕学生。不久,他愤然辞去在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三次退回了中大的聘书。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严酷的斗争中,革命队伍产生了剧烈分化。以毕磊为代表的年轻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头可断,肢可裂,革命精神不可灭”的凛然正气。面对严刑利诱,毕磊丹心似火,正气如虹,连连挫败了敌人软硬兼施的阴谋。鲁迅隐约获悉毕磊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悲愤填膺。他时常向友人提起这位瘦小精悍、头脑清晰的共产党人,并无限哀痛地说:“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与此同时,鲁迅又耳闻目睹了另一些青年截然不同的表现。8月11日,他在广州《民国日报》上读到了三名向军警督察处自首的C.Y(共青团)成员的供词。这些叛徒被血的恐怖吓破了胆。他们跪下卑贱的膝骨,把头匍匐在敌人脚下,用颤抖的双手捧上悔过书,交代自己昔日如何受共产党的“迷惑”“包围”“利诱”“威迫”,乞求用忏悔的眼泪和对革命的诅咒来换取今后的“自由”。9月10日,鲁迅又在上海《新闻报》上剪下了另一篇触目惊心的报道,一个15岁的“赤色分子”,自首之后戴上假面,由军警带领游街。途中如果遇到过去的同志,他便当场指出,这被指出的人也就随即被捕。沿途市民都将这位假面人“视若魔鬼而凛凛自惧”。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英勇牺牲和无耻叛卖,鲁迅的思想受到了巨大震动。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我在广州,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地敬畏了。”
应该感谢两位日本友人,他们为1927年在广州的鲁迅留下了忠实可靠的文字记录:一位是日本新闻联合社特派记者山上正义,另一位是日本汉学家增田涉。
1928年3月,山上正义在日文《新潮》杂志三月发表了一篇《谈鲁迅》,其中介绍了四一五政变之后蛰居在白云楼寓所的鲁迅:“在鲁迅潜伏的一家民房的二楼上同他对坐着,我找不出安慰的言语。刚好有一群工人纠察队举着工会旗和纠察队旗,吹着号从窗子里望得见的大路上走过去。靠窗外的电杆上贴着很多‘清党的标语,如‘打倒武汉政府‘拥护南京政府‘国贼中国共产党等等。在这下面甚至还残存着由于没有彻底剥光,几天前大张旗鼓地张贴的‘联共容共是总理之遗嘱‘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完全相反的标语。鲁迅望着走过的工人纠察队说:‘真是无耻!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去搜索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了。给他这么一说,我发现那倒确是一些右派工会的工人,充当公安局的走狗,在干着搜索左派工人的勾当。”
增田涉原是日本东京大学一位专攻中国文学的学生,1931年春来到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结识了鲁迅,鲁迅曾对这位异国学子谈到了四一五政变后他的思想变迁。鲁迅动情地说:“国民党把有为的青年推进了陷阱。最初他们说,共产党是火车头,国民党是列车;由于共产党带着国民党,革命才会成功。还说共产党是革命的恩人,要学生们一齐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面前行最敬礼。所以青年们都很感动,当了共产党。而现在又突然因为是共产党的缘故,把他们统统杀掉了。在这一点上,旧式军阀为人还老实点,他们一开始就不容共产党,始终坚守他们的主义。他们的主义是不招人喜欢的,所以只要你不靠近它、反抗它就行了。而国民党所采取的办法简直是欺骗;杀人的方法更加狠毒。比如同样是杀人,本来给后脑上一发子弹就可以达到目的了,而他们偏要搞凌迟、活埋,甚至连父母兄弟也要杀掉。打那以来,对于骗人做屠杀材料的国民党,我怎么也感到厌恶,总是觉得可恨。他们杀了我的许多学生。”(增田涉:《鲁迅传》,卞立强译,《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11月出版。)
出现在增田涉《鲁迅传》中的这段话是经过鲁迅本人校阅的,译文系名家据原件译出,无疑反映了鲁迅的真实想法,道明了他为什么从广州到上海之后政治立场会发生重大转变,值得高度重视。不过,这毕竟只是鲁迅这位革命人道主义者在目睹一场“血的游戏”之后的内心感受。如果是一位政治家,也许会从国共两党不同的阶级属性分析双方从联合到分裂的根本原因;如果是一位历史学家,也许会从当时的国内外大背景以及双方思想、理论和政策分歧解析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深刻原因。然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只能写出这种用鲜血凝成的文字: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而已集·题词》)
在鲁迅广州时期的杂感中,有两篇给读者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一篇是《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另一篇是《小杂感》。
《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写于1927年4月10日。当年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直鲁联军纷纷溃逃;3月22日,北伐军完全占领上海。3月23日,北伐军逼近南京,直鲁联军退守徐州、蚌埠。“沪宁克复”捷报传来,号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举行盛大庆典。在喧天的锣鼓声中,鲁迅想到的却是辛亥革命后在南京修建的烈士纪念碑1913年被复辟帝制的军阀张勋捣毁,又想起了诚实谦和的革命前驱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绞杀。他谆谆告诫广大民众:“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他特别提醒革命者,要正视“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的进行。” 鲁迅的预测不幸而言中,表现出他思想的穿透力和见解的前瞻性。就在鲁迅写作这篇杂文的一周之前,即1927年4月2日,李济深、黄绍竑应蒋介石急电邀约由粤抵沪,参与他们的清党密谋。无怪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对工人纠察队大开杀戒,李济深4月15日凌晨也在广州实行戒严,罪恶的枪声立即掩盖了数天之前广场欢庆的鞭炮声。正是在4月15日这一天,蒋介石正式发布了《清党布告》,公开打出了反共的旗帜。
《小杂感》写于1927年9月24日,是一组格言式的杂文,其中最短的只有十个字:“凡当局所‘诛者皆有‘罪。”这就是广州四一五政变后鲁迅的直感,揭露了当时以“党”代“法”、滥杀无辜的黑暗现状。最为特别的是,当时的滥杀与虐杀又往往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所以鲁迅写道:“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当代读者如不了解中国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的那段历史,读到以上这段杂感就会如读天书。而如果了解那段历史,就能感到鲁迅以最凝练的语言对那个时代作了最形象而准确的概括。
那是一个争夺革命话语权的时代。中国国民党在倡导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倡导阶级革命,中国青年党在倡导全民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在倡导社会革命……革命在知识界是一种普遍崇尚的美德。正如梁启超所言,革命是“人生最高之天职”。而国共两党采用的革命手段主要是暴力。无政府主义者鼓吹暗杀,也是暴力。中国青年党反苏反共,只是没有军队,也同样崇尚暴力。暴力革命伴随的自然有牺牲:有人为真理、为信仰而献身,有人却稀里糊涂被卷进了革命漩涡,又稀里糊涂丢掉了性命。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或反革命的”。在革命与反革命、“红”与“白”处于二元对立状况时,不承认有“第三种人”存在,也不愿为“第三种人”提供一条狭窄的灰色生存地带。在这种特殊的年代,的确是“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之名以行!”
除开创作杂文,鲁迅在广州的八个多月当中还发表了十余次讲演。鲁迅1927年1月25日日记:“下午往中大学生会欢迎会,演说约二十分钟毕,赴茶会。”这次活动实际上是由中共广东区委所属的中山大学支部主办,陪同鲁迅登上讲台的就是共产党人毕磊。鲁迅的讲词曾于1月27日、2月7日、2月8日分三次登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专刊,记录者为林霖,后收入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一书,1927年7月由北新书局出版。不过,钟敬文编辑《鲁迅在广东》一书时,把有关鲁迅和听众互动的文字删掉了。据1927年2月8日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专刊第28期报道,鲁迅讲毕,有一位听众即席发言说:“我得到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如同得到了爱人。”鲁迅随即打断他说:“爱人是爱人,鲁迅的著作是鲁迅著作。有了爱人是不能革命了,若以鲁迅的著作来代表爱人,恐怕不太好。有了爱人的人,只管看鲁迅的著作,这是不要紧的,看了以后,再去恋爱也可以,否则,用鲁迅著作代替爱人,那恐怕于现代青年有害。”鲁迅幽默的回应,在现场引发了一阵笑声。
其他经鲁迅校订并结集的讲演有《革命时代的文学》,《读书杂谈》(均见《而已集》),《中山大学开学致语》(见《集外集拾遗补编》)。最长也最特别的一篇学术性讲稿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这是鲁迅在国民党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讲演会”上的讲演,许广平现场翻译成粤语,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欧阳山(罗西)和邱桂英记录,又经鲁迅本人审阅。1928年12月30日,鲁迅在致老友陈濬(子英)信中说:“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
那么,鲁迅借谈魏晋事寄寓了什么人生感慨呢?传统的说法是:鲁迅借司马懿篡位,影射蒋介石背叛新三民主义,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但事实上,司马懿只是这次讲演中偶一提及的人物,绝非论述中心。鲁迅致陈濬的同一封信中提到,当时的著作者“实处荆棘”,而历史上志大才疏的孔融终不免为曹操所杀的厄运,可谓前车之鉴。据此推断,鲁迅借古喻今的着重点,是在思考具有叛逆性格的文人,身处乱世应该如何安身立命?如何能够在党派纷争、杀机四伏的环境中“师心”“使气”,获得心灵的最大自由?“师心”就是写出“心的真实”,“使气”就是慷慨悲歌,无所顾忌,使文章充满情感、气势和力量。
众所周知,魏晋时代是一个内忧外患、政治高压的时代,但同时又是中国古代精神史上最为解放、清峻通脱的时代。所谓“风度”,其实就是一种形神融合的精神风貌。鲁迅“破帽遮颜过闹市”,跟魏晋士人宽衣博带、不修边幅的做派相互吻合;鲁迅“漏船载酒泛中流”,跟魏晋士人在风涛险恶之时仍能昂首向天的精神一脉相通。“躲进小楼成一统”——这是鲁迅独战时运用的“壕堑战”战术,克服了魏晋士人在“出仕”与“归隐”之间身份选择的纠结。“管他冬夏与春秋”,就是魏晋士人“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 的任意率性,这是一种生命意识和个体意识的最高表现。以上诸方面,都充分体现出鲁迅后期对魏晋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鲁迅来广州之前,当地报纸副刊刊登的多是用粤语写成的无聊小品,教材中充斥着陈腐的文言文,整个文坛像沙漠般沉寂。为了推动南中国的新文学运动,鲁迅在广州期间还支持组织了南中国文学会,并创办了北新书屋。据1927年3月16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自文学巨子鲁迅先生南来后,广州青年对于研究文学之望,甚为炽盛。中山大学周鼎培、林长卿、倪家祥、邝和欢、邱启勋,广州文学社杨罗西、赵慕鸿、黄英明、郑仲谟等,拟联同组织南中国文学社,以发扬南中国文化,出版定期刊物,名《南中国》,由鲁迅、孙伏园诸先生等提挈一切。”报道中的“杨罗西”即欧阳山。他在《光明的探索》一文中回忆了3月14日下午在惠东楼太白厅召开成立会的情况。他说,当时的目标是在广州文学社的基础上,吸收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南方省份的文学青年,把影响扩展到整个南中国(1979年2月20日《人民文学》第2期)。会上有人怕他们的同人刊物不好卖,如果赔本,出了一期之后就难以接着出了。鲁迅出了个主意,他说:“要刊物销路好也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就在南中国文学会成立的同月25日,广州惠爱东路芳草街40号二楼出现了一家北新书屋,主要出售北京北新书局和未名社的出版物。这本是孙伏园先生的创意,但开张前夕他却跑到武昌编报纸去了,只剩下了两间空荡荡的房子。鲁迅掏腰包付了60元房租,书店终于跟广州读者见了面,而且门庭并不冷落。鲁迅得意地说,好在中山大学没有欠薪。即使赔钱,他也希望广州这片文艺沙漠能出现一片绿荫。
回想起从厦门到广州的经历,鲁迅觉得状如橄榄:到厦门之初冷冷清清,离开时却盛大欢送;到广州之初是盛大欢迎,1927年9月27日离开时则冷冷清清。然而在这八个多月的短暂日子里,鲁迅却在这块商人和军人主宰的国土上留下了坚实的足迹,撒播了新文化的种子。
(作者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