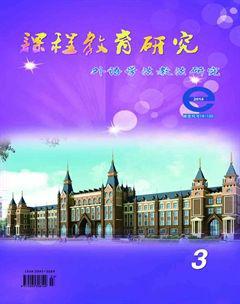古汉字中“象形”“指事”“意会”造字方式对平面设计影响的研究
吕诚
【摘要】我们从古汉字的设计思维得到的对平面设计的启示,最重要的是其背后对“象”与“意”的平衡把握中所体现的对设计行为宏观理解:设计不仅仅是物的设计,更是用最优的路径解决问题的统筹安排。
【关键词】象形指事意会设计思维平面设计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3-0025-02
一、“六书”与平面设计
思维的发展产生语言,语言的符号化形成了文字。每一个跨越过程都是一次相对具象的概括与提炼。人类在上述的提炼过程中遵循了一定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价值取向。从信息传达的过程上说,文字将语义信息通过具体图形准确传达,这种方式就是平面设计。
在汉字的长期发展中,六种汉字结构逐渐被后人以清晰的方式归纳提出: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说“六书”是“造字之本”。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从顺序上说象形、指事、会意才是可以用来产生新的汉字的造字之法,而转注和假借是不能产生新的汉字。故而本文研究的内容为隶书之前的象形、指事、会意字。
二、“象形”“指事”“意会”造字方式对平面设计影响的研究
(一)象形字的图形语言与造字思维特点的分析
1.凝练的线条与关系性的图形语言——“象形”造字方式的形而下层面分析
象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顾名思义,象形字就是按着实物的形体,用笔画概括性的描绘出来。为了能够更好的通过具体的文字图形表现客观世界与主观理解,象形字在创制上,就要求象形字的笔画尽可能的凝练;从主观思维方式上,就要求人们用整体的关系性图形组合方式。
我们可以得到:
(1)象形文所描画的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实物,其中包含了先人以联系的方式看待事物的特点,而达成这样的目标,就必然用以简化的灵活的线条。
(2)象形文字是以一种“关系性”的图形构成状态来传达其背后的意义的。当一个图形符号的抽象化程度越高,则这个符号在承载语义的宽度上就越广,也为主观情感的灌入提供了宽广的空间;而以整体的、关系性的构图方式出现,则为笔画造型打开的无限可能。
正因为象形文字在图形层面上的这两种特点,所以其传递出的设计上的形态美感,就不是一般图案花纹的形式美、装饰美。因为“一般形式美经常是静止的、程式化、规格化和是去现实的生命感、力量感的东西”[1],而它是富含“生命暗示的”。
2.“象”与“意”的整体把握——“象形”造字方式的形而上层面分析
先人在文字的使用中,体会到了图形在表达抽象意义上的局限,而这种局限是不能通过细致描画来解决的;但同时又感受到了客观事物之间具有的抽象联系,而图形正可以通过对要表达事物与其周围环境的抽象描画,在相互的关系中,反过来确定事物本身意义。正是在这种“象”与“意”矛盾发展中,文字的创制最终上走向了既非如古埃及象形文字一般的复杂描画,又非如拼音字母的纯抽象图形,而是用凝练化的线条、关系性的构图方式表现具象或抽象的事物。
至此,“意”传达的客观需求与“象”表达范畴的局限,终于在整体的观察视角中整合到了一起。我们可以得出:在象形字创制与发展的过程中,对事物信息之“意”与图形表现的“象”之间的矛盾的思考,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系统化诞生的源头,并到了清代总结归纳出“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无非一阴一阳之和而成。尽器,则道在其中矣。”[2]
(二)指事字的图形语言与造字思维特点的分析
1.“指事”造字方式形而下层面的分析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历史上对指事字的理解历来分歧很大,但公认的观点为:“指事字就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再加个指事符号作标记的一种字。”
指事符号往往就是一个“点”,其添加的位置,表现出先人对已知世界(特别已经形成象形字的实物)的一次认识深化。在许慎的定义中给出的例子是“上”“下”,其他的例子则更好的说明这一点,如“本”“末”:它们的本体都是象形字“木”字,但在“木”的底部添加了指事的符号,就表现了树木的根,即为“本”;而在“木”字上端添加就表现了枝叶之“末”。
2.“象”与“意”的平衡取舍——“指事”造字方式形而上层面的分析
指事字在六书中的数量是绝对少数,因为绝大部分字都不需要用指事的方式:如果单纯的表示实物,则可以用象形的方式,反之表示抽象的事物则可以用会意的方式替代。
从古汉字发展顺序的角度上来说,指事字打开了汉字用具象图形表达抽象概念的大门,为后来的意会字的诞生进行了过渡与思维方式的铺垫。如果说象形字暗含了由“象”表“意”、寓“意”于“象”的整体观,那么指事的诞生则在具体的方式上完成了这种可能。如上文所举例,“本”“末”不仅具有方位概念,也具有价值概念,指事字正是通过对象形字图形的补充,通过具象的实物传达了抽象的意义。
(三)意会字的图形语言与造字思维特点的分析
1.象形文字图形的组合——指事字形而下层面的分析
《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定义是“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意思就是在图形上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组合在一起,用以表达抽象的意义。左民安在《细说汉字》中将会意字主要分为两类:“同体会意与异体会意”[3]。“同体会意”就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的象形字组成新的会意字。“森”“众”“淼”“惢”就是这类汉字;“异体会意”相较于第一种,就是用不同的象形字所组成的会意字,这种会意字在占会意字总数中的绝大多数。如“疆”,字的左边是丈量土地的器具“弓”,而右边是“田”,而在田与田之间有一横分界线,其表达用器具丈量土地划定田界。疆的本意是界线,而后将其引申为抽象事物的边界。
2.象形组合的逻辑推导——指事字形而上层面的分析
会意字在造字方式上反映了,在图形意义的传达中,格外注重人的逻辑推导。这也是图形能够表达主观情感的原因。而这一点是象形字和指事字中业已萌芽但未曾表现出来的,前者体现了相对被动的描述,而后者却体现出了相对主动的逻辑推导。
“象”通过组合扩充了自身的表“意”能力,而“意”通过“人”逻辑推导的介入,将“象”的语义丰富了起来。从此,象形不再仅仅表达自身实物的信息,也不再通过指事符号表达有限的抽象概念,而通过象形组合的方式,将人的思维推导过程拉入了图形的解释中,极大了丰富了图形对语义的承载能力。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也正是如此,会意字反过来更加深化了先人对“象”与“意”的统一的认识。
(四)“象形”“指事”“意会”的设计思维对平面设计的影响
1.象形造字方式对中国平面设计的影响
象形字造字方式带给设计的启示,在于其解决“象”、“意”矛盾中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
(1)平面设计的图形语言与其语义信息之间的整体把握。
(2)平面设计产品对“产品—商品—废品”流通环节的整体把握。即,具象的产品与抽象的流通规律之间的整体把握。
在象形字所体现的平衡“象”与“意”关系的设计思维中,“意”不仅仅是商品本身所要传递的信息,更包含了对人与自然的考量;具体对平面设计而言,就是平衡产品、平面设计的“象”与“意”、消费者、环境(产品投放环境与自然环境)、废品等关系。这种以联系的、统筹的观点看待平面设计的特点,将使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上去看待平面设计在商品生产环节与销售链条上的自身定位与意义。而这种设计思维真正意义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器”和谐特点。
endprint
从更大的角度看,所谓平面设计、工业设计、环境设计都是在历史的发展中细化出来的,而它们在解决具体的问题时,或许只有技术应用与成品物质形态上的的不同,但在平衡人、人造物、环境的关系中,在更优化的解决问题的追求中都是一样的。
2.指事字的设计思维对平面设计的影响
在指事字对会意的转变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图形语言与抽象语义之间的平衡与取舍。指事带给平面设计的启示有如下几点:
(1)从生理角度上说,视觉形式太过则会视觉疲劳。
(2)从视觉语言的局限性的角度上说,图形不可能完全准确的表现出技术信息与情感,相反的,唯有在图形语言相对清晰的程度上留有余地,才能最大程度上将语义信息与人的主观思维进行充分的交流,以至逐渐准确。反之,如果视觉语言过于弱,那么视觉上也平淡无奇,其语义就不明确。
(3)从平面设计的角度上来说,对图形语言的解读本身就不可避免的带有语义的模糊性。但恰恰是这份的可控的模糊性,才给平面设计中艺术成分的灌入带来的足够广阔的空间——如果只为求“意”的详实与精确那么用科学的数理语言即可。中国传统设计中所散发出的那份意味深长形式美感与意境,正是这份模糊性使然。
3.会意字造字思维方式对平面设计的影响
会意字所表达的抽象概念,并不由组成会意字的单个象形字来传达。对“异体会意”而言,组成文字的几个象形字,并非牛马不相及的两个实物,它们具有内在的语义联系。正因为如此,组合起来形成的图形语言具有逻辑上的推导性质,这个推导的结果就是会意字所要表达的意思,而这个推导过程是需要人的思考赋予的与补充的。
假设象形字A与象形字B组成了会意字AB,那么与其表达意思C之间形成的关系就是:AB=A+B+——>C。
这种语言的传达方式是迂回的,但传达的语义却是相对清晰的。在迂回的图形表述与人的主观推导之间,有着广阔的思维空间、情感空间。这种启发、引导思维过程的图形语言方式,是“意境”产生的必要条件,也是所谓“中国风格”根本特点之一。因为意境存在于人们的思维的构建中,它不存在于客观的世界,它是人们借景寓情、寓情于景的产物。
(指导老师: 舒湘鄂)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2]王夫之.《思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左民安.《细说汉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