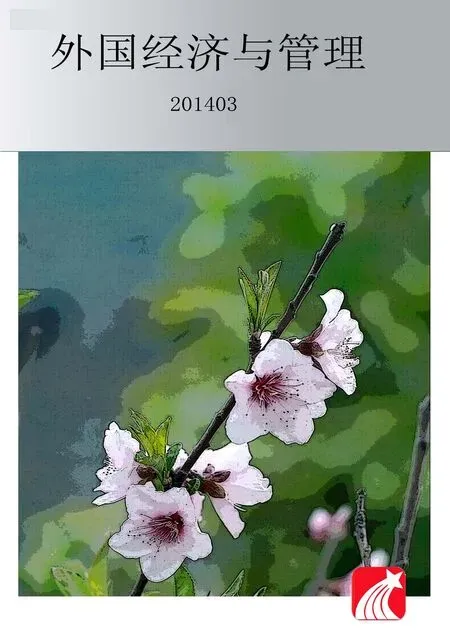合作式谈判研究述评与展望
苏 勇,程骏骏,吴 展
(1.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200433;2.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商学院,悉尼NSW 2006)
一、引 言
随着中国持续融入全球经济版图以及我国境内外商业活动的日渐频繁,经营者正遇到越来越多的人际、团队内外、部门和组织内外的商业谈判问题。这一现实对我国在谈判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显见的需求。当个体或组织间涉及利益冲突时,谈判是普遍用于解决争端的一个决策过程(Pruitt,1981)。合作式谈判行为(cooperative negotiation behavior)一方面受谈判过程中各类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影响整体谈判进展,是谈判中非常重要的行为现象。在谈判中,参与者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来提高评估双方行为的准确性,打破谈判僵局,最大化联合收益,并为深化伙伴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Thompson,1991;Imai和Gelfand,2010;O’Connor等,2005)。合作式谈判可以给组织带来丰富的商务机会,熟悉合作式谈判的相关技巧也能够提升经理人商务沟通的绩效。
研究谈判行为的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曾将其他领域的相关理论引入谈判研究中,用以解释谈判者行为背后的内在规律。基于这些理论思想,管理心理学家设计和实施了许多行为实验,考察影响谈判行为过程的各种因素,丰富了谈判学研究。针对合作式谈判,Pruitt 1981年在其《谈判行为》一书中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探讨了此前二十几年的合作式谈判行为的实验研究成果。此后三十多年来,该领域的相关实验成果仍然层出不穷,发展甚为迅速。然而,各个谈判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各不相同,考察的相关变量之间联系较弱,导致实证成果散落于各种理论和不同视角之间。这表明,只有通过系统性的评述才能理清这一领域的发展脉络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本文的目的在于,综合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合作式谈判的实验研究所依据的视角、理论和研究成果,讨论合作式谈判机制研究从静态到动态的演变,分析现有研究的趋势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考察了1980-2012年间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的关于合作式谈判的实验研究。我们将“谈判”作为文章题名关键词,检索到216篇谈判研究文献,然后通过人工查看摘要的方式,选取那些从被试行为层面测量过合作式谈判行为现象的研究报告。由于在很多研究谈判者行为策略的文献中,合作(或整合)与竞争(或分布)(cooperative or integrative vs.competitive or distributive)两种谈判行为特征被假定为分处在同一维度的两端,因此这些报告的共同点是测量过至少一个以上的行为特征。基于此,我们将27篇核心实验研究报告及其中32项独立实验作为论述的主要证据①。由于每篇实验研究报告主要聚焦于谈判过程中的一到数个因果关系和若干理论,通过将这些关系和理论集中起来分析,我们可以从相对宽广的视野对合作式谈判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提炼出相关实验所基于的视角差异和理论流派。
二、国外合作式谈判研究述评
(一)合作式谈判:信息、技术与协议
谈判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最早由博弈论专家和行为经济学家进行,他们将谈判各方视为完全理性经济人,即能够充分理解和分析所获得的信息,并能采取最优对策。然而,在真实世界中,谈判各方都是受内外部条件制约的社会人,谈判者行为不可能遵循“最优路线”,因此最终的收益往往是每次谈判任务中支付矩阵(payoff matrix)上的次优解。于是从心理角度分析谈判行为的研究范式随后兴起:社会心理学家将谈判者视为社会人,借助科学实验探讨谈判者个人、外部条件和谈判任务结构等因素对谈判过程和收益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谈判行为研究集中于妥协式和竞争式谈判行为,较少涉及合作式谈判(Druckman,1967;Esser和Komorita,1975)。自80年代早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合作式谈判的成因及其影响(Kimmel等,1980;Carnevale等,1981;Grigsby和Bigoness,1982)。与竞争式谈判行为不同,合作式谈判行为现象包括主动向对方寻求信息并提供关于己方偏好和利益的信息,回报对方的让步行为,在不同议题之间提供相互支持,创造合作的谈判氛围,减少竞争行为,创造性地寻找新的解决方案等。其目标是为了完成令各方满意的互惠性协议(Graham等,1994;Pinkley,1995)。合作式谈判中有三个关键要素:有关各方利益偏好的信息,实现双赢的谈判技术(如扩大馅饼法、滚木法等),最终的整合式协议。
(二)研究视角:动机、认知与综合导向
谈判行为的实验研究视角可大致分为“动机(motivational)导向”和“认知(cognitive)导向”两个流派,合作式谈判行为的研究也如此。动机导向的研究基于谈判者对自己和对方利益的不同关注程度,而认知导向的研究基于谈判者处理信息的缺陷以及行为的不完全理性(Trötschel和Gollwitzer,2007)。2000年以后,陆续有研究文献整合了这两类视角,研究者基于动机流派和认知流派的相应理论思想和成果,对合作式谈判相关变量间的关系进行了综合考察。
动机视角的研究文献主要考察谈判者自身倾向、情境因素与双方互动机制是怎样影响谈判者行为和谈判收益的。该视角的文献着眼于影响谈判资源分配的因素。谈判中涉及价值申明(value claiming)和价值创造(value creation)两类行为过程。无论谈判双方拥有多少资源,都需要在彼此之间进行分配。在此过程中,谈判者的社会动机将产生重要影响。早期研究将社会动机作为一种个体差异来测量,使用社会价值倾向(SVO)作为衡量指标,将谈判者从理论上分为竞争型、利己型、合作型、利他型四种。随后的研究更侧重于情境因素对谈判者社会动机的影响,在实验中操纵被试的社会动机以分别唤起亲社会和自利两类动机。后者的代表性文献包括De Dreu等(1998)对社会动机与谈判行为关系的研究,以及Schei等(2011)对混合动机的研究。
由于动机视角和认知视角的研究文献相互引证较少,两派之间较为隔离。然而在实际谈判中各种影响谈判者社会动机和认知过程的因素都会对谈判行为发挥作用,只从单个角度分析未免偏颇。针对该情形,近年来出现了综合视角的研究文献。例如,De Dreu提出的动机性信息处理模型就是建立在谈判者动机和认知两个心理过程基础上的。综合视角的代表性实证文献所包含的变量范围一般较广。例如,Trötschel和Gollwitzer(2007)对事前行动计划、得失框架及社会动机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表明,增强谈判者亲社会动机并辅以行动计划,可以克服损失框架(loss frame)对联合收益的负面影响;Imai和Gelfand(2010)对文化智商、合作动机、求知动机之间关系的研究显示,文化智商高的谈判者具有高度的合作动机和求知动机,并能通过一系列合作谈判策略实现高收益。以往的跨文化谈判行为研究过分注重各种文化差异的比较而忽视了解决方案的提供,Imai和Gelfand则另辟蹊径,证实了文化智商可以作为提升多元文化情境中谈判人员绩效的一个切入点。
(三)合作式谈判的形成机制:情境与个体因素的综合作用
针对合作式谈判的形成机制,学者们主要关注影响谈判者行为的前因变量、调节变量等。在设计实验时,通过随机化排除不相关变量的影响,能够对一到多个关键变量展开深入的分析,从而确证其影响机制。
谈判者的社会动机是重要的前因变量。实验表明,谈判者的社会动机可以通过情境诱导(如将谈判目标与奖金挂钩)和个体天然差异两种方式作用于谈判行为过程。具备合作倾向或者被诱发出亲社会动机的谈判者同时关注自身和对手的利益,表现出较少的争论和较高的信息沟通频率(De Dreu等,1998),并在面对竞争型谈判对手时也表现出合作行为(Schei等,2011),有助于避免谈判僵局(Trötschel等,2011)。而亲社会动机与谈判者换位思考技巧的交互增强作用,能够促进双方分享私有信息从而提高共同收益(Van Beest等,2011),降低谈判破裂的风险。
诠释水平可以影响谈判者的心理距离,进而影响谈判行为。当实验者诱导被试对某个事物产生较远的心理距离时(高诠释水平),被试对该事物的诠释是抽象、简单、非情境化的;在相反条件下,被试对事物的诠释则是具体而明确的。Giacomantonio(2010)对谈判者的关注点(利益或事项)与诠释水平的高低做了2×2的因子设计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诠释水平和关注点的配合(高诠释水平×对于利益的关注,或低诠释水平×对于事项的关注)可以诱发更多的解决问题行为,这时双方的合作程度都很高。
研究者还发现,谈判者的行为存在性别差异。Kimmel等学者(1980)设计了谈判目标水平和信任度两个变量的2×2组合实验,发现在任何情形中女性都比男性更多地分享信息,并能够准确理解对手的偏好。Kray及其同事(2001)发现,对性别的刻板印象能显著影响不同性别谈判者的谈判方式。当女性明显知觉到这种刻板性别的印象之后,会从心理上产生抗拒,在谈判中会变得更为主动和具有竞争性。有些情境因素则会调节谈判中的性别效应。例如,当各方都明白谈判任务的收益结构时,谈判中的性别差异会被显著地削弱。
个体情绪也会影响谈判者在协商过程中是否愿意保持合作。Forgas(1998)认为,情绪会让谈判者不完全理性,愉快的谈判者更倾向于合作式谈判(如使用“滚木”技巧等)。这一研究结果与Carnevale和Isen(1986)的早期研究相似,后者表明正面情绪和避免眼神直接接触都能降低双方的争执程度。Van Kleef等(2004)则考察了情绪的人际影响。他们发现,谈判一方并不会因为对手的快乐情绪而增强自身的合作行为;相反,如果对手显露出愤怒情绪则更容易做出让步。
合作式谈判的形成也受个体内部或外部其他因素的影响。有过失败经历的谈判者在将来谈判中的合作意愿较低(O’Connor等,2005),而在谈判前向参与者提供合作式整合策略(integrative tactic),谈判者在沟通过程中更倾向于合作式谈判(Weingart等,1996)。谈判者所代表群体的合作性对于谈判代表会产生直接作用,代表鸽派(合作倾向)利益的谈判代表的开价相对于鹰派(竞争倾向)代表更为温和;同时,在被代表的群体中鹰派成员相对于鸽派成员对谈判代表的行为具有更强的影响(Steinel等,2009)。
日益丰富的语文课程课外学习资源,如工具书、各种图书、报刊、电影、电视、网络等,为学生的学和老师的教提供了广阔的利用空间。但在对课外学习资源利用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语文课程课堂教学资源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作为课堂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的课文插图的作用。教师对教材中精美而又符合文本内容的课文插图合理利用,既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又有利于提高小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对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培养观察、想象和语言表达等能力也大有裨益。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谈谈在语文课堂中对插图利用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四)合作式谈判对结果的影响:经济收益、协议质量与主观结果
由于西方研究者一贯重视谈判的经济收益,因此大多数研究都将谈判一方或双方的经济收益作为结果变量,并建立了谈判行为对于经济结果的回归模型。经济收益类型的结果变量包括联合收益、较少一方的收益、相对收益以及己方收益。早期研究将联合收益和较少一方的收益放在一起进行比较(Kimmel等,1980;Carnevale等,1981)。绝大多数研究都证实了合作式谈判能够促进联合收益。其中包括解决问题行为(Giacomantonio,2010)、多事项提议(Imai和Gelfand,2010)、相互妥协(Pinkley,1995;Forgas,1998)、信息沟通和交换(Thompson,1991;De Dreu等,1998),以及高度的合作氛围等,这些合作行为可以显著提升双方共同的经济收益。主流文献之所以大规模采用这项指标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联合收益计算较为简明,解释较为直观,只要将双方收益加总就可得到结果,也可从达成的谈判方案中推断出来。第二,联合收益是双方通过合作产生共赢的最为直接的经济体现。Thompson等(1996)则提出相对收益来衡量双方收益的差异程度,该指标反映了谈判收益在两方之间的分配结果。他们对比研究了团队—团队、团队—个人及个人—个人三种不同的谈判形式,发现团队形式增强了团队整体层面的合作谈判行为,使团队成员感受到相对于单个谈判对手的优势;随着成员之间熟悉程度的加深,团队凝聚力和成员间理解程度也会加强。Kray等(2001)学者在对谈判者性别差异的研究中将己方收益作为目标变量,结果表明刻板印象的唤起方式对谈判某一方获取最大经济收益具有调节作用。
研究证实,谈判行为过程对谈判协议的最终状态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在实验中若规定时间截止后双方必须终止谈判,在某些议题上的僵局就会产生未决事项。Grigsby和Bigoness(1982)将未决事项的数量作为合作程度的重要代理指标,发现合作行为越强,就会在更多议题上达成一致,而且未决事项更少。谈判方案的另一个指标是帕累托效率,它是指就目前谈判方案而言还存在多少更优方案能够改善双方的境况。这一谈判指标和联合收益有很大相关性,因为它以联合收益本身作为更优方案数量的依据。谈判方案的帕累托效率与合作式谈判行为过程正相关,而与分配式谈判行为负相关。可见,无论是未决事项的数量还是帕累托效率,都是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来看待谈判质量的。
在西方文化中,谈判双方参与谈判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这是西方主流文献的共识,有学者称之为元假定(meta-assumption)。但是随着学者对文化差异的认识的不断加深,谈判理论也逐渐关注非西方文化中谈判主体的非经济性动机。Curhan等(2006)学者认为,应重视谈判结果中的社会心理变量。他们提出的框架包括谈判者对收益结果的感受、对自身的感受、对谈判过程的感受和对双方关系的感受。迄今为止,合作式谈判对主观变量的影响还没有形成统一结论。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主观变量难以定义,变量的选取和测量还不存在类似联合收益这样公认而简明的指标。第二,谈判者的主观感受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被试所处文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合作式谈判行为与谈判者事后回顾时的整体满意度之间的作用关系,因被试组文化的不同而呈现正向、负向以及不显著等结果,无法形成一致结论(Graham等,1994)。不过鉴于主观性指标愈加频繁地出现在谈判研究当中,今后学者们对影响主观结果变量的各种机制也将会形成统一的认识。
(五)理论的引入:涵盖前因、过程与结果
在近三十年的谈判研究中,学者们从相关领域引入大量理论框架来探索合作式谈判的内在机制,从前因与后果来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利用理论来解释前因变量、调节变量、中介变量和合作式谈判行为之间的关系。De Dreu和Weingart进行过一项元分析,确证了双重关注模型和合作理论,并显示合作倾向结合不轻易妥协的行为会导致高度的合作行为。Schei等也运用了这两个理论,并将其延伸到混合型动机的谈判者行为研究中,结果表明,合作和竞争倾向混合的谈判组合在使用合作式谈判技巧和联合收益方面,接近合作动机谈判组合的表现,并显著高于竞争型的谈判组合。Forgas(1998)使用情感注入模型分析情绪对谈判行为的作用,发现谈判者的乐观情绪容易增强合作行为。这是一种情感注入的过程,这时谈判者放弃预定的谈判策略转而采用启发式策略来评估实时状况。被引入的行为形成机制理论还有策略选择模型(Kimmel等,1980)、结构化目标/期望理论(De Dreu等,1998)、前景理论(Trötschel和Gollwitzer,2007)等。第二,通过理论来讨论合作式谈判与收益之间的关系。Kray等(2001)在分析谈判收益的性别差异时引用刻板印象理论和心理抗拒理论来解释性别刻板印象的不同唤起方式(隐性/显性)导致的不同效果。世俗求知论则主要用于认知视角的研究,比如时间压力和换位思考对于联合收益的交互作用。被引入到讨论“行为—收益”机制的理论还有诠释水平理论、理性行为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等。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参与者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的合作程度会受到多样化情境和个体因素的综合作用,而且各种不同视角的研究文献都将联合收益及其相关指标作为首要的结果变量,有的研究者还考察了谈判的主观结果变量。考虑到不同研究视角和各种理论模型,本文将合作式谈判这一领域的研究模式整合成如图1所示的研究框架。可以看出,有些因素在不同视角的研究文献中都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例如,性别差异对于谈判行为的影响,以及过往谈判经验的影响等。

图1 合作式谈判的研究框架
三、国际研究总体评价
我们发现,三十多年来合作式谈判国际主流文献的研究视野基本保持固定。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聚焦于一对一(dyadic)形式的谈判,甚少关注于其他谈判形式。虽然有部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一对一的谈判模式,但是大多数研究仍然遵循着将一对一谈判的实验成果推广到现实世界的推理思路。但在现实中,一些对企业绩效有影响的商务谈判形式并不采取一对一的做法,因此迄今为止谈判领域的实验研究文献能在多大程度上向真实世界复制自己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第二,谈判行为研究中所测量的谈判行为类型常常受实验程序的限制。谈判心理学家们通过设计谈判任务来跟踪并测量实验参与者的行为策略,而谈判收益范围都是被预先设置好的。实验参与者努力提高各方最终收益的行为,实际上变成了买卖双方在谈判支付矩阵上选择某些选项的过程,这些选项就代表了某种收益组合。例如在混合动机(mixed-motive)谈判的实验研究中,研究者分配给参与者一些成对的整合性和分布性待议事项以及一两项兼容性事项,并且提供相应事项的收益分布信息,让参与者权衡如何讨价还价。这种实验设计确保了整个实验过程是受控的,但也使谈判参与者失去了利用更多谈判技术来寻找创造性解决方案的机会,比如搭桥技术(bridging)就是一种需要另辟蹊径来解决谈判问题的技巧(Pruitt,1981)。我们认为,重新设计实验程序可以克服传统实验手段的局限性。比如在设计一项主要谈判任务的同时,设计一系列不完全相关的谈判任务供参与者选择,可以增加谈判问题解决方式的多样性,为实验参与者提供更多发挥创造性的空间。第三,该领域的研究一直被线性模式所主导,即决定因素(或条件)—行为过程(或策略)—谈判结果。这种模式反映出的静态思维是:所有条件对于谈判行为和收益产生的影响是恒定不变并贯穿整个谈判过程的,但时间效应在真实世界的多轮谈判中起显著作用。Paese和Gilin(2000)的研究就表明,信息披露对于谈判者报价时需求水平的影响在多轮谈判中是逐渐下降的,而且在一系列谈判回合中谈判者行为会发生改变。因此很多内外条件对谈判过程和结果的影响会随着时间而变化,考虑了时间效应之后,谈判研究很可能会在目前静态、线性的研究范式基础上有所突破。
四、未来研究展望
根据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讨论,本文认为该领域有可能在以下方向上实现突破:
(一)谈判者行为的动态过程
如上所述,该领域多被传统的线性、静态的研究模式所主导,如果运用动态、非线性的眼光考察谈判过程中的各个变量,则变量之间的关系会出现明显的变化。新的模式可能是几个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一系列谈判回合、初始行为的差异、谈判者行为间的相互影响。在实验室之外的商务谈判者之间往往需要通过多轮谈判才能达成协议,并且谈判者会根据以往的谈判经历来采取行动(O’Connor等,2005),同时,在每一轮谈判中,谈判者的情绪和行为也会相互影响(Paese和Gilin,2000;Van Kleef等,2004),所以谈判者的行为策略会随着谈判进程的展开而出现变化。比如,在跨文化情境中文化背景迥异的谈判者在谈判桌前碰面,开局时双方的行为差异通常是非常显著的,如果在谈判结束前双方行为趋向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谈判者行为的演化过程。在实证研究中,为了能够测量这种动态过程,研究者须收集到多个时点上的数据。因此研究者应设计出前后连贯的一系列谈判任务,以观察并记录参与者在这些任务中行为的前后变化,同时充分的时间跨度也是提高数据质量的一个必要因素。
(二)谈判者之间的关系对谈判过程的作用
在大多数谈判实验中,作为买卖双方的被试都是彼此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且谈判实验大多为一次性的,双方的关系对于谈判过程不会产生影响。而在现实世界中,商务协议的最终完成是前后连贯的一系列沟通、交涉的结果,买卖方之间的关系动态很容易影响谈判的走向及结果,因此谈判研究长期以来缺失关系视角的现象也为很多研究者所诟病(Gelfand等,2006)。学者们认识到,在很多互赖性自我构念(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文化较强的社会中,个人在自我定位时往往将自我嵌入到一个大的社会系统当中,其认知的重点是关系和情境(Brett和Gelfand,2005)。很多来自亚洲或南美洲的谈判者对关系资本的重视,与这些社会中对于社会和谐的强调以及阶层制的文化特征相一致。所以,从关系视角来看待谈判过程,就会发现谈判中的合作现象不仅是某些行为的集合,而且是双方整体关系状态的表现。双方关系相互依存并对谈判方案的形成产生作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主观变量。今后会出现更多关系视角的谈判研究,结合关系网络在很多非西方社会中所发挥的特有作用对谈判双方的行为进行新的诠释,将能产生一系列重要的发现。
(三)关系动态与动态关系
结合动态视角和关系视角,学者可以从动态关系这一新的视野开展谈判中合作机制的研究。Gelfand等曾经在谈判关系的研究中创新性地提出“关系型自我构念”(relational self construal,RSC)和“关系动态”的概念。RSC是指个体基于和他人的关系来看待自身的程度,而这一程度在谈判双方之间并不一定保持一致。因此双方的RSC至少形成四种配对状态(高-高,中-中,低-低,高-低),Gelfand等学者将这四种配对状态称为关系动态,并提出不同的关系动态对于谈判者的经济资本和关系资本的影响方向及强度是不同的。根据本文对于多回合谈判中时间效应的讨论,在短期内保持固定的关系动态在更长的时期内会改变。比如在跨文化谈判中,谈判者之间最初很可能是高/低不一致的关系动态,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互动,最后会形成某种一致性的(或高或低的)关系动态。已有实验表明,跨文化谈判中谈判者行为调适的程度对于谈判者获得的印象评价这类主观变量有显著影响(Francis,1991)。因此关系动态变化以后,对客观和主观两类谈判结果变量的影响也会相应变化。在综合动态视角和关系视角后,就会发现谈判者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谈判双方保持的其实是一种“动态关系”。针对动态关系的未来实证研究,研究者同样需要对于单一谈判任务的实验结构做出改进,设计出具备充分时间跨度的多任务谈判程序,以利于收集纵向数据。另外,在谈判研究中分析动态关系,传统的静态线性分析模型(如多元线性回归)已不适用,应该同时考虑纵向数据的处理以及谈判双方的相互作用,这需要采用新的分析工具。近年来发展得较为成熟的一个建模方法是行动者—对象互赖性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参见Cook和Kenny,2005)。由于APIM可以用于分析纵向数据,其对于深入揭示谈判过程中各类因素随时间的稳定性(行动者效应),以及谈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象效应)非常适用。因此,要突破这种传统研究范式去分析谈判者的关系动态,须在实验设计、数据收集、分析模型等方法层面做出相应的改变和创新。
(四)西方成果在跨文化情境下的重新论证
西方的谈判行为实验研究成果及引用的理论中很多均具有普遍性意义,比如前景理论中的锚定效应和框架效应,因为得与失是人性中通用的概念。但是现有谈判心理学的主流研究主要基于美国学者的视野,一些理论和实验成果在普遍性方面有其局限,并不是所有的实验结论都能够在新情境当中被重新确证。比如,问题解决型的合作行为对于双方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就因被试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明显差异(Campbell等,1988)。再如,相对于西方谈判者而言,中国谈判者交流的情境性更高,测量谈判双方之间提问与回答的频度和质量并不能完全反映谈判过程中信息沟通的实际情况,因为有很多沟通是通过非语言信息交换来实现的。未来的研究应当将早先实验当中被确立的变量关系放入新的文化情境下重新检验,一方面观察其方向和强度是否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观察是否会出现新的关系,从而发现条件、过程、结果之间新的行为机制。与此相似的是针对跨文化谈判情境的研究:由于主流实验研究中混合文化背景的谈判组合较为少见,而且几乎全部采用无谈判经验的学生样本,因此如果能够提高收集到的数据的质量,使其体现真实世界中不同国家商务谈判者的行为特性,这样的实验研究就具有更高的启发意义。
(五)利用本土概念发展合作式谈判研究
相对于中国日渐频繁的谈判实务和国际主流研究进展而言,国内对谈判行为的研究历史不长,还处于起步状态。我们以“谈判”为关键词在一些顶级中文学术期刊当中进行广泛搜索,发现有8篇文章报告过实验研究成果,集中发表于2004-2011年(有6篇测量了合作式谈判行为特征变量),国内实证研究结论与国际研究成果基本一致。如亲社会动机的谈判者在谈判中更愿意交流信息,且信息分享的数量和质量更高,对谈判事项的判断更准确。针对混合动机谈判组合的国内研究表明:混合动机倾向的谈判组合获得的联合收益在合作倾向与竞争倾向的谈判组合之间(韩玉兰等,2010),尽管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结论与Schei等学者对于混合动机的研究成果相似。此外,很多国内文献属于建言献策式的研究。相对于西方的研究范式,中文文献总体上更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比如很多国内谈判论文主要阐述谈判实战当中的技巧和策略。该类文章固然可以为读者提供直接效用,却不能借由互相印证形成体系。本土研究应遵循理论构建、实证检验、理论完善这一路径,进行体系脉络的梳理,并通过高质量的实验研究来夯实基础,以利于新发现的产生。
国内研究者在借鉴现有研究方法、实验程序和理论来源的同时,也应看到西方的很多理论和概念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本土情境中不一定具有相对应的意义。因此也有本土文献利用新的构念来发展自有理论,并最终普及到主流研究当中。比如针对中国社会文化中特有的“中国式关系(guanxi)”、“人情”、“面子”等本土现象的研究(Hwang,1987),以及将圈内人关系情境引入到谈判研究当中的尝试(Liu等,2012)。正如“管理的中国理论”是用于解释本土学者首先观察到的管理现象和解决中国企业家的管理问题(徐淑英,2011),利用发端于本土情境的概念来研究中国商业谈判者的行为过程,既可为促进我国商务人士在谈判中更好地与对方合作获得双赢形成理论基础,也可为本土概念普及到国际研究中做出贡献。
总之,合作式谈判不仅是一种确保买卖各方延续其商业关系进而长期互惠的重要行为策略,也是在复杂的任务情境、谈判条件和心理因素的驱动下联合谈判伙伴以整合谈判资源的过程。将谈判视为双方相互影响的一系列沟通过程的集合,研究者可以转变以往针对静态行为的研究范式,从关系动态的视角来考察谈判中的合作现象,跨文化谈判情境则为该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国内研究者在借鉴和检验国际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应参照现有理论发展本土情境中特有的概念。
注释:
①限于篇幅,本文未将这32项独立研究列于文中。若须查看详表以了解各项研究所涉及的全部变量,可联系通信作者。
[1]Carnevale P J D,et al.Looking and competing:Accountability and visual access in integrative bargaining[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1,40(1):111-120.
[2]De Dreu C K W,et al.Social motives and trust in integrative negotiation:The disruptive effects of punitive capability[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8,83(3):408-422.
[3]De Dreu C K W.Time pressure and closing of the mind in negotiation[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3,91(2):280-295.
[4]Forgas J P.On feeling good and getting your way:Mood effects on negotiator cognition and bargaining strategie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8,74(3):565-577.
[5]Francis J N P.When in Rome?The effects of cultural adaptation on intercultural business negotiation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1,22(3):403-428.
[6]Gelfand M J,et al.Negotiating relationally:The dynamics of the relational self in negoti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2):427-451.
[7]Giacomantonio M.Now you see it,now you don’t:Interests,issues,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n integrative negotiati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0,98(5):761-774.
[8]Grigsby D W and Bigoness W J.Effects of mediation and alternative forms of arbitration on bargaining behavior:A laboratory study[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82,67(5):549-554.
[9]Hwang K K.Face and favor:The Chinese power game[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92:944-974.
[10]Imai L and Gelfand M J.The culturally intelligent negotiator:The impact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CQ)on negotiation sequences and outcomes[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10,112(2):83-98.
[11]Kimmel M J,et al.Effects of trust,aspiration,and gender on negotiation tactic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0,38(1):9-22.
[12]Kray L J,et al.Battle of the sexes:Gender stereotype confirmation and reactance in negoti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1,80(6):942-958.
[13]Maddux W W,et al.Chameleons bake bigger pies and take bigger pieces:Strategic behavioral mimicry facilitates negotiation outcome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8,44(2):461-468.
[14]O’Connor K M,et al.Negotiators’bargaining histories and their effects on future negotiation performance[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5,90(2):350-362.
[15]Paese P W and Gilin D A.When an adversary is caught telling the truth:Reciprocal cooperation versus self-interest in distributive bargaining[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00,26(1):79-90.
[16]Pinkley R L.Impact of knowledge regarding alternatives to settlement in dyadic negotiations:Whose knowledge count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5,80(3):403-417.
[17]Pruitt D G,et al.Gender effects in negotiation:Constituent surveillance and contentious behavior[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86,22(3).264-275.
[18]Pruitt D G.Negotiation behavior[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1.
[19]Schei V,et al.Can individualists and cooperators play together?The effect of mixed social motives in negotiation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11,47(2):371-377.
[20]Steinel W,et al.When constituencies speak in multiple tongues:The relative persuasiveness of hawkish minorities in representative negotiation[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9,109(1):67-78.
[21]Thompson L L,et al.Team negotiation:An examination of integrative and distributive bargaining[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6,70(1):66-78.
[22]Trötschel R and Gollwitzer P M.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and the willful pursuit of prosocial goals in negotiation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7,43(4):579-598.
[23]Tröschel R,et al.Perspective taking as a means to overcome motivational barriers in negotiations:When putting oneself into the opponent’s shoes helps to walk toward agreement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1,101(4):771-790.
[24]Van Beest I,et al.Honesty pays:On the benefits of having and disclosing information in coalition bargaining[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11,47(4):738-747.
[25]Van Kleef G A,et al.The interpersonal effects of anger and happiness in negoti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4,86(1):57-76.
[26]Weingart L R,et al.Knowledge matters:The effect of tactical descriptions on negotiation behavior and outcome[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6,70(6):1205-1217.
[27]徐淑英.中国管理研究的现状及发展前景[N].光明日报,2011-07-2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