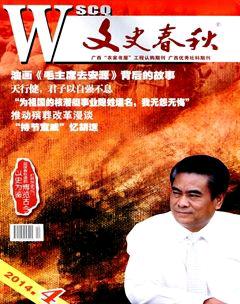大师的雅量
崔鹤同
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于责己,旷达宽宏,这就是大师的雅量。
1912年3月,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后,无意中读到胡玉缙写的《孔学商榷》。由于内容生动、材料丰富、翔实,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一连读了几遍后,便决定将胡玉缙聘请到部中任职。于是,他指示下属官员起草了一封信。
当时,胡玉缙在学术界还是无名小卒,与蔡元培素昧平生。没想到,胡玉缙接到邀请信后,非但没有感激,还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抗议。
原来,问题出在蔡元培让下属写的信中的个别字上。那封信的全文是:“奉总长谕:派胡玉缙接收(教育部)典礼院事务,此谕。”按字面理解,“谕”和“派”两个字是上级对下级的,包含着必须服从的意思。而胡玉缙这时还不是教育部雇员,不存在上下级关系,因此他感到不是滋味;特别是“谕”字,本来是封建专制时代使用的一个“特定词”。对此,胡玉缙认为无法容忍。
蔡元培接到胡玉缙的抗议信后,内心深为不安。他立即给胡玉缙复信表示歉意,称“责任由我来负责”。
因部属拟稿用字失当,蔡元培主动承担责任,向人道歉。此事看似虽小,但从中折射出的这种律己不苟的高尚情怀却是十分可贵的。
胡玉缙被蔡元培的诚意所感动,欣然答应到教育部任职。后来,胡玉缙成为著名的国学大师。
无独有偶。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在北大礼堂作了一场关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学术讲演,礼堂座无虚席,连窗台边都挤满了听众。梁启超在演说中认为,《老子》一书有战国时期作品之嫌,并诙谐地对听众说:“我今对《老子》提出诉讼,请各位审判。”
几天过后,梁启超真的收到一份“判决书”。这是一篇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写成的学术论文,文中称梁先生为“原告”,称《老子》为“被告”,自称是“梁任公自身认定的审判官并自兼书记官”,以在座“各位中的一位”的身份“受理”梁先生提出的诉讼,进行“判决”:“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在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判决书的署名是张煦。
原来,张煦(怡荪)当时听了不以为然,依靠自己从演讲现场匆匆记下的几页笔记为原材料,针对当时已名满天下的梁启超的观点,连夜撰文,逐一进行批判:“或则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于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文章洋洋洒洒,长达数万言,全文分析严谨、逻辑严密、材料充分。
写就以后,张煦将文章寄给了梁启超。心胸宽阔的梁启超收到文章后,十分赞许作者的才华,尽管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然亲自为该文写了如下题识:“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后来,张煦的学术论文连同梁启超的题识,在《晨报》全文发表。
一个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敢于向权威挑战;一个是学者风范,热情奖掖后学,文章一出,学术界纷纷传为佳话。
张煦因为研究《老子》,和梁启超结交。此后至1935年,张煦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的讲师、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讲授“国文” “楚辞” “韩昌黎文”“文学专家研究”,开过“文学史” “古代汉语” “文字学”“梵藏修辞学”和“佛典翻译文学”等课程,终成著名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蔡元培和梁启超严于责己,宽宏大度,甘为人梯,提携后生,不愧为一代大师。
还有一例是关于闻一多的。年轻时,闻一多对鲁迅缺乏好感,更谈不上敬重,他写信给梁实秋,标列“非我辈接近之人物”,鲁迅首当其冲。1944年10月19日,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8周年晚会,晚会组织者对要不要邀请闻一多参加感到为难:闻一多过去被认为是“新月派”,骂过鲁迅,请了他也不一定来,即使来了他也不便发表演说,但是不请他又不好。于是组织者派人去和闻一多商量,征求他的意见。闻一多听后,马上表示一定要参加,还要演讲,同时又主动帮助去请别的教授。
在纪念晚会上,闻一多发表演讲之前先回过头去,向悬挂着的鲁迅画像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说:“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鲁迅以前骂我们清高是对的。他骂我们是京派,当时我们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对的。当时如果我们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
由于激动,闻一多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先生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
最后,他回身指着鲁迅画像旁挂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又说:“有人曾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就他的这两句话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种勇于解剖自己的精神,令在场的师生听后,无不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