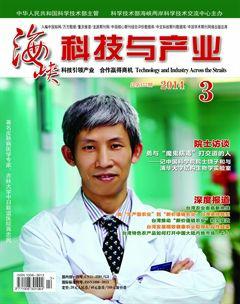滋兰树蕙 种德修福
张晗
多面辛希孟
辛希孟被公认为是“集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于一身的著名学者型书法大家”。
“科学”和“教育”是辛教授的老本行,他在这些领域内的成就有目共睹,不需赘述。令人称奇的是,在退休之后,他的书法作品备受追捧。“童子功”加上深厚的文化素养,一起成就了辛希孟的书法艺术。
2010年,辛希孟当选“世界华人艺术领袖”。这个称号不仅是他在书法艺术上收获的公开评价,也是对他跨界身份的一次高度认可。“在欣慰之余,我更觉肩负使命的重大——为了传统文化的不断传承,为了书画艺术的交流碰撞,更为了慈善事业的发展进步”。
2004年,也就是他退休的第二年,他以“记忆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靓丽人生”为宗旨,以个人创作、推介名人名作、举办沙龙和专题研讨会、联系海内外同行交流与合作为主要活动方式,创建了“北京溪梦轩书画艺术工作室”。以此为窗口向海内外同仁展示与传播祖国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
辛希孟恪守传统,书法功力深厚,作品平实大方、雅俗共赏,点画之间透露难以言传的意境。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入编出版社出版的书画艺术作品集四十余种。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艺术大师三人行》一书中,收录了欧阳中石、辛希孟和沈鹏的作品;《中国国宝书画三大家》选择了辛希孟、赵无极和韩美林作为代表人物,该书由中国国际出版社出版;与范曾合集《聚焦中国书画名家》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他与吴冠中、徐悲鸿、靳尚谊、刘大为等二人辑十余种;全国邮票总公司专为辛希孟出版“中华艺术大家”专题邮票二版,现已成为邮市上的“新宠”。书法也是他参与国际交流的最佳方式。在柬埔寨西哈努克前国王85寿辰之际,他的一幅“福寿康宁”被送至柬埔寨皇宫。西哈努克倍感欣喜,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句“柬中友谊万岁”。
辛希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只要是助贫、助教、助残等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并于2008年7月获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人民代表报》等单位联合颁发的“中国公益事业形象大使”荣誉称号。“夙夜匪懈”是辛希孟书写次数最多的条幅。“无论是学问还是事业,有追求的个体都应该把勤奋作为第一律令,勇猛精进,一日不可懈怠”。
日前,本刊记者专访了辛希孟先生。
本刊记者:图书馆学给人的印象是皓首穷经,当初怎么选择这么个专业?
辛老师:或许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或许是血脉相承吧,我们家称得上书香门第。早在上中学时,图书馆就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很有书山学海中遨游的感觉,在和书本的交道中,我由衷地感到惬意与畅快。当母校保定一中图书馆的藏书不能满足需要以后,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就去当时的河北省图书馆。时间一久便逐渐与工作人员熟了,借这些机会常常帮助他们打登录号、贴书标、写书卡等,以换取阅读新书的便利。
报考大学时,本想去新闻系,但当时北京大学的新闻系调整到了人民大学。我有北大情结,想想还是报考北大图书馆学系吧。水到渠成的事。
本刊记者:北大图书馆学系的创始人是王重民先生,他很受胡适等人器重。他好像也在保定一中读过书?
辛老师:是的,他就读的是保定直隶第六中学,后来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师从高步瀛、杨树达、陈垣等专攻文史。胡适提到的应该是王先生当时的一项特殊的“文化任务”。他被派往法、英、德、意、美等国的著名图书馆搜求流散的珍贵文献。1947年回国后,王先生任职于北平图书馆,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在北大中国文学系创办图书馆学专科(后改本科),他任系主任。
本刊记者:你毕业后在文献情报中心工作,这个选择有什么机缘吗?
辛老师:毕业之际,许多政府部门、军事机构和科研单位到北大要人,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就是现在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有两个人对我的这个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很感激他们。第一位就是刚才提到的王先生。1960年,我跟随他参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善本书展览,而后又来这里进行毕业实习。通过参观、实习,尤其是接受了王先生的指教,进一步认识到科学院图书馆的实力、优势和前景。
另一位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业务处长赵继生先生,我听了一次他的专题报告,内容是关于科学技术专业图书馆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规划。这个报告听后令我血脉贲张。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选择没有错。当时我不过是一个不谙时务,也没有实践经验的小青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咱们国家的图书馆事业做了一些工作,也被年轻人们称作“专家”。我真的要感激很多人。
本刊记者:做文献工作,是不是要埋首于故纸堆?
辛老师:那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且一点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枯燥。在我的工作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为《图书情报工作》的诞生而奔波。到图书馆工作不久,根据当时工作需要和个人专长,我从国际文献交换组调到业务处研究辅导组,协助范文津老大姐编辑《图书馆工作参考资料》。这是一种以发表本馆本系统图书资料工作实际经验和技术为主的专业刊物。就是这本颇受馆内外欢迎的出版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冠以“宣传封、资、修”的罪名被勒令停刊。
拨乱反正后,经反复研究,决定创办一种新的刊物,定名为《图书馆工作》。这项筹备任务落在了我和赵继生先生肩上。有一些人视编辑工作为“为他人做嫁衣”。但根据我的切身体会,办好一个专业杂志,不亚于建立一个研究中心。
我不仅要组稿改稿,还要亲自下厂校对,送取清样。为保证编辑质量,扩大期刊的影响,我先后向历史学家尹达、诗人何其芳、语言学家吕叔湘、物理学家钱三强、生物学家汤佩松约稿,并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
为了给这本新刊创标立誉、扩大宣传,我书包里总装着几本新刊《图书馆工作》。哪里有会,我就往哪里跑,相机约稿,随时征求意见。那时候办刊物确实很清苦,但事情办成之后的成就感很大。
1979年初,它更名为《图书情报工作》。我直接找到著名诗人、学者、佛教协会领导人赵朴初先生宅邸,请他题写刊名,赵老欣然答应。写完后他非常谦逊地说,如果觉得不好,我可以再写。赵老的美德,令我没齿难忘,我也一直将其作为自己的楷模。
本刊记者:郭沫若曾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当时您已经在科学院图书馆工作了,您和他的交往多吗?
辛老师:很多。在读“六本书”期间,我经常给郭老送书和其他资料。满城汉墓出土的文物,最早就是放在我们图书馆的一个会议室里,他也常过来做研究。我和郭老的零距离交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本刊记者:你的书法研习主要受到哪些书家的影响?
辛老师:我从四岁开始练字,二王、颜真卿、赵孟頫、米芾都临过无数次。魏碑我也练得较多,现在有评价说我的书法碑味儿很浓,这也是自然发生的。对于书法的习练和钻研,进得去、出得来很重要,一味地模仿是不够的。对经典作品,主要还要体会其中的精神、气质,才有望自成一体。
本刊记者:对于当代书法的圈层现象,你的看法是?您似乎没加入书画协会,你是有意要和这类机构保持距离吗?
辛老师:我没有加入书画协会。书法对于我来说就是兴之所至,我觉得正是我书法中的某种轻松,打动了那些喜欢它的人。
我和其他书画人士接触不是太多,可能是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吧,有时候很疏懒。我也听说过有些大家向别人赞扬甚至推介过我的作品,照理说应该致谢一下。想想还是不去了吧,君子之交,心中有数就是了。
本刊记者:可否介绍一下溪梦轩书画艺术工作室的现状?
辛老师: 鉴于我进入书画界比较晚,经济积累有限,很多经济界的朋友愿意提供空间和经费建立工作室。现在已经筹备就绪的有北京、无锡和漳州等处,有效工作和展示面积共计1500多平方米。现在我主要是创作作品,他们组织经营。
我对于经营不在行,我只负责创作,他们也都是一群有文化理想的人。
本刊记者:对于您书法作品的藏家类型和分布,您做过调查吗?您想过修正自己的书法风格来获取更多追捧吗?
辛老师:没刻意地统计过,价格我听说卖得很贵。有不少学者、专家同行喜欢我的字,也有很多喜好书画艺术的公务人员和企业家,各种类型的藏家都有。我从没把它当成一个生财渠道。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开始享受政府津贴,现在我坐地铁出行,我从来不是物欲至上的人。喜欢我的书法,那他就收藏嘛。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做到雅俗共赏。“传承文明、靓丽人生”是我的信条。
本刊记者:你如何看待现在的书法风潮,比如“流行书风”?
辛老师:我看过一些,我不发表意见了吧。是风,就让它刮一阵儿吧。
本刊记者:关于书法内容。您写过“夙夜匪懈”这样富于文化意味的词句,也有“鼎盛中华”这样“正确”的表述,还有“福寿康宁”这样世俗而诚恳的祝愿。您如何看待书法内容所能传达的公共语义?
辛老师:这个需要根据具体的创作语境。我会送一些作品给大小朋友们,比如给学生,我会写“夙夜匪懈”,希望他们培养信念、坚持学习、不断努力。
对于新人,我会写“松萝共倚”。是夫妇刚柔相济、阴阳协调的意思。给同辈人,我写“福寿康宁”,那是我真心觉得老年人的幸福观就是这么四个关键字:避祸、长寿、健康和宁静。
本刊记者:您如何看待书画的养生功能?
辛老师:我七十多了,每天我要步行四十分钟,台阶也要爬上爬下差不多600个,身体还算可以。退休之后,我每天晚上从十点到十二点,写两个小时的字。最近听从建议,提前到九点半到十一点半。我没想过用书法来作为养生手段,自然而然。如果说有什么经验,我觉得一个人无论他退休之前职务多高、成就多大,退休之后要调整好心态,就是一个普通人嘛。
以前可能在庙堂上呆的时间多了,现在正好可以深度接触社会,三教九流,都要接触。另外,要坚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坚持,加上有兴趣,应该就可以养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