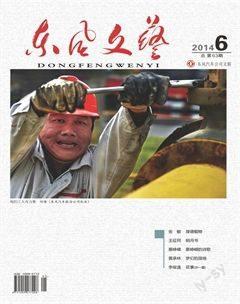不一样的世界(外八首)
叶露明
如果你看见了风
那也不是幻觉
他经过的城市、村庄
人群,以及逝去的、将来的时光
都是你不曾抵达和梦见的
不一样的世界
不一样的故事
潜伏在不一样的心房
一片树叶,一颗果实
也不一定知道一条根须
生长的方向,触摸的地方
或许有黄金、钻石、紫水晶
但他可能更愿意亲吻粪土
和有亡灵的头盖骨
如果你看见了风
千万别妄图记住他的模样
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而你,其实也一样
路口
在那里扎根的
有一朵蒲公英,开败了
风再大一点
子女们就越散越远
附近还有一棵银杏树
时间再久一点
他哑了,就会更加沉默
人们曾经过这里
开垦出一个出发的路口
人们又离开这里
荒芜出曾经的模样
如果要说有什么改变
请你拨开落叶和杂草
看看这足迹踏平的地方
再也没有一颗种子
能够探出脑袋
这里是一条路
无数人经过
也是一个路口
没有人肯停留
寻找
季节从不慌张
渗透,去它去的地方
你恍然大悟
你走得仓皇
或者没有方向
你为了温暖而逃跑
但风雪就在心里下啊,下啊
一直到你错过了春草绿
一直到你看到了秋草黄
远山是远山
始终与你拉开遥远的距离
别人的烟火
只隔一张离析梦与醒的薄雾
你总在不停地寻找
始终不明白什么是得到
童话故事的结尾
是生活,在最初
就打上的死结
两半
白云一朵,分两半
一半作马,一半作骑士
天空是草原,有时也是海面
风起时,骑士扬起风帆
像个水手,身披急雨和星辰
风停时,白马张开翅膀
像尊雕塑,撑起时光与骄傲
一朵云,分两半
奔跑时互相牵扯
谁做谁的领袖
沉寂时彼此僵持
谁是谁的累赘
或许多情才是个笑话
一朵云就只当是一朵云
可当世界本来
就是两半的时候
我想醒着做醒着的梦
到了梦中
再做梦着的梦
倦鸟
栖一树寒枝
或是一瓣繁花之上
掠过蓝宝石的湖面
羽毛一样斑斓的山野
迁徙在人间的朝暮晨昏
在春天铺开翅膀
季节就化作,一条砸破冰面
裂纹逃向远方的闪电
闪电一般呼啸而来的
是疾雨一样的子弹
一片羽毛抵抗一个冬天
一段飞行撕碎一个夜晚
总有那么一天
不知疲倦的飞鸟
会不知疲倦地返航
立冬只是一场暧昧
如果昼不连着夜
梦不伴着醒
四季不曾更迭
没有年复一年
我们就这样孤身而立
和每一个苍白的旁人,在一起
在一望无际的时光里放逐
像一片被随手撕破的纸张
在风中,等风来,看风走
没有刻度计算生命
也没有聚散掂量爱情
种子就做一颗种子
果实就做一颗果实
你在此刻生存
就不会往未来迁徙
不会在旅途赞颂
也不会在别处消逝
立冬就终止于是场暧昧
风雪只纷扬在它自己的经纬
一个碎纸片一样的你
飞与不飞都不用在意
你只是一张碎纸片的你
寂寞是一颗哑炮
风停下来了,它就不再是风
火熄灭了,它就不再是火
就连季节的变迁
也有它一去不返的临界
曾经有一只鲜艳的蜻蜓
休憩在我的指尖
然后,连同我的时光
私奔到晨光里,到夕阳下
到严冬里的荒野中
无从收敛
还有一只苹果
我带它去旅行
放它在列车的窗口
在人潮涌动的九月
它听过我枕边的呓语
也目睹了我愤怒的心海
这枚不幸的苹果
跌落在了雪山的崖间
被遗忘了红润的容颜
一场风雪与游戏
和世间的一切
都极易丢失,走向终结
唯有时光、爱情和寂寞
不曾真的来过
也不会真的灭亡
而寂寞,是一颗不会爆炸的哑炮
种在每一张迷惘的手掌上
像一星半点的萤火
郊野的墓园
第一次,在大巴的窗口
看到那片墓园
夏天里,野草漫起
像暴雨后涨起的池水
流窜在他们的四周和
彼此的间隙里
在那片墓园的不远处
隐隐有些散落的矮房
在那片墓园的近处
有成片的杂草侵蚀的田园
第二次,在大巴的窗口
我刻意去找寻那片墓园
空气的低温加剧了旷野的辽远
白杨树只剩几片发黑的枯叶
鸟窝被枝桠刺破胸膛
悬挂在天幕上
依然是那片墓园
深眠在里面的先人们
似乎没有等来他们的子孙
或者是草木太急躁
轻易就抛开了思念的间距
第三次,第四次
不记得有多少次穿行在那条路上
有时我也能看到那片墓园
而有时,我也看不见
我没有在夜晚,路过那片墓园
但我看见了
没有灯火的郊野
会将它的领域,延展到
天幕上最暗的那一颗星辰
在星辰的下方,你看
有你的童年,也有我的故乡
在竹林的石阶上
鸟雀在四点钟醒来
然后是清泉两旁
开花的鱼腥草
下了一夜的露滴
和时刻不停的流水
在夏季的竹林里
晨曦被托舉在半空中
漏下的星星点点
都撒在青亮的石阶上
停靠在沟谷里的筏子上
一支竹篙插住涟漪与
湖底的淤泥
在水波荡漾开的前方
细网里挂满银梭般的野鱼
当第一串跫音叩响
在这竹林的石阶上
月亮和太阳,就悄悄地
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