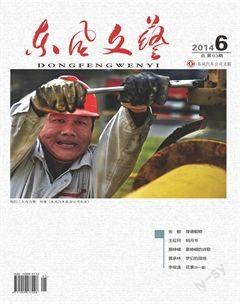嘟嘟
邓炎清
嘟嘟是一条杂毛狗,通身浅黄色,间杂几处轻描淡写的水墨色。嘟嘟是我们从宠物市场买来的,听人说出生不到五十天。宠物市场就在百二河边那片水杉树林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露水市场。平时大家有什么需要交换的,诸如猫、狗、鸟类,乃至热带鱼类,树木花卉类,都往这里带,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一个以宠物交易为主的露水市场。在这里,经过一轮象征性讨价还价,连嘟嘟脖颈上那根绳索在内,我们总共花了七十元。说实在,嘟嘟也就只值这个价钱,虽说腿脚是有点矮短,脸型也是有点紧凑,一看就知道是经过了杂交改良的品种,但到底只是一条小草狗,血统又高贵不到哪里去吵,混迹于宠物市场就能把身价抬上去?嗤!
嘟嘟这个名字是邓等给取的。邓等是我们的女儿,已经九岁了,上到了小学三年级,正是发奋用力的阶段。她哭着闹着要养宠物,我们就用这样一条狗来敷衍她。邓等倒也开心,还没把它抱上车,就给它取好了名字。“嘟嘟,嘟嘟,嘟嘟”,她冲它欢天喜地的叫着。嘟嘟呢,一上车就圆咕溜秋地趴着了,也不哼唧,也不动弹。你摸它皮毛,挠它痒痒,它就怯生生地往后躲,往身子里面缩,缩成一个圆圆的小肉团。过一会,再用眼角瞄瞄你瞟瞟他,一副受了委屈的小孩儿模样。到后来才终于露出一点狗性来,在后排车垫上扎扎实实地拉了一泡尿。“狗东西”,我气得大叫,老婆和女儿却放声笑起来。所谓事不关己也,在平时,这车内的卫生是不算她们分内活。
嘟嘟回到家里也是这样。刚进门它就挣脱邓等,立即钻到了木质沙发底下去,任你怎么喊就是不出来。木质沙发底下那里有一只废弃的旧拖鞋,它钻进去之后就蹴在上面缩着了。从此以后,那里就是嘟嘟的狗窝了,是它翻箱倒柜做了坏事之后的避难所。那只废弃的旧拖鞋呢,是它睡觉用的席梦思,是它用来锻炼狗性的啃噬物,也是它长大之后春心荡漾长夜难眠时的寄情物。后来,我们在阳台用包装纸盒给它做过一个狗窝,但各种引导之类的尝试都失败了,它就是不从,我们只好作罢。这是后话。现在,嘟嘟蹴在那只旧拖鞋上面,又一次很实在地撒了一泡尿。好大的一泡尿吔,从沙发底下曲里拐弯一直流出来,流到了客厅当中。我老婆当时差点没气得晕过去。这回轮到我开乐了。
那是二○○四年三月。太阳已经亮丽得有了温度,天空也已开始蓝得晃眼睛。桃花说红就红了,杨柳绿得婀娜多姿。屋外各色草木花卉纷纷扰扰,伸胳膊的伸胳膊,亮嗓门的亮嗓门。所谓“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大自然就是这样,各有各的序列,各有各的轨迹。我的轨迹是上班下班,偶尔加一两个班。从宠物市场回来,我就被电召去加班了。回到家已是晚上八点钟。“老爸,嘟嘟吃火腿肠了。”“老爸,嘟嘟吃了三根火腿肠了。”“老爸,嘟嘟听得懂它的名字了,不信你拿火腿肠叫它。”我这才又想起家里多了一个嘟嘟。“嘟嘟,”我拿一根火腿肠冲沙发底下喊,它果然慢慢凑过来了。我算是明白了,“嘟嘟”这个名词对于它就是吃,或者干脆就是一根粉红色火腿肠。
事情就是这样。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嘟嘟总是以为,普天之下,狗粮就是火腿肠,饿了就该吃火腿肠,而且,它那一副狗下水也只认火腿肠了。我们觉得这样下去不行,长此以往,它可以吃穷一个家庭的。于是,嘗试给它加稀饭,把火腿肠切得细细的拌到稀饭里去,再用力搅匀。但是收效不大,嘟嘟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它的舌头一舔,再一卷,便把那些丁丁块块细小的红颜色舔进嘴里,卷到肚里,就是不捎带进去一点稀饭,顶多只是在嘴巴上胡须上沾染一点稀饭沫。
吃饱了,嘟嘟就开始玩自己。用粉红色舌头舔两个小爪子玩。它趴在那里耐心耐烦地舔,左一口右一口地舔,上一口下一口地舔。在这一刻,它哪里还是一条狗,仿佛变成了一只猫。但如果你以为它真的像猫一样地爱清洁,讲卫生,那你就错了,大错特错咧。它是无所事事,无事生非,在憋闷之中给自己找一点乐子罢了。嘟嘟舔得尽心了,疲惫了,就四仰八叉地稍事休息一会。感觉缓过劲来了,便又投入地玩自己。这一回是改用啃了。起先是抱住那只旧拖鞋啃,感觉味道不够好,不够特别,只是象征性地啃了一会便丢下了,它径直跑到门口,在一堆鞋当中挑选了一只新的高跟鞋,叼住,拽到沙发底下去,这才尽情地啃了。它从前往后,从上往下,一路啃下来,那高跟鞋就全是牙印了,鞋袢也被它活生生地给拽掉了。苍天呀大地呀,那鞋可是老婆刚买回来用于搭配那套新春装的。老婆在衣服鞋帽的搭配上是刻意的,挑剔的,完美的,如果不能如她的心愿,她是绝不勉强迁就的,所以,每到换季,挑选与搭配衣服鞋帽就成为她个人乃至我们全家一个极其繁复的工程。嘟嘟居然不懂这个,胆敢啃噬老婆的高跟鞋,看来这回它的狗命不保了。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天空刚刚刮起风暴,眼看就要黑云压城城欲摧了,却忽而变得风和日丽了。听得老婆的尖叫声,嘟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躲进沙发底下,并且以吓得魂飞魄散缩着一团的姿态,很快博得了老婆的恻隐之心,取得了她最终原谅它,并回报了它一个笑容,也就解除了丢命之警报。
好久以后,老婆还常常聊起这件事。她说,怪不怪吧,那一瞬间,我怎么就突然觉得那模样是我们邓等了。又说,我当时可不就真是这样想法,把它当做邓等了。她问,换了你,你会向一个乞求你原谅的小家伙抡一巴掌或踢一脚的吗?又说,我想你是不会反对向一个小可怜突然笑一个的吧?
日子就这样过去。嘟嘟慢慢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成为了我们家庭里的一员。下班时节,听得门口脚步声,或者掏钥匙的声音,嘟嘟就一准守候在那里了,只等门一开就迫不及待地扑向你,就像孩子扑向父母亲一样。它迎接到了你,就用舌头舔你,舔舔你这里舔舔你那里,还把头一个劲地依附于你的某个部位,使劲地蹭着。蹭够了,就给你做游戏。
嘟嘟的游戏总是老三样,一日咬尾巴,二日硌痒痒,第三就是追逐赛。所谓“咬尾巴”,是这样的:它追着自己的尾巴咬着玩,转着圈圈追着自己的尾巴咬着玩,眼看快要咬着了,身子一动,尾巴就又跑了,总快咬着了,总是咬不着,如此循环反复着,逗得你心花怒放,放声大笑,情不自禁奖励它一根火腿肠,或者一段鸭脖子。它就更加乐此不疲,直到气喘吁吁实在是跑不动了。所谓“硌痒痒”就是:它四脚朝天地躺着,原地转着圈圈,让你来硌它下巴的痒痒,或者硌它肚皮的痒痒,它就咧着嘴笑着,享用着。见此情景,即使你心情不好,你也往往是乐于逗它一逗的。第三样追逐赛一般是在室外,那里场地大,跑得开,跑起来了也够尽心。嘟嘟开始是陪你散步,它一忽儿绕你前面,一忽儿绕你后面,转着圈儿地绕,然后欢蹦乱跳地往前跑一气,边跑边往回看,引导你追它,它又不真的拼命跑,看你没有追上或者没有追逐的意思,它会重新引导你来一遍,直到你真的开始追逐它。说实在的,我并不喜欢这种游戏,嘟嘟之所以屡次玩儿它,问题在于老婆与孩子,她们乐意。只要出门散步,她们总是带上它,还唆使它玩儿这个,我有什么办法。或许动物世界里也是有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准则的,嘟嘟大概是知道并遵守的罢。
转眼嘟嘟来我们家已经两年了。据介绍,像它这个岁数,若是人类,应该是妙龄女郎的年纪,早已到了谈情说爱,甚至谈婚论嫁的时候。果然,问题说来就来。这时期,听得门口脚步声,或者掏钥匙的声音,嘟嘟也还是守候在那里,等门一开也还扑向你,但仅只是扑向你而已,它不再伸舌头尽情地舔了,也不再真地依偎于你某个部位用劲地蹭了,它现在所做,就像邓等此类小学生放学后必须要做一篇功课,就像我们这班公务员在单位往往道貌岸然例行公事,程序化了,模式化了。嘟嘟做完上述功课,就迫不及待地往外跑。一溜烟跑完五层楼,跑到了楼底下,又快步跑到对面楼房第二个门洞,守候在了那里。嘟嘟仰着脖颈望,拖着长音汪,它是在等对面三楼的那只咖色泰迪,它是在给泰迪发信号。嘟嘟的爱狂热、奔放,就连示爱也是大胆的,热烈的,不加掩饰与修饰的,就像刘晓庆,就像木子美,就像敢于爱到国外的芙蓉姐姐。但这又注定是一个不确定的追求与等待的过程。因为它要等到泰迪的主人回来放泰迪出来,它才有可能得到这份爱。那只泰迪倒也值得嘟嘟爱,一来,它与嘟嘟年龄相仿,看上去就像人类中有涵养、有地位、有气质的帅小伙,所谓高富帅是也;二来,它对嘟嘟也算爱得明确与热烈,每当嘟嘟在楼下呼喊,它也一准会在三楼答应,还火急火燎地拨弄着窗玻璃,冲着嘟嘟汪汪地叫。对此,楼下那个胖得跑油的女邻居跟老婆开玩笑,说,拜托,你家嘟嘟是女的耶,矜持一点好不好,别动不动往人家那里跑?我心想,敢情又不是你,饱汉不知饿汉饥。又想,像嘟嘟这样的杂交草狗,对泰迪是高攀,它为什么要顾这份矜持,装这份含蓄?得到就是硬道理吵,傻B。
这期间,嘟嘟晚上常常是抱着那只废旧拖鞋辗转反侧,或者发一气呆,或者折腾一回。发呆时,它似乎有想不尽心思,连火腿肠也不肯多吃几口,连游戏也不想多做几回了;折腾时,它又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舔过咬过啃过之后还不罢休,再用脑袋撞,撞地板,撞墙壁,撞木质沙发Ⅱ也。有时,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嘟嘟在撞墙,就会顿生怜悯,坐到沙发上跟它说一气。我说,这时节哪有那么趁手,你就将就着用一回拖鞋?又说,要不给你支烟抽抽,缓释缓释一下情绪?最后回到床上,被它弄得居然也睡不着觉了。就想那红楼梦里大观园,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但凡是水做的,薛宝钗是如此,林黛玉也是如此吧。
好容易等到五一黄金周,我们终于决定了送嘟嘟走。原因是,邓等即将小学毕业,这期间,她不能有一丝一毫分心。正好我们计划去武汉,看我们省吃俭用在东风阳光城购买的一套房子,于是决定把嘟嘟捎上,送得远远的。
也许是第一次走高速,速度快晕车的缘故,嘟嘟打自上车就不欢实,它蹴在变速杆后面,一路都是迷迷瞪瞪,恍恍惚惚的。到了武汉下了车,也还是似睡非睡,不吃,不喝,蔫蔫的,怏怏的,就像是刚大病了一场的样子。
第二天往回赶,趁在蔡甸服务区加油的机会,终于把嘟嘟哄下了车。然后,点火,关车门,摇上窗玻璃。但此时,汽车行驶是缓慢的,是在慢慢地往前“埂”。我在看汽车后视镜,在看嘟嘟。这时,嘟嘟像是睡醒了,它突然划动四条矮而短小的腿,朝我们车辆拼命追过来,追过来。邓等呢,早已经趴在后窗玻璃上泪眼汪汪了。她对它喊,你快呀,快跑呀。又对我们说,我再听话,一放学就做作业还不行?到最后车转过身来,恶狠狠地冲我们大吼,你们都是侩子手,你们这是要杀了它。再看看旁边的老婆,她也已两眼泛红泪光闪闪了。心头就像是被什么揪了一下地疼。哧一溜一,我踩下刹车,摘下前进挡,拉起手刹,推开了车门。不一会,车内又恢复到从前,高声阔论,大呼小叫,像过节赶集,像过年聚会,气氛热烈,其乐融融也……
也是活该嘟嘟有一个美好未来,我们呢,也终于不必再当“刽子手”了。回到十堰第二天,嘟嘟就有了一个新归宿——陪那个孝感老太太在小区值守自行车棚了。这可是一个欢天喜地、两全其美的事情。
在我们回家路过自行车棚的时候,孝感老太太正在门前的几张麻将桌间逡巡。听得汽车声,她转身朝这边望,又朝车里的嘟嘟笑。整个过程也就三五秒,这事搁在平时再正常不过,跟眨眨眼摸摸鼻子没什么两样,稀松平常的。但这一次却例外,老太太的一望一笑产生了化学反应,老婆的灵感一下给激灵出来了,于是叫停车,朝自行车棚走去。也就上一趟厕所工夫,老婆喜滋滋地回来了。她一进门就蹲下来,伸出两只手,冲着嘟嘟动情地叫唤,来,乖乖,到妈妈这里来。又吩咐我们烧水给嘟嘟洗澡。她说,到别人家去,哪有不收拾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听这口气,仿佛是要嫁姑娘。真的Ⅱ也,她这一次可不真是把嘟嘟当作姑娘了。她帮它洗澡,用飘柔牌香波,搓一遍,又揉一遍。还给它梳理毛发,剪指甲。看那架势,如果可以,她真敢给它描眼影、抹口红……
嘟嘟在我们家吃的最后一顿晚餐,一定留在它的记忆里,它比火腿肠还高端、大气、上档次——吃烤鸭。嘟嘟呢,也还真给面子,就一个来回,一只烤鸭就被它风卷残云消灭得只剩一个骨架了。临了,卷了卷舌头,开始做“咬尾巴”的追逐游戏了。
一周过去,我们有意无意间又吃了一回烤鸭。这回除了骨架还剩下不少内容。我们就全部打包带上,在黄昏时节,散步到了自行车棚。在散步时,自然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文地理,聊风土人情。聊着聊着就到了自行车棚。就看到一道黄色闪电冲出来,径直朝我们扑将而来,是嘟嘟Ⅱ也。它是听到我们说话声音才冲出的吧?这情景就仿佛失散的孩子突然听到了父母亲。因此,它有这样速度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让我至今都不甚明白的,这个身材与腿脚都相对矮小的家伙,那刹那是哪里来的能耐,居然一跃就到了我们胸前,与我们一般高了。事后,我们还隔三岔五地谈论起这件事。老婆说,我算是明白了,动物,尤其是像嘟嘟这样的狗类,它的忠诚可以瞬间放大它的能耐,哪里像我们人类!说到人类,就捎带讥讽地拿眼朝我瞟。什么意思?你!
这以后,黄昏时节,嘟嘟也偶尔回访我们。它爬上五楼,听一会,发觉有声音或者有亮光,就用爪子抓。进得门来,就舔我们手,就追逐尾巴做游戏,就四仰八叉转圈圈。也用鼻子嗅,也啃,也偶尔得到火腿肠或者鸭脖子。就十几二十分钟,感觉够了,就打道回府,从不耍赖在五楼多呆一会或者干脆过一夜,纵使邓等暗中使了不少手段也留不住它。它得回去,它要跟孝感老太太一起做值守自行车棚的活计。
再后來,嘟嘟来得更少了,到最后,终于一次也没来了。听人说,孝感老太太回去了,她把嘟嘟也一并带回去了。难怪。又不知过去几天,孝感老太太的外甥女告诉邓等说,嘟嘟做母亲了,它一窝生了五个小宝宝。我们知道动物是不搞计划生育的,就遥想嘟嘟这以后该是如何应对生活。
邓等终于发奋努力,考上了中学。我们还是朝九晚五,上班下班,偶尔也加一个班。又一个春天到来,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嘟嘟一丁一点消息。孝感老太太的姑娘买了新房,搬到别的小区去了。
这年暮春时节,我出差到柳州。我是第一次到柳州。发觉满街是突突的摩托车,是狗肉招牌和狗肉店铺。摩托车后面拖着的多是黑的、黄的、白的、花的狗。店铺伙计在用火焰枪烧黑的、黄的、白的、花的狗毛。就眼神慌乱不够用了。我在柳州街头开始了寻找,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地寻找,寻找嘟嘟和它的孩子们。因为我突然认定,摩托车后架上,或者左右店铺里,一定总有一只是嘟嘟,也一定总有五只是嘟嘟的孩子们。找着找着心头就像是被什么揪了撞了似的疼,来不及躲闪,也没想躲闪,就汪汪汪地吐了,吐了柳州一大街。
还没等到事情办完,我当天夜晚就搭乘火车往回赶了。坐到火车上,才感觉疲惫极了,也虚弱极了。在睡眼蒙胧中,再回望渐行渐远的柳州,惚兮恍兮,它模糊得没有了形象,哪怕是轻描淡写几笔勾画的轮廓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