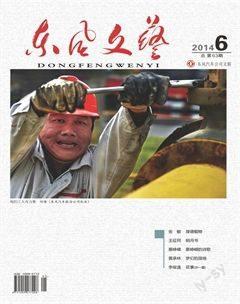天空飞来的鱼
王庆高
小时候,我很喜欢抓鱼,但抓鱼我却不在行。我的邻居同学德胜父亲抓鱼非常内行。德胜和我是很要好的小伙伴,只要他父亲去抓鱼,德胜准告诉我。我就死皮赖脸地缠着父亲跟他们去抓鱼。
我们村的人抓鱼都是到南河滩那里去。南河滩再向南两公里许就是黄河大堤,那里是一大片黄河湿地,水洼星罗棋布,蒲草、芦苇铺天盖地,水禽、野鸟出没其中,简直就是一片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夏天或者秋天,一旦遇到暴雨或者连阴雨,各处水洼自然连成一片,南河滩就变成了沼泽天国。那时,水洼里的鱼多得很,有鲫鱼、鲤鱼、草鱼、白莲、火头、鲶鱼,还有格牙和甲鱼。大鱼一般在深一些的水洼里,有的火头鱼大得很哩,一条有七八斤重,很吸引人。
抓鱼一般用撒网、罩漏和鱼叉。由于水洼里生长有许多杂草和芦苇,撒网在这里施展不开,德胜父亲常用的渔具是罩漏和鱼叉。我父亲杀猪宰羊内行,抓鱼并不内行。父亲没有鱼叉,就拿粪叉叉鱼。粪叉是叉粪的,太重太笨,没有鱼叉好使,所以总是扎不住鱼;用罩漏罩鱼,也是一门技术,眼看着大鱼游来游去,可是一下罩漏,鱼儿就飞了。父亲只能罩住一些小鱼。父亲抓鱼却不爱吃鱼。吃鱼是我的喜爱。父亲常常是为给我解馋才来抓鱼的。德胜的父亲是抓鱼的能手,鱼叉在他手里简直就是神枪,只要他瞄准了的鱼几乎百发百中:使用罩漏罩鱼,下罩的时机和方位把握的也很准,只要有鱼撞入他的视线,一准儿跑不掉。每次抓鱼,他父亲常常抓得很多。
我們在一起抓鱼,德胜家的成绩非常令我羡慕。我不服气,就怪父亲不会干,夺过罩漏自己罩。十来岁的小孩子,个头只有罩漏那么高,哪里能罩住鱼?气得我直掉眼泪。德胜一见这情景,就从他父亲的鱼兜里摸出一条送给我。我赌气不要,“啪”地一声给他打到水里,那条鱼半死不活地在水里漂泊,我甩开罩漏一罩,哇!罩住啦!我眉开眼笑逗着说,我也罩住鱼啦,我也罩住鱼啦!这时候,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德胜也跟着捧场,一起下手到罩漏里抓鱼。鱼抓出来,我父亲不让我要。德胜父亲就说,拿着拿着,一条鱼算个啥嘛!可我还是循着父亲的眼色把鱼还给了德胜。
鱼还给了人家,可我的心里像灌了蜜,抓鱼的信心倍增,我很兴奋地继续用罩漏罩鱼,一下、两下、三下,也不知罩了多少下,都没有罩住鱼。我鼓足了劲儿的心囊裂开了缝,气儿刺刺往外冒,眼看就要瘪下去的时候,天上突然飞来一条鱼。那鱼一落水,好像还不认识我,总是翻过身子愣着眼神看我半天,才摇摇尾巴,缓缓地寻找他该去的地方。这时候,我的罩漏已经准确无误地落下水,给这条飞来的鱼扎好了不大不小的篱笆院子,任它在那里自由畅游一会儿。这档儿,我抬头去看我的同学德胜,我怀疑又是他给我的救助或者是怜悯,我不要他这样做。德胜好像什么都不知道,自顾自地一起一落罩鱼。我问他,是不是你扔过来的鱼?他的头摇得像拨浪鼓。我说,你别不承认,天上怎么会飞来鱼呢?他诡秘地笑了。我毫不犹豫地把鱼装到了他家的鱼兜里。
我赌了气,非抓到鱼不可。我信心更足了,技术似乎也更熟练了。一下,两下,三下,不知罩了多少下,我终于罩住了一条斤把重的红鲤鱼。我大声喊着德胜,请他来帮忙。我们俩一起下手抓住了鲤鱼。我死死地扣住它的腮,在浅水洼地里奔跑,一边跑一边叫,红鲤鱼,红鲤鱼!我抓到了红鲤鱼!
水洼地里响起一片笑声。